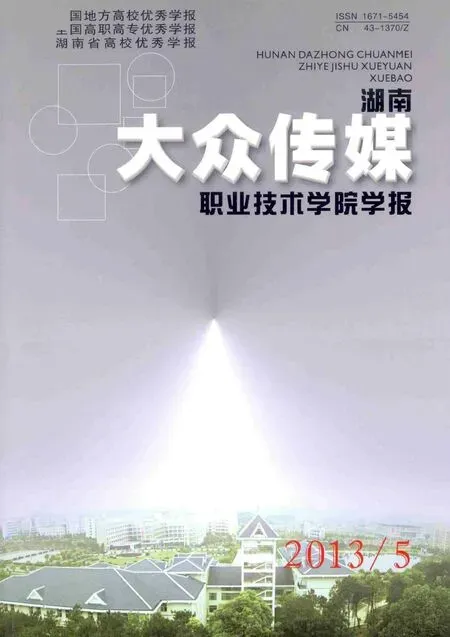权力话语对政治文献英译影响刍议
谭燕萍 康钦珏
(1、2.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权力话语理论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他所说的“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一种弥漫于人类存在的网络关系;它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传播和控制的工具;权力如果争不到“话语”,便不再是权力。语言作为言语乃至话语,它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构成内在的网络系统,无形中牵制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话语并不等同于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社会介入力量。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表明,作为传播媒介,话语或语言并不是纯客观的透明体;它不仅反映社会意识形态,还参与社会事物和关系的建构。而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翻译过程和译本的传播都无法避免权力话语的烙印。翻译活动受到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权力制约,外部权力制约包括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制约、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和强势文化所造成的话语权力的制约。政治文献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和讲话、党和政府的文件及工作报告等;是外界了解中国的国情、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政治制度、政治立场等最权威的资料来源;因此题材必定具有特殊性,同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其翻译工作当然要求更加严格苛刻,若翻译不准确或者错误,小则难以理解,大则产生误解,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一、政权机构及其意识形态对政治文献英译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决定了其主流意识形态。译者的翻译目的、译本取向和翻译策略与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权力话语难以达成一致。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的翻译往往比其它文本更活跃,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译本又通常遭到压迫、抑制。从中外翻译史来看,国家机器以其特有的方式对政治文本进行操控的实例比比皆是。香港回归联合申明——“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交还”一词英译中,英方选用“return”,但词典中该词意思“bring,give,put or send sth back to sb”,而中方则坚持使用“restore”,在字典中,restore的释义为“bring back to original state by rebuilding, repairing, repainting, amending etc.”。英方使用“return”一词明显体现了其回避的态度,不愿公开承认历史错误和不平等条约。而“restore”一词又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政治立场。这一例子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和影响。
此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权机构组织上性质独特,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下,有执政党和国家独特的政治目标和政策轨道。因而产生较多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精神”、“科学发展观”等;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词汇,在英语中并无直接对应项,它影响着英译活动的进行。在英译时,又因其政治性的特殊性质,译者必须从头至尾仔细衡量其用词的政治含义及其影响;程镇球先生说,“政治文献英译要讲政治,要有政策头脑和政治敏感,特别是涉及我党政策、国家利益”。[1]不能偏离党和国家的政治目标和政策轨道。
二、民族文化交流中权力话语差异的不平等影响
在处于长期殖民压迫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中,民族之间文化关系自然形成了不平等,并由此而产生了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差异。英美两国的译者在翻译弱势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大多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即用具有英美文化特色的话语再现原文,这完全表现了强势文化的霸权主义与民族中心论,从而使弱势民族文化特色趋于消失。正是出于保持原文的异国特色、抗拒文化帝国主义的背景下,韦努蒂提出“异化”翻译策略。目前,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弱势文化的国际文化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处于弱势,因此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习近平主席于2012年提出“中国梦”。众所周知,“美国梦”概念的英文表达为“American dream”。因此,在国内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对于“中国梦”的英译就顺理成章使用“Chinese dream”,但《英语世界》2013年第三期《中国梦:China dream还是Chinese dream?》一文中,对“中国梦”的英译提出了质疑。英国Random House的编辑Stuart Berg Flexner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军队中出现了一些表达方法,用Chinese指disorganization, noise and confusion(无组织,喧嚣,混乱),比如:a Chinese attack(中国式进攻)是a noisy, badly executed attack(喧嚣、混乱的进攻);因历史、社会和地理诸多因素的影响,使Chinese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中国日报》2013年4月19日的一篇报道“China dream in Africa”,该报道关于“中国梦”的表达就并未使用“Chinese dream”。因此在政治文献英译中,译者要意识到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避免处于话语弱势地位。
三、译者自身的主观意识在翻译活动内部权力的制约影响
无可置疑,社会意识形态等外部权力对译者的翻译目的、译本取向和翻译策略影响同样深远,作为独立体,译者具有自己鲜明的爱憎和审美标准,这种个人的喜好在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矛盾冲突时也可能占上风。除了在选择翻译文本、确立翻译目的时,译者的主观意识发生了重要作用;作为隐形的权力话语,也制约着翻译活动。如,在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传统与习俗出现差异和矛盾时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实就是译者在自身主观意识作用下,在源语文化权力话语与译入语文化权力话语之间进行合理权衡,并选择后者,反之则是异化的翻译策略。
此外,由于译者受母语或者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进行政治文献的英译时中式英语的出现频率较高。在中国政治文献中通常会出现许多重复用词,尤其是常用词义强烈或者语气较绝对的副词、形容词等,如“彻底废除”,“积极推进”等。在句式、篇章方面,汉语重“意合”,行文中的逻辑联系具有隐含性,汉语多用主动语态和短句,而英语常用被动语态和长句。汉英差异使译者在翻译中便容易出现“中式英语”。如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制化,(摘自中共十八大报告),译文1,ensure that all government works are legalized.译文2,ensure that all government functions are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law.对比以上译文,译文1是典型的中式英语,通过借助外语的自身发展特点,许多译者在“法制化”英译时使用英文中表示“化”的词尾-ise或者-ize,但如果使用legalize有语言僵化、死板之感,明显不如in accordance with law顺口自然,而“国家各项工作”作为一个笼统概念与“工作”一词又无法搭配,其真实意思是指国际政府的工作,即政府机关要履行的职能,因而应译为“all government functions”。
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能让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清醒的认识到翻译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本转换,政治文献的汉英翻译涉及到国家政策、大政方针、领土主权等政治方面问题,同时还影响到我国国际形象以及外国人对我国现状的了解。政治文献英译受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影响,并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在翻译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译者应把“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概念注入到翻译中,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