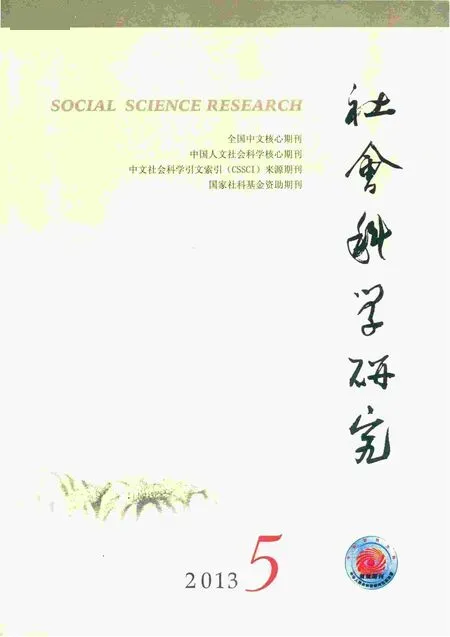明中后期蒙学读物的出版
张献忠
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中,以坊刻为主体的盈利性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书商的市场意识大大增强,竞争策略日趋多元化。①参见拙文《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江汉论坛》2012年第8期。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的品种也日益丰富,其中蒙学读物成为商业出版中的重要门类。与前代以及明前期相比,这类读物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编纂形式活泼,其受众也不局限于孩童。
一、明中后期蒙学读物刊刻的盛况
明代的蒙学教育非常发达,基层城乡普遍设有社学,除此之外,还有私塾和宗族成立的义学、乡学,这些都担负着蒙学教育的职责。另外,明中后期,在江南等地区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垮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把各个阶层的人们裹挟进商业社会中,而商业社会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知识,这也进一步促进了蒙学教育的发展和蒙学类读物的出版。
明中后期,蒙学类读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急剧增加。沿袭前朝的做法,明中后期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很多教材性质的蒙学读物,最著名的有约嘉靖年间吕近溪编纂的《小儿语》和稍后吕坤编纂的《续小儿语》,万历年间萧良有编纂的《蒙养故事》、明末程登吉编纂的《幼学故事琼林》等。这几本书在晚明清都非常畅销。《蒙养故事》刊行后,崇祯年间的杨臣铮又作了增补,改名为《龙文鞭影》,该书很快成为一本教材性质的启蒙读物。光绪年间,李恩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校正和补充,在序中,李恩绶说:“明贤《龙文鞭影》一书,风行已久。童子入塾后,为父师者,暇即课其记诵,盖喜其字句不棘口,注中隶事甚多也。”〔1〕这几种蒙学读物虽然很受欢迎,但鲜见明刻本传世,原因如前所述。
无论是“三百千”还是《小儿语》和《续小儿语》,这些教材性质的蒙学读物都采取了排偶和韵语的形式,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但这类读物也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就是过于追求易记易诵而忽略了趣味性。这些蒙学读物虽然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内容,但文本本身缺乏故事性和可读性。《蒙养故事》和《幼学故事琼林》虽然开始采用“故事”的形式,但仍然以排偶和韵语为主,“故事”主要是注解性的。另外,“三百千”之类的读物乃至《蒙养故事》和《幼学故事琼林》,内容都比较浅显,主要适合幼童,八岁以上的儿童就要学习更深的知识,前引吕坤《社学要略》中的话亦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商业出版的迅速发展和通俗文化的兴起,明中后期,一些书坊主和作者开始将蒙学知识与通俗读物嫁接,推出了一大批故事类的蒙学读物。故事类蒙学读物的编纂在宋元时就开始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胡继宗编纂的《书言故事》和元朝建安人虞韶编纂的《日记故事》。这两部书因其注重故事性,在明前期就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很多学者都将其作为蒙学读物,如明前期的郑文康 (1412-1465)在其文集《平桥稿》中记载了一个八岁的儿童“能暗诵《日记故事》数十首”〔2〕,黄佐(1490-1566)在《泰泉乡礼》中规定乡学“教以《朱子小学》和《日记故事》”〔3〕,叶盛 (1420-1474)在《水东日记》中也提到《日记故事》,并说“故事书坊印本行世颇多”〔4〕。由此可见,《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在明前期就很受欢迎,并出现了很多同类书,这就为故事类书培育了一个广阔的市场。正是看好这类书的市场前景,明中后期的书商纷纷采取了跟进策略,他们首先请人对《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进行改编,增加了大量的注释,有的还添加了明代的内容。这不仅使《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更加通俗易懂,而且富有时代气息,因此更加符合受众的需求。仅据现存的各家书目所载,这两部书就至少分别有十余种刻本。考虑到年代久远,很多刻本已经散佚,因此实际的刻本还要多。这也可从现存刻本的序言或扉页题识中得到佐证,如刘龙田万历元年刊刻的《新锲类解官样书言故事》扉页题识就提到“数十种坊间刻本递相沿袭”①转引自长泽规矩也《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三辑,“解题”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黄直斋也说“近来坊间刻者种种”。不仅书坊之间递相沿袭,而且有的同一家书坊就有多个刻本,如建阳的郑世豪宗文堂在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八年、万历三十六年三次刊刻了《书言故事》,同是建阳的书林刘龙田也于万历元年、万历二十四年两次刊刻,其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上表中所列的各种版本的《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无一例外地都对原有的内容进行增删,有的还加入了明代的内容。此外,所有这些刻本都增加了大量注释和解析性的文字,从而更适合童蒙和文化层次低的读者阅读。这种以既有的《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为底本进行改编的做法,一方面可以节省一部分稿酬,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大缩短出版周期,从而尽快占领市场。但众多书坊一拥而上,改编和刊刻一两部书,实际上是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其结果必然会使这两部书的市场迅速达到饱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书商的惯用手法就是贬低其他版本,竭力宣传自己的版本是名家校订,如黄直斋在《新锓增补万锦书言故事大全》的题识中说:“重梓胡继宗先生《书言故事大全》。近来坊间刻者种种,不失之漏而失之差也,甚为不便。今请徐先生分门析类,校正差讹,增补遗漏,精录刊行,以便士君子之观览,乃儒林之阶梯也。买者请认集义堂为记。书林黄直斋识。”这还不够,黄直斋还以“金陵原板”相标榜,实际上纯粹是欺骗受众。即使确实是“校正差讹,增补遗漏”,一般的受众如果有了其他的版本,也不会因新版本精良再买一部,更何况各家书坊都这样“自卖自夸”,一般受众根本无法知晓到底哪个版本更好。为了从同质化竞争的泥潭中摆脱出来,一些书坊主开始寻求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不再低水平重复,而是千方百计寻求和组织编纂、刊刻新的作品。当时,书坊刊刻的明人编纂的故事类启蒙读物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余种。
明中后期刊刻的故事类蒙学读物中,有的侧重于道德教化,如各种《日记故事大全》以及《金璧故事大全》、 《养正图说》、 《人镜阳秋》等,有的侧重于辞藻和文化常识的介绍,如各种《书言故事》以及《新镌翰林考正历朝故事统宗》、《艺林聚锦增补故事白眉》等。这些故事类蒙学读物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的,内容非常丰富,如万历十九年郑世豪刊刻的《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以十二地支为序,分为十二集,每集一卷,共252个门类,分别为:
卷之一 子集 (凡一十一条) 人君、圣寿、父母、祖 (父、母)、孝养、宗族、兄弟、媒妁、婚姻、夫妇、翁婿
卷之二 丑集 (凡一十六条) 亲戚、子孙、无后、女子、妇人、宠妾、妓女、仆隶、称呼、谦称、人品、古今喻、孩孺、幼敏、耆老、寿考
卷之三 寅集 (凡一十七条) 师儒、儒学、学问、苦学、不学、朋友、交情、父执、问别、会遇、访临、延接、宾主、叙扰、恶宾、馆宾、道教
4月14日下午,青海省水利厅副厅长宋玉龙紧急召集湟中、湟源、大通、互助四县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保障灾区城乡供水安全作出部署,要求四县水务局分别组建15人的应急抢险小分队,由一名局领导带队,以最快速度投入到灾区救援。同时青海省防汛机动抢险队调集20t吊车1台、1m3吊车1台以及必备的抢险物资抵达灾区展开救援,另有320挖掘机2台、装载机2台、运输车辆6台以及工程抢险救援人员25人集结待命。
卷之四 卯集 (凡二十四条) 神仙、释教、鬼神、隐逸、自足、农田、渔钩、商贾、送行、行役、水程、问归、医者、地理、相者、谈命、卜筮、巫者、画者、传神、射艺、博弈、乐技、杂戏
卷之五 辰集 (凡一十八条) 身(体、说)、身 (体、譬)、颜貌、恶貌、残疾、恶性、小儿、庆诞、疾病、问疾、凶事、死丧、赙丧、葬事、送葬、祭奠、挽悼、坟墓
卷之六 巳集 (凡一十二条) 声名、名誉、志气、德量、宽恕、瞻仰、谈论、评论、求教、奖誉、赞叹、谗佞
卷之七 午集 (凡一十七条) 怨仇、报复、排难、豪奢、富厚、贫乏、俭薄、谒见、不遇、干求、馈送、托庇、请托、感佩、送谢、哂笑、梦寐
卷之八 未集 (凡一十七条) 科第、诸科、恩例、同年、不捷、聘召、荐举、买爵、仕进、同官、清廉、贪污、致仕、黜责、不调、任子、命妇
卷之九 申集 (凡二十八条) 朝制、三省、宰相、枢密、参政、中书、舍人、御史、两制、卿监、郎宫、史官、谏官、学官、百官、府主、监司、郡守、通判、幕职、教授、县宰、县丞、县尉、主簿、武官、盗贼、狱讼
卷之十 酉集 (凡三十六条) 天文、时令、正月、元日、立春、人日、上元、二月、社日、三月、上巳、清明、立夏、四月、五月、端午、六月、立秋、七月、七夕、中元、八月、中秋、九月、重阳、立冬、十月、十一月、冬至、十二月、除夕、闰月、岁月、地理、花木、果实
卷之十一 戌集 (凡二十一条) 都邑、市肆、第宅、学校、斋舍、书史、文章、诗词 (赋)、书翰、祝颂、起居、问候、神相、字学、字辨、禽兽、水族、走兽、牛马、羊、百虫
卷之十二 亥集 (凡三十五条) 酒、醉饮、茶、馔食、米、蔬、饣甫啜、事物、文物、笔、砚、纸、墨、器物、扇、床、衾、席、酒杯、冠履、衣服、金宝、乐器、琴、瑟、琵琶、笙、箫、筝、笛、笳、鼓、钟、灯火、拾遗
故事类蒙学读物的大量出版无疑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应当归功于出版的商业化。很多明中后期刊刻的故事类蒙学读物之所以现在还能见到,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图书的刊刻量很大,另一方面也与这类图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强有关。正是因为这类图书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因此受众并没有仅仅把它看做蒙学教材,而是同时将其看作休闲读物,又因为内容的丰富性还可以随时备查阅,这就使这类图书没有像“三百千”一样在用过之后被一扔了之。
除了各类综合性的蒙学读物外,明中后期的书坊还刊刻了大量专门性知识的启蒙读物,其中,刊刻最多的是对学和音韵学的启蒙读物。每一个儿童在学做文章之前,都要先从对对子开始;另外,明中后期,在很多社交场合,稍微有点知识的普通市民百姓也以作诗、对对子为雅好,互相酬和。正是看到了人们对对学知识广泛而巨大的需求,明中后期的书坊纷纷刊刻这类图书,流传到现在的就达十余种。
除了对类知识的启蒙读物外,明中后期书坊还刊刻了很多算学、音韵学、诗学等专门知识的启蒙读物,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明中后期蒙学读物的编纂特点和受众分析
(一)明中后期蒙学读物编纂的特点
为使蒙学读物更适合目标读者群的需要,书坊在组织编纂蒙学读物时,充分考虑了这一年龄层的接受能力。在体例上,从最初采用排偶和押韵这种单一的形式逐渐发展到采取多种形式,尤其是故事类蒙学读物将传统经史读物中的人物、典故以叙事的形式呈现给受众,更具可读性;在内容上,对《书言故事》、《日记故事》这类既有的文本重新编辑加工,加以注音和注释,使之更加通俗易懂,明人新编纂的故事类蒙学读物也都有大量的注音注释;在形式上,加入大量的插图,使之更加生动活泼。具体地讲,明中后期蒙学读物在编纂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绝大多数蒙学读物都没有定本,无论是“三百千”还是《日记故事大全》和《书言故事大全》,以及专门知识的启蒙读物,都处于不断的演进过程中。这些书最初可能是士大夫之家或者塾师自己编纂的供子弟诵读和学习的材料,并没有要成书的意图,但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逐渐得到认可,精明的书商就有了将其编纂成书的打算。由于版权意识淡薄,在得到市场的认可后,其他书商往往予以翻刻,翻刻时一般都要作以修订,请名人或增补,或注释。在不断的增删和演进过程中,新的修订者往往被关注,最初的作者反而被忽视甚至淡忘。书商也着力强调某某名人增补、某某名人注释,有的版本甚至连最初作者的名字都不署,直接署增订者的名字。萃庆堂刊刻的《重刻增补故事白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书署“安仁邓志谟鼎所补”,而没有原著者的名字,以至于当时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邓志谟是该书的作者,在邓志谟著、郑大经四德堂刊刻的《重刻袁中郎先生校订古事镜》题识中,郑思鸣写道:“豫章邓公胸包曹植,笔压董狐,先修《故事白眉》,后著《事类捷录》……”显然郑思鸣直接将邓志谟看做《故事白眉》的作者。这固然是书商的商业策略,也与这类书的无定本和演进性有关。这类书大多很难确定哪个是作者,即使是《书言故事大全》和《日记故事大全》最初的作者也未必是胡继宗和虞韶。正是因为没有定本,众多书坊主才敢于明目张胆地请人对以前的版本进行改编和修订,于是才有了数十种版本的《书言故事大全》和《日记故事大全》。这些版本之间虽然内容大同小异,但在类目和结构以及繁简程度上存在差别,有的差别还比较大。比如黄直斋集义堂刊刻的《新锓增补万锦书言故事大全》和郑世豪刊刻的《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仅从目录根本看不出是一种书,内文的版式和排列也有很大差别,前者分上下两栏,上栏约占整个版面的1/6,主要是尺牍、柬札和名言佳句的摘录,下栏才是主体内容;后者则不分栏,没有尺牍、柬札和名言佳句的摘录。尺牍、柬札和名言佳句的摘录是原来的刻本所没有的,显然是书商和增补、编校者所加,这种增补和编校工作,不仅使新的刻本与原来的刻本相区别,而且增加了附加值,版式也更为活泼,从而激发了读者的购买欲望。
第二个特点是图文并茂。书坊刊刻的蒙学读物大都图文并茂。有的上图下文,如集义堂刊刻的《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刘龙田刊刻的《新锲类解官样日记故事大全》卷一《二十四孝》,清初日本翻刻的《分类合璧图像句解君臣故事》都是分上下两栏,上栏为图,约占整个版面的1/3,下栏为文,与今天的连环画有点类似。有的一事一图,如《养正图解》、 《人镜阳秋》,其中《人镜阳秋》是对页连式。无论是上图下文还是一事一图,其中的图片都不再仅仅承担装帧的功能,而是作为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是对文的形象化再现,文是对图的阐释。这种图文互补的设计风格,使文本表达的内容更生动。
(二)明中后期蒙学读物的受众
对于“三百千”之类的读物,其蒙学读物的性质无论是在明代还是现在的学术界都没有任何疑问。但对于明中后期盛行的故事类、诗学类和对类通俗读物,很多学者特别是教育史专家都将其定性为蒙学读物,如张志公先生就将故事类类书视为蒙学教材。①参见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将其定位为通俗类书,如刘天振先生认为,“从当日编纂者的体裁意识看,他们是以普通类书相期许的”。〔5〕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从当时书商的视角看,这类书首先是定位于童蒙读物,这在书名中也有所体现,前文所列举的图书书名中经常有“便蒙”、“启蒙”、“幼学”等字眼。有些学者之所以将这类图书仅仅作为通俗类书,乃是由对这类图书的受众定位的不同理解所致。
毫无疑问,蒙学读物的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儿童。社学与义学、乡学都应算作童蒙教育,社学一般招收15岁以下的儿童,“早者五岁开蒙,晚者七岁入学”。②参见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50、160页。据此,蒙学读物的受众主要是5-15岁的儿童。如前引吕坤所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百千”,故“三百千”的定位非常明确,基本上是八岁以下的幼童,所以没有人怀疑“三百千”蒙学读物的性质。而故事类、对学、诗学、音韵学等蒙学读物,其受众很大一部分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大概在8-15岁之间,对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来说,“三百千”显然过于浅显,他们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故事类、对学、诗学、音韵学等蒙学读物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另外,故事类等蒙学读物的受众除了童蒙外,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成人,这些成人实际上也处于启蒙阶段,对他们来说也是接受蒙学教育。明前期中国还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的民众主要靠经验的累积来从事生产活动,社会交往也比较少,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对书本知识的需求不迫切。但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南方一些发达的城镇开始步入商业社会,而商业社会中的民众仅靠经验的累积是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商业活动和人际关系的,他们需要像幼童一样掌握蒙学知识。也就是说,蒙学不单针对童蒙,我们不能因为这类书的受众包括成人读者就否定其蒙学性质。当然,不可否认,故事类、对学、诗学、音韵学等除了作为蒙学读物外,一些下层文人也将其作为工具书以备随时查阅,而且书商在宣传营销时也千方百计扩大读者群,如《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扉页的广告语说:
此书乃吴奕斋先生所编述,分类解释,文简而易知,不惟有益于童蒙,虽老师宿儒亦得以资其闻见者矣……
《京本音释注解书言故事大全》目录后的题识中也说:“小学者赖之以开聪,大学者资之以助词”,“不惟便初学之见,而士大夫开卷亦足以警策”。〔6〕这说明,这类书也可以作为一般的工具书。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将其划归普通的类书或工具书之列,因为即使这种宣传性的题识和广告中,也是首先考虑“有益于童蒙”、“小学者赖之以开聪”,他的目标受众是童蒙和迫切需要掌握蒙学知识的一般市民。实际上普通的日用类书中也有很多蒙学知识,但我们不能因此将其划作蒙学读物,这类蒙学读物和普通日用类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蒙学读物部头较小,一般一两册,而普通日用类书则部头较大,动辄七八册,甚至十来册。前者重在启蒙知识的教育,后者重在为四民大众提供参考,方便查阅,具有百科全书和工具书性质。
明中后期蒙学读物刊刻的盛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蒙学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但我们如果将某些蒙学读物混同于一般的日用参考书,就不能够正确地考察当时蒙学教育的客观情况,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1〕〔明〕萧良有.自叙〔A〕.〔清〕李晖吉,徐潜续编.龙文鞭影〔M〕.岳麓书社,1986.
〔2〕〔明〕郑文康.沈氏三殇塟志铭〔A〕.平桥稿:卷十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黄佐.乡校〔A〕.泰泉乡礼:卷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刘天振.明代通俗类书研究〔M〕.齐鲁书社,2006.189.
〔6〕〔日〕长泽规矩也.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三辑〔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