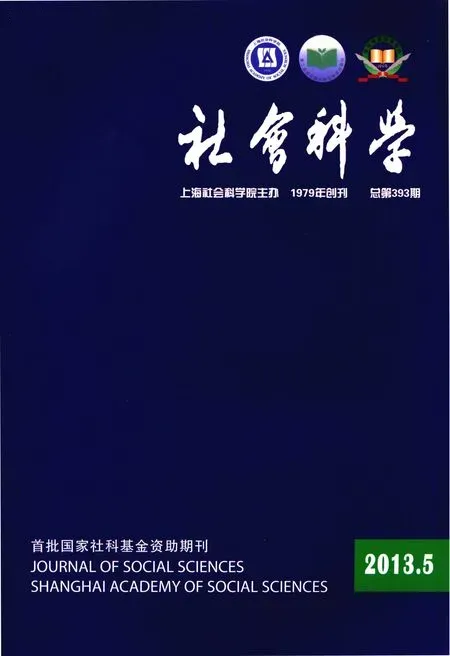论汤亭亭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
张喜华
汤亭亭作为一位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华裔作家,也是最负盛名的华裔作家,其作品被广为研究,也受到极大好评。她的《女勇士》获得1976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非小说类奖;1980年的《中国佬》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同时获普利策奖提名;1989年的《孙行者》获得美国笔会小说奖。汤亭亭作品的相继出版和获奖确立了她在美国的文化身份和文学地位。美国评论界认为汤亭亭“完成了以前其他美国华裔作家所无法完成的事情:将回忆录、传记、历史、口述史、诗歌、故事讲述和神话融为一体,表达了美国华裔的跨国经验,重新定义了华裔个体和集体在美国的身份”①Pendery,David“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o the United States,1850-2004:new perspectives”.Asia Ethnicity,Vol.9,No.3,Ro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October 2008,p.212,216.。《女勇士》的叙事策略、女性主义思想、经典改写等都是评论界广为赞誉的地方。该书出版后,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广泛欢迎,美国报纸、媒体、主流评论界称赞《女勇士》是代表性的自传性作品,是中国故事。但与此同时,汤亭亭的作品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赵健秀等亚裔批评家批评其歪曲中国文化,充满偏见。汤亭亭本人强调这是“美国故事”。在各种评论声中,《女勇士》成为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汤亭亭认为身份不是既定事实,而是一种永不完结的生产,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总是在表述之内,而非在表述之外。②Pendery,David“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o the United States,1850-2004:new perspectives”.Asia Ethnicity,Vol.9,No.3,Routledge,Taylor& Francis Group.October 2008,p.212,216.汤亭亭在《女勇士》中的表述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深思的地方,如,她表述了什么?她如何表述?她的表述视角是什么?她在什么话语框架中表述?她为谁表述?她又表述了谁?汤亭亭的作品到底是美国故事还是中国故事?汤亭亭选取表述内容的标准是什么?汤亭亭表述话语的深层含义是什么?汤亭亭作品在跨文化交际中负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呢?汤亭亭利用中国文化为资源,将美国作桥梁,通过表述来生产一种另类的文化视角,在对汤亭亭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
一、汤亭亭的文化身份需求
文化身份是包含华裔作家在内的诸多流散作家在创作中常见的主题。黑人作家、亚裔作家的很多作品都借助家庭的代际关系、生活体验、文化意象和具有特色的语言来表达身份差异和身份需求,力求唤起主流社会的注意和认可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艾利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以黑人英语进行写作,描写黑人族裔本身的特点和所遭受的社会不公正待遇以及社会偏见来突显这个族裔的生存状态,从而确立了她们黑人作家的文学身份。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书写第三世界独立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确立了他英国移民作家中佼佼者的身份。当然,要确立什么样的身份,要突显什么样的身份,这取决于作家本身的综合性社会因素。有些作家要确立的是本族裔的文化身份,有些作家要确立的是身居主流的文化身份,不一而足。
人不能离开身份而存在,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求与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乐黛云:《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332页。汤亭亭的美国公民身份毋庸置疑,无需赘述,但是,作为华裔作家,其在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却不会随其公民身份而自然确立。在此,汤亭亭的身份当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身份概念,而是指其文化身份,是她对于某种文化的自我归属感。由于汤亭亭华裔的特点,她和本土美国人有太多的差异,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在美国人眼里是典型的华裔特征。但是她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是受美国文化熏陶而成长的,处在两种文化之间,汤亭亭在写作中表现出她的身份焦虑。她的身份焦虑来自于中国和美国对她的不同期待,来自于两种文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她需要借助书写来表述,来明确身份,去除身份焦虑。当然汤亭亭本身并不存在要在中美两种文化身份中做抉择的矛盾和焦虑,她非常明确自己的美国身份,但是这种自我认同的美国身份需要社会的认同,需要借助表述来确认,需要一份“独立宣言”来向世人明示。所以汤亭亭要解构的是中国文化身份,要建构的是美国文化身份。霍尔在《谁需要身份》一文中说“身份是在成为谁而非是谁的过程中关于使用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而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我们是怎样被表述,我们怎样自我表述”②Hall,Stuart,“Who Needs Identity”,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ed.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London:sage,1996,p.4.。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利用中国文化资源,改写中国历史故事来建构女勇士,女勇士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成为谁”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表述的过程,也是一个身份确立的过程,身份建构在她的表述之中。身份不是寻根,而是怎样和根关联来寻求差异,“通过差异来定义身份”③Grossberg,Lawrence,“Identity and Cultural Studies:Is That All There i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ed.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London:Sage,1996,p.89.。汤亭亭的表述是差异表述,她突显和强化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母女之间的冲突就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矛盾的结果。汤亭亭描写中国文化荒诞残忍怪异的一面,对之加以拼贴改写,在差异和比较中来定义身份,稳固身份。所以要研究汤亭亭的身份立场,就必须对其表述进行分析和细读。
《女勇士》中的母女象征着中美两种文化,母女间的冲突和矛盾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处于两种文化中的女儿历经文化困惑、文化冲突到文化定位的转变过程,实现了对自己身处两者之间的身份建构。《女勇士》标榜为自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女儿经历的文化困惑就是作者的文化困惑。汤亭亭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迥然各异。学校里她经历美国文化,家里母亲教授她中国文化,给她讲述各种荒诞怪异、阴森恐怖的中国故事。在两种文化面前,她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危机,采用了文辞和意象层面的表述策略。从作品中的‘I’和‘here’两个字以及鬼怪意象可见一斑。
对于汤亭亭来说,重申身份、确认归属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过程也是痛苦的,她需要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找出差异,在差异中确定身份。汤亭亭指出“显然,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一个出生在美国的人自然就是美国人”①Kingston,Maxine Hong,“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Ed.Guy Amirthanayagam.London:Macmillan,1982,p.59,82.。中国人指责他们是‘鬼子’,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女勇士》中的鬼怪是过去,是中国,是中国文化,是汤亭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阐释,她通过各种想象性的鬼怪故事和荒诞离奇的道听途说的上一辈人的故事来试图重建华裔的族裔身份,通过这些鬼怪来和美国现实进行对比,服务当下,对族裔身份进行定位。作者将想象中和故事中的中国过去和现实的美国并置,而作者就处于过去与当下、想象与现实,中国与美国,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种种二元对立之间。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李根芳对《女勇士》中的鬼怪如是认为:“在母亲文化和主导的美国文化之间,好吃鬼两者都是,又两者都不是,她占据着这两者之间的空间。”②Lee,Ken-fang,“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he Exorcist:A Reading of Kingston's and Tan's Ghost Stories”,Elusive Illusions:Art and Reality,MELUS,Vol.29,No.2,Summer,2004,p.115、118.“身处两者之间,如何取舍,如何走向,两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到底有多宽,这都取决于叙事者。只有当叙事者开始意识到她的‘鬼怪’意象时,她才能够逐渐认识她是谁,她属于何处。”③Lee,Ken-fang,“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he Exorcist:A Reading of Kingston's and Tan's Ghost Stories”,Elusive Illusions:Art and Reality,MELUS,Vol.29,No.2,Summer,2004,p.111.美籍韩裔作家和亚裔美国研究教授金伊莲 (Elaine H.Kim)认为“汤亭亭笔下的鬼怪表明了语言间更为复杂的纠结,进一步证明了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文化的不可调和性,以及与这种不可调和性有关的语言的异质性”④Kim,Elaine H.,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P,1982,p.200.。
“为了让我觉醒的生活美国化,我关掉所有的灯,这样就看不见任何面容。我把所有丑陋的东西都塞进梦里,这些梦都是中文的,是讲述令人费解故事的语言”⑤Kingston,Maxine Hong,“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Ed.Guy Amirthanayagam.London:Macmillan,1982,p.59,82.。中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中国文化是丑陋的梦,是令人费解的语言,是扭曲的生活。鬼怪在当代美国族裔文学的功用不容忽视。“通过对过去想象性的恢复来重建族裔身份,用对过去的新描述来服务于当下。”⑥Lee,Ken-fang,“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he Exorcist:A Reading of Kingston's and Tan's Ghost Stories”,Elusive Illusions:Art and Reality,MELUS,Vol.29,No.2,Summer,2004,p.115、118.面对着她眼里扭曲的中国传统家庭和美国正常生活,女儿选择离家出走,“离家出走意味着离开中国,离开母亲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及语言习惯,为了解文化差异提供机会”⑦张延军:《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多重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在她对美与丑、正常与非正常、人与鬼进行比较之后,她的选择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离家出走,离开和拒斥的是母亲的中国文化,迎接的是美国文化。身处两种文化之间,叙事者更愿意接受美国生活和美国社会。霍米·巴巴指出“两者之间”(in-betweenness)⑧Bhabha,Homi,“Culture's In-Between”,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ed.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London:Sage,1996,p.54.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涉,而是一个混杂(hybridization)的过程,它涉及“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意义。⑨Eliot,T.S.,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Harcourt Brace,New York,1949,pp.63-64.汤亭亭在这一动态混杂过程中,通过种种努力来追求美国正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成功地赢得了美国社会的认同。在汤亭亭的叙事策略中,她有意把母亲的故事贯穿其中,母亲的角色和叙事者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以突显和建构叙事者的身份。她的写作过程就是她的身份确立过程。如赵健秀所说写作就是斗争一样 (Writing is fighting),汤亭亭的写作就是争取身份的斗争,她用中国经典和西方观点作利器,操纵叙事者,赢得了这场身份斗争。在边缘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女勇士》的成功明示了汤亭亭在美国和华人世界的身份,她很清楚自己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汤亭亭要以什么样的形象来稳稳伫立在美国呢?她“试图超越文化、语言、性别等界线,塑造强大的女主人公形象”①张延军:《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多重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中国文化里厌女,那么“我”就要做“女勇士”,来解构厌女的中国文化,她“认识到自己与男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不同,承认自己在这三个层面上的‘他者’身份”②Begum,Khani,“Confirming the Place of‘The Other’:Gender and Ethnic Identit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New Perspectives on Women and Comedy.Ed.Regina Barreca.Philadelphia:Gordon and Breach;1992,p.154.。西方的中国“他者”身份是汤亭亭竭力要消解的。她属于美国,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文化里令人生厌的女人,不是西方人眼中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具有抗争精神,敢于与母亲文化决绝的斗士,敢于解构白人世界中“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来确立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权形象的女勇士。作为边缘阶层的华裔美国知识女性成为勇敢的“文字斗士”,通过文学创作确立自己的身份,汤亭亭在白人世界了发出了声音,表达了斯皮瓦克的“允许边缘群体说话的政治要求”。但是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甚至亚裔作家是允许在西方说话了,在西方文化所谓的多声部发声中,汤亭亭有了自己的声音,但她的发声是在西方主流允许的框架内的发声。
汤亭亭根据美国人和美国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想象来创作,不断强化美国对中国厌女和非理性传统的东方主义建构。所以,连美国学者都认为汤亭亭无意中就在她的书中建立了一个东方主义框架来使她自己有别于她的母亲和中国文化,在此过程中,她复制美国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和问题。③Mylan,Sheryl A,.“The Mother as Other:Orientalism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Women of Color: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20th-Centure Literatur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6,pp.132-152.艾略特所指出,传统是不能继承的,需要艰辛的努力才能获得。④Eliot,T.S,.“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The Sacred Wood: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New York:Barnes&Noble,1964,p.49.华裔作家占用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汤亭亭书写的中国文化都是来自母亲的故事,是道听途说的东西,是霸权话语所需要和预设的内容。
李根芳认为,“华裔在白人主导社会中重写文化差异,身处后殖民时期,在西方语言文化和非西方语言文化之间,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之间,汤亭亭和谭恩美跨越两种语言和文化,通过文化翻译和阐释来建构身份,突显了混杂的过程。对她们而言,第三空间或两者之间的空间为歧义打开了空间,有了歧义,就能产生意义”⑤Lee,Ken-fang,“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he Exorcist:A Reading of Kingston's and Tan's Ghost Stories”,Elusive Illusions:Art and Reality,MELUS,Vol.29,No.2,Summer,2004,p.2004.。汤亭亭在华裔文学中确实是突显了文化差异,也通过差异塑造了空间,但是这种差异不是在挑战整体霸权,即便是挑战了霸权,那么挑战霸权的目的也是为了跻身霸权行列,获得霸权身份。她夸张的文化差异不是服务于建立华人或中国文化的身份,而仅仅是服务于确立汤亭亭等华裔作家的美国身份,归根结底是寻求处于夹缝中华裔的美国文化身份,是边缘走向中心的努力,是对中心接纳边缘的期盼。
汤亭亭在《中国佬》一书中想要用金山勇士来取代邪恶的傅满楚、狡诈滑稽的陈查理、厨师、洗衣工或者更为宽泛的令人费解的中国人形象。“她想要用《中国佬》中她创造的英雄传统来取代主导文化中‘有选择的传统’,在这种英雄传统中,美籍华裔不再受到边缘化。”⑥Linton,Patricia,“What Stories the Wind Would Tell: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Ethnic Women Writers VI.MELUS,Vol.19,No.4,Winter,1994,p.38.汤亭亭刻画的英雄传统是背离和拒斥了中国社会,宁愿死在美国也不回中国的一批华裔男人的英雄传统。在《中国佬》中,汤亭亭为自己祖先的美国身份进行辩护,从祖父辈到父辈再到自身,几代人都在建设美国,那么她的上几辈人就应该是美国人,到她这一代就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的两种文化的困惑和两个社会的认可程度都使得她不得不在《中国佬》中借助家史来进一步证明和巩固她的美国身份。
归一化后得:Y1=(0.33,0.29,0.29,0.09),Y2=(0.44,0.37,0.19,0.00),Y3=(0.35,0.41,0.24,0.00),Y4=(0.39,0.39,0.22,0.00),Y5=(0.32,0.37,0.21,0.10),Y6=(0.29,0.29,0.33,0.09),Y7=(0.32,0.36,0.32,0.00),Y8=(0.29,0.33,0.29,0.09),Y9=(0.29,0.29,0.33,0.09)。
汤亭亭在表达她的身份需求时也激起了评论界不一而足的反响。华裔作家程美兰 (Linda Ching Sledge)说在汤亭亭的文本中有些东西是明确的,“单纯文本意义上的神话被刻意改写成文学模仿,这也许是西方故事或变体的民间故事的反讽类比”①Sledge,Linda Ching,“Maxine Kingston's China Men:The Family Historian as Epic Poet.”,MELUS 7.4 ,1980,p.3-22.。《女勇士》和《中国佬》都是作为非小说来出版的,很多研究者不断对作品的文体提出了问题。如果这些作品不是小说,那就应该能从中窥见现实中的个人生活。②Yalom,Marilyn ed.,Maxine Hong Kingston,Women Writers of the West Coast:Speaking of Their Lives and Careers,Santa Barbara:Capra,1983,p.14.那么汤亭亭就把她的生活世界和经验世界融在了文本中。金伊莲在“如此对立的人:美籍亚裔文学中的男人和女人”一文中注意到因为汤亭亭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她的写作成为了对美国亚裔问题严峻考验的一些亚裔男性作家,尤其是赵健秀,严厉指责她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内容,称她为“西方成见的黄色代言人”,她篡改中国历史,中伤中国男性。赵号召严格而又博学的亚裔批评家为了文化融合要明辨真伪,他指责汤亭亭夸大中国男权态度,有意误述中国历史和传奇。③Kim,Elaine H,.“Such Opposite Creatures: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9,1990,pp77-79.
显然,有很多华裔读者也认为汤亭亭没有正确地表述他们,没有正确地表述华裔的文化历史。以福柯“占用客体”④Foucault,Miche,l“What is an Author?”,Textual Strategies: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Trans.and Ed.Josue V.Harari.Ithaca,NY:Cornell U P,1979,p.148.的话语分析为基础,罗伯特·威曼表明“占用”(Appropriation)的概念为讨论社会资源和利益冲突提供了有用的框架,社会资源和利益冲突驱使了作者和读者活动。⑤Weimann,Robert,“Text,Author-Function and Society:Towards a Sociology of 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odem Narrative.”,Literary Theory Today.Ed.Peter Collier and Helga Geyer-Ryan.Ithaca,NY:Cornell U P,1990,p.92.没有占有,就不可能表述。⑥Linton,Patricia.“What Stories the Wind Would Tell: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Ethnic Women Writers VI.MELUS,Vol.19,No.4,Winter,1994,p.42.“为了‘表述’作家占用他们书写的世界,将之变成他们的资源,对之行使权力,使之反映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反过来,读者占用文本和文本中的文化世界。更进一步说,占用实际上涉及自我投射和同化;在将事物变成他们自己的过程中,作家和读者将他物和他人异化。占用的作者和读者与他们所占用的资源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允许不同层次的认同和不同程度的‘距离、异化和物化’”⑦Weimann,Robert,“Text,Author-Function and Society:Towards a Sociology of 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odem Narrative.”,Literary Theory Today.Ed.Peter Collier and Helga Geyer-Ryan.Ithaca,NY:Cornell U P,1990,p.94-95.。汤亭亭创作的社会资源来自中国文化,她占用中国文化传统,占用中国经典和典故,占用母亲的现实世界和故事世界,占用他者话语,但汤亭亭以“美国视角”改变了她所占用的资源的意义。这个占用和书写的过程是表述过程,是自我身份建构过程,是以确立美国身份为利益追求。她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她占用的文化资源和世界,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她所占用的世界保持距离,将之异化和物化呢?
“汤亭亭为金山勇士、她自己和别的美籍华裔 (言外之意,还处于边缘状态的其他移民)等‘真正’的美国人宣称真实性,这一声称的必然推论就是她把中国文化传统当成了异类和他者,从而又把她作为‘真正’华人的真实性置于了疑问之中。”⑧Linton,Patricia,“What Stories the Wind Would Tell: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Ethnic Women Writers VI.MELUS,Vol.19,No.4,Winter,1994,p.40.所以汤亭亭处于矛盾之中,她的美国真实性和中国文化的真实性形成一套悖论。汤亭亭表达文化身份需求的策略是自我东化。“华裔对华人进行东方化是为了突显自己的美国性,汤亭亭和其他华裔女性作家一道通过书写来描绘令人厌恶的华人身体和洋泾浜英语,指责厌女、男权的亚洲传统,将华人语言、身体和文化当成东方化了的、令人厌恶的客体。”⑨Ma,Sheng-me,i“Orientalism in Chinese American Discourse:Body and Pidgin Author(s)”,Modern Language Studies,Vol.23,No.4 ,Autumn,1993,p.116.汤亭亭在反对西方将她当成客体的同时又将中国文化当成了客体,予以西方视角,在西方期待的东方主义话语框架下来建构自己的美国身份,而不是华人身份。她的这种东方化是一种主动迎合的自我东方主义。
二、汤亭亭作品的自我东方化
赵毅衡在分析海外华裔作家时将这个群体分成了三组,一组是以华文写作的海外居留者,二组是以英文写作的海外定居者,三组是以英文写作的华裔后代。在这三组作家中第二组和第三组几乎都以中国文化中落后的内容为题材,例外不多,这表现出海外华裔作家创作的局限性。“强势作家,努力避开接受定势,追求出乎意料的新颖题材;弱势作家,有意无意迎合文学场的期待域……期待定势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西方读者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是作家们有意的培养。”①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2005年第2期。由于直接或间接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西方读者的心里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刻板形象的定势,他们期待视野中的东方中国就是长期以来在各种文本中勾画出来的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裹足、鸦片、文革等都是让西方人津津乐道的中国产物。时至今日,和西方人交流过程中依然还有巨大的文化差异。西方人津津乐道裹脚,中国题材作家就写小脚。如哈金的《等待》(Waiting)中的小脚女人穿越时空;邝丽莎在2005年出版的《雪花秘扇》中极其详尽地讲述了裹足的过程,裹足的痛苦,以及裹足夺去小女孩生命的过程。裹足是西方人对中国女人的思维定势,那么华裔作家也无异于给自己的创作裹上了足,按照这种定势来书写中国。多元的中国文化在东方主义的视野里变得刻板、单调、神秘、落后、怪异,和西方文化形成二元对立。汤亭亭等作家作品中描绘的中国人是迎合“美国社会的中国人”②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2005年第2期。。
学者对香港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项华裔作家汤亭亭的调查,发现学生们普遍认为《女勇士》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表述错误,甚至是诽谤和中伤。作者有意使用夸张的手法来取悦西方读者,读者们会认为中国人都是野蛮无理性的。事实上,汤亭亭的《女勇士》以自传标签来突显故事的真实可信,以满足白人读者对他者世界中女性生活真相的窥探欲。故事令人生厌的夸张、扭曲、误解和偏见比比皆是。汤亭亭进一步丑化了中国文化……作为熟识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可以明辨这些华裔作家作品的真伪表述,但是那些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会被这些“美国之心”的故事误导和塑造,汤的中国文化与真正的中国文化相去甚远。③Wilcoxon,Hardy C,.“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eyond the Horiz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2,Problems of Otherness: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Spring,1996,pp.317-318.同为美籍华裔的作家赵健秀对有些华裔作家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华裔“通过伪造中国文化来迎合美国白人,白人也许会很高兴地看到美籍华裔如此偏爱美国价值,以至于生产出了“白人种族主义作品”④Chin,Frank,“Word Warriors”,the“View”section of The Los Angeles Times,June 24,1990.。
遗憾的是,汤亭亭作为华裔,身居美国,不但没有向美国读着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反而强调她作品中“中国文化”的真实性,以自传体的形式来刻画不存在的中国文化。《女勇士》不但没有克服已有的西方偏见,客观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文化,相反,“她以对刻板形象的证实来为东方主义话语煽风点火”⑤Yuan,Shu,“Cultural Politics and Chinese-American Female Subjectivity:Rethinking Kingston's Woman Warrior”,MELUS,Vol.26,No.2,Identities,Summer,2001,p.209、208.。“对于不知情的白人读者而言,汤亭亭现身说法,作为内部人士在讲述自己的家族血泪和中国文化传统,但在华裔和华人读者面前汤亭亭则呈现出一种第一世界妇女的优势地位,以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份来替第三世界不能自我表述的下等人审视、思索她们的悲剧。”⑥Yuan,Shu,“Cultural Politics and Chinese-American Female Subjectivity:Rethinking Kingston's Woman Warrior”,MELUS,Vol.26,No.2,Identities,Summer,2001,p.209、208.文本中她无名姑妈、月兰姨妈以及她沉默寡言的华人同学等在小说中都无法表述自己。在东方主义话语框架内东方是无言的,东方的女性更加无言,不能表述自己,叙事者以美国人视角替她们表述,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表述”。汤亭亭就成了来自主流社会的表述者。
汤亭亭1940年出生于美国加州,那么这个时间以前其父母早已经侨居美国,怎么可能经历大跃进,经历文革,经受迫害呢?《女勇士》中莫名其妙的反共思想完全是西方意识形态熏陶下的产物。《女勇士》时间跨度很大,从东汉末年的蔡文姬到南北朝时候的花木兰,从宋朝的岳母刺字到自己母亲的讲述。“汤亭亭的叙事占用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历史事实和另一种文化中的故事,她组织这些素材来给美国人讲述她需要他们聆听的故事”①Linton,Patricia,“What Stories the Wind Would Tell: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Ethnic Women Writers VI.MELUS,Vol.19,No.4,Winter,1994,p.39.,寻求美国社会的认同。汤亭亭的话语表述确实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和接纳,因为她所言说的都在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框架内,没有超出西方读者的理解期待。
身体层面的东方化。“在东方主义话语框架中,知识成了权力的载体,操纵着小说和令人费解的部分世界……华裔作家为了寻求文化认同,为了融入白人社会,不惜在写作中借用白人的视角和白人的目光来关注中国和中国移民,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华裔作家在文本话语中对中国、中国移民和美籍华裔进行东方化。这种种族的自我脱离揭示了隐藏着的自我厌恶。”③Ma,Sheng-me,i“Orientalism in Chinese American Discourse:Body and Pidgin Author(s)”,Modern Language Studies,Vol.23,No.4 ,Autumn,1993,p.104.汤亭亭占用华裔身体,把不同于白人的身体当成缺陷和拙劣。和异化的语言一样,华裔的身体也遭到了东方化和丑化。《孙行者》中兰西 (Nanci)长着一张东方人的脸,化妆师在给她化妆时得煞费苦心才能处理好她的那双眼睛。“There’s just so much we can do about these eyes.”④Kingston,Maxine Hong.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M].New York:Knopf,1989,p.24.萨克斯·罗默笔下的中国男性形象是典型恶棍傅满楚,而《孙行者》中的中国男性则多是个子矮小的黄色男人,加上一些猥琐行为,这些小男人只显得“更小、更黄”(littler and yellower)。无论华裔还是罗默笔下的中国男性的刻板形象都是对华裔男性的简单漫画似描写,这种刻画满足了西方凌驾于中国的优越性。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中国应该是一个落后、无知和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国度,西方可以随意想象中国人形象,恶棍和女人化的男人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了。“华裔作家的这种自我东方化不但暴露了自我厌恶,更损害了他们笔下的书写客体;中国和中国人,自我东方化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试图反映中国形象,却折射了华裔作家的自我形象。”⑤Ma,Sheng-me,i“Orientalism in Chinese American Discourse:Body and Pidgin Author(s)”,Modern Language Studies,Vol.23,No.4 ,Autumn,1993,p.105.
如果说语言和身体层面的东方化还只是表象的话,那么《女勇士》最深层次的东方化是对中国文化的东方化。“东方主义不可避免地和性别纠缠在一起……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这种权力统治着东方和女性。”⑥Ma,Sheng-me,i“Orientalism in Chinese American Discourse:Body and Pidgin Author(s)”,Modern Language Studies,Vol.23,No.4 ,Autumn,1993,p.107.华裔作家,尤其是汤亭亭的作品中女性是永恒的话题,通过母亲的故事,展现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扭曲的私密命运。中国文化的厌女、迷信、落后守旧的传统都被她夸张地进行了表述。汤亭亭不厌其烦地表现中国文化中令人厌弃和神秘、迷信的方面:历史传说、儒道佛教、一夫多妻、裹足弃妇、气功武术、听书看戏、猴脑宴席、文革斗争,等等。这些文化现象正好吻合西方对中国文化已有的认定框架。因此荒诞怪异的《女勇士》深受美国读者褒奖,在西方读者看来,《女勇士》如同一桌满汉全席,他们期待的美餐尽在其中。作者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出发,在两种文化中做出选择来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汤亭亭的文化选择印证了东方主义,这一印证反过来又巩固了她的美国身份。
汤亭亭的作品用母女关系来指涉东方和西方,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西方文化。女儿们想摆脱母亲的束缚,成为美国人。母亲们唠唠叨叨讲述中国故事,女儿们忙着追求美国身份,这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美国社会教会她们美国的生活准则,她们习惯成自然地按照美国的准则生活,而社会又将她们排在“少数民族”之列、正宗的美国人之外,社会偏见与她们天生的中国式谦虚、温顺交织在一起,令他们在地道的美国生活中束手无措,迷惑不已,从而导致危机或失败。母女间争执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冲突中夹杂着不少中国人难以接受和想象的荒诞怪异插曲。汤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让在中国文化里熏陶成长的中国人无法接受,作品中的文化与现实中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华裔作家对中国素材的占用实际上就主流美国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占用,主流文化不会在少数族裔的语境和条件下来考察其文化和传统,而是以主流和主导的视角来看待族裔文化,华裔作家呼应着美国主流文化声音,因而受到了来自汉学家、中国读者和评论家的批判和质疑,认为她们歪曲了中国传统文化。汤亭亭说她不是要表现中国文化,她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那么读者不禁要问,她书中描绘的家史、文化习俗、花木兰、蔡文姬等不是中国的吗?汤亭亭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报告时,学生们恳求她不要把中国人写得那么丑陋。她回答说,她是美国人,她只能这么写,正面的形象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来写。
“要有信心和能力来表述一种文化或群体,作者或读者就必须是内部人 (insider),而非局外人 (outsider),如果汤亭亭的作品熟知中国文化的读者读来觉得陌生,美国读者读来觉得怪异,华裔男性作家读来觉得虚假,那么她的基本立场在哪里呢?”①Linton,Patricia,“What Stories the Wind Would Tell: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Ethnic Women Writers VI.MELUS,Vol.19,No.4,Winter,1994,p.41.答案是很显然的,汤亭亭不是中国文化的知情者和内部人,她把自己当成了局外人来书写中国故事,她以美国人的身份在戏说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为美国读者带来了异域风情,自传体和回忆录的形式为东方主义话语平添了来自“东方文化内部”的声音。“身份的确立是一个发声的过程。”②Hall,Stuart and du Gay,Paul ed.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p.3.这些声音哪怕怪异,哪怕费解,哪怕刺耳,也比沉默要强得多,在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借叙事者很清楚地发出没有声音就没有身份的宣言。但汤亭亭的声音实质上并没有跳出东方主义话语桎梏。汤亭亭利用对中国经典的拼贴在《女勇士》中突显女性力量,在《中国佬》中则对中国男性进行去势。陈昱利用新历史主义的“颠覆”和“含纳”(suberversion&containment)的观点对汤亭亭的作品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汤亭亭试图移植中国故事来颠覆美国主流话语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同时改变华裔女性形象,确立华裔女性作家在美国的身份,而这一颠覆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含纳在美国主流话语中。在话语霸权中成长的她潜意识中还是陷入了话语权力机制留下的陷阱中。③陈昱:《汤亭亭和赵健秀对中国经典的改写》,http://wenku.baidu.com/view/e0094e3710661ed9ad51f32c.html.汤亭亭颠覆的是中国文化,接纳的是东方主义,所以她的话语才能让美国主流接纳,得到主流的认可。
《女勇士》通篇充满类比,无名姑妈、月兰、沉默女孩和花木兰、勇兰、“我”形成鲜明的对比。前三者是失败者,后三者是胜利者。前三者是悲剧,后三者是奇迹。成功和奇迹的出现就在于身份抗争的胜利。东方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将东西方两极化。东方是沉默的,柔弱的,像小女人;而西方是强大的、善于言说的,像大男人。汤亭亭一方面批判男权社会,而又矛盾地陷入了男权主义中。无名姑妈、月兰、沉默女孩柔弱、沉默、是需要保护的女性;花木兰、勇兰、蔡文姬和“我”是刚强的、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男性化了的女性。《女勇士》最后一章蔡文姬的故事极具隐喻意义。蔡文姬以外族的音乐来表达自己的经验和内心世界,以外族的文化来表达自己的思维,这样方可以在外族和本族间游走,而汤亭亭正如蔡文姬,她占用英语、女性主义和美国视角来强化和批判中国的厌女思想,那么她占用的美国思维成了她成功的桥梁,她建构的成功的自我女勇士形象和奇迹正是建基于东方主义话语框架下的美国价值评判标准,正是在这同一话语框架下言说,才有了“我”女勇士的成功,所谓的成功即是美国身份的确立。
汤亭亭本人极力辩驳她作品的东方主义特点,也曾自己撰文来阐释如何解读她的作品。她“努力避免有人指责她将亚裔经验置于美国文化语境之外,因为牢记亚裔作为外来者和局外人的刻板形象,所以她将无名姑妈与《红字》里的海斯特联系在一起来取悦女性主义读着和批评家”①Yuan,Shu,“Cultural Politics and Chinese-American Female Subjectivity:Rethinking Kingston's Woman Warrior”,MELUS,Vol.26,No.2,Identities,Summer,2001,p.218.。汤亭亭要告诉读者和批评家她的写作是基于西方语境和西方视角来的。她迎合西方女性主义来摆脱亚裔言说的嫌疑,她强调自己的美国身份和美国经历,这样避开了中国读者和学者的批判。所以汤亭亭在香港面对中国学生的责问时,她说中国故事应该由中国人来写,而不是由她美国人来书写。《女勇士》和《中国佬》不仅没有对美国主流话语和主流文化产生任何冲击和颠覆,相反,她刻画的文化形象中充满片面性,产生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是在东方主义话语框架中言说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是有意无意的自我东方化。采用美国的东方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男权体制,凸显自己的美国视角,从而确立自己的美国身份。
三、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问题
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认为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 (essence),而是一种立场(positioning)。因此存在一种身份的政治,一种立场的政治,而这种政治并不能保证一种超越一切的、毫无质疑的“出身的法则”(law of origin)②Durham,Lisa Lowe,ed.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Immigrant Acts: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83.。身份不是简单的共享历史和祖先,而是纵横交错的话语、实践和姿态。汤亭亭对母亲文化的拒斥显现出了她追求文化身份的努力。那么在她确立身份的过程中,她明白华裔的出生并不是她的本质身份,在美国主流社会,她的祖先和出生无法帮她确立自己在主流社会的地位,所以她必须要有一种立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汤亭亭选择在美国主流话语接纳的东方主义话语框架下来言说西方读者爱听的“中国故事”,来改写、拼贴中国故事以确立自己的美国身份。华裔作家中不仅仅是汤亭亭,还有不少在写作中也都存在着自我东方化现象,刻意强调自己的美国身份。比如谭恩美就希望人们不要称她为亚裔美国作家,很多场合她坚称她是一名美国文学作家。她们借中国来否定中国,借中国文化来否定中国文化,从而达到肯定西方、肯定英美文化,确立西方身份的目的。由于不同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海外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立场和态度、文化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华裔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有的承继中国文化,保留中国文化之根,如林语堂、于梨华、毛翔青等;有的则否定中国文化,极尽夸张之能事来丑化中国文化,认同西方文化。其实,即便在很多白人作家的中国题材作品中也有不少客观和公允的写作立场,那么身为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渊源的华裔作家何以要自我东方化呢?汤亭亭的自我东方化不是个案,而是代表着一个群体,他们凭借否定中国文化来认同西方文化,通过认同西方文化来获得西方的身份认同。这一部分作家的文化认同问题在跨文化交流中值得反思。
“康拉德选择了英文,却几乎从来没有写波兰;贝克特选择了法文,作品中看不出任何爱尔兰情结。”①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2005年第2期。汤亭亭以英文写作,却几乎不写美国,而是专事中国,但自己又否认是在写中国。在康拉德、贝克特和汤亭亭之间有共性,更有差异。共性是他们都是某种程度的流散作家,不以自己的母语写作。差异是他们创作的题材不同,社会影响不同。康拉德和贝克特的作品虽然不写自己的母文化,但关怀的是更普遍更宽泛的人性问题,所以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要远远超过汤。在这种差异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基础差异值得发掘。康拉德和贝克特的故国故园属于整体的西方,属于同质文化内的迁移和流散。而汤亭亭属于异质文化之间的迁移,尽管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但作为移民的第二代,她和父母文化联系非常紧密。她在“中国”和“去中国”两者间难以划清界限,所以才会很矛盾地书写着中国,又否认是在写中国。她笔下的中国是真实的,同时也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因为她占有的文化资源的源头是真实的,是中国独有的,如花木兰、蔡文姬、岳母刺字、儒释道,等等。说“不真实的”是因为她对这些真实的文化源头进行了改写和拼贴,倾注了西方色彩,尤其倾注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色彩。所以她自己都在“是”与“不是”间游走。华裔作家和康拉德、贝克特身处的社会基础不同,社会期待也不同,题材选择不同,创作路径也就大相径庭。
首先,华裔作家认同西方主流文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从18世纪以来形成的仇华影响世代相传,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在西方历史上和文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直到上个世纪初,即便是在中国本土,洋人还将华人与狗相提并论。意识形态和刻板形象的集体投射使得华裔在西方遭到不可回避的社会歧视。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冷战时期,华人一直成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不良国际关系的“牺牲品”,美国政府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及其美国的公众情绪是决定美国如何对待国内华裔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大多数的民众仍然固守一种广为接受的错误观念,即美国的华裔应对他们祖国的行为“负责”,这种冷战思维的现实直接影响了华裔作家的思维定势和他们的经验世界,最终影响了他们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初到美国的华裔由于语言障碍,无法以英语表述自身的独特意识,这些华裔的后代在美国出生成长,掌握了作为霸权语言的英语,但又无法依赖中国文化的传承来树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既不为主流社会接纳,又无法融入中国文化,更不愿意接受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出生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后代发现自己是游离于美国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文化认同成为华裔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西方,华裔作家的写作往往开始于剥离自己固有的文化身份——即对华裔文化传统的反叛,这种情形在美国表现又尤为突出。对那些以写作为生的华裔作家来说,中文和英语都是“外语”,他们是一群没有母语的人。由于历史上的种族排斥、刻板形象和意识形态影响,中国成为了西方的参照“他者”,华裔也就自然成为了主流的“他者”,他们即便加入美国国籍也并不能够享受到与白人甚至是黑人相等的公民待遇,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永远是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是被称为ABC的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华裔在文化上的无身份感与华裔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的社会建构有着密切关联。
其次,华裔作家认同西方主流文化有其个体的原因。汤亭亭的《女勇士》讲述的是母女的故事,是以女人为中心的作品。《中国佬》讲述的是祖父和父亲的故事,是华裔男性的故事。将两部作品综合起来,正好是汤亭亭一个家族的侨居历史。在这两本书中都涉及女人或男人的“沉默”,沉默也是一种表述,“沉默”中夹杂着闪烁其词,给予西方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人在中国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待遇,中国到底有多可怕,中国到底有多怪异,以至于他们宁死也不回故国,至死也不提往事?从这两个文本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汤亭亭的父辈逃离中国,宁死不归,他们对中国没有故国情怀。汤亭亭父辈转述给孩子的是厌女、残忍、落后、守旧和愚昧的中国文化,这种中国形象由父辈反复灌输给下一代,他们即便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也是望而生畏。个体家庭的“家史”和东方主义话语相互印证,巩固了东方主义话语偏见。
除了家庭教育外,汤亭亭还从小接受西方系统的体制化教育,生活学习在西方社会,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会接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以及其它东方国家的固有看法。她虽然和康拉德、贝克特一样都是接受的西方教育,但是却没有勇气和胆量去触及宏大的题材,只是拘束在华人圈,没有凭借西方的人文精神给予人性更广阔的人文关怀。在直面强势文化时,这一类华裔作家的个体反应和应对策略是认同美国文化,接受强势文化,就范于东方主义,她貌似客观的自传故事中充满主观偏见和臆想。她的策略是自己选择东方化,通过文本来强化东方主义意识。作者有选择地聆听母亲的故事,加以改写;有选择的选取中国题材,进行拼贴;有选择的选取中国文化,进行东方化,所以作品才会让中国读者陌生,让美国读者觉得充满异域情调和中国特色。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把西方流传的中国菜单做了大大的补充和细化,突显中国人的残忍和怪异,让读者顿生恐怖之感。“‘我’厌恶的并非是中国饮食,而是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①Wong,Sau-ling C.,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48.种种厌恶和取舍都是出自作者的个体原因。
面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汤亭亭这一类华裔作家表现得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她们对母国的文化只记他们有兴趣的事情,没有兴趣的事情他们会“忘记”。她们还会因为需要而创造一些中国神话、中国文化。《女勇士》中尽管罗列了大量的中国风俗、神话、饮食,但是汤亭亭本人在小说完成之前,从未到过中国。1989年,她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提到“我担心到中国后会发现以前写的一些东西会与事实不符”②Skenazy,Paul,“Kingston at the University”,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Hong Kingstong,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ed.,Jackson:Mississippi UP,1998,p.134.。汤亭亭在多个场合申明她的作品中的中国是她想象出来的,是创作的。她明确表示她写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事实上,汤亭亭是在用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具体意象和情节,讲述她的美国故事。如果如汤亭亭本人所言只是想象,那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她写作中的主观臆断。与西方人一样,她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化是落后、愚昧、神秘和不可思议的,通过解读汤亭亭作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可以感觉到汤亭亭的中国文化认知不仅受到了东方主义的影响,而且她在自觉的加以“自我东方化”,她笔下的当代中国明显地带有美国意识形态痕迹和东方主义话语色彩及思维定势,作品中展示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加强了西方读者“东方话语”影响下的“他者化”。这种东方化和他者化的策略暗合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东方研究“异文化”的路径,西方读者之所以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他们大多带着猎奇和文化偏见看待这部作品。难怪西方评论家大多把《女勇士》的成功归功于其“带有东方色彩、不可思议、神秘而具有异国情调”③Kingston,Maxine Hong,“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Ed.Guy Amirthanayagam.London:Macmillan,1982,p.56.。更有评论认为该作品中充满了恐怖和迷信。国内也有研究者指出汤亭亭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坛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她描述的“正常的美国”和“怪异的中国”有关。④王理行:《中西文化的冲突、对话和超越——论20世纪美国华裔文学》,《译林》2002年第3期。所以赵健秀指责汤亭亭等华裔作家,迎合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口味,歪曲、篡改中国文化,混淆真与伪的界限,误读误用中国经典和传说,曲意取悦白人读者,歪曲华裔美国人本来的面目,因此竭力维护出生在美国的不被“白化”的华裔美国人身份,认为汤亭亭等人作品中的中国和华裔美国人是白人种族主义想象的产物。
结 论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意识,因此,人们总是以其自身的经验世界出发,去审视别的民族、别的文化。华裔作家的移民背景同样影响了他们写作内容的选择和文化身份的确认。有些华裔作家渴望去中国化,进入白人社会,但又无法完全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于是他们采取的策略是认同主流文化,在霸权意识形态需要的话语中进行创作,他们过分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创作中的价值取向约束了他们作品的文学性。文学不是谈意识形态,文学是人学,是要以人性为书写目标,一些华裔作家以身份和族裔来写作,以狭小偏执的题材为内容,必然导致其文学作品的品格不高。这样的作品要么如同赵健秀所言根本不是华裔文学,或者不是文学,即便算得上是文学,在文学史上也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在西方主流文化里成长的华裔作家选择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话语来表述中国,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选择上的惰性,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起西方批判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工具,以西方的视角,如“女勇士”一般朝着中国文化大刀阔斧砍去。这种文化认同和文化取向是很成问题的,跨文化过程中需要辩证的文化认同观。华裔文学创作应该摆脱东方主义话语的束缚和影响,选择宽泛普适的题材,跳出狭小的圈子,方能确立其在世界真正的文化身份和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