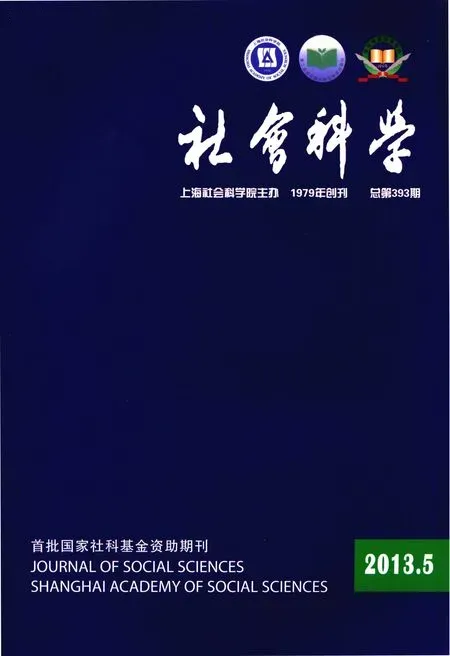鲁迅形象在德国的最初建构——以两部早期的鲁迅博士论文为例*
范 劲
1939年,王澄如在波恩大学完成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一篇探讨中国革命的论文》(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这篇论文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反响,但对于鲁迅符码后来在西方话语场中的升起来说,还是有某种预兆性。荷兰人拉斯特 (Jef Last)则在战后德国第一个写出关于鲁迅的专著,即他1959年出版的《鲁迅——诗人和偶像:一篇探讨新中国思想史的论文》(Lu Hsün-Dichter und Idol: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euen China),接续了王澄如之后中断近二十年的研究的线头。
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揭示了中心符码对于文化形态的组织作用。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对遴选出来的少数初始符码的叙述和发展。任何一种符号性认知都意味着对认识目标中的主要和次要因素做出有效区分,凡是从自身系统角度看来并非意义承载者的因素,对于认识主体来说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对于跨文化认知,即在本文化内为异文化腾出空间的行为来说,初级符码系统的建立至关重要,后来发生的符码转移都要受这个最初参照系的牵制。①Yuri M.Lotman,Universe of the mind: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translated by Ann Shukman,New York:I.B.Tauris,1990,p.58.因此,鲁迅就成为了文学场中的引导性符码,对德国的中国文学地貌形成意义非凡。事实上,在模式化特征明显的德国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场上,孔子、胡适、鲁迅几乎成为三种原型因素,分别代表中国的“传统”(和谐、无我)、“现代”(科学、疑古)和“未来”(革命、自我反思),围绕着它们组织起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场。而就鲁迅符码的形成来说,这两部最早的鲁迅专著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王澄如的鲁迅论文:鲁迅的革命精神之源
王澄如,女,1909年生于贵州,1932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1933年至1934年在上海国民党妇女部任秘书职。1936年赴德,先后在柏林、科隆和波恩学习教育学、哲学和报刊学。1939年9月在波恩大学汉学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导师为汉学家石密德 (Erich Schmitt),论文最初刊于1939年的《柏林大学外语学院通报》 (Mitteilungen der Ausland-Hochschule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1940年作为单行本出版。
论文分六部分。继导言之后,第二部分为鲁迅生平,包括:1.童年时代;2.颠沛的求学岁月;3.中国的革命时代;4.逃往厦门;5.在“革命之城”;6.上海的晚年。其脉络主要来自林语堂的回忆和《而已集》、《夜记》。第三部分为《“文学革命”》,包括:1.鲁迅的“文学革命”功绩;2.鲁迅作为文学的内在革命的斗士;3.身陷文学批评中的鲁迅;4.鲁迅对于批评家的希望。第四部分简单介绍了鲁迅的文学作品,包括:1.《狂人日记》;2.《呐喊》;3.《彷徨》;4.诗歌;5.杂感、论文、研究;6.总结。第五部分谈鲁迅和外国作家的关系,包括:1.鲁迅作为俄国文学的朋友;2.鲁迅和易卜生。第六部分为结语。
王澄如让德国汉学界第一次了解到,在胡适——一度的现代中国文化的象征,普鲁士科学院首位亚洲籍通讯院士——的炫目光环之下,竟还有一个重量级的现代中国作家存在,和胡适同为文学革命的重要推动者和白话文学的缔造者。她给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界定,即新旧时代的分野:“鲁迅不仅是革命的第一位政论家,还是唯一一位在文学革命之后还能称得上作家的中国作家。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阶段。旧小说总是写文人雅士,是浪漫的。然而在读到鲁迅《狂人日记》时,我们的感觉是,就像突然有光亮射入阴暗的庙宇。我们一下子由中世纪进入了新时代。”①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27,1,2,27,28.
她的中心问题是,何为鲁迅其人和作品的根本特征?她认为,鲁迅的魅力就在于他的高度复杂性。鲁迅不能被归入任何一种诗人类型或文学思潮,他既非唯美主义者,也非哲学家或革命家,种种称谓都只代表了其全部人格的一部分。“鲁迅的人格不能被纳入任何系统,即便其形成和时代密切相关,而他又是这样关注时代”②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27,1,2,27,28.,这句话在论文中屡次出现,体现了作者对于鲁迅的基本认识。由此就可理解,为何鲁迅的思想从来没有一种系统的形式。非但如此,鲁迅不满于同时代人给他安上的“革命的理论家”的帽子,他之所以成为诗人和作家,不是因为对时局不满或向往革命,而是因为内在而深层的对善和正义的渴望需要得到表达,这种愿望绝非由单纯革命可以实现。让他成为诗人的“仅仅是他对艺术的热爱和他的艺术天赋”,这里包含了他的“内在使命”和“命运”③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27,1,2,27,28.。他和一般的革命鼓动家的区别就在于,“他 (鲁迅)是一个全心地投入他的艺术的人,而非一个伟大时代的先知和宣告者”④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27,1,2,27,28.。
可是反过来,难道因为鲁迅没有高唱无产者颂歌,就不是革命者了吗?恰恰相反,王澄如认为,如果因此否定鲁迅的革命性,实际上是误解了革命文学的任务和意义。她说:“革命的艺术不仅属于各种不同的文学作品,毋宁说,我所说的革命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艺术了。社会形势如此复杂,革命须处理种种不同情况,需要许多方法前提,才能让人理解生命的意义。”⑤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27,1,2,27,28.这个论述无疑引申自鲁迅《革命的文学》中革命和文学关系的三阶段论:革命前没有革命文学,惟有被压迫者的哀诉;革命时没有革命文学,因为革命者无暇旁顾;只有革命后才有革命文学。而鲁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作家自身是革命者,才能创造革命文学。这就产生一种暗示,革命本身才叫真正的艺术,而革命文学毋宁说是一种事后的拙劣模仿。作者相信鲁迅的文学魅力正源于深沉的革命意识,而其革命意识来自文学家的创造冲动和敏感天性本身,这就是她所谓鲁迅的“文学之内在的革命化”,而她的论述,就是要呈现这种斗争的“方向、目标和方法”①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34,59-60,55.。换言之,鲁迅的革命意识是超越党派路线和理论的更深刻的政治实践,即一种“生命原则”。在不多的理论术语中,作者反复提及“生命”,如“生命意志” (Lebenswille) (2次), “生命原则”(Lebensprinzip)(1次),“生命冲动” (Lebensdrang)(1次),“生命势力” (Lebensmächte)(1次),“生命秩序”(Lebensordnung)(1次),充分体现了20世纪初德国盛行的生命哲学的影响。显然,作者竭力把鲁迅的革命意识抽象化和本体化,有意把它和政党观念相区分。她还断言,鲁迅同情俄国革命,不是因为他赞同社会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而是肯定革命的“原初的过程和特性”,他所针对的并非中国某一具体的政治观念,而是“敌对的生命势力以及它们的社会与文化专制”②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34,59-60,55.。他想达到的不是新的阶级专政,而是一种更公正更有意义的“生命秩序”。
这种由下层民众所承载、以摆脱旧的社会秩序和偏见为目的的“生命意志”的存在,正是20世纪中国的精神变迁和欧洲的一致之处。这一过程既孕育了具有革命和创造精神的人物,也造成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阶层,只能喊喊口号,却无法深切地体察时代问题。王澄如在易卜生和鲁迅之间所做的比较,无形中暗示读者,鲁迅不属于“软弱的知识分子阶层”。易卜生和鲁迅同为现实主义作家,无情地揭出时代的病苦和腐败,然而,易卜生走的是伟大的孤独者之路,故极度悲观和绝望,鲁迅和他的角色却没有陷入这一深渊,因为鲁迅和青年革命者并肩前进。易卜生从不给出解决方案,而鲁迅却仿佛抓着人物的耳朵,逼他看清事情的真相和自身的过错。易卜生的戏剧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问号,鲁迅的小说背后则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作者认为鲁迅作品忠实地反映了时代及其种种主导趋势。农村生活是他关注的重点。他那个时代,由于洋货涌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农村日趋凋敝,成为贫苦生活的写照,而鲁迅的生命和写作正是面向穷人和被压迫者——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鲁迅想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人和人生,什么样的深渊隐藏在背后,这一努力将他和俄国文学联系起来,并且将他引向后者。”③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Berlin:Reichsdruckerei,1940,p.34,59-60,55.作者认为,鲁迅接近俄国文学正是出于对以消遣为目的的中国旧文学和英美文学的反感。
王澄如的重点是鲁迅和革命的关系,她根据1931年出版的《转变后的鲁迅》中收集的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文章,在第三部分中特意设计了一个鲁迅和梁实秋的虚拟对话场景,将鲁迅对于革命和文学的关系的态度较完整地呈现出来。梁氏作为“不革命”一方的代表,强调写人性的文学比写某一阶级的文学更深刻,而鲁迅认为并没有关于人本身的文学,普遍的人性不过是人身上的食色之类的生物性或动物性,文学必然是有阶级性的。
这部论文的学术水平纯属一般,主要是对中国评论家观点的照搬和转译,但也体现了彼时德国汉学界的一般风气。④参见范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对于Heinrich Eggert于1939年在汉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的产生过程》的评价,这篇论文基本上就是转述和照抄胡适观点。作者主要的参考书就是一部《鲁迅论》,反复引用的几篇文章为方璧的《鲁迅论》、钱杏邨的《鲁迅》、林语堂的《鲁迅》、茅盾的《读〈呐喊〉》等, 《呐喊》、 《彷徨》、《朝花夕拾》等集子却并未真正读过。因为完全缺乏对作品的细读和对历史背景的掌握,在照搬中也错讹不断。如她先是说,鲁迅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精神领袖,让许多年轻作家在他的杂志(《新青年》)上发表文章。⑤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p.7,4、23,15,14.而在第17页又提到,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周树人的字成了“像材”,⑥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p.7,4、23,15,14.周作人成了兄长,⑦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p.7,4、23,15,14.许广平则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⑧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p.7,4、23,15,14.可最荒唐的还是鲁迅作品的介绍。显然作者把《狂人日记》误认为鲁迅自己的日记了,所以她把《一件小事》当成《狂人日记》的一部分。从一句莫名其妙的评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殷切地要求青年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写情诗和春天的诗,抛开‘旧酒囊’,追求符合时代和他们的任务的新的生活形式”①Wang Chêng-ju,Lu Hsü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p.45.中可看出,作者原来并未读过《狂人日记》,这一句不过是照抄雁冰《读〈呐喊〉》。另外,作者说鲁迅有两部诗集,一部是《野草》,另一部是《朝花夕拾》,并自称从两部中各选出一首以飨读者,一首是悲观、犹疑的《淡淡的血痕中》,另一首是表现如潜行的“地火”般的革命激情的《题辞》,而事实上,两首诗都出自《野草》集。
二、拉斯特的鲁迅论文:从诗人到圣像
拉斯特 (1898—1972年),荷兰著名左翼诗人和作家,1932年到1938年间加入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加入国际纵队作战。他是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密友,1936年两人一同访问过莫斯科,纪德在为拉斯特的小说Zuyderzee法译本写的序中,称赞他不仅在作品中,而且在行为举止和整个存在中都是“一位诗人”,还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②转引自 Basil Kingstone,“Jef Last and André Gide:The record of a friendship”,in:Canadian Journal of Netherlandic Studies,Issue III,ii(Spring,1982),p.92.。拉斯特从1917年到1920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中文,1955年到1957年在汉堡大学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指导下完成以鲁迅为题的博士论文。傅氏为德国汉学元老福兰阁之子,他领导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在当时西德的汉学研究机构中是最关注中国当代的。而在冷战氛围下,西德读者更感兴趣的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鲁迅作为共产中国的文化偶像被摒弃在视野外。③参见 Lutz Bieg,“Lu Xun im deutschen Sprachraum”,Wolfgang Kubin(Hrsg.):Aus dem Garten der Wildnis,Bonn:Bouvier,1989,p.178,p.180.拉斯特不意成了战后德国鲁迅研究的先行者。④东德方面,还有1957年在莱比锡大学完成的两篇国家考试论文,葛柳南(Fritz Gruner)论文是对《摩罗诗力说》前三节的翻译和评论(Übersetzung und Kommentierung von Lu Hsüns Artikel Die Kraft der romantischen Poesie,Abschnitt 1-3),伊尔玛·彼得斯(Irma Peters)的论文是《论鲁迅对于传说素材的处理》(Behandlung alter Sagenstoffe durch Lu Xun),但都没有公开出版。
论文分七章。第一章导言;第二章《鲁迅和他的前辈们》;第三章《“共产主义者”鲁迅》;第四章《1937—1945年战争前后共产党方面对鲁迅的评价》;第五章《评价转变的原因》;第六章《鲁迅——人和作家》;第七章《鲁迅和“革命文学”》。博士论文原题“对鲁迅评价的转变及其原因”,正式出版时改为“鲁迅——诗人和偶像”。言下之意,鲁迅从左翼阵营围攻的对象到“中国的高尔基”,从落伍者到毛泽东称颂的新圣人,乃是时代交替的结果,揭示这一转变的原因,就能对现代中国精神氛围的变迁有一个生动认知,而文章主要内容也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共产主义世界对鲁迅评价的转变
1930年,沙科夫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作出决议,把中国文学运动划为三个方向:创造社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语丝社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和新月派代表的市民资产阶级文学。鲁迅属于小资产阶级作家中接近无产阶级的成员。1932年莫斯科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Literaturnaja enciklopedija)说得更清楚,鲁迅在意识形态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作品的基础是乡村生活及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向黑暗现实抗议,却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结论,因为“他的革命勇气不够”,《呐喊》和《彷徨》尤其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特性”。他在文学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惜乎停留在“旧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自外于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洪流,仅仅由于国民党压迫的加剧和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才又转向世界革命。⑤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euen China,Frankfurt a.M.:Metzner,1959,pp.26-27,28.这种评价在抗战结束后被彻底推翻。何干之1946年版的《鲁迅思想研究》中,鲁迅对革命文学的嘲弄,被引来证明当时上海左翼激进文人的投机性和宗派主义。与此相应,在费多尔仁科眼里,《文学百科全书》用来显示鲁迅“小资产阶级本质”的《呐喊》恰恰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新纪元:“《狂人日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有机综合,真实地反映了为争取改造社会而进行的斗争情形。”那些不屈从于“吃人”社会的人甚至和苏联发生了关联,譬如《一件小事》中无比高大的人力车夫“明显地象征了苏联的无产阶级”⑥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euen China,Frankfurt a.M.:Metzner,1959,pp.26-27,28.。波兹德涅耶娃则认为,鲁迅从未超然于政治,而是参与了所有的革命活动和组织机构。针对《文学百科全书》提到的“1925到1927年的革命大波”,她写道:“从1925到1926年,当反动派转入攻势,进步团体遭到迫害时,鲁迅积极投入到进步师生反对政府措施的斗争中……1930年初他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从而把自己的活动和共产党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①[俄]波兹德涅耶娃:《鲁迅为了中国文化和新民主的斗争》,转引自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29.拉斯特从两方面总结了这一评价上的转变:1.尽管鲁迅在1928年到1930年发生了“转变”,共产党方面到1932年才停止了对他的攻击。在他死后,评价才完全转为正面。而直到抗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后才开始了对他的圣化;2.对鲁迅的新评价不仅指向他个人 (特别是对促使他转向的“危机”的强调),还涉及他1928年前的作品。而神化个人,很可能是要让人们淡忘与鲁迅同时代的非共产党作家。②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29.
2.评价转变的原因
评价转变的原因在哪里?论文虽然以此问题为核心,对问题的阐述却远远谈不上清楚。这一章分为三节:1.充满矛盾的鲁迅:“严重的危机”;2.西化的鲁迅;3.“中国人”鲁迅。
首先,革命和文学的复杂关系是鲁迅的主要问题。何为革命?革命可以走多远?应不应该有一个界限?《而已集》反复地纠缠于这类问题。革命少不了流血,不可能因为害怕牺牲就退缩,但又有多少宝贵的年轻生命因此而丧失。拉斯特说,鲁迅在《而已集》序诗中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革命总不免流产,而清朝的覆灭带来更多的混乱、腐败、贪污和军阀混战?其次,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作为教师和作家,在这里写写杂感就够了吗?难道不应该到前线去,加入革命者的街垒战吗?左翼理论家对此有现成、清晰的答案,鲁迅却没有,直到1928年至1930年这个思想、人生的转折点,才意识到了无产者的力量和前景,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也使他的立场日益明确。正是这一“剧变”(scharfe Schwenkung)使他受到共产主义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成为新的鲁迅评价的出发点。然而,拉斯特问:这一“剧变”果真如此剧烈吗?尽管从鲁迅的后期作品中无法推断,他真正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然而他先前也从未表现出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苏联的成功让他相信无阶级社会的可能,可在他1932年前的文章中,也从未反对过十月革命和苏联。
《西化的鲁迅》一节探讨鲁迅和西方思潮的密切关系,其价值就在于,作者以当事人的历史感,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鲁迅和国际左翼阵营的思想联系。拉斯特首先披露了西方左翼作家的心路历程。他说,西方作家从19世纪下半叶起日益显著的社会批评倾向,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预备。一战的爆发终结了乐观主义情绪,失望之下,他们希望以世界革命阻止第二次灾难的出现。他们为新发现的俄国文学所振奋,盼望在俄国革命中寻回俄国作家的精神,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个国际现象。然而一战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在无产者和青年人面前的自卑,一战象征了自己的阶级、自己那一代人的失败,这种自卑感成为靠拢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三十年代,新一代革命作家进一步激进化,要求彻底批判先前的“同路人”作家。而最终,越来越多的理想主义者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理想和斯大林主义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显然,鲁迅和西方作家在诸多方面相一致。鲁迅早年崇拜雪莱、拜伦等“摩罗”诗人,19世纪末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俄国的经典作家对于他更具有重要意义,激发了他的社会良心。鲁迅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决定性一刻几乎同时出现,且具有相同后果:一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欧洲作家的心态,鲁迅最绝望的时刻则是1912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上台,而希望重燃,是由于《新青年》在1918年邀他写稿。和这一时期的西方作家一样,鲁迅更重视的是生活和实际革命活动 (相比之下,文学没有太大价值)。这种政治化环境对欧洲和中国作家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均起到了消极影响。甚至在一些文学外领域,双方也有着重叠之处,譬如对柯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的木刻,鲁迅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作家均表现出极大兴趣。拉斯特还注意到,鲁迅和欧洲的“同路人”作家几乎使用同样的套语,他特别列出了其中三种:1.“同路人”的一个惯常论据,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不可信,这在鲁迅文中同样存在;2.他们都断定,诗人的革命想象过于浪漫,以至于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3.他们都嘲笑那些“沙龙共产主义者”,一旦虚荣心和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类人就会脱离革命。
鲁迅却又是典型的中国人。尽管他以反传统自居,蔑视抱残守缺的国粹家,但他热爱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他更愿意穿长衫而非西装,就是一个重要象征。鲁迅极为熟悉中国旧文学,他在东京时向章太炎学习考据学,并不像冯雪峰所言,仅仅是仰慕后者“不屈服的革命精神”,而是出于对国学的热爱。①Feng Hsüeh-feng,“Lu Hsün,his life and thought”,in: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ün,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4,p.228.转引自 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43.他的旧体诗绝非单纯的自娱,而是表达了某些最深沉的情感。他的作品充满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典故和影射,如他的《一件小事》就和刘基的《卖柑者言》具有相同结构,都表达了尖锐的社会批判,都表现了作家和下层民众的直接接触和由此导致的自省。
综合这一章涉及的三个方面,倒也不难整理出拉斯特的逻辑理路,即评价转变的原因在于鲁迅自身的矛盾性,以及西方当代思潮和中国传统对他的交替影响造成的不确定性。
3.鲁迅的思想和人格
跳出了这种评论的漩涡,拉斯特试图重新总结鲁迅的思想和人格特征 (第六章)。他认定,鲁迅最明显的性格特征是深沉的感伤,这种感伤同时也是反讽精神的来源,伤感和反讽的混合,构成了鲁迅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风格特色。但他的全部愤懑和郁结,针对的与其说是贫困和剥削,不如说是阿Q式的冷漠和心灵贫瘠,“鲁迅希望通过改变思想,通过承负这些思想的伟大人物,而非通过‘生产力的改变’,以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②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51.。鲁迅号称“中国的高尔基”,拉斯特却认为,称他为“中国的果戈里”更为合适。鲁迅第一篇小说的篇名来自果戈里《狂人日记》,他临死前仍在从事《死魂灵》的翻译,而阿Q岂不就代表了中国的“死魂灵”群像。鲁迅和果戈里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作品中显示的那种人格分裂。拉斯特援引德里森的《作为小说家的果戈里》说,果戈里从整体上看乃是悲观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果戈里生平中的一件轶事,说明了他和革命的行动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一次,年轻的果戈里独自在家,听着钟表的滴答声,经历了以下一幕心理剧:
我看见了猫,看着它眼中的绿色火焰,我感到了害怕,于是把它扔进池塘,当它试图从那里面爬出来时,我用一根棍子把它逼了回去。我害怕。我发颤,同时感到一种快意,也许是报复它吓着了我。但当它淹死时,当水面上最后的涟漪消逝时——现在是完全的寂静了——我突然对猫生起了深深的同情。我感到良心被噬咬。就像溺毙的是一个人……
与之平行的是《铸剑》开始时的场景。在水瓮中绝望挣扎的老鼠,让少年眉间尺既同情又憎恶,在杀它和救它之间摇摆不定,将它捞出,旋又扔回瓮中,最后还是忍不住夹出来,但随即又一脚踏死了它,可是仍觉得老鼠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拉斯特将这一段话完整地译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他这种情感的分裂,因为他的同情,眉间尺才无法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替父亲向暴君复仇。”同样将该小说和鲁迅的革命意识相联系,波兹德涅耶娃的关注点就全然不同,她断言故事的基本思想乃是“人民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人民铸造武器,并将推翻压迫者——这就是1924到1927年大革命所产生的思想”③[俄]波兹德涅耶娃:《鲁迅的讽刺故事》,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拉斯特眼中的眉间尺是注定无法承担革命重任的分裂主体,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既同情濒死的老鼠,同时又对 (像叶赛宁那样)无法经受革命的恐怖有负罪感,这就是鲁迅的“二心”。在拉斯特看来,鲁迅作品没有明确的理论和政治表态,而只有一再出现的、对于革命或反革命的牺牲者一样的同情,对于艺术、文化和人的沦亡的忧思,这正是他被左翼阵营指责为“二心”的原因所在。同样,他最终的“干预”决定,也是出于同情,出于阻止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恐怖造成更多牺牲的愿望。
拉斯特曾作为荷兰左翼作家的代表,于1932年在莫斯科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工作了九个月,1934年又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大会,他还是左联驻莫斯科的诗人萧三 (埃米·萧)的朋友,对于莫斯科的文化政策和中国左翼文化界的实际氛围,都比较熟悉。他以亲身经历作证,在30年代初的中国左翼作家眼里,中国革命作家的领袖还不是鲁迅,而是丁玲和茅盾。他忆起在高尔基家度过的一个夜晚,一位年轻中国女士向高尔基献上一位被枪杀的中国女诗人的带血迹的手稿,这一晚,并没有人提到鲁迅。葛林总结拉斯特论文的特点是:1.拉斯特从一个“政治性作家”的立场来描述鲁迅。对历史情境的亲身经历,使他区别于一般学院派批评家,也因此使论述带有随意性,且超出了正统的学术对象范围;2.文中大量征引俄文材料,这些材料显示出,1930年左右中国的意识形态论争和苏联有多么密切的联系;3.拉斯特把中国事件置于更大的、世界性的范围来加以观照,这一框架容许研究者对其对象做出更自由的判断。①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3、65、55,59,66.
不难看出,在介绍左翼文化界对鲁迅的评价的同时,拉斯特力图还人物以真实面目,实现“去魅”的意图,由此和苏联、东欧的官方批评家拉开了距离。在《鲁迅和他的前辈们》一章,拉斯特强调,尽管鲁迅对白话文推广的贡献无可置疑,却并非首倡者,白话文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胡适的倡导之功也不容抹杀,因此费多尔仁科、波兹德涅耶娃等苏联批评家对胡适的漠视和贬低就纯属歪曲历史。除鲁迅之外,中国新文学的缔造者还包括钱玄同、赵元任、陈独秀、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梁启超、严复、蔡元培、林纾、章太炎等。鲁迅的“中国新文学之父”实在只是一个死后的封号。拉斯特意在提醒西方读者,即使承认鲁迅的伟大,也不应忽视他背后如此之多的“前辈”(Vorgänger)。在《“共产主义者”鲁迅》中,拉斯特指出,鲁迅同情共产党,是因为厌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即便他在1930年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也只是一个追随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理论的孟什维克。他眼里的鲁迅,毋宁说是中国两千年儒家传统精神的体现。②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3、65、55,59,66.而当波兹德涅耶娃试图将鲁迅塑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父,并把《纪念刘和珍君》读作鲁迅转向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证据时,拉斯特反驳说,鲁迅敬重的乃是刘和珍作为一个人的品质,而刘和珍和共产党的联系,不过是鲁迅的敌人的诬蔑之辞。这种去共产主义化的做法,无疑和他本人的政治态度变化密切相关。纪德从莫斯科归来后,对苏联的社会现实公开表达了失望(《访苏联归来》),拉斯特因为和纪德的关系受到牵连,在西班牙被逮捕和审查,他同斯大林主义者的分歧日益扩大,双方最终决裂。③Basil Kingstone,“Jef Last and André Gide:The record of a friendship”,p.91.故他在论文中一再暗示,如果鲁迅活得更久,是否还能保持革命信念——换言之,是否和他一样成为幻灭的“共产主义者”④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3、65、55,59,66.。拉斯特的反共态度,自然导致了不少主观性的夸张描述和歪曲的结论,对此,不仅葛林已有所暗示,当时的一位中国留德学人杨恩霖在其随后的评论中更明白地表示拒斥。⑤譬如针对拉斯特说的,共产党到1932年才停止攻击鲁迅,在他死后,才开始正面评价鲁迅,而直到1949年后,才有了鲁迅崇拜,杨恩霖说,鲁迅的“转变”乃是战士的主动行为,说共产党方面的“攻击”是无稽之谈,所谓“攻击”不过是正常的文学批评而已,而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对鲁迅作出了最高评价。另外,拉斯特相信,神化鲁迅是有意打压同时代的非共产党作家,对此杨恩霖反驳说,作者全然不知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事实上,“郁达夫、闻一多、刘半农、刘大白、郑振铎、叶圣陶、朱自清……成仿吾等和鲁迅同时代的非共产党作家的作品都广受欢迎”,都没有被忘记,而鲁迅本人也不是共产党人。杨恩霖留学东德,他这篇评论发表于1962年,不难看出,他的回击同样和特殊时代相联系,不无意识形态性的情绪色彩。Yang En-lin,Rez.: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Berlin 1959,in: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H.4(1962),pp.300-304.
三、结语:鲁迅早期形象的政治化
如果说王澄如和拉斯特构成了早期鲁迅接受的两站,其实中间还隔着一个过渡性的评论,那就是傅吾康写在1955年的对于捷克汉学家克勒波索娃 (Berta Krebsová)的专著《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布拉格,1953)的书评。傅吾康一方面指出,克勒波索娃著作中许多翻译上的错误和遗漏都和王澄如论文惊人地雷同——暗示前者抄袭了后者。①Wolfgang Franke,Rez.:Berta Krebsová:Lu Sün,sa vie et son œvre,Prag 1953,in:Ostasiatische Lieraturzeitung,Nr.3/4(1955),pp.170-175.作为这种抄袭的例子之一,傅吾康举出王澄如翻译的鲁迅“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王澄如译为“如果我们要为革命服务,我必须成为革命者,建立一种革命文学”(Wenn wir der Revolution dienen wollen,müssen wir Revolutionäre sein und eine revolutionäre Literatur begründen),克勒波索娃的译法犯了同样错误:“如果我们要为革命服务,我们必须首先自己成为革命者,建立一种革命文学。”(Si nous voulons servir la revolution,nous devons tout d'abord être nous-mêmes révolutionnaires et fonder une littérature révolutionnaire)这让我们觉察到王澄如给予她的强烈影响。事实上,克勒波索娃延续了王澄如的政治视角,关注的主要是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只不过她把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评论也纳入论述。另一方面,傅吾康指出了克勒波索娃著作的几个重要缺陷。除了和王澄如一样的比比皆是的翻译错误,一个重要不足是对鲁迅登上文学革命舞台时的历史语境和脉络呈现得太过简略,没有提及鲁迅的诸多“前辈”(Vorgänger)的预备作用,也没有注意到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核心地位。②Wolfgang Franke,Rez.:Berta Krebsová 1953,pp.171-172.这一不足,在他的弟子拉斯特的著作中得到了修正(《鲁迅和他的前辈们》成为专门的一章)。而拉斯特对鲁迅和国际共运的关系的探讨,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从王澄如到克勒波索娃的论述理路。
拉斯特论文也多次指出王澄如的错误。王澄如认为,鲁迅在共产党成立七年后仍没有加入任何团体、党派的原因,是反感于共产党内的派别纷争,并举出《而已集》中的一段话为证:“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③鲁迅:《而已集》,载《鲁迅全集》第3卷,上海复社1938年版,第438页。拉斯特说,此处自认为“唯一正确”的团体实为国民党而非共产党,王澄如是张冠李戴了。他还指出,“三闲集”被王澄如误译成了“三个假期的书”(Das Buch der drei Ferien)。④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44、30.
尽管如此,两人在论题设定、切入角度等方面仍有相当的一致性,鲁迅的复杂人格,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鲁迅和农民的关系,鲁迅和俄国文学的关系,尤其是鲁迅和左翼批评界的纠葛,成为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就印证了洛特曼的观点,最初的参照系往往对后来的符码建构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我们在面对王澄如这篇西方鲁迅研究的青涩的开场白时,也要从形象学和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待其价值。她的基本观点,即鲁迅不属于任何既定类型和思潮,鲁迅的人格不属于任何既定系统,还是颇为中肯的,并得到了拉斯特的继承。为了说明鲁迅的不容简化的复杂性,拉斯特引用了让·蒙斯特尔内特(Jean Monsterleet)的一句话:“他 (鲁迅)的个性和作品都带有矛盾的特征。他是一头斯芬克斯女妖,人们最好将她留给她的谜语。”⑤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44、30.拉斯特论文最有价值之处,正是将外界对鲁迅评价转变的原因,归结为鲁迅本身思想的极端复杂性和他亦中亦西的边界位置。最终,王澄如把鲁迅的革命精神概括为一种和生命冲动息息相关的热烈的爱,而拉斯特归之于一种不问党派的深沉的“同情”。
为什么鲁迅和政治的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个问题也是拉斯特书的序言作者葛林 (Tilemann Grimm)所关心的。鲁迅是文人、诗人,拉斯特也是诗人气质浓郁、并不适合从事政治的人,葛林不由得要问,为什么一个“作家写作家”的评论,会被收入一套以政治、经济为服务对象的丛书?⑥这套丛书名为《汉堡的亚洲学研究所丛书》(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in Hamburg),收入对于中国和亚洲的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研究著作,拉斯特的专著为丛书第5卷。前4卷分别是《南亚和东亚的发展状况研究》(卷1)、《东南亚和东亚的发展状况研究》(卷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经济上的密切关联》(卷3)、《现代日本法律中的外国影响》(卷4)。葛林对他自己抛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也透露了当时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一般看法:
在一个极权国家的生活空气——这种空气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巨大的影响——中,文学不仅仅是在排他性的美学的意义上的“纯”文学。它是经济的、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整体的一部分,而且自身也悄然变成一种隐蔽的政治——成为活动于日常生活前台的各种权力的镜子。这一点,我们由鲍里斯·帕斯特纳克可以得知,他无奈地陷入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碾磨。故而更近地认识鲁迅这位“中国新文学之父”,了解他作为文人是怎样和政治纠缠,政治又是如何对待作为文人的他,必然会引发持久的兴趣。①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1、4.
中国是“极权国家”,故中国文学只能是“隐蔽的政治”。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鲁迅自然也成为单一的政治符码,他的其他方面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在三十年代进入德国的几篇零星的鲁迅作品译文中,鲁迅已经被冠以激进的革命作家的称谓。与这一最初印象相呼应,王澄如第一个去探究其革命性的内在根源,克勒波索娃盛赞鲁迅的无产阶级立场 (毛泽东成为最好的鲁迅读者),拉斯特则视之为共产主义的神话,而杨恩霖基于维护祖国的政治情感,又对拉斯特作出回击,这成了一个辩证交替的封闭循环,将死后的鲁迅再次卷入湍急的政治漩涡。在鲁毕直看来,妨碍鲁迅在德国的接受的,正是鲁迅作为政治作家的身份本身,这种政治性倒不一定是拥护某个正确的党派,而是他作为革命者为他的受欺凌的、沉默的同胞代言这种姿态本身。②Lutz Bieg,“Lu Xun im deutschen Sprachraum”,p.177.但是,反过来说,惟有鲁迅身上具有的这种难以驯服的他者的陌生性,才既让接受者望而生畏,也使他有可能——在经过一段历史沉淀和心理适应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下一个主导符码的备选,去更新德国读者业已熟悉的诗意的古代中国和崇尚西方科学、民主精神的“五四”少年中国的旧印象,并且对西方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真正的冲击。
鲁迅初进入西方公众视野,就是这样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形象,这构成了鲁迅早期接受的一个重要特征。说到底,这就是西方世界对整个当代中国的编码,因为这时的鲁迅尽管受到漠视和抵触,却已经开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当然代表,是“他的人民在他那个时代的真正的代言人”(葛林)③Jef Last,Lu Hsün-Dichter und Idol,p.1、4.,“最近四十年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傅吾康)④Wolfgang Franke,Rez.:Berta Krebsová 1953,p.170.。而这个新的超级符码的基本内涵就是从内到外的革命精神,怎样看待这一符号,从什么角度、在什么层面上、运用什么理论去将它具体化,成为今后进一步扩展、细化的鲁迅研究的一个不言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