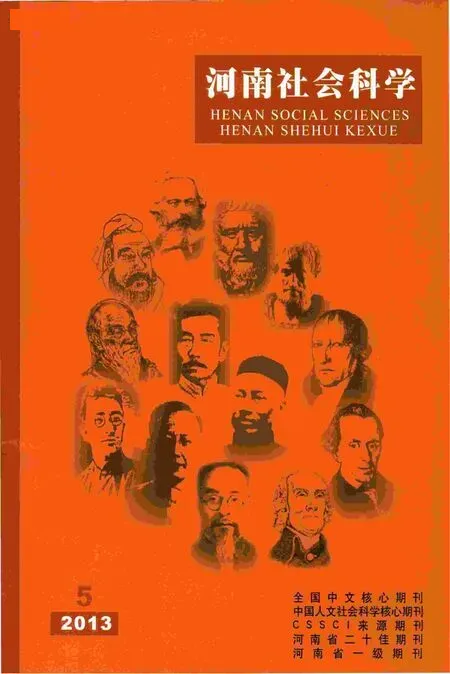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
徐小跃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儒道佛三家是通过各自的方式来确立它们各自的价值观的。儒家通过追寻人性之源,确立了仁爱之道;道家通过探寻宇宙之根,确立了慈柔之道;佛家通过悟诸法之相,确立了慈悲之道。而儒道佛之价值观的确证则是直接来源于它们的“人道法天”的方法论,或说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如下即对此展开讨论。
一
儒家坚信作为人之为的“明德”、“几希”(良心)这一超越社会道德意义的美恶之“至善”之性,是外在天地自然所赋予的,即“天命之谓性”。(《中庸》语)孟子亦言:“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而充当人性之源的“天”,其本身是有德性、有精神的神圣存在。《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朱熹对此句曾有过解释,认为所谓“生道”即是“仁道”。也就是说,天地有性、有道、有理、有心,而此“性、道、理、心”即是“仁爱”。确证“天”性是为了给人性寻求一个绝对和神圣的“终极者”,从而提升人的尊严感和神圣性。因此,儒家哲学内在地要求人们当“尽其心,知其性”,最终达到“知其天”(孟子语)的目的。上下贯通、内外交融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于是唤醒、呈现、光明、遵循内心本存的天性也就当然地成为儒家哲学的逻辑进程和人道教化的必由之路。《中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之谓也。人所率之性和所修之道乃是天性天道也,这是儒家典型的“人道法天”的方法论,亦是“天人合德”的思维方式。而儒家的这种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所直接表征的又恰恰是它要宣扬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儒家的方法论直接呈明的就是价值观,它们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体。无论是《周易·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是《周易·文言》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无不是非常明确地表达着这种统一性。
在中国哲学体系中,道家与儒家一样,它的价值观的确立是牢固建立在其“人道法天”的方法论和“天人合德”的思维方式之上的。在老子和庄子那里,一方面人之为人的根性被称为“自然”、“天然”、“素朴”、“玄德”(老子语),另一方面人的这一玄德亦被说成是来源于被老子视为“天地之始”(《老子》一章,下引只注篇名)、“万物之宗”(四章)、“万物之奥”(六十二章)的“渊兮湛兮”(四章)、“惚兮恍兮”、“窈兮冥兮”(二十一章)、“寂兮寥兮”(二十五章)的“道”。在道家看来,这一“道”是构成万物之性的“一”。也就是说,万物之性,当然也包括人性,皆从此“一”而获得。此“道”、此“一”之性乃为“自然”也。也就是说,因为作为天地之始、宇宙之根的“道”的性德是“自然”,所以,由道而生的万物当然地具有了这一“自然”之性德。这一点庄子较老子说得更加明白和直接。庄子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刻意》)天道如此,人道何为?于是老庄又使用了非常著名的“人道法天”的方法论和“天人合德”的思维方式。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庄子说:“循天之理——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从老庄对“天地自然”之德性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道家所谓的“天德”乃为“自然”。如果说儒家的“天”与“人”要合的是“仁爱”之德的话,那么,道家的“天”与“人”要合的就是“自然”之德了。被道家称为“天之道”,“天之德”的自然,具体则又表现为“身退”(九章),“不有”、“不恃”、“不宰”(十章,五十一章),“不争”(六十八章,七十三章),“不害”(八十一章)。所有这些都反映着天道天德的慈柔之性。而人就应该效法这一天之德性,实现了天人合德的方法,亦就践履了道家所主张的价值观了。老子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六十七章),“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六十八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在这里,道家的方法论是直接服务于其价值观的,这就鲜明体现出道家价值观与方法论统一的哲学特征。
二
体用不二,本末一如,应是中国哲学一个显著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当然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思想。这一“体用不二”和“本末一如”既可称为本体论,又可称为方法论,其本身就最能证明和支持本文所持的观点,即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在具体讨论有关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本体论本身的问题及中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差异性问题进行探讨。
在我看来,本体论应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谈“先后”问题,要谈“本来以存”问题,要谈“源流问题”,要谈“根本”问题,要谈“永恒”问题,要谈“本体”与“现象”关系问题。但在谈到“本体”与“现象”关系时,不同的本体论形态的观点就呈现着诸多的差异性。西方本体论者认为“本体”与“现象”可以分离为二。而中国的本体论者绝不主张“本体”与“现象”的分离,而坚持认为是相即不离的。中国人用“本末”的范畴来表达这层意思再贴切不过了。树根谓之“本”,树枝树叶谓之“末”。树根树枝如何分得?一分树就死矣!但那些主“不分”的本体论者又在对待“本体”自身的定性上产生了分歧,而关于这一点恰恰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派认为本体现象虽然不二不分不离,但它们有主次、高下之别,主干为主、为贵、为高、为母,末枝为次、为贱、为下、为子。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就是魏晋玄学的“以无为本”的“贵无派”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本体”为更重要、更根本的存在,认为“它”相对于“现象”、“迹”来说具有“优先”、“优越”、“优势”、“优秀”、“优长”等属性和地位。另一派认为本体是一理、一统,但分别而显著的“用”、“万理”、“分殊”之理同样是“体”,只不过后者把“一体”、“一理”具体化、显著化罢了。我们常说的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主张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体是用之体,用是体之用”都是在也只有在上述的规定和意义上来理解和认识才能成立。说得再具体些,对那些将“体用”分高下的本体论者,你就不能用那些话去评价它。在中国哲学中,实际上先秦儒道两家都主此论,宋明理学当然更是如此。
比如儒家所谈的“人性之善”,此“善”是实然的、是自然的、是超然的(至善纯善,即是超越善恶的那种无善无恶之“善”也),但当此“善”一旦“流行”开来,人们就会以不同和别异的“名”和“言”,或说“概念”、“范畴”来表达和反映此“善”。所以这才有了那么许多“德目”: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忠孝节礼义廉耻、忠恕敬诚、中和中庸、仁智勇三达德等无一不是用来表达“善”的。《大学》中的“明德”、“至善”就是体。而“止于至善”具体展开那就是“用”矣。《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由此可见,“至善”(“明德”、“良心”)之体反映在不同“身份”、“角色”上,遂显出“仁、敬、孝、慈、信”之用。而就此“用”的性质、本质来说,那就是“体”的性质、本质,两者就不存在所谓“高下”、“本末”、“精粗”之别了。
宋明理学为了强化和贯彻这一本体论的特征,试图对本体之“理”、“道”作出所谓的“限制”性规定。例如在“理”前面加上“实”、“天”、“一”等词,从而提出“实理”、“天理”、“一理”等范畴,如此是欲凸显“理”的“实际存在性(有)”、“自然存在性(不是外力强加,不是人为设定)”、“统合存在性(至上性,超然性,与“用”无分高下、主次性)”,这样的“理”也就成为本体之“道”矣。理学家的观点与《大学》的观点一样,是把“至善”视为“体”,把善在不同方面的流行和发用视为“用”。程颐说:“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以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道也。”[1]朱熹说:“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2]简单地说,在程朱看来,作为“本体”的“善”一旦流行开来(用之体),就会以不同和别异的“名”、“言”,或说“概念”、“范畴”来表达和反映此“善”(体之用),“体用”皆在“道”、“善”的意义上完全统合,此乃真正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体是用之体,用是体之用”的本体论的本旨要归。
从对“体用不二”方法论的讨论中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这一方法论的运用的直接目的就是要表达和阐述其价值观的。它绝不是纯粹的思辨性运思,而是为了确证一个思想体系中的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具体说来,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儒家思想,欲通过“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来阐发儒家发明的“诸德目”以及通过这些德目以实现人的根性的呈明,即“止于至善”的目的。在这里,儒家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就达到高度统一。
三
用以上对本体论的认知来研究佛教思想,我们会发现在佛教思想里有着特殊的本体论思想。例如,在佛教那里,“虚空”、“至道至理”被视为不可断分、先前存在、构成万物等本体性质。“常乐我静”正是对“本体”永恒性、寂静性、超然性的最好注脚。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哲学是一种本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石的“缘起性空”(中道)思想就不能在诉诸本体论的范式下进行讨论。因为“空色”问题不存在“先后”问题,不存在“高下”“主次”问题,也不存在“理一”和“分殊”的问题。换句话说,不管在什么意义和性质下的本体论都不在“缘起性空”的概念框架之列。“空”(缘起、相依、关系、联系、变化、发展)是“色”(诸行诸法,宇宙万有,一切现象)的属性。“色”的属性是“空”,“空”是“色”的属性,此即《心经》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也。由此可见,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和思想,与本体论要表达的“本体”与“现象”不相分离的思想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绝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佛教的“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之“三是偈”强调的仍然是空色(有)不异之旨。
“中道义”,或说“中道观”是佛教所建立和遵循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主旨是强调人们对“诸行”、“诸法”及其本性的把握和观想都不应偏执一端、落于一边。佛教喜用“非有非无”、“即有即无”、“不……不”等句式来表达它的“中道义”、“中道观”。佛教所谓的“空”是在宣扬这样一个观念:诸行诸法皆是一个“无”与“有”、“间断性”与“连续性”的对立统一体。认识它的实相一定要同时注意这两个维度,如只偏重一方,即为偏见,即为“偏执”。因而佛教主张不执“有”,也不执“无”,即做到“有无双谴”是也。这是佛教不变的思维方法。
为什么佛教喜谈“即有即无”、“非有非无”呢?其中关键点为:它是站在“运动和变化”的立场切入事物和问题的。“有”是在“间断性”、“当下”(现在性)上去理解和把握的,而“无”则是在“连续性”、“发展性”、“变化性”、“未来”上去理解和把握的。既存在“变化运动发展”,那么世上就没有一样存在是一成不变的,从“已经变了”的状况上来说,“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原来的它)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辩证法和佛教为什么会将“联系”(关系、相依、无我、因缘)与“发展”(运动、变化、无常)作为它们的“两大法则”(佛教谓之“法印”)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们所申论的就是要人明白,宇宙间的一切,当然包括人,是在“关系网〈场〉”中的存在,是在“发展域”中的存在。既然是“关系场”中的存在,那你就一定要觉悟到“你”是,而且也只是“此场”中的“一个”元素、分子、角色、部分、局部。也就是说,“你”是“关系场”的“一个”,那么,“你”就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你”也只是“关系场”的“一个”,那么,“你”就千万别以为“你”就能代表你的“整体”,所以“你”就不要妄自尊大,唯我独尊。同理,既然是“发展域”中的存在,那你就一定要觉悟到“你”是,而且也只是“此域”中的“这个”瞬间、部分、阶段。也就是说,“你”是“发展域”的“这个”,那么,“你”就要有所敬畏;“你”也只是“发展域”的“这个”,那么,“你”就千万别以为“你”就能代表你的“全部”。所以“你”就不能盲目乐观或盲目悲观,由此“你”就会平静和淡然地面对“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这“八风”了。同样,你也就不应该“放不下”它、“想不开”它、“忍不下”它,你应该更轻松、更潇洒、更自由地来面对所有的对象,这才是正道。
总之,“空”论,或说佛教之“空”,是强调万物存在的状态。万物存在的状态乃是“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有又是无”。如果你抓住双方的任何一方,那你得出的一定是“假的”、“不真实”的。而当你双方都统一地体认了,你所看到的才是对象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通过“中观”方法所认识的“对象”才是“真实”的、“真理”性的认识。因此说,佛教的“中道观”实际上就是“全面的观点”(“诸法无我”),就是“发展的观点”(“诸行无常”),一句话,就是辩证法的观点,就是“对立统一”的观点。
由此观之,所有方法论的终的,是使人们明白一个理论的真实性究竟在哪里。方法论错了,一切理念都会跟着错,包括价值观、人生观都会跟着错。对孔子的那句名言亦应站在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得更深些。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只有“利”好“器”,即正确、准确地掌握了“方法论”,你才能做好事,你才能解释概念和范畴的真义,你才能掌握真正的知识,你才能引出与此方法论紧密相联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许多内容。如前所述,儒道两家通过“人道法天”、“天人合德”以及“体用不二”的方法论各自所要阐明的是仁爱之道和慈柔之道。而无论是儒之仁爱,还是道之慈柔,它们所欲呈明都是人之为人的“明德”、“天德”之性,而欲实现的价值终的乃是“止于至善”、“与道为一”,在这里儒道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实现了高度统一。而佛教的责任、敬畏、感恩、忍让、放下等理念以及慈悲之道,恰恰就是从它的“缘起相依”、“即有即无”、“非有非无”的“中道”方法中直接推导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这里,佛教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亦就达到了高度统一。而儒道佛三家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也正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和重要特征。
[1]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A].二程集(上册)[C].
[2]论语集注(卷三)[A].朱子全书(第六册)[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