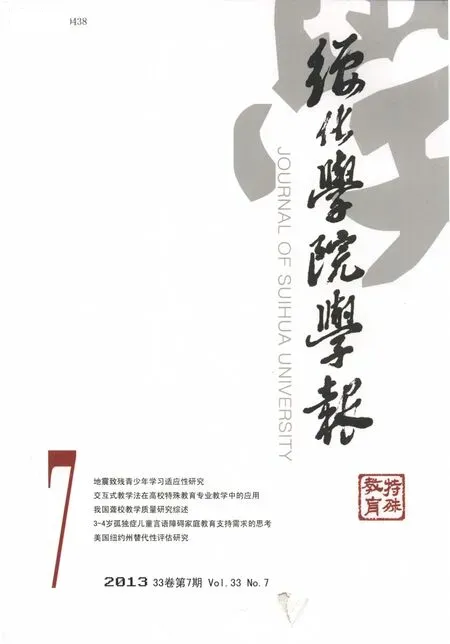美国残疾人教育法中的人权理念
李晓光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6)
一、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历史概括
19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对残疾人获得平等权利是一种促进,残疾儿童的家长开始为他们的孩子呼吁获得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特殊教育的立法和改革开始受到关注。
1968年,残疾儿童早期扶助法案(the Handicapped Children’sEarly Childhood Assistance Act;P.L.90-538)、 残疾儿童早期教育方案(Handicapped Children’s Early Education Program)联邦政府以经费补助的方式,鼓励各州政府规划实验性的早期教育方案和学校,以充实儿童早期生活经验,提供3至5岁的特殊幼儿和其家庭所需的各项服务。
1972年,经济机会修正法案(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Amendments;P.L.94-424) 启蒙教育计划必须保留10%名额给特殊幼儿。
1975年,《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P.L.94-142)保障所有身心障碍者接受免费及适性公共教育的权利,并规定为所有身心障碍学生拟定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以及安置于最少限制的环境。
1986年,《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修正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Amendments;P.L.99-457)保障出生至 3岁身心障碍婴幼儿接受早期疗育服务,及3至5岁身心障碍儿童接受学前特殊教育的权利,并规定需针对身心障碍婴幼儿及其家庭之需求,拟定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IFSP),且各州政府必须办理全州的早期疗育方案。
1990年,障碍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y Education Act;P.L.101-476,IDEA)该法案将1975年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更名为《障碍者教育法》,这种服务对象称谓上的改变体现了在特教用于上的“以人为本”的理念[1],即障碍只是人的某种特征,不应把人等同于障碍。在94-142公法的基础上,改进鉴定措施、增加个别复健服务、在个别化教育计划中加入转衔服务及辅助科技服务、赋予身心障碍儿童有优先参与学前教育计划的权利,以及扩大最少限制环境的概念等。
1991年,障碍者教育法修正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Amendments;P.L.102-119)在IDEA的基础上,强调早期疗育服务应于最大限度适合的环境下进行、建立转衔政策和程序、为3至5岁身心障碍儿童拟定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提供身心障碍儿童补助经费,及赋予家长更多权益等。
1997年障碍者教育法修正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Amendments;P.L.105-17,IDEA1997)在IDEA的基础上,增加发展迟缓儿童的定义、初始评估和再评估的相关规定、强调早期疗育服务应是家庭取向的、增加早期疗育服务对象及规定各州领导机构应筹备学前身心障碍儿童之转衔计划等。
2004年,障碍者教育促进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P.L.108-446,IDEA2004)在 IDEA的基础上,针对特殊教育人员的任用资格、身心障碍学生的鉴定程序、学习障碍的鉴定程序、个别化教育计划、早期疗育服务、身心障碍婴幼儿服务,以及家长参与和正当程序等方面的条款进行修订。
二、美国特殊教育法的发展趋势
美国的残疾人教育法律的发展呈现出几个趋势:
(一)对待残疾人的理念由医疗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
医疗模式亦称为生物医学模式,世界卫生组织残疾人定义是以身体结构的生理与生物基础为主,在此概念下,疾病与残疾的关系是身体健康系统→病理→出现病症,残疾被定位为身体系统产生病变,且有具体可诊断的病症,残疾人被视为病人,也就是说残疾人本身是以病人的角度接受各种治疗与复健。此为“个人模式”,以个体健康、疾病与残疾经验为主,并不考虑外在环境与社会结构因素对身心障碍的影响,而残疾人成为医疗介入之客体。[2]
社会模式理论不从慈善救济、专业需求、补偿或是经济观点对待残疾人,而是从权利观点看待残疾人,强调残疾人的尊严及国家应祛除社会障碍,使所有人均能享有充分之尊严及平等权利,因此社会模式也被称为“人权模式”(human rightsmodel)。[3]现代的民主和法治社会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所以社会模式要求把身心障碍的人士作为社会的主体,保障他们参与社会的平等机会和自由权利。
1990国会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案》(ADA)标志着“社会模式”在美国立法上的胜利,国会承认把残疾人排除出社会和类型化是历史的错误,这种隔离是人为的,是一贯的不公正和不必要的歧视和偏见。作为一种反歧视的法律,《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给予残疾人和普通人同等的对待。[4]此后的特殊教育立法中都体现了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例如。《障碍者教育法案》中规定“全纳教育”以体现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
(二)从隔离教育到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的倡导者W.Stainback和S1Sta2inback(1984)对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隔离、各自平行发展的双轨制体系提出明确的批评,认为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应该“重新组合、建构、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教育体系以满足所有儿童的学习需要。”1975年,美国颁发了《所有障碍儿童教育法》(PL94-142),该法提出最大限度地将残疾学生安置在普通班级接受教育,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1990年10月,美国政府将1970年制定的《障碍者教育法》改为《残疾人教育法》(PL101-467,简称 IDEA),该法将“障碍儿童”(Handicapped Children)改为“残疾儿童”(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同时,又增加了两类新的残疾,即孤独症或自闭症和脑外伤,这一名称的更改和残疾种类的增加,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府依法保障各类残疾儿童拥有平等接受适当教育的权利。同时,该法案还明确规定:如果有适当的辅助服务设施,全纳教育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要将残疾儿童安置在普通班级。1997年6月,美国政府又一次通过了重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法修正案》。该法案强调实现残疾人的免费义务教育,以满足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保障残疾儿童和家长的权利,提出最少受限制环境原则和适当教育原则,并从法律上强调了全纳教育的必要性,进一步推动了全纳教育改革运动。
全纳教育指出,教育是一种权利,意味着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被这种权利所拒绝。尽管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是很重要的,但这不应压倒个人的权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萨拉曼卡宣言》提出了所有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要关注和接纳那些历来受排斥遭歧视的弱势群体儿童。[5]
(三)从“消极人权”到“积极人权”再到“连带关系权利”
人权的历史分析是由是法国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Karol vasak)完成的。瓦萨克提出了三代人权理论。他认为:第一代人权即各项个人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这一代人权的特征是国家对这些权利的实现负有消极不作为义务,被称为“消极人权”。第二代人权即要求国家积极参与的社会权利,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这一代人权的特征是国家对这些权利的实现负有积极作为义务,称为“积极人权”。第三代人权是关于人类生存条件的集体性“连带关系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卫生环境权和共同遗产权等。[6]消极人权宪法往往要求政府不作为就可以使人权得到较好的保障,目的是避免公权力对人权的侵犯。但是国家不能仅以消极不作为来保障人们的自由,还须积极地给付、介入,方确保人们的权利不因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实质侵害与不平等,甚至损及人的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日益多元,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于是,国家不断地被要求介入国家的角色由消极变积极,由防御到服务。积极人权给予弱势群体实质的平等保障,诸如健康权,工作权,受教育权,语言权。这些权利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保障残疾人的语言权,使他们拥有使用盲文和手语的并受到尊重的权利,利用语言接受平等的教育,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机会,进而去工作,在工作中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工作权,包括有机会在开放、具有包容性和对残疾人不构成障碍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中,为谋生自由选择或接受工作的权利。比如《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认为残疾人获得工作和接受教育的能力不仅受其伤害和疾病的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他人的歧视和社会构建的限制。注重为残疾人创造无障碍的生活环境,关于残疾人权利的五项条款中的每一款,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残疾人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条件。而1973年前的政策认为残疾人在就业方面所面临的障碍是由于其伤残和疾病的限制造成的,如果这些限制因素被消除或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补偿,残疾人的就业及其他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除了一些很少的例外,1973年前的政策注重对残疾人进行收入损失和健康成本方面的补偿以及减少他们在行动方面的障碍。[7]
从美国政府特殊教育立法进程分析,美国对特殊教育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法案体系逐渐完善,这些法案对残疾儿童融入普通学校、构建全纳教育环境提供了立法环境。同时,美国立法条文细致,对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种类以及界定明确,为普通学校接纳他们以及教师认识和教育他们提供了依据,最少受限制环境和有针对性制订符合个人学习需要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要求明确具体。[8]
三、对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评价
美国的残疾人教育法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方面,各种保护法案互相衔接,彼此呼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从美国所订定专为残疾人的诸多法案,及各种法案中均提及残疾人的相关权益与服务表现上,我们发现美国对残疾人的保护措施可谓无时无刻地、积极而广泛地维护。而由法案间的统整性,更可见其法案的周延。例如对辅助性科技的定义,《障碍者教育法》中所定义的内容,完全依《辅助性科技法案》中之定义。又如早期疗育或如家庭介入课题等等,则无论教育、权益、复健、辅助性科技等各领域之法案均予以规范,法案间彼此呼应整合之功能相当明显。[9]
另一方面,法律规定了残疾儿童教育公平的标准、程序、方式,具有可操作性,保障残疾儿童平等地享有与普通儿童同样的教育权利。《障碍者教育法》的最后一条要求是法定程序权利。如果父母不相信孩子所在的学校正在履行《障碍者教育法》的义务,这一要求赋予了家长启动一系列措施的权利。如在一个公正的官员在做出该儿童所接受的教育计划是否恰当的判断之前,家长可以要求听证。
尽管美国的残疾人教育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美国的主体法案相当多元,常让执行者觉得有些繁杂。一件工作在相关的法案中均予以提及,例如转衔、早期疗育、家庭角色介入等等,让执行者得去顾及每一法案的条例指示,而难以整体性充分掌握。又如申诉管道,虽然各个法案内均有提及,但是一旦障碍者遇到困难时,总会分散心力,或向各个单位纷纷提出,或不知该正对那一个单位进行直接的申诉。另一方面,教育法中对个别重要的词汇没有进行必要的阐释,容易引起争议。“免费及合适的公立教育”、“最少限制环境”和“相关服务”在在残疾人教育法中重复出现,但法律却没有对这些词语做出足够清晰的阐释,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争论。[10]
四、美国残疾人教育法对我国残疾人教育立法的借鉴
(一)重视家长参与及权利
美国在1975年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中即强调父母参与和决定其孩子教育过程的权利,包括孩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IEP)。1986年的《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修正案》强调早期疗育服务的对象包括孩童及其家庭,且孩童的家长必须参与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IFSP)的制定和过程。1991年的《障碍者教育法修正案》更赋予家长更多权利,亦即如果家长认为他们的权益受损,可以拒绝任何服务或转衔的要求。2004年的《障碍者教育促进法案》(IDEA2004)更提及,家长必须告知地方教育机构孩童发展上的问题,以及他们对此问题希望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期待地方教育机构有何种作为。
儿童与家庭的互动及关系,对于儿童的成长及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早期疗育服务相当重视儿童家庭的参与。美国于特殊教育法案中就特别强调家长参与孩童特殊教育与相关服务的权利与义务,并以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的实施,让身心障碍儿童的家长能密切地参与早期疗育服务计划,而这也是我国早期疗育政策中所忽略的部分。因此,我国在早期疗育政策的制定上,可以考虑明文规定家长参与早期疗育服务的权利与义务,以保障身心障碍儿童及其家庭的权益。
(二)建立和完善早期疗育服务系统
美国于2004年的《障碍者教育促进法案》(IDEA 2004)中指出联邦政府应提供经费,协助州政府为身心障碍儿童及其家庭,建立和维持一个协调的、多专业的、跨机构的早期疗育服务系统。
我国虽于《残疾人教育条例》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领导,统筹规划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逐步增加残疾人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残疾人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残疾人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残疾人教育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儿童、少年实行义务教育纳入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并统筹安排实施。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对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检查,应当包括对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工作的监督、指导、检查。”
我国早期疗育相关的主管机关没有建立通报系统,而且未在政策中妥善规划一个协调的、多专业的、跨机构的全国性的早期疗育服务系统。
(三)立法完备系统、整齐划一
从美国所制定为残疾人的法案以及涉及残疾人的权利义务的政策上来看,我们发现美国对于残疾人的保护措施积极、完备和广泛。各法律法规间统整且周延。例如对辅助科技的定义,《障碍者教育法》所定义的内容,完全依照《辅助科技法案》的定义。又如早期疗育或家庭介入,在教育、权益、和辅助性科技各领域的法案都予以规范,法案间彼此呼应。这对于我们以后的残疾人教育的立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如何整合《残疾人教育条例》、《义务教育法》和《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的衔接和统一。
[1]Mitchell L Yell,David Rogers,Elisabeth L Rogers.The Legal History of Special Education:That a Long,Strange Trip It’s Been[J],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1998,19(4).
[2]Aaron A Dhir.Human Rights Treaty Drafting Through the Lens of Mental Disability:The Propos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41 STAN.J.INT’LL.2005,193.
[3]Arlene S.Kanter,The Globalization of Disability Rights Law,30 SYRACUSE J.INT’L L.&COM.2003,247.
[4]42U.S.C.§12101(a)(2),(9)(2000)(emphasis added).
[5]UNESCO.The Salamanca Statement on Principle,Policy of World Conference on Special Needs Education[R]Paris:1994.
[6]Karel Vasak,Pourune Triosième Géné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in STUDIESAND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RED CROSS PRINCIPLES IN HONOUR OF JEAN PICTET,1984,837-839.
[7]杨伟国,陈玉杰.美国残疾人就业政策的变迁[J].美国研究,2008(2):63-76.
[8]钱丽霞.全纳教育:历史演进与实施政策[J].中国特殊教育,2009(1):20-24.
[9]陈丽如.美国身心障碍者重要法案之陈述[J].台东特教,2004(19):41-47.
[10]杨柳.美国残疾人教育法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8(6):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