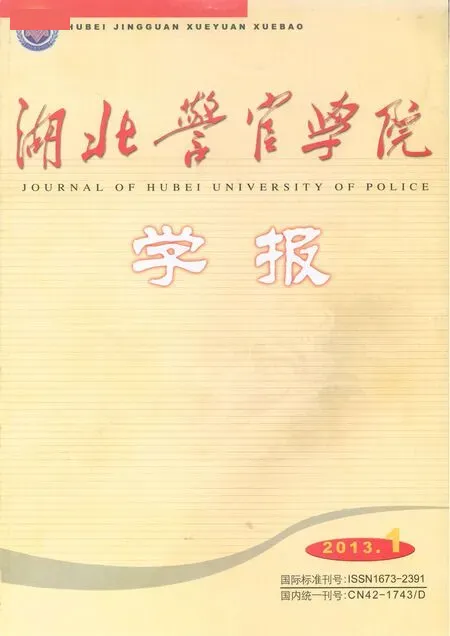以个案为视角解析“贿款归公”非犯罪化问题
丁海英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浙江 杭州310002)
一、基本案情
某市级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李某,在担任医院药剂科主任兼药事委员会成员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逢年过节多次收受医药公司负责人或医药代理商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现金、商场消费卡等财物,累计收受贿赂10万余元。收受上述贿赂后,李某将消费卡7万余元用于个人及家庭生活开支,将1.7万余元贿款用于科室人员加班补贴、物品添置等公务开支,2011年7月,为响应医院号召,将其中1.3万元贿款主动上交医院廉政账户,后于2011年底案发。
二、分歧意见
在本案办理过程中,就犯罪数额认定出现了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作为药剂科主任,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业务单位贿赂,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但其收受贿赂后用于公务及上缴廉政账户部分的3万余元,因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不属于刑法第385条第2款中“归个人所有”,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在担任药剂科主任期间,收受业务单位贿赂,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李某收取贿赂之时即已实质侵害到受贿罪法益,系受贿既遂,收受贿赂后的各项支出系其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处置,可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三、法理评析
众所周知,刑法的宗旨是对各种法益的保护,刑事犯罪的认定是因为行为人对受保护法益造成了侵害,如果侵害已经产生,则成立犯罪既遂,如果造成的仅是侵害危险,则为犯罪未遂。
我国之前有关受贿罪法益(客体)的通说为国家机关正常管理秩序,但由于该通说缺乏具体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在实践认定中不具操作性最终被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说(又称廉洁性说)代替。对不可收买性和廉洁性两种表述,有学者提出廉洁性本身含义不明确,对公务人员本身廉洁还是职务行为廉洁也不明,因此提出应对两种说法进行严格区分。[1]笔者认为,受贿罪法益讨论的是职务行为,并非受贿主体本身,无论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还是廉洁性,两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即行为人不应以其职务而获得不正当报酬,因此,两种说法仅是表述不同,不必进行有此无彼的区分。为行文方便,涉及受贿罪法益时本文均采用不可收买性表述。
在确定受贿罪法益内容之后,再看受贿犯罪的既遂标准。犯罪既遂是刑事法学的重要内容,是犯罪认定和刑罚适用的重要依据。理论界关于受贿罪的既遂标准有多种观点,[2]但基本还是围绕受贿罪客观要件进行讨论,主要可概括为谋利标准说、法益侵害说或收取财物标准说以及取财、谋利双重标准说。
笔者赞同第二种,即收取财物标准说(法益侵害说)。第一种、第三种观点都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判断既、未遂标准的必要内容,存在以下弊端:
首先,谋利标准说最明显的漏洞是无法解释对索贿行为的认定。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成立受贿罪,其中并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求。实践中也存在并无为他人谋取利益考虑仅因自身职权存在对他人利益的制约而索要财物的行为,此种行为显然已侵犯受贿罪的法益,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且危害程度比被动收受财物而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的受贿行为更严重,当然需要对其进行刑事处罚。按照谋利标准说,则人为缩小了受贿罪的规制范围,将索贿行为排除在外。
其次,谋利标准说含义模糊,缺乏作为标准应有的确定性和唯一性。根据2003法院纪要,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即谋利说内部至少具有上述三种不同标准。虽然纪要明确了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承诺,即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但承诺并不是一个外化的行为,它不像“实施”有文件批示、会议表决、具体指示、表态同意、积极推荐等具体客观行为体现,也不像“实现”有项目核准、合同签订、货物采购、款项到账等客观结果可反映。承诺既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认,在无明确表态下收受了财物是否可以认为是默认,如果不是,则如何去界定“承诺”内涵,目前并无更详细具体的司法解释,仍需谋利说支持者进一步的研究。如是,那么相当于无论是否表态予以收受都视为承诺,这和收取财物说又有何区别呢?
最后,谋利说将既遂点后置,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不强。如谋利说作为受贿罪既遂标准,则即使行、受贿双方对贿赂事实都已供认,反贪部门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对谋利过程中的承诺、实施、实现各个环节进行取证,否则无法认定受贿既遂成立,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不清,无法使案件顺利进入起诉、审判等下游程序,一旦如此,不仅会使侦查取证等司法成本急剧增加,还将人为拖滞办案程序。
因此,笔者认为,排除谋利内容的收取财物标准说更合理,更具操作性。司法实践中,收取财物标准又区分为索贿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两种情况。
对于收受型受贿,应以受贿人收受财物为既遂点,且受贿人应明知该财物系其职权行为的对价。如果行贿人在受贿人不知情下将财物置于受贿人控制下,如趁拜访之际偷偷将贿款放于受贿人抽屉,而受贿人并不知道该贿款存在,则虽然形式上受贿人已收到财物,但因无主观故意而不予认定。
对于索贿型受贿的既遂点,实践中一般以受贿人索取并收到财物,视为受贿既遂。但也有学者提出受贿人向行贿人提出索要即受贿既遂,无须等到其收到财物为限。①张明楷教授在其著作《刑法学》(2011年版)第25章第3节(P1077-1078)中提到索贿情况下,受贿人的索要行为即侵害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即使其尚未现实取得贿赂,对受贿罪法益的侵害已经造成,应视为既遂。其认为刑法规定“索取”不能解释为索要并取得,因为取得即收取,已明确为受贿罪既遂,立法者无需重复表述,对此应将理解重点置于对索要行为的入罪考虑上。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受贿人虽有索要意思表示,但行贿人未应允,在未取得财物的情况下,受贿人对其职务的不可收买性法益尚未造成现实侵害,仅存在侵害威胁;第二,如索要即成立受贿既遂,则犯罪数额如何认定,在量刑上又如何体现,如受贿人索要100万元,是否以100万定,如此应处10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如受贿人仅索要1万,则量刑仅在1年左右,如此悬殊刑罚,仅凭受贿人索要时的一念之差,一人之言,如此刑法适用是否过于轻率。因此,对于索取型受贿,应以索要并取得财物为既遂点。
回到本文案例,李某作为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在其职务存续期间,多次收受业务单位人员礼卡、礼金,在其明知对方以私利谋取其公权,即以贿赂换取药品、医药器械的销售以实现其正当或不正当的利益,仍然予以收受,则从李某收取行贿方财物之时,其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即已遭到现实侵害,成立受贿既遂,虽然其收受贿赂后有将贿款上交廉政账户和用于公务等“归公”处置行为,但无法改变该部分财物的作为受贿犯罪数额的性质。
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将“贿款归公”非犯罪化的判例,如湖南省新田县原教育局局长文建茂受贿一案[3],新田县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其中34000元贿款虽用于捐赠、上交局财务以及教育局公务开支等,但仍系受贿犯罪数额。然而,该案上诉至永州市中院,二审判决却认定该34000元可以从受贿数额中扣除,不应以受贿论。事后,该案一度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贿款归公是否非犯罪化的争论。
肯定者[4]认为,收受贿赂后上交单位、用于公益或公务,是行为人将权钱交易所得回归于公利,公权目的是为公众服务,事后将所得贿赂归公并未真正损害到国家公权,无明显社会危害性,应将此和事后个人挥霍或据为己有进行区分;同时行为人受贿后将款用于公益或公务,也进一步证明其对贿赂无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应予以刑事追究和惩罚。肯定论者还援引刑法385条第2款,认为其中收受回扣后“归于个人所有,才成立受贿罪”的规定,正是对“贿款归公”非犯罪化的潜在性立法支持。
否定者[5]认为,受贿罪所保护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非行贿方的个人财产权,一旦行为人收取财物,受贿罪客体即遭到实质侵害,成立受贿既遂,赃款去向并不影响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内容,行为人对赃款的事后处置或补救无法改变既遂事实。
笔者也不赞同将“贿款归公”一律作非犯罪化评价,如果这一处理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执行,则势必会带来以下不利后果:
第一,混淆受贿罪已有既遂标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如前所述,受贿罪中的既遂标准是收取财物,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财物,或明知系贿赂仍予以收受,即构成受贿既遂。根据赃款去向来定罪,以后续行为去解读先前行为的主观状态,从而判断定性,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是人为臆想的新定罪标准。按这种思维逻辑分析,则所有侵财类、贪贿类犯罪的侦查取证都需延伸至赃款去向调查清楚为止,否则就无法辨别行为人实施先前犯罪时是否具有相应犯罪的主观故意,若行为人收受贿赂或非法占有财物后未及处理即被查处,是否就无法认定其构成相应犯罪或仅作犯罪未遂处理?显然,该种处理方式罔顾现有受贿犯罪既、未遂规定,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第二,违反法益保护原则,造成社会价值标准失衡。贿款归公一律非犯罪化,将人为限制受贿罪的规制范围,也势必影响到不存在谋利情节时对受侵法益的保护。而且,刑法适用的意义除惩治犯罪,维护法益外,还具有社会价值指引功能。如按这种处理方式,以赃款去向来判断罪与非罪,造成的社会导向会是只要将受贿款合理使用,则受贿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公权也完全可以和私利进行交易,只要交易所得归公即可。那么,人们会问,是否一切职务行为都可明码标价,是否可以用金钱或其他利益去换取任何公权力为自己谋利,如此以权谋私、损公利己将成为社会常态,这恐怕与我们的立法原意是背道而驰的。
对“贿款归公”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律作入罪或出罪处理,而应根据行为人是否存在受贿犯罪故意进行不同评价。受贿罪的故意内容和侵财类犯罪不同,并非是将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而是用其职务行为获取不正当报酬,即权钱交易的故意,是明知财物系职权对价而予以个人收受的故意。刑法第385条第2款中“归个人所有”的立法原意并非是排除了对财物非法占有的故意,就不成立受贿罪,应该理解为行为人对权钱交易并无主观故意,如财物并非其个人职权对价,如不知情或无法拒绝下被动收受财物等情况,才可以认为行为人不存在受贿故意。比如,案例中的李某,如业务单位所送贿赂并非给其个人而是单位,其作为科室主任只是代为收受,则当然不能对其以受贿罪论;又如行贿人将贿赂款交由他人转交或在拜访时偷放隐蔽处、暗中夹送,李某在不知情下收受了贿赂,且又无法退还,但其及时上交单位或用于公务,也不能以受贿罪论。
因此,成立“贿款归公”非犯罪化的法理依据是行为人不具有受贿故意,即权钱交易的故意①此处仅讨论收受型受贿归公是否排除犯罪的情况,对于索贿型受贿,因其在实施索要行为时即对权钱交易系明知并积极追求,当然具有受贿的故意,收取贿赂之时即受贿罪既遂,并不存在事后归公脱罪情况。。下面对司法实践中两种具体归公情况的非犯罪化判断作一简要分析:
第一,贿款上交。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已明确在排除行为人因自身或者相关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将赃款上交情况下,对行为人将所收财物及时上交的,不以受贿论。但对于什么时间内上交视为及时,两高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予以明确。对于及时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对收受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为便于司法操作,有必要对此进行统一。笔者现依据经验法则结合客观情况作一分析。首先,“及时”是指一个合理的时间段,那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何时为起算点。既然要排除的是行为人对受贿故意的存在,起算点应该是行为人对财物系职权对价的认识之时,而非收到财物之时,因为现实中存在行为人并不知情而被动收受财物的情况,或者行为人对财物性质存在认识错误的情况,如简单从收受财物起算,势必不够客观。其次,应考虑行为人有所认识后是否具备上交条件。现实中存在行为人虽然认识到所收受的是贿赂,但存在上交的客观障碍,如此时其人在外地无法上交,或财物已在其不知情下被使用,需要时间筹款退交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给予一定障碍排除时间。最后,在行为人已具备上交可能性下,可根据现有国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上交规定,建议以一个月为限。
第二,贿款公用。2006年,上海市高院、市检察院率先在司法层面对贿款用于公务的非犯罪化进行了明确,[6]规定了某些情况下受贿款(物)用于公务可不认定为受贿罪。此举也曾引起社会上的一些非议,但该规定并非如反对者所言的随意造法,其主旨仍是强调受贿罪中故意的认定,并对现实中不具有受贿故意的收受财物情况予以明确,提供司法操作依据,所以该规定是切合实际,值得肯定的。
笔者所理解的用于公务非犯罪化,其法理依据也是行为人并无受贿故意,具体实践中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判断:首先,行为人必须是在无法拒绝情况下被动收受财物,客观上已无退还可能性;其次,收受后应立即公开来源并在单位或部门财务处登记数额及使用情况;再次,用于何种公务不能由其私自决定,应由单位或部门讨论决定,且公用中杜绝夹杂私用成分;最后,与及时上交一样,用于公务非犯罪化也需排除因自身或者相关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将赃款如此处置的目的。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62-1063.
[2]郭竹梅.受贿罪新型暨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188-190.
[3]王鸿谅.湖南新田县教育局长受贿案调查[J].三联生活周刊,2006(30).
[4]王小清.贪污受贿赃款数额认定当中“扣除法”之我见[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8).
[5]于志刚.受贿款物用于公务(公益)问题的思考[J].人民检察,2007(7).
[6]上海司法部门下发“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 接受“纯感情投资”一般不定为受贿[EB/OL].http://news.sina.com.cn/o/2006-09-05/03539935040s.shtml,2012-09-26.
——由行为属性说转向职务属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