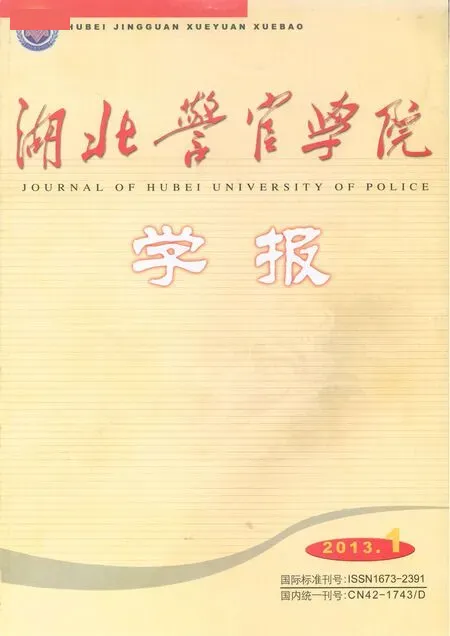“赔偿”与“赏恤”
——从清末扬州教案的审理看中西法律文化之不同
乔 飞
(河南中医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8)
清末扬州、广州、陕西等教案的处理,呈现出了中西方关于受害人损失赔偿法律观念的不同。西方人认为,教会作为受害方,得到中国的赔偿是应该的。因此,非但不对中方的给付行为心存感激,相反还时常指责中方在许多方面尚有欠缺。中国官员则认为,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或财产权利,官方颇费周折,是对西方人的恩典行为;西方人不知感谢,反而抱怨,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本文兹以扬州教案为例,分析此现象及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原因。
一、扬州教案的发生
早在l866年11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已到扬州购地建教堂传教。[1]1867年12月,天主教教士又在扬州开设学堂、药房、育婴堂作为引人入教的手段。1868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也在琼花观巷内赁屋传教。这一年,天主教育婴堂内婴孩因疾病及条件有限,出现陆续死亡现象。当时,由于《湖南阖省公檄》等绅士揭帖宣传的影响,加上扬州有人到处张贴揭帖,指控“育婴堂系为食小儿肉而设”[2],于是民众之间纷纷传闻传教士有“剖取幼孩脑髓眼珠种种不法之事”。扬州士绅多次聚众并散发揭帖,鼓动群众驱逐洋人洋教,但传教士并无离开之意。扬州士绅再次聚议,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3]8月府学考试期间,群众及考生在秀才葛寿春的带领下,向天主教教堂及戴德生等人住所投掷砖石,打毁门窗房瓦,并且声言焚烧。戴德生于8月14日、19日两次写信给扬州知府孙恩寿,要求官方制止民众暴行,但知府答复只能出示谕禁。8月22日,天主教教堂雇工掩埋幼孩尸体,被群众捉住,送至江都县衙。经检查幼孩均为因病死亡,根本没有剖取脑眼之事。但掩埋幼孩尸体的消息一传出,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愤怒的人群在葛秀才率领下,前往天主教教堂。教士金缄三等人此时不在扬州,于是人群又涌向戴德生的住处。戴德生见势赶忙前往扬州府衙求救。愤怒的群众撞开大门,推倒墙垣,砸坏门窗,拆毁家俱,搜查了戴德生的住宅并将宗教书籍烧毁。[4]传教士李爱恩眼被击伤,戴德生夫人及白爱妹小姐因躲避侵害而跳楼受伤。[5]此即晚清著名的第一次“扬州教案”。
二、英方请求“赔偿”,中方给予“赏恤”
在英领事麦华佗向扬州知府提交的“起诉书”中,详细描述了传教士遭受迫害和抢劫的过程,并以附件形式详细开列了英教士所受损失的清单:

附件6索赔备忘录
另有所用华人共17名,所失衣履家具共计洋438元,又失洋43元,总共计1612元,合银1128两4钱正。[6]
麦华佗在《致扬州知府文》中明确提出,“须银若干两,送交本领事转给被抢各人,作为赔偿物件并医伤及各项费用”。[7]即索要价银的性质是“赔偿”,用途是补偿传教士所受的各项损失。扬州知府因为无管辖权,此案呈送至总督曾国藩处。曾国藩对英方请求处理绅士一项坚决拒绝,但对于赔银一项请求很快答应:“至毁失物件之价及医伤费用,本大臣昨已酌给赏恤银一千两,由上海道送交贵领事查收转给。即以此为该教士买补物件及养伤一切之用”。[8]显然,曾国藩对给银的理解与英方不同。他的理解是“赏恤”而不是“赔偿”。“赏恤”是基于在上者对在下者的恩赐与怜悯,所赐财物往往是领受者不该得到的;“赔偿”则是基于平等的法律关系而发生,是行使法律义务的表现,对于领受者来说,赔偿的财物是应得的。
麦华佗对于曾国藩用“赏恤”代替“赔偿”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对于曾国藩的“格外恩恤”,麦华佗首先表示“极为感荷”。其次,认为对于“自愿酌给赏恤银一千两”,如果作为“赏恤该教士之款”,作为领事的他“或可代收”;如果“以此款为赔偿”,作为英方提出请求的赔偿义务之履行,“是非就此了结”,麦华佗则“势有不能”,不得不“置之不收”。接着,麦华佗进一步质问道:“揆度案情,传教士受害被抢,究竟应赔与否?”如果不存在应该赔偿的理由,那么“无论何款,概不能请”;如果应该赔偿,则英方“业已开单”。假如清单中并没有虚假报价,“自应照数赔给”。对于曾国藩“自定小数”,开始“酌给赏恤”,后来却作为“了案赔款”的裁判方式,麦华佗认为“似非敦礼平允之道”。[9]
曾国藩愿“赏”不“赔”还有其另外理由。首先,他认为条约内只有“抢掳者按例严办,追赃交还”之规定,而没有“赔偿”的相关内容。其次,如果出现抢劫财物的情况,受害人若能指明加害人的姓名,此时“罚令交赃”,可称之为“追还”,亦可称之为“赔偿”,因为此时的给付者是加害人。但扬州教案中,英方对于抢物者“实无姓名可指”,没有明确的被告人,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宽仁之心,“本大臣代百姓出银发给戴教士等”,这笔费用自然名为“赏恤银两”。也就是说,作为加害方的中国百姓有给付义务,但中国官方本来并没有给付的义务,只是英方不能指出具体的抢劫人,官府主动“代百姓”给发银两。这一行为并不是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而是超越法律的“恩典”行为。
三、“赔偿”与“赏恤”背后的法律文化分析
中英双方对于经济补偿性质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差异。曾国藩的“赏恤”,是“权力本位”思想的自然流露,也是中国传统“行政司法”法律传统的必然体现。而麦华陀要求的“赔偿”,重在表达一种“权利”诉求,其背后也与英国“专司司法”的制度环境有关。同时,中英争论也暴露出中方的法律观念与国际法相违背。
(一)中方主张“赏恤”的背后,是“行政司法”文化
传统中国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常用家庭的“父子关系”来比喻。官员就是百姓的“父母官”,官民关系被宗法伦理化。在清末变法之前,中国的司法始终是行政事务的一部分,地方行政官员就是法官。百姓之间发生纠纷去官府诉讼,不是请求被动、中立、独立的裁判权威根据法律理清是非曲直,而是“请老爷为小的做主”。官员始终是“在上位者”、有权势有能力的“庇护者”,而不是近代西方司法中的“居中裁判者”。诉讼程序中,当事人称法官为“大老爷”、“青天父母”、“老父台”等,法官则称涉案百姓为“逆子”、“刁民”。法官有权对被告、原告、证人等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人拘捕、笞讯。无论是原告、被告,也不论是否有理,审判中均有可能受到笞杖刑讯。即中国传统的司法诉讼为“家长”式的司法模式。[10]这种司法模式是权力本位、官本位、等级社会的产物,是官民权力配置极度失衡下的必然结果。在此司法制度下,百姓若不将自己置于极度卑微的地位,就无法让官员注意自己的冤屈。而官员对案件的处理,就如同父母解决孩子之间的纠纷,体现着儒家倡导的“仁政”。官员在其中既可获得为政业绩的成就满足感,又能获得“为人父母”的情感心理慰藉。近代西方法律语境下的“权利”意识,在这种诉讼模式中很难体现出来。法官与涉案当事人之间不是横向的、平等的控辩审三方平衡制约关系,而是纵向的、上下的如同父母与子女之间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法官对当事人不仅享有司法裁判权,而且拥有全方位的行政管理权。当事人向法官寻求的不是基于法律的“权利”保护,而是寻求“在上者”替自己“做主”。法官给当事人判决,也不是纯粹基于法律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大人”对“小人”的“赏恤”;不是给予当事人自己本来就应当拥有的“权益”,而是“老爷”对“小民”的“恩典”。虽然历代成文法典对各级官员的司法行为规定了一些责任措施,但官员的权力相对于当事人而言依然绝对强大。承继儒家礼法文化的法律传统使得官员们乐于把自己塑造成百姓的“仁慈父母”形象;百姓之间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变成了百姓与官员之间道德上的情感伦理关系。当事人自己的“权利”就这样奇妙地转变成了官员们的“赏恤”。曾国藩正是以这种法律文化意识去处理扬州教案的。
(二)英方主张“赔偿”的背后,是“专司司法”文化
麦华陀坚持要求中方“赔偿”,亦有其法律文化渊源。英国自12世纪就产生了专职的法庭,[11]司法与行政事务相对分立。12—13世纪,职业化的法官和律师队伍出现并成长,使得司法机构又逐步走向职业化。[12]1688年“光荣革命”后,司法权又从王权中获得了独立地位。[13]在法官的权力构成上,与传统中国司法中的法官相比,英国法官的权力相对小得多。首先,法官仅有司法审判权,没有行政管理权。其次,即使是司法审判权,英国法官也不是全部拥有,司法权内部存在“分权”格局。英国的诉讼模式,采用的是颇具民族特色的陪审制、对抗制,法官无法对当事人进行司法独断。陪审制度由亨利二世在一系列的诏令中确立;刑事案件中,事实部分由陪审员以公正的立场和普通人的常识作出裁决,法律问题则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作出判决,两者结合使得整个案件的裁判更为公正。民事案件中,由陪审员决定责任程度和赔偿数额。这样,司法裁判权一部分由陪审员控制,而陪审员来自民众,一般与涉案人属于同一社会阶层,使得司法审判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陪审制度也就成为英国历史上保护个人权利、反对特权和滥用司法权力的有效手段,成为英国自由、民主传统的基石。[14]再次,“对抗制”的诉讼方式,使得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在审判格局中相对较高,法官可以引导审判方向和控制审判节奏,但不能主动调查事实或询问证人,而只是充当消极仲裁人的角色。这样,法官的权力在程序上再次受到限制。最后,法官根据陪审团的裁决作出最终判决时,必须以“遵循先例”为原则,其实体性的权力也受到很大的制约。法官在这种处处受限的情况下,对当事人很难滋生出“父母”对“儿女”般的心理,自然不会有“赏恤”之心,只能循规蹈矩地“依法裁判”了。
至17世纪,英国已经有正式的侵权行为法法律部门。中国民众侵入戴德生住宅,打毁房屋物件殴伤传教士,在当时的英国法律中属于侵犯私人利益的侵权行为,在英国适用侵权行为法。对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恐吓与殴打构成对人身的侵害,对房屋、财产、书籍的损毁构成对财产的侵害。侵权行为要承担侵权责任。早期的英国侵权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没有明确的界限之分,12世纪时,二者才逐渐区分开来。侵权行为主要采用绝对责任原则,即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对他人造成损害结果,就要承担法律责任。15—17世纪,“过错责任”原则逐步形成。被告人若能证明其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没有主观过错,就可不负法律责任。作为鼓励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过错责任”原则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直盛行。承担侵权责任的形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扬州教案按照英国人的法律观念,无论适用何种归责原则,都不存在免责事由,应承担侵权责任无疑。英方提出请求的民事部分,就有数种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赔偿损失如索要银两,恢复原状如将传教士房屋照原样修好,消除影响如要求出告示晓谕居民凶犯已依法惩办,声明英国人在扬州居住是条约赋予的权利,赔礼道歉如写信或派人去请传教士仍回原处居住。[15]英方要求中方承担这些法律责任,是作为中方民众对英国教士造成损害结果的过错补偿,也是西方历史上一直流传的通过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文化的体现。
(三)中方的法律观念不但与英方不同,而且也与当时盛行欧美的国际法规则相冲突
曾国藩认为扬州案中“赔偿”的责任主体是百姓,官府不应负赔偿责任。官方所给银两是“赏恤”,是恩典,是英国人应该感恩戴德的。当时,国际法已在欧美各国通行。[16]按照国际法规则,一个国家因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或具有国际不当行为,会引起国际法上的法律后果,从而要承担国际法律责任。国家机关的职务行为要承担国际法律责任。承担责任的原则一般是过错责任原则,有些情况下也适用无过错原则。构成国家不当行为的要件有两个:一是引起国家责任的行为根据国际法能够归因于国家,二是该行为是违背了国际义务的行为。国家机关的行为、经内国法授权行使政府权力的其他机关的行为、实际上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的行为,在国际法上都是国家行为。国际义务主要来源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等国际法渊源。对国际义务的违背包括主动违背有关国际法规则的积极作为,也包括应履行而未履行国际义务的消极不作为。对于应该归责的国家机关行为,不论该机关是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机关,不论其行使的职务是对内或对外,也不论其在国家结构中处于上级或下级地位,其行为均为代表国家的行为。以国际法规则分析扬州教案,扬州府、两江总督的行为都是中国国家行为。中英双方签订的双边条约,可以视为中方履行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戴德生等传教士在案发前数次请求中国地方政府予以保护,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要求予以防范和制止,但扬州知府的做法是虚与委蛇,实际上没有履行保护责任,造成绅民放心大胆地实施打教计划,以致酿成教案。扬州府的行为可视为应实施但未实施的消极不作为,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反。而一国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就要承担国际责任。其形式有终止不当行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保证不再重犯、限制国家主权等。由于政府未能履行条约义务而导致外国人在本国遭受损害,作为两江总督给付银两的行为,显然属于代表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赔偿行为。这与从道义或友好关系出发的“赏恤”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曾国藩称其给银两行为是“赏恤”之说法,与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也相背离。
晚清教案是鸦片战争后中西政治、文化交汇碰撞的产物。一方面,它见证着西方列强对清帝国的殖民侵略;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西方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冲击。就法律文化而言,中国两千年延续的传统司法理念,在教案这一特殊案件审理时开始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与限制。这一尴尬现实,在感情上令中国人痛苦,然而理性地来看,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为进入中国本土的是相对先进的法律文明。
[1][2][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2辑):577,5 78,588.
[3]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 7:401.
[6][7][8][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 6 册)[M].上海:中华书局,2000:28,29,30,36,37,61.
[10]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09-211.
[11][12][13][14]程汉大.英国法制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1:57,1 05,119,334,266,460.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6册)[M].上海:中华书局,2000:28-29.
[16][美]惠顿.万国公法[M].丁韪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