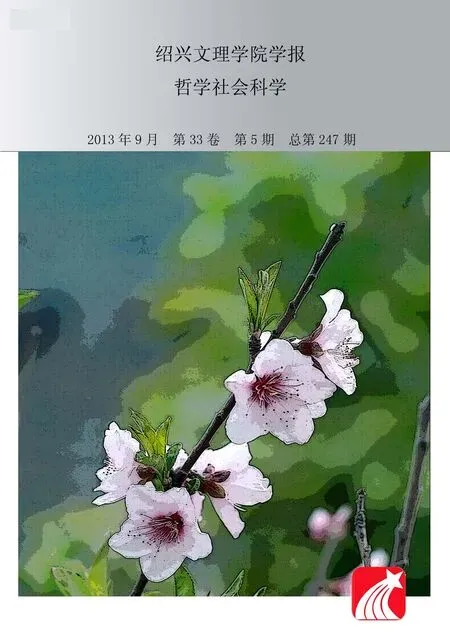“老中国”形象的空间与场域展示
——越文化空间中的鲁迅小说“场域设置”
黄 健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310028)
通过越文化的特定空间和场域,展示“老中国”的形象窘态,是鲁迅从越文化视阈思考中国命运,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独特之处。从思想内涵上来说,鲁迅所选择的是广泛存在于国民心理和性格中那些落后、愚昧、无知、麻木的精神,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从形象展示上来说,则是为最大限度地反映国民劣根性,展现“老中国”闭塞、保守、停滞的形象。而之所以多选择越文化的空间和场域,鲁迅考量的依据,一是基于对越文化空间和场域的“熟知”,个人对“老中国”的独特经验和心理感知,易于借此进行清晰的表达和展示;二是作为原本是中国最富裕地区之一的越文化区域,它的衰败则更能展示出“老中国”的形象窘态。通过越文化独特空间与不同场域的设置,从中反映“老中国”的落后和国民的劣根性,在鲁迅看来,则更能反映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种种际遇和关键问题,如同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描绘出整个拉美大陆在空前的变革中遭遇整体的孤独、惶惑一样,鲁迅在越文化的空间和场域中,也写出了整个“老中国”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中的窘迫之状,揭示出一个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老大”的国民劣根性,显示他对于中国变革之难的深邃思考,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人生、国民性格的整体认识、把握和深刻的反省。
一、“S城”:“老中国”的固态空间
任何场域都显示出其空间所存在的主客观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网络,它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空间构型,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寓意性,以及自身意义生成的机制。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华康德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在鲁迅的小说中,以“S城”为代表的越文化地域空间,原本是中国区域文化的一个最富有诗意的文化场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区域。然而到了近代,随着现代性蔓延而不断产生社会的分化,这个曾经是富甲一方的区域,却日益显示出其一副老态龙钟的景象,如同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所展示的那样:“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面对着“大约太老了”[2]的近代中国,鲁迅的小说是通过置于越文化空间的“S城”的场域设置来展示它固体化的空间的,其特点是择取他最熟习的越文化的空间和场域,来对“老中国”的形象窘态进行的认真透视,展开他对于中国落后的深度思考。对于鲁迅来说,“S城”是他的故乡,但在他看来,这也是“老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空间和场域,是“老中国”的一个形象缩影。作为生活和成长空间的“S城”,他不仅仅只是熟习,而是有着深切的内心体悟,用他的话来说,他在“S城”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3],“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4]。在小说中,鲁迅通过“S城”的场域设置,表现出了中国文化鲜明的世俗性特点。对这个世俗化空间和场域的描绘,鲁迅的心情是沉重的,伤感的,但又始终都努力地去展示其中的若干“亮色”,以表现他对“老中国”最终出路的深层考量。像小说《在酒楼上》对“S城”空间和场域的描述:“城圈本不大”,且是“深冬雪后,风景凄清”。这幅“冷色调”极浓的空间和场域,给人一种冷漠和停滞不前的感官印象。鲁迅在这个本不大的“城圈”场域,设置了“洛思旅馆”“一石居酒楼”和“废园”三个颇具象征寓意的场域。第一个场域只是“我”“竟暂寓”的落脚点,它“租房不卖饭”,且“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彩,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第二个场域则是“生客”眼中的那“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依旧是五张小板桌”,仅是将“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的“酒楼”。而第三个场域却是远眺到的“废园”,但它“不属于酒家”,顽强生长在那里的“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无疑,在小说中,“S”城的“洛思旅馆”和“一石居酒楼”的场域设置,其寓意是象征着“老中国”固态、迟钝、麻木和闭塞的形象展示。“我”与“阿纬”在“酒楼”的偶遇,尤其是置于“我”面前的“阿纬”,他的那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很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去了精采”的模样,与“旅馆”和“酒楼”构成了第三种的“场域”设置,说明“我”“阿纬”在“S城”的空间场域里,构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网络关联。无论是人与环境的关联,还是人与人的关联,都逃脱不了“被制约”的命运,就像一只“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阿纬早已消磨了他原先的人生意志,如同他自己所感叹的那样:“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功夫:当时什么法子也没有”,而即便是现在也是什么都没有,“踪影全无!”“老中国”的停滞不前和闭塞守旧,消磨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阿纬,使他只能是“现在就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自然麻木”。在鲁迅看来,越文化地域空间所表现出的人事现象,不只是单个的孤立事件,相反,则是带有一种普遍性。因为在历史的“破坏”又“修补”循环中,“老中国”一直未能走出“奴隶”时代,只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两个时代里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所谓中国历史“超稳定”的状态,而在这个空间场域中,“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5]212即便到了民国也是如此,“老中国”形象阴魂仍然挥之不去。鲁迅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6]“老中国”的停滞和闭塞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如同王德威所指出的那样:“(老灵魂)是以背向——而非面向——未来。他们实在是脸朝过去,被名为进步的风暴,吹得一步步地‘退’向未来。”[7]鲁迅透过越文化的空间场域,表达了他对于“老中国”的整体认知和把握,画出了在“老中国”固态化的空间场域中“失意者”的经典画像:他们背对现实,打磨时光,并连接过去与现在,积聚对抗未来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极为冷酷的空间场域中,鲁迅要考量的是如何从中找到一种可以“破局”的力量:“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有,或许没有,但都必须“走”,只要“走”的人多了,在本没有路的地方,也就有了“路”了。从这个维度来看,在小说中,鲁迅设置的第三个空间场域——“废园”的象征寓意就十分的明显了:“寒风和雪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因为“废”寓意着“破”,自然也蕴含着“立”。
置于越文化空间的“S城”及其所展示的“老中国”形象,其停滞、闭塞、守旧和冷漠的气氛,始终是弥漫在整个空间和场域,给人以一种空前未有的压迫感,众多的不觉悟者则是使少数的先觉悟者感到格外的“孤独”。在小说《孤独者》中,“S城”的空间和场域设置,不论是由“城”延伸到“山村”,还是由远(“山村”)到近(“书铺子”“客厅”),也仍然离不开越文化的空间要素和色彩,并带有“老中国”之“城”的沉重背影。那个离城“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的“寒石山”村,说是乡村,却又离不开“城”,也可以说是“S城”的另一网络空间。在这里,无论如何变化,都“全是照旧”。在这个空间和场域里,作为先觉悟者的魏连殳也不得不向世俗低头,但内心却极其的孤独:“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在“S城”的网络空间,鲁迅还设置了一个“书铺子”的场域。在这个原本的静雅之地,魏连殳仍然无法摆脱来自世俗的羁绊,看似清静无为,与世无争,但依然会有“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尽管孤独一人,但“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还不给连殳安住”,结果“被校长辞退”。与此相关的“客厅”场域,则“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屋中间的圆桌还在,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臜吵闹的孩子们的,现在却见得很闲静,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不论是“远”,还是“近”的空间场域,都是令人窒息的,无处逃遁,这是魏连殳一类的先觉悟者们的孤独之源。“老中国”的空间就是这样无形有形地压迫着每一个人,就像叔本华一针见血地说到的那样:“每个人的生命,往往是个悲剧”,因为“作为意志最彻底客观化的人类,在同样程度之下,是所有生物中最贫困的……从本质上看,希望就是痛苦,整个人生都在厌倦和痛苦之间来回摆动”[8]。“孤独”在鲁迅小说文本中与具体的情节似乎无关,然而,在来自“S城”的孤独心理感受,却如鱼得水地附在人物身上,深深藏匿着对过去、现状,特别是对固态化的世俗现实的一种最深沉的忧伤。
越文化空间的“S城”的固态化,不仅在虚构世界中如此,在现实世界里也是如此。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鲁迅依然表达了他对“S城”的某种失望:“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在他看来,共和制的民国建立,还只不过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看似在变,却又什么都没变。“S城”所折射出来的“老中国”镜像,依然如故,仍然是一张巨大的网络空间,让人“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5]215了,鲁迅由此获得“中国太难改变了”[9]164的一种刻骨铭心的心理认知。
二、“鲁镇”:“老中国”的异化空间
皮埃尔·布尔迪厄确立“场域”的概念,旨在把社会划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又密切相连的空间。在他看来,社会是个“大场域”空间,它由一个个相互独立又相连的“子场域”空间构成,而每个“子场域”空间都具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规则。对于鲁迅来说,越文化空间有着诸多的“子场域”空间,而“鲁镇”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虚构的“鲁镇”是越文化空间中的一个颇具特点的“小镇”场域,它的独特性在于有着像“酒店”一类的公共场域,如在小说《孔乙己》中,鲁迅就特意提到“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如咸亨酒店那“当街的曲尺形大柜台”,孔乙己就是经常在这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不论客观的形势如何风起云涌,他依然迂腐、固执和麻木无衷。他无视时代的变动,也不知镇外的变化,而是依旧依照自己的方式“过着日子”。尴尬的身份,迂腐的行为,固执的心理,守旧的观念,表明他是一个“背时者”“落伍者”。在鲁镇,咸亨酒店一类的公共场所,无论是掌柜、小伙计,还是那短帮长衫的平民百姓,无一例外地都显示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旧态。他们聚集在酒店这样的公共空间,嘲笑、捉弄他人,由此获得某种快感。其实,这个看似热闹,却没有人情的小镇,彼此都处在“看”与“被看”、“示众”与“被示众”之中,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与“爱”,无法做“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在不断异化的空间和场域:外部空间在异化,如同“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内部空间也在异化,如同孔乙己所感叹道的:“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孔乙己终究抵御不过来自内外异化空间的挤压,默默地死去。对于鲁镇来说,即便他生前有时也“使人快活”,但只不过是一种被人取乐的对象而已,“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鲁镇还是鲁镇,与“S城”一样,在异化中不断的固化,成为一种常态,如同鲁迅后来感叹的那样:“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9]164
《祝福》所展示的“鲁镇”,与《孔乙己》不同,它是构成“杀死”祥林嫂的特定空间场域。小说虽然没有指控究竟谁是迫害祥林嫂之死的“凶手”,但实际上生活在“鲁镇”的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杀手”,有的是有形的,有的则是无形的。鲁四老爷、四太太、祥林嫂的婆婆、柳妈、卫老婆子,以及其他的鲁镇男女老少们,共同组成了以越地“鲁镇”为代表的中国旧文化、旧传统的罗网,用不同的方式对祥林嫂进行了肉体、精神的摧残、迫害,使祥林嫂始终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时代里苦苦挣扎,最后只能是孤寂与落寞地死去。鲁迅所描绘的越地“鲁镇”,是一个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村镇”,如费孝通所说,它虽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0]。乡土气息极浓的“鲁镇”,在鲁迅的笔下,显然不是一个迈向现代社会的对象和结点,而是相反,是一个阻碍物。它自身固有的生活逻辑系统,构成了特定的异化空间,无论是外部的空间,还是内部的空间,都是如此。如外部空间的场域展示,鲁镇的气象是:“旧历的新年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要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漫了幽微的火药香。”年年依旧的村镇迎新年的气氛,永远不会改变,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训”,谁也不能动,越地民俗更是如此。民国虽然建立了,但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感觉,依然按照“旧历”过新年。祥林嫂不是鲁镇的人,作为外来者,也是一个异己者,她置身于这样的空间环境,只能接受被异化的命运:“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外部空间环境如此,内部空间环境能好吗?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
“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无法说清楚的魂灵,在表明疑惑的同时,也表明了内部空间的一种“紧张”:有,还是没有,这真是一个问题。然而,无论有还是没有,都显示出内部空间的异化早已使人产生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怀疑。这是异化空间对人压迫的必然结果。一个无法获得自身变革动力的封闭社会,只能是在不断异化的固态化中被驱逐、被消失。
《明天》中的鲁镇“原来是僻静的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显然,这既是越地的风俗,但也是由它所呈现出来的“老中国”的一种“旧态”。鲁迅在这里设置了两个独特的空间场域:一是“咸亨酒店”,这里依旧热闹:“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二是“间壁的单四嫂子”的家:“自从前年守了寡,便须专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他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显然,这里展示的鲁镇,与《孔乙己》《祝福》所展示的并无两样,也是一个使人异化的无形空间,即便是对一个守寡的“粗笨女人”也不放过。单四嫂子在丈夫死后,恪守“夫死从子”的妇道,只希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养活儿子。但是,她身处的鲁镇,却连这点小小的心愿也不满足她,尽管她总是幻想“明天”会变好,但她真的还有“明天”吗?这个一再被称为“有古风的”的村镇,实际上已没有了“古风”的淳朴,由老拱、蓝皮阿五、何小仙、咸亨的掌柜、王九妈这些无聊、麻木、自私的看客而构成的有形和无形的“杀手”,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吞吃着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在鲁迅的笔下,越地的鲁镇并不是世外桃源,其异化的空间场域,处处都展示着“老中国”形象的闭塞、愚钝和落后窘态。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曾说:“每个文学家归根到底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他希望他的作品读过之后,产生一幅画立刻产生的那种印象。”[11]通过越文化空间的“鲁镇”场域的设置,鲁迅对“老中国”的形象进行了“蒙太奇”式的定格,形成一幅“老中国”形象独特的画面感,不仅越文化的地域色彩极为浓厚,同样,整个“老中国”形象的“老态”“旧态”,国民的愚昧、麻木和无知之状也都跃于字里行间,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带来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反省。
三、“未庄”:“老中国”的衰败空间
相对“S城”“鲁镇”来说,“未庄”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展示的另一个重要的越文化空间和场域。它不是一座城,也不是一个镇(尽管鲁迅还将它称作为“村镇”),而是一个既具有典型的越文化风俗,又具有典型的“老中国”衰败特征的村庄。鲁迅对“未庄”是这样描写的: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
表面上看上去是江南水乡——越地的秀丽景色,但“内骨子”里却处处透露出“老中国”的衰败景象。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未庄似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革命党”已进了县城,而未庄却依然“没有什么大异样”,更何况县政权只是改头换面为“革命”新政府,“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不过改称了什么”。在未庄,无论是有权势的乡绅赵太爷、赵秀才父子,还是普通的百姓,都依然如旧地生活着,不是对外部的“革命”茫然无知,就是另作图谋。如未庄的几个“盘辫家”,与假洋鬼子有交往,听他吹嘘“革命”而将信将疑,故采取盘辫子这种依违于清政府和革命党之间的“骑墙”做法,足见“看风使舵”的投机性格。还有阿Q、王胡、小D一类游民,靠着“精神胜利”法,过着“倚强凌弱”的生活,嗜酒、赌博、打架、偷盗、调戏妇女,作奸犯科,乘势作乱,为己谋利。在未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内心深处的隔膜,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上的愚昧落后,都呈现出“老中国”衰败的形象。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任何场域都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同时,任何场域又都旨在使那些进入空间和场域的人明白,你、我、他都构成了这个空间特定的场域关联,并形成这个空间场域的主导或“颠覆的力量”[12]。“未庄”虽然是越地的一个普通乡村,但它也具备了“老中国”社会的所有要素。在小说中,“未庄”空间的外置场域,是通过诸如“土谷祠”“酒店”“赵府”“钱府”“静修庵”“破衙门”“法场”等一系列极具越地景物特点来显现的,这些彼此看似并不关联的场域,却共同构成了“未庄”作为“老中国”形象的空间要素:静止、停滞、破败、衰落……而鲁迅之所以选择这些典型要素来进行外部场域的设置,展现它所谓“原先的阔”到如今的衰败,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告诉人们,活动在这个空间和场域的人,已变得非常的“老朽”,恍若是日益变化社会的“局外人”。正是从这个特定的维度,鲁迅对一群生活在这个特定空间的人的内部场域进行了设置,凸显出他们的迂腐、愚昧、麻木、无知、守旧和苟活的精神特征。在小说中,赵太爷、假洋鬼子、阿Q、王胡、小D、吴妈……所有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人,其内心的场域形态尽管各不相同,但其本质特性则并无两样,精神上的迂腐和守旧,不思变革,不思进取,整天在一个“绝无窗户”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或昏睡不醒,或混混沌沌“过日子”,用“精神胜利法”麻痹灵魂,且“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5]217。透视这群人的内部生活及其精神场域,不仅可以审视其悲剧的人生,省思那些“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如何被“毁灭”[13]192的过程和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更深层次地反省“有着四千年历史”的“吃人”的本性:“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5]217“未庄”这个自然景观看上去还保留着秀丽的江南越文化景观的乡村,精神的“内骨子”里却处处都透露出衰败的人文气息:“从这一天以来,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其实,何止只是从“这一天以来”呢?实际上,在整个中国被迫进入以现代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以来,不都处处散发着“遗老”的“气味”呢?“造物的皮鞭”再不“到中国的脊梁上”,再想动,可能也不能动了,因为“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14]
米勒曾指出:“小说的解读多半要通过对重复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的鉴定来完成。”[15]在越文化空间中,选择“S城”“鲁镇”“未庄”这三个有着颇有些重复特点的越文化地域空间场景,来对“老中国”形象进行场域的设置,鲁迅也就为“老中国”的形象叙事,带来了一种极具象征寓意的叙事空间的扩展。尤其是它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姿态,不仅丰富了叙事空间的地域性特征,而且更是以其对越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个人经验和心理感知,传达出了对特定空间和场域的固化、异化、衰败的深度解读。同时,在诉诸文本的多重意象中,不同场域境况的书写,也多维度地呈现出“老中国”形象的表征,使之成为空间意识表达的最好道具和方式,也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以“仁”为中心指向的象征性的认同价值,整体上遭遇解体,但在特定的文化区域还仍然存留,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如果不重视这种对这种空间的审视,也就不能真正来推动中国整体的进步。因为任何一个文化的空间和场域,它都具有高度渗透性质,外显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动,同样会影响内显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变动,如果不来一场灵魂深处的反省,在最高的意义上显示“灵魂的深”,也就无助于整体的国民性改造。同样,如果不深入地分析与把握这种空间的内部构造,描绘出其独特场域的实际境况,也就难以揭示“具有四千年文明”的“吃人”本质,无法真正做出吻合现代化发展潮流的自我选择。因此,鲁迅选择自己熟习的越文化空间进行独特的场域设置,目的是要透过特定的文化空间,择取典型场域,进行细致的解剖,确立一种标本或样本,获得“以点带面”的批判效果,揭示出“老中国”独特的空间结构、场域境况和逻辑运行方式,达到对其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和“本没有路”的“希望”从中走出一条真正的“地上的路”,引领众多的不觉悟者在思想启蒙的洪流中,获得对自身蒙昧状态的最终超越。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87.
[2]鲁迅.两地书·四[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
[3]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5.
[4]鲁迅.朝花夕拾·琐记[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3.
[5]鲁迅.坟·灯下漫笔[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2.
[6]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
[7]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88.
[8][德]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李成铭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406.
[9]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4.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Ⅱ.
[11][法]德拉克罗瓦.德拉克罗瓦论美术和美术家[M].平野,译.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136.
[1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性[M].谭立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30.
[13]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2.
[14]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65.
[15][美]J.H.米勒.小说与重复[M].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