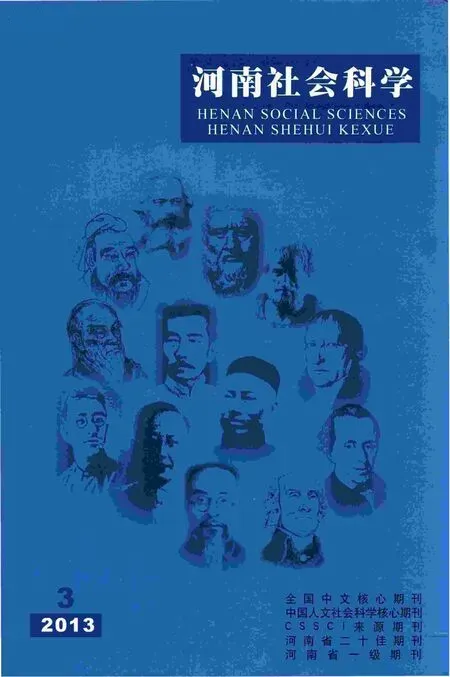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
郑永吉,安 莉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8;2.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 昌平 102209)
一、《赵氏孤儿》与欧洲文学关系研究史回顾
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各国的“旅行”及其生发的各式各样的译本、改编本,可谓比较文学史上的“超级”典型,甚至被认为“迄今为止是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享有的最大,如果不是唯一的光荣”[1]。综观中国学术界对《赵氏孤儿》的比较文学研究历史,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高潮。1931年,范存忠先生以《中国文化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影响》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部分对《赵氏孤儿》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各种“改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32年,范希衡先生以《伏尔泰与纪君祥——对〈中国孤儿〉的研究》获得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相较而言,范存忠先生侧重于分析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希衡先生侧重于本事的考证与主题的处理,但二人均具有明显的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研究特色,同时注重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善于运用“中国古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法则”[2],可谓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考证与“格义”相结合的综合研究。
新时期以来,《赵氏孤儿》继续在文艺界和批评界引发人们的关注,对其世界传播路径及事实方面的研究更为翔实丰富,对《赵氏孤儿》为代表的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的比较研究有所开拓,研究角度也更多样、新颖和独特。1988年,孟华女士以《伏尔泰与中国》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其中有不少章节论述了《赵氏孤儿》与伏尔泰之间的关系,论文颇受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文学史研究会主席勒内·波莫(Rene Pomeau)等的好评[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伏尔泰《中国孤儿》首次在中国上演,以及诸多《赵氏孤儿》现代话剧、京剧版本的上演,一股不小的《赵氏孤儿》研究热潮又一次掀起,其中又以《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两剧的关系研究为主。这些研究或者阐释《赵氏孤儿》对于东西方文学/文化融会的历史作用[4],或者比较《赵氏孤儿》与西方各改编本或者西方悲剧的思想主题与艺术特征[5],或者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角度研究《赵氏孤儿》的各种改写[6],或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西方对《赵氏孤儿》的接受[7]。
曹顺庆先生提出,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来看,文学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新范畴,它“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8]。本文拟采用曹顺庆先生提出的变异学的思想和方法,尝试对《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文本旅行”所产生的“变异文本”及其“回归之旅”,进行新的思考。
二、文化异质性是“变形”译本在欧洲流传的原因和动力
1733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将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杂剧首次译成法文,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两年后,全文发表在杜赫德(J.B.du Halde)编辑的《中华帝国志》(简称《中国通志》)上,“成为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就十八世纪来说,它是唯一在欧洲流传的中国戏剧”[9]。马若瑟的译本以宾白为主,删去了原剧的全部词曲歌唱部分,元杂剧中“曲白相生”之妙,《正音谱》所谓的“雪里梅花”,王国维所谓的“元剧之文章”,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因子全部遭遗弃[9],马若瑟解释说,删译歌曲是因为“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唱词曲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4]。言下之意,只有欧洲人能够理解且愿意理解的“事物”和“语言形象”才是值得翻译的。根据马若瑟的译本,杜赫德这样理解中国戏剧:中国的戏剧和小说没有多少差别,悲剧和喜剧也没有多少差别,目的都是劝善惩恶[9]。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若瑟这种翻译策略是成功的,是得到当时法国人(也是欧洲人)赞赏的。事实上,在18世纪的欧洲,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随着《中国通志》的流行而大大流传开来,法、英、德、意、俄、波兰等国都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译本、改编本。而《赵氏孤儿》较完整的法文译本直到1834年才由东方学家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翻译并在巴黎刊行。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的译本诗文并茂,还附加有关搜孤救孤的历史记载文献,尽管更加贴近《赵氏孤儿》的“原形”,却远没有马若瑟残缺的、不完美的译本的影响大。
从变异学的角度来看,《赵氏孤儿》的译本旅行线路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赵氏孤儿》不是我国主动翻译介绍出去的,而是由外国传教士翻译出去的。由于当时中欧之间的交流刚刚起步,中欧文化交流只有通过来中国传教的宗教使者或者商船等极少的途径,才有可能穿越中欧之间地域、语言与文化的重重障碍。时处康乾盛世,天朝缺乏主动交流和学习的动力和意愿,中欧之间的文化异质性被放大至极限,只能靠欧洲人主动介绍中国,来缩小差异。第二,《赵氏孤儿》不是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地被翻译出去的,马若瑟是有意识地将与欧洲戏剧传统不相符的文学质素和信息“过滤”,进而“归化”为欧洲人能够接受的文学表达样式,因此,《赵氏孤儿》法译文是“变形”的。为了满足欧洲人对“中华帝国”这一异域形象的幻想和期待,在欧洲人能够并乐于承受和理解的范围之内,马若瑟极具创造性地选择了上述的翻译策略。因而,在双方异质性无限大于同质性的条件下,马若瑟从目的语环境的接受需要出发对《赵氏孤儿》大加删译成法文,迈出了真正发现、沟通中欧之间文化/文学异质性的重要一步。第三,朱利安的译本发表时,中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快速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增强,古老中国的“异国形象”已不再那么美好,距朱利安的译本发表不到6年,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以后,我国开始了“向西方”的历程。尽管朱利安的译本更为完整和完美,但当时欧洲已经基本形成了对中国这个“落后”的“他者”的“广泛共识”和“集体印象”,朱利安的译本自然难以复制马若瑟译本新鲜的“异域情调”所引起的审美期待和接受反应了。
文化异质性既是文学/文化交流的直接原因,也是驱动交流的根本动力。在两种文化异质性差异极大时,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往往具有较为强烈的主动翻译意识,企图通过“归化”翻译策略,增强对对方的理解和认识,在缩小异质性差异的同时,利用对方异质性因素中有利于壮大自身的部分,使之与自有文化融会,构成新的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质态,从而促进新的文学、文化和思想的发展。
三、“变形”译本引发“错误”批评,对异质性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马若瑟不完美的“变形”译本流行开来以后,引发了当时文艺界对《赵氏孤儿》的热烈评论,其中不乏一些在现在看来明显是错误乃至无知的激烈批评。在法国、英国对《赵氏孤儿》的批评中[9],因为被马若瑟“变形”了的《赵氏孤儿》译本这个“被评价”对象本身是被“过滤”和“归化”的,加上当时整个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也充斥着“东方想象”的错觉,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谓“批评”,其客观性、准确性自然值得商榷。然而,如果不是从准确性的标准来苛求这些“历史错误”,而是将这些“错误”批评作为《赵氏孤儿》译文的“孪生物”予以审视的话,那么,这些批评就会焕发出新的价值,取得与《赵氏孤儿》译文同等重要的文化地位。下面以伏尔泰为例,分析这些“错误”的批评对于异质性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
伏尔泰《中国孤儿》“作者献词”本身就是一篇对《赵氏孤儿》译文进行批评和比较的文章。他说:“《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广大的帝国所曾作和所将作的一切陈述。”伏尔泰认为,它“又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鞑靼的胜利者不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他们保护着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切艺术;他们接受着它的一切法规”;它“是一个伟大的实例,说明理性与天才对盲目、野蛮的暴力所具有的优越性”。伏尔泰还根据他所见到的《赵氏孤儿》推断,“诗剧只是在这与世隔绝的庞大中国和在那唯一的雅典城市里才长期地受到尊敬”,因此,“只有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是古代具有真正社会精神的民族”[1]。这些批评看起来充满了对《赵氏孤儿》及其代表的“诗剧”以及产生“诗剧”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穷的敬意,但是这些批评首先是对他自己创作《中国孤儿》意图的表达。尽管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研究最深、认识最广、受影响最大、论述最多”[1],代表了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群体对中国认识的最高水平,但正如勒内·波莫指出的,伏尔泰当初写作《中国孤儿》的意图是“他有意从事法国悲剧的改革。因为,这一剧种在高乃依和拉辛的杰作之后开始衰落。伏尔泰放眼世界,意在传统之外,故想在异邦发现有才华的戏剧家,给自己输入新的血液”[3]。因此,“中国”“诗剧”的异质性因素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充当了伏尔泰预设的叙述框架里的材料和证据。至于这些材料和证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伏尔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无法也没有必要去考证和验证。笃信世界主义的伏尔泰在对待外来文化时,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将这些外来文化的异质性“裁剪”、“熔化”,然后贴上“伏尔泰式”的标签,并将之内化在作品的生命里。
另外一个事实更明确地表明了伏尔泰对待异质性文化的态度,那就是他对《赵氏孤儿》的艺术评价并不高。同样在“作者献词”里,他不无揶揄和嘲讽地说,《赵氏孤儿》与法国当时的好作品相比,“蛮气十足”,因此只能拿它“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相比,这些悲剧今天在比利牛斯山那边和英吉利海峡那边还照旧受人欢迎”。而且,《赵氏孤儿》“剧本的情节延长到二十五年,正如人们称为悲剧的莎士比亚和洛卜·德·维加的那些畸形的杂剧一样;那是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变的堆砌”。在他看来,《赵氏孤儿》的艺术价值仅仅在于情节“令人难以置信”、“妙趣横生”、“变化多端”、“极其明畅”,而它却缺乏“其他的美:时间与剧情的统一、情感的发挥、风俗的描绘、激辩、理性、热情”[1]。很明显,伏尔泰是拿着古典主义戏剧的标尺来衡量《赵氏孤儿》的。《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主题的借鉴非常明显,对中国精神的把握也比较到位,但从艺术形式上看来,伏尔泰几乎没有任何借鉴。这当中自然有《赵氏孤儿》译文没有“忠实”翻译出杂剧的艺术形式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伏尔泰认为中国戏剧诚然优秀,却是停滞不前的。伏尔泰对元杂剧及中国文学发展的认识正确与否另待他论,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看,在对待《赵氏孤儿》的艺术形式时,伏尔泰的态度表面上看起来与他对待《赵氏孤儿》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大不相同,实质上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以自己民族审美性格和特征为基准,衡量和评价外来文学形式的价值。
因此,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批评,一方面,客观上是其自身对中国戏剧这一异质性文化的无知和误解造成的,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作为有强烈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对比异质性文化时自然会根据自身的话语表达需要“有意”地选择上述的价值取向和策略,使源语言的《赵氏孤儿》从主题思想到艺术形式均发生严重的“变形”,最终达到促进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改革向前发展的根本目标。
一个国家或者文化群体在面对外来异质性文化时,它的接受和反应情况集中反映在评论界的批评里。评论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化精英的主流意识,他们的论述既是对外来异质性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构成了本土与外来异质性文化对话与交流的一部分。由于异质性差异不可能完全消除,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也不可能完全融和,接受一方的批评话语必然会有一部分在对方看来是“偏颇”、“错误”乃至“荒谬”的。对待这些“错误”的批评没有必要采取愤愤不平的态度。虽然指出其中的谬误之处有利于真假判断,但发掘这些批评对于异质性文化交流的作用无疑更有意义。因此,伏尔泰的“错误”在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与他对中国的认同一样,同样值得赞赏。
四、改编本迭出:异质性文化变形和契合
《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旅行除了上述的“变形”译本和“错误”译本批评,还有一个变异形态:改编本。在18世纪的欧洲,将《赵氏孤儿》译文改编为具有东方色彩和异国情调的“中国戏”,是一种文化时尚。这些“中国戏”大多以《中国孤儿》为题。除了下面要重点论述的英国和法国之外,欧洲的许多国家也有不少改编本[10]。
如果说《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欧洲译本尽管受到了许多有意识的“删改”,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反映原著精神和故事梗概的话,那么这些根据本来就“变形”了的译本而改编的戏剧就离原著很远了,而且出于改编者政治或文学诉求的需要,所谓改编,毋宁说是借用《赵氏孤儿》译文提供的故事框架而进行的“外国题材”“创作”来得更为恰切。
在欧洲,第一个改编《赵氏孤儿》的是英国的剧作家哈切特,改编本1741年出版,标题是:“《中国孤儿》:历史悲剧,是根据杜赫德的《中国通志》里一本中国悲剧改编的,剧中按照中国式样,插了歌曲。”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改编中国戏剧[9]。剧情除了最后两幕以外,基本与原作相符,仍可看出原作的轮廓,但剧中人物堪称“关公战秦琼”,屠岸贾改成萧何,公孙杵臼改成老子,提弥明改成吴三桂,赵武改成康熙,令人有时空错乱之感。范存忠先生曾指出,该剧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戏剧意义”[9]。哈切特在“献词”中明确说,《中国孤儿》的主题是揭露政治腐败,并将英国第一个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作为讽刺目标[9]。哈切特从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文学诉求出发,有意识地寻找、运用和改造来源于《中国通志》的东方色彩和异国形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在英国影响更大的改编本是墨菲的《中国孤儿》。该剧1759年4月底在伦敦上演,大获成功,使本来同时身兼演员和谐剧作家身份的墨菲成为名噪一时的悲剧作家。从渊源上看,墨菲的《中国孤儿》是根据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进行改编的,同时采纳了赫德对《赵氏孤儿》的批评观点,并依据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译文的后两折构建故事轮廓。范存忠先生指出,墨菲《中国孤儿》的大获成功,很大程度是“由于在五十年代末的英国这戏带有现实的政治意义”[9]。18世纪50年代,时值英法七年战争,英国外部战局吃紧,内部又纷争不断,60年代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也是一个孤儿——刚刚成年。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墨菲《中国孤儿》上演,剧中演的是中国的忠臣义士为保英勇的孤儿(青年)而誓死抗击残暴的鞑靼侵略者、真孤儿最终杀死铁木真报仇的故事,因此,《中国孤儿》被认为是宣扬爱自由、爱祖国的悲剧,墨菲也被奉为爱国主义者的导师[9]。
在法国,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与莎士比亚的“可怖恶作剧”一样,其中不乏天才的构想,所以他决定将之改成一部法国式的悲剧[3]。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开始在巴黎等地多次上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轰动了整个欧洲。关于《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之间的关系问题,伏尔泰在“作者献词”和其他文献中语焉不详、前后矛盾,经过范希衡先生对《中国孤儿》对元杂剧原主题的沿袭和发展的深入辨析、对新来源的考证、对剧中人物性格的比较、对伏尔泰风俗描写的分析以及对作品中哲学论争的研究[1],已经十分明晰。范希衡先生总结说:“伏尔泰把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不免简单化、美化了一点,但是他说明了一个历史规律:低级社会接触到高级社会必然要接受高级社会的文化……《中国孤儿》这篇戏剧是拿一种个人的突变来艺术地表达这种社会的转变过程。”[1]此为不刊之论。然而,伏尔泰这部明显带有与卢梭辩论色彩的戏剧,在对待《赵氏孤儿》这个异质性文化/文学文本的时候,其意并不在于发扬《赵氏孤儿》的精神和艺术,而在于通过化用《赵氏孤儿》中契合自己的思想观念的部分,服务于自己的文学与政治需要。伏尔泰的个性特征、艺术观念、哲学思想无疑受到了《赵氏孤儿》的启发和影响,但是在他的创作过程中,《赵氏孤儿》所内蕴和代表的异质性中国元素,已经完全异化和内化为《中国孤儿》的一部分了。
在启蒙时期的欧洲,以接受《赵氏孤儿》为基础而进行的改编,不可避免地对《赵氏孤儿》进行了“有选择”的误读,这首先是由于《赵氏孤儿》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更是由于改编主体在面对异质性文学样式时,异质性文化元素与自有文化因素发生了契合(而非一致),激发了主体的创作冲动。虽然改编者在改编过程中或多或少留有原剧《赵氏孤儿》的影子,但从性质上讲,这种改编已经完全变成了改编者的“创作”,而这种创作成果又明显地区别于改编者本国的其他文学,带有清晰的异质性文化色彩和异国形象。
五、“回归之旅”的对话:《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同台演出
1990年7月20日至22日,从中欧文学交流史看,是《赵氏孤儿》在欧洲最负盛名的“产儿”——伏尔泰《中国孤儿》的回归“省亲”之日。在天津召开的中法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之比较研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之邀,在会议开幕式上演出了《中国孤儿》。这是此剧在中国的首次公演。剧本由孟华、袁俊生翻译,由林兆华导演。戏剧内容本身没有多大改动,但在形式上却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给人以强烈的时空跨越与交叉感。林兆华利用中国传统老戏园的特殊建筑款式,《中国孤儿》在台下演出,在幕间的时候又让河北梆子的《赵氏孤儿》的一些片段在台上演出,“将中国与法国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戏剧既平行又交叉地同时展现在观众面前,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戏剧比较’演出”[11]。
与18世纪《赵氏孤儿》在法国的命运相比较,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不曾遭遇被“截肢”和“整容”,而是较为“真实”(完全的“真实”从来都是不可能的)地在故事的故乡的演出中展示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性格,因而是幸运的。而更幸运的则是,它与原汁原味的中国戏剧(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的地方化与现代化)“交叉”演出,在跨越时空的“比较”与“对话”之中,形成巨大的反差,同时又重构了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使得在不同的异质性文化下产生的两种文本(包括它的演出形式、思想特征和艺术价值取向)既排斥和对立,又“离间”和互补。
二者的同台演出这一文化交流事件的意义还在于,它使处于《赵氏孤儿》世界旅行路线“起点”的人们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唤醒他们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学的世界地位和历史价值,并从中发掘新的艺术灵感,塑造新的艺术生命。2003年,中国话剧舞台同时上演了两出《赵氏孤儿》,分别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国国家话剧院各自创作、分别排演,导演分别是林兆华和田沁鑫;2010年底,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也在全球上映。这些现象说明,不管异质性文化/文学交流与对话具有怎样的偶然性、随意性、不可复制性和天然的变异性,也不管接受主体出于接受需要可能会使异域文化/文学的原著产生怎样的“变形”,毕竟,正是由于异质性的存在,才使得交流双方得以从异质性中发现或重新发现对自己有所补益的“互补性”元素,不断为本民族和处于相对“他者”地位的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融入新鲜的异质性文化血液。
爱德华·赛义德这样描述“理论旅行”:“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个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知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12]从对《赵氏孤儿》的世界旅行路线图来看,在文学/文化交流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与“理论旅行”相对应的“本文旅行”:这个“旅行”的起点和终点都不只是求同。在“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个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的过程中,由于对异质性的发现和吸纳,原文本发生了变形,原来属于源语言环境的文学变异为目的语环境的文学。元杂剧《赵氏孤儿》影响了欧洲的文学,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赵氏孤儿》与诸多“变异”的“华裔”们在互相观照中,彼此发现了民族文学的另一种世界含义。
[1]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
[2]贾植芳.范译《中国孤儿》序[A].《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法]勒内·波莫.《赵氏孤儿》的演变——伏尔泰与中国模式[J].国外文学,1991,(2):6—16.
[4]钱林森.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法文学的首次交融[J].文艺研究,1988,(2):117—129.
[5]王立新.《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两种思想与艺术的对话[J].国外文学,1991,(2):44—56.
[6]吴戈.《赵氏孤儿》的文化改写:古代/当代/中国/外国[J].戏剧艺术,2004,(3):12—24.
[7]杨健平.从《赵氏孤儿》在欧洲看艺术接受中的民族变异[J].文学评论,2002,(2):14—20.
[8]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6,(1):116—126.
[9]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24.
[10]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55.
[11]夏康达.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天津人艺的演出[J].中国戏剧,1990,(10):20—21.
[12][美]爱德华·赛义德.理论旅行[M].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