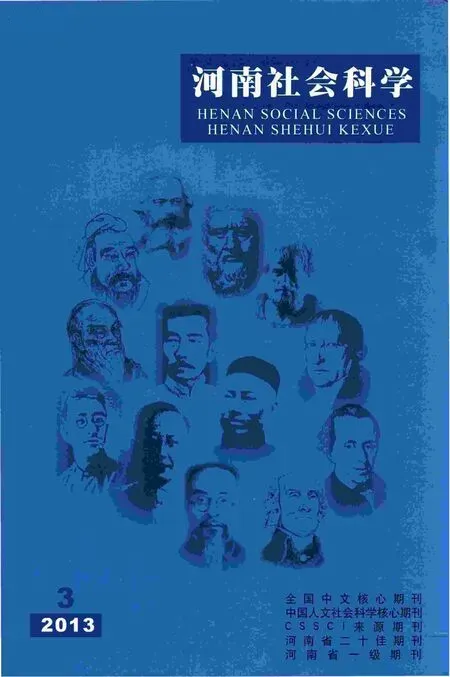拯救巴门尼德的“现象”——论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应
钱圆媛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
在《论天》298b10-25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一方面巴门尼德的学说取消了自然和运动,认定我们对生灭的确信都是假象;另一方面,他们首先发现唯关乎不动不生灭者才能有知识。对于前者,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191a20-25中表明他要解决巴门尼德学说带来的自然研究中的困难;对于后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巴门尼德学说中的不动者属于第一哲学的研究范围。
这表明,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的回应有两个方向,一是解决巴门尼德学说对自然和运动的挑战,二是把巴门尼德的“存在”带回第一哲学来讨论。这两个方向上的回应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亚里士多德要求“拯救现象”和穷尽存在之意义的努力,他试图为存在赋予一个统一的形而上的意义体系。其中,第一个方向上的回应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并集中体现在《物理学》、《论天》、《论生成和毁灭》等自然学著作的相关内容中;而第二个方向上的回应则贯穿于亚里士多德存在学研究的核心,涉及《形而上学》等著作中对存在的结构、本是(substance)、不动的动者等问题。
二
不少研究者已注意到,亚里士多德针对巴门尼德问题的言论,不仅涉及自然和运动领域,还包含着对第一本原和本是的探讨。这一点可以说是被公认的。然而,笔者仍惊讶于,这些相关的研究并没有沿着这一公认的分野及其相互关系对亚里士多德的巴门尼德回应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Guthrie一方面指出,巴门尼德将存在和思维视为同一的,他的唯一实在的“一”预见了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纯思的“神”。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巴门尼德之所以在长诗的第二部分论述“凡人的信念”,这是将之前被视为虚假的现象世界引入系统性和一致性的尝试。但Guthrie认为这一尝试只意味着对自然学的拯救,因此他在专门探讨亚里士多德哲学时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其如何说明运动和拯救自然现象,但对于他之前提出的“神”与巴门尼德的“一”的关系这一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解释和回答[1]。
Coxon的看法是,比起《物理学》中的批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谜团般的章节里更为同情和肯定巴门尼德,承认“是否‘存在’和‘一’是本是,这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同时认为巴门尼德的“一”是对形式的哲学洞见[2]。但遗憾的是,Coxon尽管敏锐地指出了下述事实,却未对此追问下去:“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接受了巴门尼德的‘一切事物在恒是(essence)上都是一’并将之视为他的哲学洞见,但这一观点正是在《物理学》中被亚里士多德斥为‘违背经验’而加以批判的错误观点。”
Thanassas在研究中暗示,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巴门尼德问题时抱着对最高实在和现象之关系问题的关注,“当亚里士多德将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述阐释为‘被迫服从于现象’的时候,存在的真实和世界现象的关系仍是尚未被追问的”[3]。但随即他就转入了对柏拉图和巴门尼德的关系探讨,而放过了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考察。
Curd也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回应的不同路向:一方面,她明确认为巴门尼德的论证及其关于知识、存在和运动的观点,既是对晚期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大理论挑战[4]。另一方面她又指出,巴门尼德对“是什么”的探讨相关于亚里士多德的“ousia”(本是)和“to ti en einai”(恒是),这一联系也贯穿在根源于巴门尼德思想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5]。但Curd并未把这一点发展为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问题的积极回应,而是认为继承了巴门尼德学说遗产的是柏拉图而非亚里士多德:随着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哲学家开始考虑别的问题,爱利亚学派的影响消退了。
对此,Halper认为,“存在如何既是一又是多”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源自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独特研究进路[6];同时比起柏拉图学派的办法,亚里士多德通过阐明事物是“一”和别的东西的复合来避免巴门尼德“一切都是一”的结论,从而形式和复合物是在不同意义上的“一”[7]。
Cherniss则颇多批判,他首先指责亚里士多德强行将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运用到自然运动领域:一方面,为了在前人的哲学中为其原因理论找到必然根据,亚里士多德将巴门尼德不合理地阐释为一个质料主义者,将其长诗中的白天和黑夜解释为质料性的火和土。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将巴门尼德的“存在”强作自然范围内的解释,然后又声称这一“存在”只是“一”而不能完成此任务,并由此拒斥了巴门尼德的“存在”[8]。在笔者看来,关于亚里士多德是否误读了巴门尼德的“火”和“土”,这仍是有争议的。但无疑巴门尼德有必要在长诗中说明运动和自然,这不仅体现在长诗开篇的女神告诫中,亚里士多德显然也认同这一必要性:在986b18,他同情地指出巴门尼德被迫跟从现象而承认感觉的多。因此,就算亚里士多德将巴门尼德的自然本原视为质料因的萌芽,也不能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将巴门尼德视为质料主义者,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地方认为巴门尼德的学说属于存在研究(如192a35,298b17,318a2-6,986b18,1089a3)。就第二方面来说,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的一元论兼有批判和认同,而非彻底拒绝,亚里士多德的永恒、完满的“神”显然有巴门尼德不动的“一”的影子。Cherniss也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论述的相异尤其体现在自然现象和形式领域上,认为亚里士多德并不满意于仅仅将巴门尼德的存在视为形式,而是认定巴门尼德不得不将“一”重又设立为“感觉的多”的领域中的两个本原,即热和冷,这就是质料因和效力因的萌芽[8]。笔者认为,实际上Cherniss在此虽已触及了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的不同阐释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仍没有将这一问题置入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学说体系中去探讨,也没能追问这一问题对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另外,Cherniss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评论对我们研究的误导还在于,它使我们无法看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和“多”的关系为主线的[8]。但实际上,“一”和“多”的关系问题恰恰是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地方都关注的问题,也体现在他对巴门尼德的自然学说和存在论证之间关系的讨论中。
Palmer则看到了Cherniss过于指责亚里士多德不顾历史原貌“改写”古代哲学史的倾向并试图挖掘其在巴门尼德问题上的见解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同样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论天》中都强调巴门尼德的存在更属于第一哲学而非自然研究。他还提醒我们,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的理解要受其哲学发展和体系框架的影响[9]。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说明,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的回应贯穿着他的哲学体系的发展并渗透到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对巴门尼德学说长久的深思熟虑的体现;而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展及其最终面貌与他的巴门尼德回应有关联,他与巴门尼德的思想对话本身就构成了其哲学的一部分。在知识问题上,Palmer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从巴门尼德那里认识到,真知识要求其对象是不动的实在或具有不动的性质(298b14-24),巴门尼德首次指出了不动者与变化者在认识论上是不同的。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和自然学说的关系上,认为“真”和“意见”是对同一对象在理智和现象方面的不同论述[9]。只是Palmer并不倾向于认同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存在论证的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巴门尼德并不是在探讨“世界”的不同模态或几种平行的“可能世界”,而是陷入了现象和最高实在相分离的困境——不仅现象成了不可知的,而且我们也达不到关于最高的“一”的知识。
三
就笔者所识而言,虽然上述观点中都不乏对亚里士多德回应巴门尼德学说的洞见,但限于各自的研究主题和角度,这些洞见还不足以构成对“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难题的回应”这一问题的清晰全面的回答,而这一回答显然对理解亚里士多德和巴门尼德意义重大。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的回应,在精神实质上是一种试图重新将自然现象和最高实在联结在一起,从而为存在赋予一个统一意义的形而上的努力,这也是其试图追问和穷尽存在的任务体现。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巴门尼德回应不仅包括对巴门尼德学说直接或间接的提及、分析、批驳或认同,还包括他在自己的哲学中对巴门尼德部分学说的运用和发展,以及应对巴门尼德困难的出路。
可以说,这一回应带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典型风格:
第一,亚里士多德并不注重重现巴门尼德问题的历史,而总是以自己的目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式来理解和重组历史上的巴门尼德的论题;他也注意考察后巴门尼德的自然学家,以及柏拉图对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应,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并最终给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回应不限于历史上的巴门尼德本人,而且还包括就巴门尼德问题本身及其影响的回应。
第二,这一回应从属于其“拯救现象”的哲学任务:回应巴门尼德既是统一运动现象和最高实在的努力,也是对巴门尼德学说的“现象拯救”。因为,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现象”不仅包括可观察的经验事实,还包括常识信念和贤哲的重要观点(100b21-9)。这些现象是研究的起点和来源,因为其包含着部分真知灼见。这些现象也包含在研究的终点里:研究的最终成果将能够对这些现象提供更清楚明白的解释。
第三,这一回应也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来源:
巴门尼德在其《论自然》中的论证引发了著名的存在难题:(存在)存在着,(存在)不可能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可能存在(F6,F7[1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一论证的推论有二,一是得出自然不存在,运动不可知;二是得出存在是一。
这是一个兼具颠覆性和洞见性的论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既依靠感觉,又通过与此相调谐的逻各斯去知道这个世界——存在既统一又非单一,运动既非完满亦非虚无。回应巴门尼德的难题亟待说明,永恒的“一”和不动者也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可感事物的本性中。我们不仅要借助可感事物而且需不可感者来解释现象世界。关于形式如何与可感世界相联结这一难题,柏拉图于其《巴门尼德篇》中的艰难尝试不能令人满意,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学说就是在继承应对这一爱利亚疑难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11]。
同时,解释现象的不动者是事物的第一因,因而是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最高智慧和最幸福的生活内容。因此回应巴门尼德的问题不仅是对巴门尼德学说中的洞见的拯救和对自然现象的拯救,它的更多的意义还存在于《形而上学》B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中,诸如:“存在不可感的本是吗?”“生灭事物和不变的事物的本原是否是一样?”“一和存在是本是还是属性?”等等。
四
笔者认为,要全面掌握亚里士多德就巴门尼德问题的诸多回应,需要我们重视该回应在自然著作和《形而上学》这两个方向上的显著差异——巴门尼德的存在问题“偶然”引起了自然和运动的困难,同时“存在”本身是第一哲学的内容。这意味着,该回应至少要包括两方面任务:一方面,要通过为自然和运动重新找回其知识上和实在上的合法性来回应巴门尼德对运动和自然的拒斥;另一方面,要探讨最高实在是否存在,它的性质以及它如何统一运动现象,最高知识如何统一自然知识以及如何获取它们,以此来克服巴门尼德存在论证造成的“现象”与实在分离的困难。其中,第一方面要求驳斥巴门尼德难题对自然学基础的倾覆,并为建构一个不受其学说消极影响的自然哲学奠基。第二方面则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巴门尼德学说的困难,也意味着对巴门尼德存在学说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将巴门尼德的“形式”一元论批判性地发展为“多种意义”的、以形式为核心的存在学说;不动的“一”被创造性地发展为“不动的动者”以作为运动之终极来源、宇宙秩序的根源和可理解性的最高依据。同时,这两个方向的回应虽有不同,但并非截然分立、毫不相关。为回应自然学的挑战,亚里士多德运用了许多形而上学的原理,如存在的多义性、四因说、不动的动者概念来为自然哲学奠基;而在第一哲学上的回应中,他常常运用自然哲学的研究以为佐证,如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中直接基于《物理学》里对不动动者的研究成果来探讨第一动者的数目。因此,这两种回应虽各有其不同立场和目的,但仍在许多形而上学概念和研究内容上相互交叉并体现出亚里士多德典型的哲学思想特点。
显然,理解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对巴门尼德的回应,有助于推进对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解和阐释:
《论自然》是巴门尼德唯一的哲学著作,有3000余行,现仅存残篇150余行[2],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残篇以及古人的相关注释评价来拼接巴门尼德的思想地图。而最令现当代学者棘手的巴门尼德阐释难题是长诗中存在学说和自然学说的关系:为什么他在真理之路中判定了自然现象的虚假之后,还要在长诗后半部分花巨大篇幅去发展一种关于自然和宇宙现象的学说呢?对此,无论是对巴门尼德的严格一元论阐释,还是逻辑辩证法阐释,抑或形而上学本原论阐释,乃至模态阐释都面临着困难。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阐释则提供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即认为巴门尼德的自然和存在是不同的“体”(aspects),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巴门尼德的问题更属于第一哲学,他只是被迫承认了现象的“多”(986b18)。再者如Simplicius、Theophrastus[2]等都认为巴门尼德的两条路是对现象层面和形而上层面的不同实在的划分。这意味着,或许巴门尼德长诗中两条路的冲突恰恰是他挣扎于既希图说明绝对可知的真实,却又无法忽视去说明运动现象的反映。正是由于其缺乏对存在的多义性及其中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亚里士多德才说巴门尼德在研究存在和本原的一开始便误入了歧途。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回应既是其哲学的一部分,也是理解其哲学思想发展和最终面貌的线索。巴门尼德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深刻影响和激发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重要挑战和论题。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关于最高实在的问题上,“存在”的基本含义对于二人来说都是一致的,即永恒不动、完满单一和思之所向。只是亚里士多德批判地赋予了存在概念以新的含义,这种新含义取消了运动和不动、可感和可知之间的对立:目的因完成了柏拉图等的解释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同时可感事物为了追求神那样的永恒持存而运动,仿效和表现着持存的存在而存在着,即表现为生成、活动、非存在。神被所有的存在者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表现和效仿,它们各尽所能地追求各自能得到的持存和永恒,并根据追求到的永恒的不同程度而又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时,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有必要为自然现象给出理由,只是亚里士多德更好地统一了自然现象和最高实在。最后,笔者倾向于认为,由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内部存在一些困难,如“知识研究普遍,而认识对象却是个别的”这一两难,他的回应并不能令人满意。然而他的回应仍有尚待挖掘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和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运动学说及其第一哲学相关理论的反观镜:一方面,这有助于理解《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巴门尼德回应同时涉及了《物理学》和更高的第一哲学:在什么意义上,两者是可以截然划分的?是否《物理学》中的相关探讨单属第二哲学,而《形而上学》中的回应就是第一哲学的?显然,《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都涉及了对四因、潜能实现以及不动动者,这些论题到底是属于第一哲学的研究还是第二哲学?另外,应当怎样看待这些探讨中的不同和一致之处,这是否暗示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还是亚里士多德基于不同视角和目的作出的不同回答?另一方面,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回应将有助于理解《形而上学》中“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qua being)的研究、潜能/实现研究以及“不动动者”的关系问题——首先,亚里士多德承认巴门尼德的“一”触及了不动不生灭者,因此对巴门尼德的回应当属于神学的范围;同时,亚里士多德在191a35-b30中指出,巴门尼德的困难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区分存在的范畴意义及其关系,二是诉诸潜能实现概念。前者涉及《形而上学》核心卷中对being qua being的静态研究,而后者涉及亚里士多德对存在的动态研究。因此,笔者相信,探讨亚里士多德如何在这三个方面回应和解决巴门尼德的困难,将使我们对整个形而上学,或者说第一哲学的统一问题有新的理解。
[1]Guthrie,W.K.C.A History ofGreek Philosoph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Coxon,A.H.The Fragments of Parmenides:A Critical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the Ancient Testimonia and a Commentary[M].Las Vegas:Parmenides Publishing,2009.
[3]Thanassas,P.Parmenides,Cosmos,andBeing:A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M].Wisconsin: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2008.
[4]Curd,P.K.A PresocraticsReader[M].Indiana:Hackett Publishing Co.,2011.
[5]Curd,P.K.The Legacy of Parmenides:Eleatic Monism and Latter Presocratic Thought[M].Las Vegas:Parmenides Publishing,2004.
[6]Halper,E.C.One and Many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Books Alpha-Delta[M].Las Vegas:Parmenides Publishing,2008.
[7]Halper,E.C.One and Many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The Central Books[M].Las Vegas:Parmenides Publishing,2005.
[8]Cherniss,H.F.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resocratic Philosophy[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Press,1935.
[9]Palmer,J.Parmenides and Presocratic Philosoph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0]Graham,D.W.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The Complete Fragments and Selected Testimonies of the Major Presocr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Owens,J.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M].Toronto: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Pub.,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