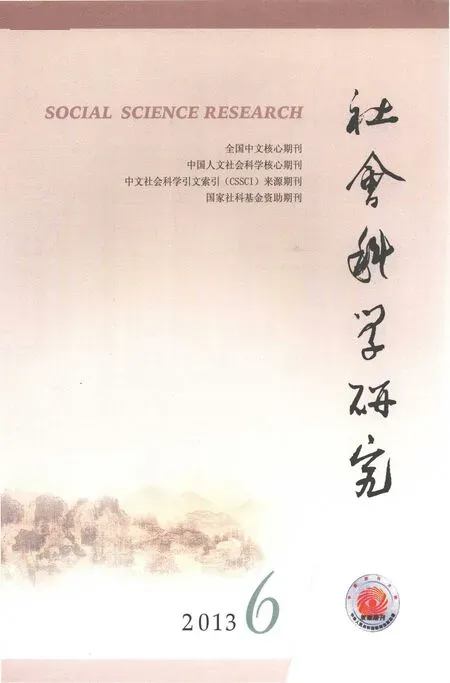《所罗门之歌》和《接骨师之女》的记忆书写比较
蒋欣欣
《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是美国当代非裔作家的杰出代表、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的获奖力作,该书通过追溯家族历史以重新认识自我。而《接骨师之女》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则是华裔文学的中坚力量、继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之后得到学界认可的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代表作品,叙述过去经历以解决自我认同危机。虽然这两部小说都经记忆重述过去、重构历史,但是,在叙述记忆的体裁、存储记忆的媒介、传播记忆的载体等方面却表现出深层的、根本的差异。由此,对不同族裔文学作品的记忆研究可从导致差异的社会框架 (哈布瓦赫语)出发,阐释文学作品重述过去的价值取向,挖掘其重构历史的文化诉求。进而,文学作品,作为存储和传播记忆的媒介,一方面具有建构记忆和增补信息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又保存着对记忆的过程和问题的批判性反思。〔1〕
一、叙述记忆的体裁
《所罗门之歌》(以下简称《所》)和《接骨师之女》(以下简称《接》)都涉及在记忆中追溯家族的历史,特别是对先辈姓名的找寻构成这一回忆的主要线索。前者基本采用男性成长小说的体裁,后者主要运用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形式。这一叙述记忆体裁的差异体现出美国非裔和华裔文学传统的不同源头:《所》在成长小说的基础上增添黑人奴隶叙述的色彩,将欧洲文学传统与美国黑人文学传统有机融合;《接》以女性的自传体叙述为主,把华女文学①“华女文学传统”主要是指在华裔女作家中以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和汤亭亭的《女勇士》为代表的自传体书写。这些作品都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最初是为了改变白人主流世界对华裔女性的认识,逐渐演变为女性主体意识和自我观念的张扬。强调个人色彩和真实感受的传统发扬光大。
《所》被评论界一致视为黑人男性的成长小说。它主要描述主人公“奶人” (Milkman)从寻找祖父遗留下来的“金子”开始,最终破译蕴含家族历史的民间歌谣,寻回与非洲祖先相联的名字,从而实现自我身份、族裔认同的建构。在“奶人”的成长过程中,家族姓氏是贯穿其中的关键线索。他的家族,据父亲回忆,因登记户籍的白人官员一时疏忽,被冠以“戴德”(the Dead)的姓氏。于是,受姓氏的影响,整个家庭笼罩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奶人”感受不到任何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心和朋友的情谊。这一姓氏的来由描述出黑人奴隶及其后裔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进一步揭示丧失象征自我身份、连接非洲传统的姓名为其带来的心理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家族的姓氏还引出祖父被白人无辜杀害的惨痛回忆。小说中的人物采用奴隶叙述的形式来回忆父辈的这段往事,以此展现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对黑人造成的心理扭曲和文化创伤。不同的是,莫里森从原奴隶叙述的自传体表述模式中超脱出来,将黑人奴隶的个人悲剧与整个族裔的苦难历程相结合,从而撕破“历史真相”的虚假面纱以恢复族裔被抹杀、被掩埋的过去。“奶人”的父亲在回想其父被白人枪杀、与妹妹分道扬镳的经历时,不仅直指导致戴德家族心理扭曲的原初事件,而且揭露美国南部重建时期曾被主流历史话语弱化的种族暴力。这些尘封的记忆不是由叙述者独自讲述,而是受“奶人”与父亲不和的现实矛盾激发,在家庭成员的对话互动中层层揭开。正如莫伯莉 (Marilyn Sanders Mobley)所说,“经典黑奴故事把记忆当成提供事实与时间的独白式的、机械的媒介,莫里森的文本则凸显记忆的对话特质以及建构和重建过去意义的想像力”〔2〕。由此可见,莫里森改写奴隶叙述、凸显沟通记忆的目的在于,以个人的记忆书写质疑主流历史叙述的公共话语,并呼吁黑人族裔“取之于过去,用之于未来”,“在两者之间择其善者而从之”〔3〕。《所》中的记忆书写在体裁上融合了黑人个体的成长小说与黑人族裔的奴隶叙述,还在历史和现实中沟通着黑人个体与群体、族裔过去与未来,为个体认识自我、族裔凝聚认同提供回忆的养料。正是由于文学 (符号系统)本身的创造性和构造力,其中即便是个人的、私密的记忆也有助于人们形成对过去的认识和想像,并渗透到经验层面积淀成为社会心理的基础和文化范式的来源。①此处论及的是文学作为记忆的文化框架所发挥的作用,即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范式的来源和社会心理的基础。阅读文学作品能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和想像过去,并左右他们在现实中的生活体验和感知。
《接》以华裔女性的自传体叙述为主。它围绕一对华裔母女的隔阂和矛盾展开,其中穿插着母亲对其一生的自传体回忆。年迈的母亲虽然患有健忘症,在现实生活中时常丢三落四,但是过去的一切却记忆犹新,唯独想不起自己及其母亲宝姨的姓氏。为防止遗忘,母亲把她珍藏的记忆用中文写成文稿,留给生长于美国、几乎不识汉字的女儿。小说的第二部分就是母亲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的亲身经历,从中可见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女性追求真爱、实现自我的艰难斗争。这种自传体记忆以时间的线性发展为主轴,在行为的空间转换中推进,并与自我概念的形成、自我认知的取向相关联。在认知心理学中,自我概念和自传体记忆是自我知识的两个组成部分,前者代表“当前的自我”,后者体现“过去的自我信息”。自我概念的形成和维持以自传体知识为基础,同时自我概念又对自传体记忆起着选择和激活的作用。〔4〕母亲的自我概念与一个记不起来的“姓氏”紧密关联,“它藏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一层”〔5〕。可是,母亲把这一“宝贝”藏得太久,竟然遗忘它的存在。她不断地回忆“那个姓是——”,“我们到底姓什么”,试图激活与之相关的记忆。后来,母亲不得不以撰写回忆录来讲述自身的过去故事,整理凌乱的记忆痕迹,以便赋予回忆语言的形式和形象的意义。每一故事的选择和每一痕迹的激活,都是母亲对她经历的重新阐释,也是她自我概念的重新建构。于是,在参观博物馆时,母亲无意间说出“宝姨”的名字,女儿最后也发现,家族的“姓氏始终都在身边”,“在心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6〕。在找寻家族姓氏的记忆中,华人女性以自传体的叙述形式表现她们在旧中国和新世界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一可信的自传体记忆和虚构的文学作品的成功结合将强而有力地修正美国主流历史话语对她们的扭曲,改变男性主导社会对她们的无视。华裔女作家,无论黄玉雪、汤亭亭,还是谭恩美,都敏锐地意识到女性自传体记忆的意识形态价值,并将之发展成华裔女性文学的写作传统之一。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所》,还是《接》,小说中的人物都在现实矛盾的激化下,被迫以家族姓氏为线索展开回忆,重新梳理家族历史,力图寻找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然而,受美国非裔和华裔文学传统的影响,莫里森和谭恩美分别采用不同的书写体裁反映她们对记忆的独特关注:《所》重视记忆的沟通维度,以共同参与回忆的方式推动个体的成长、重述过去的传统;《接》强调记忆的自传色彩,在女性长辈的回忆中认识自我、重构历史。族裔作家正是通过回忆重述过去、重构历史的努力,将个体的、差异的记忆转换成公共记忆,从而质疑主流历史话语的暴力行径。
二、存储记忆的媒介
从某种意义来说,《所》和《接》都涉及家庭中的个体记忆。因为家庭不仅是个体记忆形成的重要环境,而且是个体记忆汇入社会记忆之前的演练场所。然而,存储个体记忆的媒介在《所》和《接》中却是不同的。前者中保存家庭记忆的主要媒介是贯穿小说始末的歌谣,后者中记录个人记忆的重要载体是被置于小说中部的故事。
家庭记忆和个人记忆是个体记忆的两个组成方面,都是私人领域中最为基本的记忆模式。家庭记忆呈纵向性,个人记忆则呈横向性。家庭记忆依赖于家族成员的代代相传,由祖辈和后代构成承继记忆的纵轴。源自祖辈的是族群性记忆,给予后代的是承继性记忆。在个人记忆的横轴上,私密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公共性记忆是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其内容包括存在于个人大脑中的想法和与日常生活状态相关的信息,也包括个体在公共领域中具有的群体性记忆。〔7〕因此,任何个体记忆势必超出纯粹私人的领域,进入一个赋予其意义的社会语境。
作为保存家庭记忆的主要媒介,歌谣在《所》中具有反复性、重构性的特点。整部小说中,歌谣“啊!甜大哥飞去了”是存储“奶人”祖辈历史的族群性记忆,也是赋予后代生存意义的承继性记忆,在家庭成员中代代传唱,总共出现过五次。前两次的歌者是“奶人”的姑姑、黑人文化的传承者彼拉多 (Pilate),所唱歌谣的形式属同一小节的反复吟唱,内容与黑人祖先飞回非洲的传说有关。歌谣第三次被唱响时,彼拉多祖孙三代正在摘黑莓,准备私自酿酒以维持生计。歌唱形式以彼拉多领唱为主,女儿和孙女的和声为辅,最后融为和谐的合唱。歌唱内容也增加了“甜大哥飞去”的后果,即“棉球儿让我窒息”、“白人的臂膀给我套上轭具”〔8〕。从歌唱形式的特征来看,作家莫里森自觉地把黑人布道所用的呼应传统运用于共同的对话回忆中;从歌词内容的变化来看,她更是有意激发黑人备受奴役、剥削的创伤记忆。后来,“奶人”在走访南部探寻家族史时,碰巧看见孩子们在玩游戏,发现他们所唱的“所罗门别把我留在这里”跟彼拉多的老歌歌词不一样。此刻,他才记下完整的歌词,并将其提供的线索与自己的家族历史联系起来,最终重构存储着家庭记忆的歌谣。“所罗门之歌”最后是在彼拉多临死前由“奶人”所唱,这暗示着他经彼拉多的指引自觉承担起传递家庭记忆的历史责任,从而成长为真正的黑人之子。于是,黑人祖辈的族群性记忆借助重构家族歌谣的方式得以保存,黑人后代的心理创伤通过承继家庭记忆的方法得到治愈。《所》中的歌谣在长辈与后辈之间纵向传承,其形式由呼到应的反复、内容由片断到完整的重构都突显组织和加工家庭记忆所必需的参与和沟通。
作为记录个人记忆的重要载体,《接》中第二部分的故事具有连续性、规范性的特点。母亲讲述的是她的母亲宝姨及其自身的故事,属于个人记忆中的私密性记忆。母女两代人的经历被叙述时独立成篇,一气呵成,这体现出叙述时间的连贯性和叙述内容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母亲记录个人记忆的用意,在于诠释过去、塑造当下,传达观念、规范行为。此处的记忆叙述明显地具有中国式说教的功能,即由长辈向晚辈灌输家庭的日常规范和社会的道德习俗。通过回忆母女之间关系的转折点——不顾宝姨的反对坚持嫁给仇敌的儿子,母亲找出无法摆脱厄运的根本原因。“我记起了她们家族的毒咒,那也是我的家族,都是因为那些龙骨没有放回葬身之处。”〔9〕正因为毒咒的纠缠,哪怕母亲已经远渡重洋,来到“没有鬼魂也没有毒咒的大陆”〔10〕,她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避免女儿重蹈覆辙,母亲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不时提及宝姨的鬼魂和家族的“毒咒”,以此传达祖上的警示,告诫女儿不要犯下她们当年的错误。生长于美国的女儿自然不理解母亲的“宇宙观”,但是潜移默化地仍受它们影响,并养成被动、妥协、认命的性格,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倍感压力和挫败。出于对女儿的爱护,母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告诉她,摆脱厄运和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痛苦,只记住曾经得到的爱。最终,在故事营造的跨越时空的回忆中,外婆、母亲和女儿合而为一。由此,故事是“在延伸的场境中的言语行为。它们使说话者和听众超越时空的限制连接起来”〔11〕,并传播着作家谭恩美对过去的深刻认识,即“过去无非是那些我们选择记住的事情”〔12〕。通过讲述“选择记住”的“过去”,华裔母女不仅传递着个人想法和私密信息,而且延续着公共的观念和规范。
《所》和《接》中人物的个体记忆都与家庭关系密切,但前者侧重家庭记忆,后者偏重个人记忆。而且,保存个体记忆的媒介也有所不同:《所》以歌谣的呼应吟唱和整合重构体现非裔家庭记忆的对话性质和沟通功能;《接》经故事的连贯讲述和行为规范展示个人记忆的传达作用和当下效应。这里,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非群体或机构,但是个体只有植根于群体的特定语境中才能记忆或再现过去。〔13〕也就是说,对家庭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书写和阐释都需在记忆的社会框架①根据哈布瓦赫的看法,“记忆有赖于社会语境”。他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主要探讨家庭、宗教和社会阶级及其传统等因素对记忆的影响。本文中的“记忆的社会框架”偏重于社会的文化语境,尤其涉及赋予记忆形式的文学体裁、口述媒介和文化载体。下展开,这将有助于揭示支配记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运作,也有利于从重塑过去、传承历史的实践反观记忆的功能。
三、传播记忆的载体
在《所》和《接》中,无论是贯穿始末的家庭记忆,还是独立成篇的个人记忆(《接》中的其他两部分大多为家庭记忆),都包含着家庭成员对往事的追忆。他们不断交流着对某一关键性事件的印象和看法,重新加工零散的记忆信息和偶然的回想行为,进而在共同的对话回忆实践中合成具有整合功能的文化记忆和集体历史。其中,维系对话回忆实践的纽带,也就是家庭成员传递记忆的载体,都与“骨”相关,前者由一副死者的尸骨连接着女儿与父亲的沟通记忆,后者以家传的“龙骨”为线索承载着女儿与母亲的对话回忆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作为记忆的不同形式和实践,家庭记忆和文化记忆相互依存,既相似,又相异。根据扬·阿斯曼 (Jan Assmann)的界定,家庭记忆属于沟通记忆的范畴。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都在现实的推动下有意地与过去打交道,并赋予过去具体的形式和当下的意义。沟通记忆存在于个体和群体回忆过去事物的互动实践中,类似于社会的短期记忆,持续时间大约八十年即三四代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下,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14〕。比较之下,沟通记忆贴近日常生活,文化记忆高于日常生活,依赖于有组织的和仪式化的沟通交往使其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所》中的“骨”是已故父亲的尸骨,连接着父辈与后代的沟通记忆。彼拉多本以为,家里挂着的一袋尸骨是父亲被杀后哥哥在山洞里杀死的白人的。受父亲幽灵的指引,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背着这副尸骨,以担负起剥夺生命后应负的责任。整部小说中,父亲的幽灵时常现身与彼拉多进行心灵沟通,时刻提醒她“不能丢下一具尸体就飞走”〔15〕。于是,尸骨不断打破时空界限将记忆叙述带往原初事件的案发现场,还不时唤起相关人物共同回忆祖父/父亲被害的血腥场景。然而,在破译家族历史后,彼拉多才幡然醒悟,自己背负的正是父亲的尸骨,还有不该遗忘的过去。可见,尸骨承载的信息有关逝去的生命,还有随之消失而被淡忘的记忆。正如“奶人”在小说结尾处所感悟的,“在这个国家有多少死去的生命和被逐渐忘却的记忆是埋藏在这些地方的名字下面呢”〔16〕。被夺走的生命和被忘却的记忆都与富有涵义的名字相连,名字既是个体自我身份、人格尊严的表征,更是沟通非裔美国人与非洲祖先的桥梁。“当你死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失去了名字,你怎样和你的祖辈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伤疤。”〔17〕因此,父亲的幽灵只有在找回家族的姓氏之后才能治愈历史创伤,他的尸骨也只有被埋于祖父所罗门纵身飞回非洲的高地之时方能入土为安。至此,尸骨完成连接祖辈与后辈、非洲旧大陆与美洲新世界的使命,由其传递的记忆也将祖辈过去的经历现实化,在后辈个体的身上发挥出医治心理创伤、解决认同危机的疗效。 “骨”在《所》中穿梭于各式人物的记忆叙述,促使黑人后代就父辈的过去进行沟通与互动,进而共同编织传承族裔历史的纽带。就此功能而言,“骨”参与黑人集体记忆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又反思遗忘过去的后果、批判割裂传统的恶习。
《接》中的“骨”是北京周口店猴嘴山山洞里的“龙骨”,既传递着母女共同的对话回忆,又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母亲借回忆的文稿告诉女儿,中文里的“骨”字表示骨头,可代表“性格”的意思,也与她家的祖传行当接骨相关。透过“骨”的含义,母亲为女儿讲述祖辈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骨”就是过去的载体。母亲的手头正好有一块由宝姨传下来的“龙骨”,据说它有着医治百病的神力。由于“骨”的功效,母女在回忆“骨”的对话中逐渐消除引起 (女儿)失声的隔阂、治愈造成 (母亲)遗忘的创伤。此外,宝姨还告诉母亲,那块“龙骨”上面的甲骨文是古人求教神谕时所刻的问题。这又进一步揭示刻有甲骨文的“龙骨”是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文物,由它传递的不仅包含“值得纪念的内容”,而且涉及中国传统的占卜仪式。〔18〕可是,小说的情节随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宝姨的父亲托梦给她,并告知她手里的骨头并非龙骨,而是他们祖先的骨头。而且,由于他们偷了先人的骨头,全家人都被诅咒,将会死于非命。家传的“龙骨”由甲骨变为先人的尸骨,这说明“骨”传达的记忆信息从公共的文化记忆缩减为父女之间的对话记忆。先人的尸骨一再地被母亲和宝姨的鬼魂提及,就好像彼拉多父亲的幽灵告诫她的一样,尸骨一定要被放回葬身之处,否则难逃诅咒和厄运。更为有趣的是,作家谭恩美又将先人的尸骨与“北京人”的头盖骨拼贴在一起,这就把读者的回忆引入历史联想空间,并根据相关的文化记忆重构抗战时期中国考古学家们为保卫历史文物所做的牺牲。在一个较之真实报道和历史编纂相对无约束力和免除责任的文学虚构领域中,“骨”传承的是谭恩美所尝试的对过去进行的表述、甚至改写。其内涵从其本意延伸到死者的尸骨,拓展为蕴含丰富文化价值和历史信息的文物,而且在与之相连的母女的对话回忆和民族整体的文化记忆之间游移不定。或许,这种微妙的处理正好彰显了谭恩美书写记忆的拼贴策略和杂糅实践,同时也揭示出她移植母国文化以协调现实冲突、凝聚华裔认同的美好愿望。在这种意义上,谭恩美笔下的“骨”更可理解为一种集体的建构方式和对过去、现在的表达工具,其功能更多的是生产和传播集体当下的共识和认同。
作为记忆载体的“骨”,在《所》和《接》中都与父亲的魂魄一起共同维系着祖辈与后辈之间的关联,既涉及连接家庭成员的沟通记忆,又包括聚拢族裔移民与母国大陆的文化记忆,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实践此消彼长。而对“骨”内涵的相异理解,则说明莫里森重写过去、批判现实的价值取向,谭恩美重构过去、形塑现实的文化吁求。前者突出的是记忆的反思潜力,后者强调的是记忆的形成潜力。〔19〕记忆,正如马提尔·斯德肯 (Martia Sturken)所说,总与“复杂的政治要求和意义捆绑在一起”,“通过不同的故事在历史中谋求一席之地而进行文化协调”〔20〕。
米兰·昆德拉 (M.Kundera)曾在《笑忘录》中指出,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丧失时。毋庸置疑,记忆已被置于关乎民族存亡的高度,既是个体“小我”感知过去的主要方式,也是其所属的“大我”群体诠释历史的重要凭证。尤其是当下文化价值观念转型的特定语境中,美国少数族裔的“历史”历经后现代话语的解构、民权运动的洗礼、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鼓舞之后,犹如冲破海口的百川在记忆的河床中奔流不息。于是,记忆便成为各族裔作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和竞相叙述的对象,展示出特定族裔群体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在着眼当下、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族裔作家,如莫里森和谭恩美,以其被遗忘、被忽视的记忆书写为族裔群体营造公开沟通的场合、治愈创伤的诊所,从而尝试着以族裔个体的、母国文化的记忆抵制同质的、主流的历史话语的实践。
〔1〕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7.
〔2〕Marilyn Sanders Mobley.A Different Remembering:Memory,History and Meaning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Toni Morrison: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Ed.Henry Louis Jr.Gates and K.A.Appiah.New York:Amistad,1993,p.358.
〔3〕查尔斯·鲁亚斯.美国作家访谈录〔M〕.粟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20.
〔4〕Q.Wang.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Knowledge.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5.4(2006):182-187.
〔5〕〔6〕〔9〕〔10〕〔12〕〔18〕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张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88,175,239,290,137.
〔7〕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74.
〔8〕〔15〕〔16〕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舒逊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56,242,380.
〔11〕〔14〕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6-127,代序9.
〔1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0.
〔17〕托马斯·勒克莱尔.“语言不能流汗”:托妮·莫里森访谈录〔J〕.少况译.外国文学,1994,(1):24-28.
〔19〕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London:Hutchinson,1973,p.52.
〔20〕Martia Sturken.Tangled Memories:The Vietnam War,the Aids Epidemic,and th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