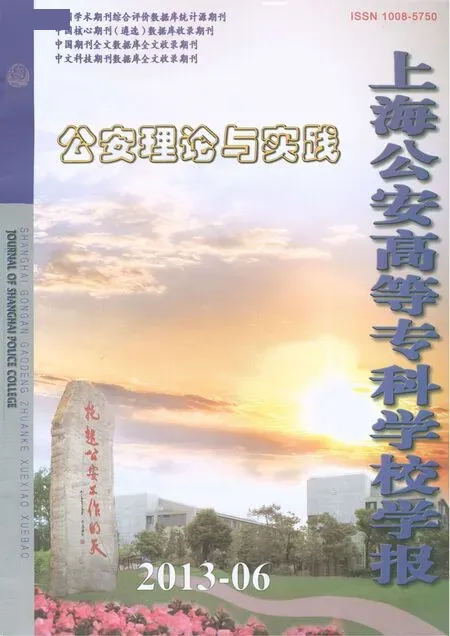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推定
周 洁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推定
周 洁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对毒品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以来都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有效解决“主观明知”认定这一困境,司法实务界已经认同在毒品犯罪的审理中可以适用“主观明知”的推定。但是,必须严格控制“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条件和运用规则,避免其成为司法人员肆意利用自由裁量权的保护伞,造成冤假错案的出现。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实践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第347条至357条11个条文对毒品犯罪规定了12个罪名,这12个罪名虽然具体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属于故意犯罪,即主观上必须具备“明知”这一要素。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对毒品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以来都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有效解决“主观明知”认定这一困境,司法实务界已经认同在毒品犯罪的审理中可以适用“主观明知”的推定,但是,“明知”的推定毕竟是一种人为的定罪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容易造成司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近年来冤假错案的频现也可窥见一斑。在采用推定的方法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有何限制?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以期为我国毒品案件的侦查提供参考。
二、“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困境
认定毒品犯罪中嫌疑人主观上具有“明知”的故意,需要找到行为人“明知”犯罪的证据,这成为了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毒品犯罪行为手段具有隐蔽性。近年来,随着毒品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在交易用语、方式、工具等方面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措施。比如,在交易中并不直接使用“毒品”一词,而是采用暗语、隐语等;改变了传统的毒品运输方式,采用人货分离,利用合法的运输工具将毒品伪装成合法物品,将毒品藏匿于伪装的夹层和隐秘的部位来躲避各种检查关卡或者采取邮寄、信用卡等支付手段异地遥控交易;利用不知情的人或者雇用“马仔”、未成年人等来运输毒品。这就对侦查机关在获得犯罪分子“主观明知”的证据方面加大了难度。
第二,毒品犯罪一般无特定被害人和犯罪现场。毒品犯罪是一种以追求巨额利润、谋求暴利为主要目的的犯罪,它有别于抢劫、诈骗、盗窃等经济型犯罪,不以暴力、欺骗或者非法占有等方式来实现。毒品犯罪的交易也仅限于特定的少数几个人之间,交易人可能在交易完成之后仍然不知道交易的相对方是谁。且双方通常都是自愿的,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和对毒品的依赖性自觉寻找、购买毒品,因此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所以,很少有人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贩毒分子。此外,由于毒品犯罪一般也不会造成直接的人身伤亡或者环境、场所等的直接破坏,所以很难发现犯罪现场,即使留有犯罪现场也很难找到足以定罪的线索、痕迹物证等。
第三,毒品犯罪行为人口供的多变性。在很多毒品犯罪的案件中,犯罪行为人在刚被抓获后的第一次讯问时,供述自己犯罪的事实,但在随后的供述及庭审中,却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予以否认。或者有些犯罪嫌疑人辩称只知道其是违禁品,并不知是毒品,以此减轻或者逃脱罪责。这样在检察机关、法院进行起诉阶段的翻供导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如何认定“明知”的问题上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导致口供无法有效证明犯罪分子的主观明知,进而致使案件很难处理。
第四,毒品犯罪分子具有很强的对抗性。毒品犯罪通常是一种有计划、有预谋的犯罪,而且往往是职业性犯罪。犯罪分子一般在每一次行动之前都会精心策划,并为一旦被查获时如何应对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有的还配备了枪支或其他可用于搏击的凶器。一旦遇到缉毒人员,能避开则避开,无法避开时便铤而走险。这种强烈的对抗性加大了缉毒工作的危险性和侦查取证的难度。[1]
三、“主观明知”推定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刑法理论界对于“主观明知”的推定存在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其在司法实务界对于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毒品犯罪这一类犯罪,比起普通的刑事犯罪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保护社会法益的角度更应当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和惩治。其次,如前所述,毒品犯罪具有隐蔽性、一般无被害人和犯罪现场、犯罪分子的口供具有多变性等特点,因此,在认定“明知”的证据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而适用推定的方法可以突破证据收集的局限性,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处罚。最后,即使适用了推定,如果有足够的相反证据还是能够予以推翻和排除的,并不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当然,“明知”的推定方法,毕竟是一种人为的定罪方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也从另一方面间接地授予了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条件,避免其成为司法人员肆意利用自由裁量权的保护伞,造成冤假错案的出现。对此,具体应注意如下问题:
(一)“主观明知”推定的基本原则
1. 以具体法规规定为原则
“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可以解决毒品犯罪中证据认定的困难,对于打击和惩治毒品犯罪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造成了潜在的损害。因此,需要由国家的具体法规规定作为其适用的基本准则,对其进行指导。就目前而言,我国毒品犯罪中主观推定规则的基本准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等司法机关所作出的意见和会谈纪要之中。如2005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毒品犯罪案件公诉证据标准指导意见》中规定的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一般证据”中的第2项“关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中规定的推定“明知”应当慎重使用的情况。200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关于毒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 。200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的对于“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即除了被告人的陈述之外,还要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以及在实施毒品犯罪行为中的一系列过程和方式等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2. 以公众一般认识为原则
推定虽然是判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有效方法,但不可否认,这对于行为人而言是极其不利的,甚至有违背人权保障的嫌疑。因此,在进行推定的同时,必须保证推论前提、推论规则、推论结果的合理性,使民众能够充分信赖推论的过程,并接受推定的结果,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公众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标准。在推论中充分考虑民众的认识标准,将推论过程、结果等建立在社会相当性基础上,才能使推论更为合理。[2]如果达不到社会大众一般的认识,那么这样的推定就失去了法理的基础。
3. 以“无罪推定”为原则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而“禁止有罪类推”是罪刑法定的重要派生原则之一。推定作为证明的一种方法,更多的是适用于民事诉讼之中,往往与举证责任倒置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在刑事诉讼中,引入推定作为一种证明方法,它的适用是一种穷尽所有方法之后的最后方法。为了限制任意推定,防止错案的发生,推定的适用仍然要严格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即在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推定其主观明知时,如果出现多种选择的可能,不能确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就要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选择。
4. 以经验法则为原则
对于推定的适用要严格按照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法则,这是推定成立的哲学基础。如关于运输毒品推定中主要的经验法则:第一,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场所。一般认为在飞机、汽车、轮船、火车上或在机场、车站、码头、收费站及短暂停留的旅社查获犯罪嫌疑人,可视为其实施了运输毒品行为。第二,藏匿毒品的位置。一般采用将毒品吞、塞入体内藏匿,或将毒品藏于人身不易为人发现地方,如藏于胸罩、内裤等处可以被认为对运输毒品具有主观明知。第三,被查获过程中的言行举止。一般毒品犯罪嫌疑人会表现出举止慌乱、神色紧张、前言不搭后语、逃跑、反抗检查等行为。第四,运输途中的行径路线。毒品犯罪嫌疑人通常不按正常路线行走,反而绕行检查站、收费站等。第五,运输的始发地与目的地。从毒品重灾区(如中、缅交界的云南省边境地区)乘坐交通工具前往内陆及沿海地区一般被认为有运输毒品的重大嫌疑。第六,报酬、好处费。高额的报酬与简单的打工行为严重不相对称时,一般也会被认为有运输毒品的重大嫌疑。第七,与经济情况不符的交通方式。经济拮据的打工仔或打工妹可能因为乘坐飞机前往目的地而被司法人员认为具有运输毒品的嫌疑。[3]
(二)“主观明知”推定的排除性事项
1. 程序不合法导致推定的排除
程序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推定的适用是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客观化,因此,更要严格按照相关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合法谨慎。通常推定的内容包括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工具、手段、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行为人的年龄、职业、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这些环节的推定必须依法进行。比如,侦查部门在具体适用“主观明知”的推定时可以设置一套严格的监督反馈机制,适时地将材料副本交予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以接受质疑。如果犯罪嫌疑或者被告人认为这些材料副本存在重大失实,可以要求原侦查部门加以改正;如果原侦查部门不改正,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向上一级侦查部门申诉或者向该侦查部门的同级监察部门举报。上一级侦查部门或者该侦查部门的同级监察部门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理由成立的,应当责令原侦查部门立即改正,原侦查部门如果拒不改正的,则其运用“主观明知”推定所取得的证据应当被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即如果其中有一个环节不符合实体和程序法的规定,那么整个推定将被排除,行为人的嫌疑应当立即被洗清,对其采取的暂时性强制措施应当立即解除。
2. 事实不全面导致推定的排除
作为推定的事实必须是全面、清晰和确凿的。全面是指通过推定所得到的事实是基于整个毒品犯罪的全部事实,而不是避重就轻,有所挑选,专门有利于侦查部门或者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清晰是指通过推定所得到的事实必须清楚、明晰,让人一目了然,能够直接运用而不是通过演绎、推理等方式再经过后期的排查得出,因为推定的事实本身就已经是“推定”而得之,不能在“推定”之上再进行第二次推定。确凿是指通过推定所得到的事实必须是确切的,不存在疑问性,与毒品犯罪案件有直接关联性。基于以上几点,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行为人毒品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保证推定的合法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是推定得以进行的基础条件,否则,很可能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基础事实的缺失会直接导致推定的排除,因为基础事实是推定的前提,司法人员以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为基础进行判断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基础事实是客观真实的。
3. 未经质证导致推定的排除
在毒品犯罪案件中适用推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质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首先,这关系到一个人犯罪与否,甚至关系到一个人是否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其次,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法律都已经明确规定了作为案件的证据必须当庭或者庭外经过利害关系人的质证,何况是经过主观推定的证据。因此,对于推定的结论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进行反驳或者质疑,并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意见的合理性,只要其提供一定的证据或者证据的线索,反驳达到合理的程度就可以推翻推定结论。未经质证排除推定的适用。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侦查部门因为破案率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质证权利,对于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推定进行质证时,应当有第三方的介入,判断推定所得的证据的渠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确保公平公正。具体可以由与毒品犯罪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检察机关介入,赋予其监督建议权。这样一方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质证权利进行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对侦查部门开展的毒品犯罪案件的质证环节进行有效监督。
[1] 普同山. 多角度证实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J].人民检察,2011,(20).
[2] 周光权. 应考虑公众的一般认识标准[J].人民检察,2007,(21).
[3] 莫关耀,景碧昆. 毒品案件主观认定中的自由心证[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1).
Deduce the Subject’s Knowledge in Drug Crime
Zhou Jie
(Shanghai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University, Shanghai 201701, China)
Ow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ug crime, it is diffi 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ubject knows he or she carries or transports drug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judicial fi eld has confi rmed the application of deduc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drug crime. However, there should be conditions and rules to restrain the application to prevent it from becoming an excuse for judicial practitioners to abuse their discretion, thus prevent wrong cases from occurring.
Drug Crime; Subject’s Knowledge; Dilemma in Practice
D915.3
A
1008-5750(2013)06-0053-(04)
10.3969/j.issn. 1008-5750.2013.06.009
2013-09-18 责任编辑:陈 汇
周洁(1989- ),女,上海政法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