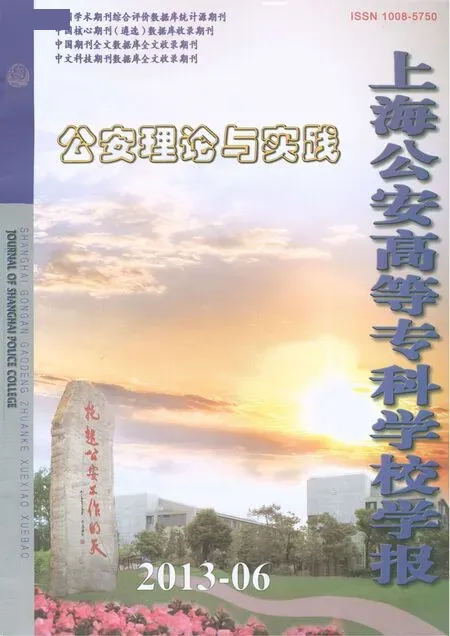关于域外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规范的考察
蔡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关于域外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规范的考察
蔡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隐匿身份侦查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隐匿身份侦查实践所证明。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是隐匿身份侦查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水岭。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实体法依据包括阻却形式违法的法定事由和阻却实质违法的超法规事由。前者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照法令行为、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行为和正当业务行为。后者包括被害人承诺行为、义务冲突行为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容许的危险。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程序法依据包括辩诉交易、不起诉和诉讼策略。
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实体法;程序法
隐匿身份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或受委托侦查的人员隐匿其真实身份实施的侦查。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这是第一次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隐匿身份侦查”进行立法规范。初步回应了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对诱惑侦查、卧底侦查,都应当适应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要求在刑事诉讼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以确认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确认由此而获得的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许容性,同时防止滥用侦查权损害公民权利”。但是,大量的争议从未停息。深究各种争议的焦点,乃在于隐匿身份侦查对现有社会观念和法律法规等因素的突破,这种“突破”引发了各种焦虑。尤其是“隐匿身份侦查”相关的程序法问题、实体法问题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和厘清,让实务界无所适从。
隐匿身份侦查实施的环境区别于一般社会环境,为犯罪环境。为了融入犯罪环境、获得侦查对象的信任,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必须体现出与犯罪环境的“契合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涉及某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隐匿身份侦查实践证明,如果隐匿身份侦查人员不能被免除于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下作出的“犯罪行为”的责任,则法律会将隐匿身份侦查人员置于“动辄得咎”的危险境地。
因此,必须对隐匿身份侦查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使之谨守法律的限界。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是隐匿身份侦查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水岭。行为限度内的隐匿身份侦查行为当然属于合法行为或免责行为,而超越行为限度进行的行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笔者试根据境外相关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对隐匿身份侦查的行为限度的实体法依据和程序法依据进行梳理,供各界借鉴。
一、域外有关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实体法依据
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实体法依据指的是实体法对隐匿身份侦查相关行为具有正当化事由的规定。即,某些隐匿身份侦查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加害性,但实质上该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行为。这些行为尽管侵害了法益,但侵害这些法益是为了救济更高价值的法益,因此是正当的,具有违法阻却事由。例如,侵犯隐私权、非法入侵住宅罪或渎职罪等。正当化事由包括两类,即阻却形式违法的法定事由和阻却实质违法的超法规事由。前者指的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可以排除符合构成要件行为违法性的事由,而后者是指刑法无明文规定,从法秩序的精神引申出来的正当化事由。
(一)隐匿身份侦查阻却形式违法的法定事由
根据各国隐匿身份侦查的立法,其阻却形式违法的法定事由如下:
1.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指的是当社会公共利益、个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对正在实施侵害的行为人采取的可能会使其受到一定人身损害的行为。隐匿身份侦查的主体可能是侦查人员也可能是一般群众、前科劣迹的人员或者犯罪嫌疑人。对于正当防卫,各国法律均规定不管主体是谁,都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因警察身份或侦查目的而改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警察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公民的身份,特别是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身处犯罪团伙当中,直接面对犯罪嫌疑人等随时可能遭遇公共利益、自己或他人利益遭受现实侵害的情况时,隐匿身份侦查人员有权根据现场情势采取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当然,隐匿身份侦查人员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否则仍然不能构成违法阻却事由。
2.紧急避险。紧急避险指的是行为人为了防止对本人或他人的合法利益、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构成现实威胁的危险,而对第三人(旁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有些学者认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行为虽然会对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或个人利益造成一定的侵害,但考虑到该行为实施的客观环境及利益权衡情况,可以成立紧急避险。但是,某些国家刑法规定:业务上负有特别的义务的人,不适用紧急避险的规定。例如,日本刑法第37条第2款,意大利刑法典第54条第2款,韩国刑法第22条第2款等。法国、俄罗斯、瑞士等国刑法则对此没有专门规定。
3.依照法令的行为。法令行为是指基于成文法律、法令、法规的规定,作为行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所实施的行为。许多国家刑法典中都有明文规定。如,1971年3月18日修正的瑞士刑法典第32条(依法律、公务或职业上之义务行为)规定:“依法律、公务或职业上义务之行为,或法律明示许可或不罚之行为,不构成重罪或轻罪。”具体包括:法律基于政策理由排除犯罪性的行为;法律明示了合法性条件的行为;职权(职务)行为;权利(义务)行为。
隐匿身份侦查在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被司法或立法赋予了合法性。如,美国不仅豁免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而且,这种豁免还是一种“概况式”的豁免,即没有罪名与实施主体的具体限制。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06条第32项规定:“为了查证核实刑法典第222条第34至38款的犯罪行为……经共和国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同意并授权,司法警察取得、拥有、运输、寄交或交付毒品给前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人或储存、保留毒品的,均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即使是在秉持强制起诉与法定起诉原则的德国,也规定“对于他人权利的侵犯仅能在现行法的规定范围之内为之”。因此,只要符合法令的授权规定,隐匿身份侦查就当然获得了合法性。
4.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可能会造成法益侵害,世界各国对此类行为的归责、免责原则和条件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认为,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公务员依照法令应当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因此,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即使构成了违法,也一般属于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规定:“完成合法当局指挥之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此种行为明显非法者,不在此限。”瑞士刑法典规定:“公务员依照法令执行上级命令是在履行职务,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均属于刑法规定的合法行为。”意大利刑法典第51条规定:“行使权利或者履行由法律规范或公共权力机关的合法命令赋予的义务,排除可罚性。”美国判例认可:获得上级准许的隐匿侦查行动中,侦查人员参与的犯罪活动应当属于违法阻却。在美国刑法中,公共权力辩护可以豁免隐匿身份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法国通过综合立法模式规定,在经过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同意并授权之后,司法警察可以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荷兰也规定了检察官批准下的“犯罪许可”制度。因此,公务员执行合法命令,其行为均为合法。“执行命令的行为排除社会危害性,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命令是上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布的,发布命令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职能。二是下级国家工作人员有义务执行上级的命令。在其执行命令时,他在主观上并不是自由的,而要受到上级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因而他就不能对其行为承担责任。”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无论是否被明确规定于刑法典之中,也无论认为其是违法阻却事由还是责任阻却事由,对该行为之排除犯罪性,学界鲜有异议。
不过,在上级命令违法的情况下,下级的主观罪过决定着阻却违法事由成立与否。一是,如果下级在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该命令的违法性,则仍不构成犯罪。负有服从命令义务的公务人员在不明知命令违法的场合,责任阻却源于行为人意志的相对不自由,在于不强人所难的法律对于人性脆弱一面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这符合期待可能性的原理。二是,如果下级“明知”该命令违法而仍予以执行的,则应承担刑事责任。不过,在隐匿身份侦查中,被聘任人员一般并非公务员,不可适用该阻却违法事由。不具有公务身份的人,即使出于维护社会的动机实施的行为,也不能因此具有正当化事由而排除其犯罪性。
5.正当业务行为。正当业务指的是即使没有法律上的明示授权,也能认定为正当的业务。正当业务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正当业务的需要而实施的客观上有损于某种法益,但因其主观要素的正当性和客观行为的必要性而为刑法所宽容,并阻却犯罪成立的行为。例如,日本刑法典第35条所规定“依据法令或者基于正当业务而实施的行为,不处罚”。其构成要件为:在主观上,行为人具有正当的从业目的,不以侵害他人或社会秩序为目的。客观上,正当业务行为对法益的损害是从事该正当业务的需要,是无法回避的现象。而且,从实质来看,正当业务行为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行为。隐匿身份侦查能否基于正当业务行为而阻却违法事由,对此,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规范不一。
英美法系当中将正当业务行为作为辩护事由,但并没有具体的类型概括。大陆法系认为正当业务行为主要包括医疗行为、律师的辩护活动、新闻报道行为和体育竞技行为。
(二)隐匿身份侦查阻却实质违法的超法规事由
根据各国隐匿身份侦查的法理及立法,其阻却实质违法的超法规事由如下:
1.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被害人承诺指的是法益主体对他人以特定方式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法益的行为所表示的允许。现代各国刑法理论通常将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作为犯罪阻却事由来对待。有的国家或地区对被害人承诺在刑事立法作了明确规定,将其作为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如意大利、韩国、中国澳门等。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中,对此并未予以明文规定,而是在理论上将其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加以探讨。其构成要件包括:一是主体要件,承诺的主体要有承诺能力,即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二是主观要件,包括被害人承诺时应该是自愿、真实的,行为人则应该对被害人作出的承诺有明确的认识。三是法益要件,仅能针对被害人有权处分的个人法益,包括除生命权和(部分)健康权以外的其他个人法益。四是时间要件,承诺的时间应该是行为前或行为时。五是目的要件,该承诺事项没有为刑法所禁止。
隐匿身份侦查在实施过程当中,也将涉及许多需要侦查对象同意的行为。如,进入侦查对象住宅或侵犯隐私等。这些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入侵住宅或非法讯问(询问),是否逾越了任意侦查的限界?对此,世界各国已经有理论、立法或判例予以解答。如,德国1992年《对抗组织犯罪法案》明确规定:“卧底警探得使用化名,于权利人同意之下,进入住屋。卧底警探不得以使用化名外之欺骗手段,获取权利人同意而进入住屋。”而美国“虚伪朋友理论”或“合理隐私预期理论”则认可了相应证言的证据资格。
2.义务冲突行为。义务冲突指的是存在两个以上不相容的法定义务,为了履行其中的某种义务,而不得不放弃其他义务的情况。其成立需要三个要件:同时存在数个互不相容的义务;义务冲突状况的出现不能归责于行为人;为了履行一方义务不得不侵害其他义务。义务冲突属于违法阻却事由,因为“对于义务冲突,法律不应宣称没有履行义务就是错误,而应当把选择履行义务的权利委于行为人,只要行为人的选择符合义务衡量原则,他的行为就是合法的”。
一般而言,刑事义务来自于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在隐匿身份侦查中,隐匿身份侦查人员也经常面临诸多义务冲突。首先,他们具有实现侦查目的、获取犯罪信息和证据材料的义务。这是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或者是被聘任人员基于聘任合同或自愿行为而具有的义务。其次,在面对犯罪时,他们基于职责或公民义务,有制止或告发的义务。如果放任犯罪行为的发生以至于发生不法后果,卧底警探同时可能成立不作为犯而受到刑事追究。但是,在冲突的义务中,他们要么履行制止犯罪的义务而放弃侦查的义务,要么履行侦查的义务而放纵现实的犯罪。这就需要通过利益衡量作出合适的选择,并通过违法事由的阻却排除其可罚性。否则,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将被时时置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并无法实施。对此,各国立法或准则有所区别。
一些国家直接通过概括性规定解除了隐匿身份侦查人员义务冲突的困境。如,美国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对于侦查过程当中发现的其他犯罪,都不具有现场制止的义务。一些国家则区分情况处理。如,《德国刑事追诉上各邦法务部与内政部运用线民与卧底警察共同纲领》中规定:“对于新发现的充分犯罪嫌疑,如加以调查将危及原有的侦查工作,卧底警察不得着手侦查工作;如果新发现的犯罪情节重大,不在此限。”同时,应该“得到检察官的同意,如果不能即时获得检察官的同意,应不迟疑立即告知检察官”。
3.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容许的危险。被容许的危险是指为达成某种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在其性质上常含有一定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此种危险如在社会一般生活中被认为相当时,即应认为是可被容许的合法行为。其具有法益侵害危险和有用性两大特征。当然,该理论主要适用于过失犯罪领域。
在隐匿身份侦查领域,基于获取犯罪信息或证据材料的需要,往往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放纵”。如,安插卧底警察而不及时将犯罪团伙抓捕归案;与犯嫌疑人一起实施盗窃、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行为。该行为具有助益侦查目的实现的有用性,但是,也具有失控的法益侵害危险。如,犯罪嫌疑人逃匿,证据被毁灭或毒品扩散到社会上等。但是,就隐匿身份侦查措施当中可能造成的危险,社会应该予以相应的许容。当然,其前提必须是隐匿身份侦查各方谨守了注意合法与合理的义务。
上述介绍只是单一的阻却违法事由,然而,在具体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各种阻却违法事由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二、域外有关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程序法依据
隐匿身份侦查行为限度的程序法依据,指的是某些隐匿身份侦查行为不具违法阻却事由或明显超越了违法阻却事由的限界,但是基于政策考虑而通过程序法予以免责的情况。如,隐匿身份侦查在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要实施调查手段并因此侵犯隐私权和住宅权等。同时,为了保障隐匿身份侦查的顺利实施,还必须实施某些附属行为。包括:为了伪造身份而伪造证件、文书;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信任而实施某些犯罪(抢劫、盗窃、殴打、持有毒品和越狱等)。这些附属行为与隐匿身份侦查本体行为相区别,其正当化事由也随之弱化甚至缺失。不过,隐匿身份侦查在实施过程中,侦查人员或被聘任人员身处犯罪团伙之中,很多情况难以预知和应对。如果贸然施加过多限制或禁止附属行为,则隐匿身份侦查无从实施。但是,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某些隐匿身份侦查行为或附属行为又构成了“轻微犯罪”——“如果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极为轻微,如果犯罪的目标可以不予考虑,如果犯罪人是本着完全值得赞赏的目的采取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共秩序而言,提起追诉只能是弊大于利”。对此,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普遍做法是:通过程序法予以免责。
(一)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律赋予了检察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包括“辩诉交易和量刑建议”等。如,在美国,检察官就可以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个部分或全部罪行的辩诉交易的机会,并签订书面的合作协议。在其接受审判时,检察官会依照《美国量刑指导手册》向法官提交量刑建议书。量刑建议书列明犯罪嫌疑人对案件的实质帮助,包括参与了何种秘密侦查、庭上作证和其他协助等。甚至,检察官可以为合作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全部的豁免权。美国绝大多数检察官都充分相信认罪程序。辩诉交易也已经取代正式审判成为美国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程序,美国辩诉交易的适用比例在90%以上。德国20%-30%的刑事案件都进行过协商,未来这种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因此,通过辩诉交易,可以解决隐匿身份侦查的某些相关犯罪的免责问题。
(二)不起诉
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不具备起诉条件或不适宜提起公诉所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决定。世界诸多国家都赋予了检察官不起诉权力。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即使犯罪证据被认为是充分的情况下,根据犯罪人的性格、年龄以及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表现情况,检察机关认为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规定,程序处理轻罪的时候,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的,经负责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检察院可以不予追究。对于尚未受到最低刑罚威胁,行为所造成后果显著轻微的罪决定不予追究时无需法院同意;已经提起公诉时,在前款先决条件下,经检察院、被诉人同意,法院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停止程序。法国刑事诉讼中有所谓“追诉的适当性”的制度,即检察官在认为提起追诉不适当的情况下,允许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实证研究数据表明,有相当部分的轻罪案件都是以不予立案决定而终结的。因此,检察官实际上都拥有着相应的权力,他们可以认为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实施一定程度上的违法行为,有助于实现预防犯罪发生或保护隐匿身份侦查策略的目标实现,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比使用实体法规则更为重要,检察官已经习惯了向警察建议各种最安全的免受追诉的秘密侦查策略。
(三)诉讼策略
诉讼策略指的是为了规避隐匿身份侦查的相关刑事责任的产生,而通过策略设计避免犯罪和追诉的产生。首先,在隐匿身份侦查的设计上,尽可能地让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处于犯罪团伙的上层,避免犯罪团伙下层所经常从事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其次,如果不可避免地必须从事某些犯罪,则可以经由诉讼设计而排除法益侵害。如,在斗殴的场合,让另一侦查人员伪装成被害人;或者对相关犯罪进行严密监控,并及时抓捕,避免对法益造成事实上的侵害;同时,隐匿身份侦查人员必须将自己参与犯罪的作用降到最小。最后,为了可能的自我入罪或程序违法,隐匿身份侦查可以仅仅限于犯罪线索和情报的运用,而不直接搜集证据或获取证据。因此,隐匿身份侦查并不进入司法视野,“法官很少能够有机会对检察官的上述建议(卧底策略)进行审查,也没有机会对卧底警探实施的非法行为进行审查”。
On the Action Limit of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
Cai Yish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 means policemen or informers cover their identity for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world practices, the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 is connected with illegal action or criminal. The action lim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ime and legal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ubstantive law, the action limit is the legal reason and the nature reason. The legal reasons are justifi able actions including self-defense, rescue, acts according to law, acts according to orders and just business. The nature reasons are the victim’s promise, behaviors confl icting with obligations and reasonable dangerous behaviors. According to procedure law, the action limit is plea bargaining; nonprosecution and prosecution tactic.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 Action Limit; Substantive Law; Procedure Law
D631
:A
1008-5750(2013)06-0079-(06)
10.3969/j.issn. 1008-5750.2013.06.014
2013-09-18 责任编辑:何银松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资助项目(编号:2012-XZQN14)“侦查思维与证据思维的构造与节点”的研究成果之一。
蔡艺生(1981- ),男,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情态证据研究所主任,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侦查学和证据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