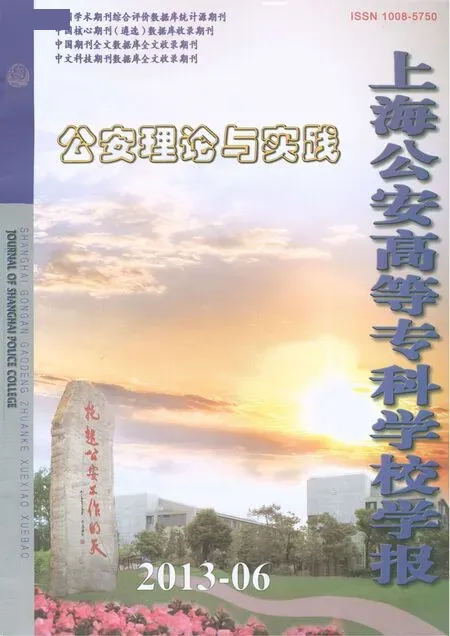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化构建
亢晶晶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化构建
亢晶晶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012《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对人民检察院在审前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相关的规定,这对于强化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的规定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将制约其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程序化”,构建专门的听证程序,明确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
非法证据排除;人权保障;听证程序;程序性制裁
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这标志着我国初步确立了人民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此规定的出台推动了我国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人民检察院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在许多地方得到了实践,并出现了相关的试点项目,积累了诸多经验。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告、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2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如何具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了负责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的部门及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的方式等,这些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又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人民检察院在审前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排除有利于阻断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及时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以来,许多地方已经相继出现了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案例。如灌南县人民检察院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季某以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具体案情如下:2012年12月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季某在他人的指使下纠集多人无故将高某家中的麻将机、不锈钢防盗窗、奇瑞牌汽车砸坏。时隔一个月,季某再次纠集多人持砍刀等工具至该县一理发店,无故将被害人陈某殴打致轻伤。案发后,灌南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季某。检察人员立即对季某进行讯问,但是季某提出在第一起案件中侦查人员存在诱供现象,且讯问时没有法定代理人在场。承办检察官立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要求本案侦查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经过审查,该院排除了侦查人员存在诱供及法定代理人不在场的可能。鉴于季某归案后没有悔罪表现,该院及时对季某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从分析该案的情况中,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是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来主持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正当性是否充足呢?承担着追诉犯罪职能的检察官如何保持中立性呢?其二是从本案来看,检察官作出决定的依据是要求本案的侦查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进而单方面作出最终的决定,这显然是违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程序”的要求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如何参与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呢?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能否对检察机关的决定申请救济呢?这些问题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前得到有效适用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笔者将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来进一步分析其中的问题,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二、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然性分析
众所周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但是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能在审判阶段适用,即只有法官才可以主持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即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辩护律师在开庭前通过诉讼动议的方式启动法官的庭前审查程序,在此之前的检察官审查和预审听证阶段,非法证据和传闻证据都不在禁止之列。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建立在美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系之上的,法官在审前程序中也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的特点以及人民检察院的特殊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在审前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然性。
1.体现了人民检察院的诉讼监督职能。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一元权力分立结构,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它产生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些国家机关必须由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个定期性的议事机构,很难对经常性的、大量的行政活动与审判活动进行动态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宪法将人民检察院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监督机关负责对刑事诉讼程序参与者的活动进行监督,以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法律得到正确的实施。我国的人民检察院的设置及其权力都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并不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及和人民法院并列的司法机关。此外,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法官基本难以介入审前程序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因此,也难以对审前存在的非法证据及时发现并排除,而人民检察院则在审前程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审查批捕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发现并确定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并追究非法取证主体的责任,减少、审查、杜绝非法取证行为,都是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职能的完整体现。但是,人民检察院在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质疑就是容易产生“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这关系到人民检察院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所做的决定的权威性,如何应对这个质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2.人民检察院承担着客观公正的义务。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检察机关都是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为了履行这个职责,大多数国家赋予检察官一项义务即客观公正义务,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又称“检察官客观义务”、“检察官客观性义务”、“检察官客观公正原则”,它是指检察官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不应站在当事人立场,而应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活动,努力发现并尊重案件事实真相。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是世界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国际准则确认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也是检察官的重要行为准则。具体到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同样也承担着客观公正的义务,此义务要求人民检察院在进行相关的刑事诉讼活动时不能一味追求打击犯罪,而是同时要注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具体言之,就要求人民检察院在进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支持公诉等活动时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唯事实与法律论而不片面追求定罪与胜诉的结果,强化对诉讼活动,尤其是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及时发现并依法纠正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并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判断证据时既要重视能够证明被追诉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也要重视证明被追诉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依法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并及时排除非法证据。因此,人民检察院的客观公正义务无疑成为了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正当性基础。
3.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需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两大目标,许多西方国家就明确指出刑事诉讼的目标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正当而迅速地处理案件,避免不必要的费用和延缓;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公共福利,保障基本人权。因此,在这样刑事诉讼目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设置将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反之,从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的第1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即将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因此相关的制度设置也围绕着实现打击犯罪的目标,而忽略了对人权的保障。2012年《刑事诉讼法》通过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并且在相关制度设置上也体现出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人民检察院承担审前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显然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众所周知,在审查批准逮捕以及审查起诉时,人民检察院作出逮捕与否或者起诉与否的决定的依据就是相关的证据,一旦存在非法证据,那么就可能导致人民检察院出于打击犯罪的考虑作出错误的决定,将犯罪嫌疑人错误地羁押,或者本不该被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而被起诉,这显然是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的。因此,通过让人民检察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查证据的合法与否,让非法证据及早从刑事诉讼程序中排除出去,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的出现,节约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当然,在审前程序中排除了非法证据可能导致侦破案件受到很大的阻力,进而可能导致放纵犯罪嫌疑人,从而难以实现打击犯罪的目标,但是,这是我国在实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道路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评析我国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人民检察院承担审前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最早其实并不是由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而是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只是后者对于人民检察院有义务排除非法证据仅仅用一条规定概括,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内容。而2012《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对具体的内容作了一定的细化,但是从目前的规定来看,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缺乏对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规定。从《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来看,仅仅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以及“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而并没有对具体的调查程序进行明确,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办案人员,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调查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通过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但是这种调查方式还是属于单方面的,并不符合程序的基本要求。此外,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中往往采取的是行政化的审批模式,而很少采用诉讼化的模式,再加上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当前的根基还不是很稳固,如果不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遵循的具体程序要求,那么很可能导致人民检察院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规制,进而导致其所要实现的目的落空。
2. 缺乏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程序参与权的保障。从目前的规定来看,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证据的合法性的时候,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及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从而作出最终的决定。法律规定用的是“可以”,因此对人民检察院来讲就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人民检察院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是否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可以参与到调查核实程序中,但是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意见对于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是否有约束力,以及约束力有多大,都是无从得知的。众所周知,审查证据的合法与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程序性问题,在西方国家被称为“审判之中的审判”。此外,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职责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表明我国也确立了辩护律师进行程序性辩护的权利,因此,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辩护律师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从当前的规定来看,并没有任何的措施来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真正参与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这样不仅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决定的权威性。
3. 缺乏对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的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的高低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完整的程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并没有对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时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具体的证明标准作出规定,而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的设定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责任是由人民检察院来承担,而证明标准则属于“确认”或者“不能排除”,那么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据合法与否的证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对于证明标准是否可以参照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所规定的证明标准呢?因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如果一味适用同样的规则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关系的平衡。
4. 缺乏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救济性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是一项权利,而对于人民检察院而言则是一项义务,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不利后果作为保障,那么义务要求对于人民检察院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而遗憾的是,法律并没有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不履行义务的制裁措施,这对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显然是不利的。此外,由于人民检察院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作出的决定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是否将被羁押或者被起诉,因此有必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对相关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但是法律规定似乎对此问题并没有涉及。对于人民检察院作出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合法、不应当被排除的决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相关的救济途径,这将违背权利救济的基本原则。
四、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化构建
人民检察院在审前程序中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是其诉讼监督职能的体现,也符合我国确立的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面临着一些质疑,主要就是人民检察院角色存在冲突,难以保持中立性,工作方式以行政审批为常态等,这些质疑显然会对人民检察院在排除非法证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产生不利的影响,再加上《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过于简单和笼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相关程序的具体内容。具体言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建构专门的听证程序。正如上文所言,当前《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并没有具体规定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应该遵循的程序,这样将难以避免人民检察院在作出决定过程中的恣意性,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对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是,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审前程序的一部分,如果也采用西方国家“审判之中的审判”的做法,那么诉讼程序的繁琐性将会导致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造成刑事诉讼程序的拖延,违背诉讼效率的要求。为此,出于公正和效率之间平衡的考虑,可以构建一个简单的听证程序,并对这个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作出一定的限制,具体内容即在审查批捕阶段或者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发现或者经过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存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该启动一个简单的听证程序,侦查机关的相关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都应该参与到这个听证程序中,双方针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相关的证明,并可针对相关的问题展开辩论,人民检察院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终的决定。当然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对于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作出一定的限制,根据学者的建议,对于简单的瑕疵证据以及需要重新补正的非法证据,侦查机关与案件当事人没有实质性异议的,就没有必要进行听证,人民检察院可以采用单独讯问或者询问的方式作出决定,以此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2. 明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的设定是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该项制度能否得到有效适用,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于人民检察院审前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都没有涉及,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相关做法的基础上将其明确化。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审判阶段中证据合法与否的证明责任在于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那么同样在审前阶段中,在人民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中,证明责任也应该由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侦查机关承担,以平衡程序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地位和能力的悬殊,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至于证明标准的设定,笔者认为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果证明标准过高将会使得侦查机关难以证明证据的合法与否,从而导致放纵犯罪;反之,如果证明标准过低,将可能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同时也将会使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失去其原本的意义。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类似于英美法系的“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以此来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3. 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程序参与权。根据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在对一个人作出不利的决定时,应该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而证据的合法与否对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将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让犯罪嫌疑人实质性地参与到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其参与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要保证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让其在程序中有机会充分表达其意见。但是问题在于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着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侦查机关,即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时候,要想实现真正的平等对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加强辩方的力量,弥补双方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为此,对于没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应该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并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以及调查取证权等权利,使得辩护律师真正能发挥作用。当然,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是否真正参与了程序,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其意见对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起到了实际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要求人民检察院在作出决定的同时应该将相关的理由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以此来实现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权力的监督。
4. 构建相应的救济机制。西方法谚“无救济则无权利”,为了使权利真正得到实现,必须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作为保障。具体到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笔者认为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证据合法、从而不应当被排除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申诉申请应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此处理结果仍不服的,有权向该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再申诉,以此来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此外,为了使人民检察院能够切实履行相关的义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程序性参与权等,可以启动程序性制裁措施,即通过宣告那些违反法律程序的侦查、公诉和审判行为为无效,使其不再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的方式来惩罚和遏制程序性违法行为。这种制裁方式是通过“剥夺违法者违法所得的利益”或者令违法行为不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的方式,来达到阻遏和拒绝接受违法行为之法律效果的作用。具体言之,对于人民检察院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自身义务,不对非法证据进行及时排除的,那么人民检察院所从事的相关诉讼活动都归于无效,以此来促使人民检察院积极履行相关的义务。
五、结语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体现了人民检察院的诉讼监督职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审前程序中由人民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尤其是如何解决人民检察院的角色存在的冲突问题,以及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审前程序中人民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还需要从实践中探索相关的经验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1][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陈卫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6-78.
[2]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6.
[3]樊崇义.刑事诉讼哲理思维[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312.
[4]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237-239.
[5]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二版)[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406.
[6]陈卫国,李红妹.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1,(4):154-160.
[7]陈卫东.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1):67-73.
[8]卞建林.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排除[J].人民检察,2011,(12):67-71.
[9]谢佑平.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排除[J].中国检察官,2010,(11):9-11.
[10]马静华,刘相玲.从制裁到预防: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机制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4):119-123.
People’s Procuratorate’s Establishment of Procedures to Eliminate the Illegal Evidence
Kang Jinjin
(Law Colleg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nacted in 2012 and People’s Procuratorate’s Rule on Criminal Procedure following the Provisions on Eliminating Illegal Evidence in Dealing with Criminal Cases have made relevant provisions for people’s procuratorate to eliminate illegal evidence in pretrial procedur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legitimacy of the investigative behaviors and protecting the criminal suspects’ human right. However, their shortcomings are that they restrain procuratorate’s role playing.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procedurize them by establishing a special hearing procedure and making clear the related provis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ir operability.
Eliminate Illegal Evidenc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 Hearing Procedure; Procedural Sanction
D631
A
:1008-5750(2013)06-0063-(06)
10.3969/j.issn. 1008-5750.2013.06.011
2013-09-28 责任编辑:何银松
亢晶晶(1989-),女,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11级诉讼法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