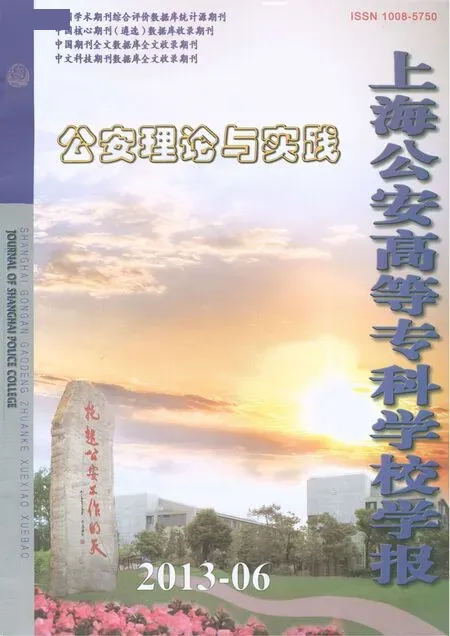试论侦查笔录类证据规范化
胡 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试论侦查笔录类证据规范化
胡 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种类中增加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确立了辨认、侦查实验、搜查、查封、扣押、提取等侦查笔录的法定证据地位。这是证据制度变革中的重大进步与发展,它一方面完善和丰富了法定证据种类,为司法机关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更多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对侦查机关依法实施侦查行为和规范制作侦查笔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在对侦查笔录的特征及证明功能分析基础之上,反思侦查笔录的现状,结合与侦查笔录类证据有关的程序性机制的研究,对如何规范侦查笔录作进一步探讨。
侦查行为;侦查笔录;证据;规范化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原有的“勘验、检查笔录”证据种类中增加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扩大规定,增加了搜查、查封、扣押、提取等笔录。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勘验、检查、侦查实验、搜查、查封、扣押、提取、辨认属于法定侦查行为。我们将记录上述侦查行为实施过程与结果的笔录统称为侦查笔录。①需要说明的是,询问和讯问也属于法定侦查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是通过询问或讯问的方式形成书面笔录作为其载体。司法实践中,讯问、询问笔录的效力等同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因此,笔者试图研究的侦查笔录类证据仅限于在法律上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侦查笔录,即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搜查、查封、扣押、提取等笔录。
《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除了勘验、检查笔录,其他侦查笔录并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但是,在实践中,不论是侦查机关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检察部门审查起诉和法院定罪判决,都将绝大部分侦查笔录作为证据在使用。多年来,立法与实践的不一致,使理论界对于除勘验、检查笔录之外的其他侦查笔录是否具有证据资格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侦查笔录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确立了侦查笔录的法定证据地位。这是证据制度变革中的重大进步与发展,它一方面丰富和完善了法定证据种类,为司法机关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更多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对侦查机关依法实施侦查行为和规范制作侦查笔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规范侦查笔录,使之发挥法定证据的应有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侦查笔录的特征
1.法定性。侦查笔录属于法定文书,是法定主体按照法定格式针对法定事项制作而成的笔录。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查封、扣押等侦查行为之后,应当将侦查行为的实施情况制作成笔录。
2.依附性。侦查笔录的形成依附于侦查行为的实施:先有侦查行为的启动与实施,后有记录侦查行为实施过程与结果的需要。换言之,制作侦查笔录属于实施侦查行为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在制作符合法律要求的笔录之后,侦查行为才能称得上全部完成。
3.工具性。侦查人员通过即时记录侦查行为实施过程与结果,不仅将侦查行为实施过程固定于笔录之中,同时也及时固定和保全了侦查活动中获取的证据信息(即侦查结果)。因此,侦查笔录是固定和保全证据的手段和方法。我国有学者指出,为了防止有证明意义的情况由于可能发生变化而失去证明价值,所以要通过各种笔录的形式将这些情况所包含的有证明价值的信息以一定的载体记录下来,以便在诉讼中充分发挥笔录的证明作用。[1]
4.客观性。侦查笔录是侦查人员对实施侦查行为时所见所闻的客观记载。笔录制作过程,是侦查人员由对侦查行为的感知转化为文字记录的过程。此过程虽然无法排除个体认识、判断以及表达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侦查人员应当尽可能如实、准确地记录侦查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事实和情况,避免主观夸大或缩小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事实。
二、侦查笔录的证明功能
侦查笔录是记录特定侦查行为过程和结果的书面记录。与形成于犯罪发生之前或者发生过程中,由案件当事人遗留或者形成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不同,侦查笔录形成于犯罪事实发生之后,是由侦查主体在实施侦查行为时按照法律要求针对法定事项制作而成的。在刑事诉讼中,正是因为侦查笔录记载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信息,才具有证明案件实体的意义和作用。侦查笔录不同于其他证据的特殊之处决定了其独特的证明功能。
1.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及收集过程起证明作用。侦查笔录的客观记载形象地展示了实物证据的来源以及收集过程,使之与案件待证事实发生联系。因此,法庭对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来源及其收集过程的审查,主要是通过审查侦查机关制作的各种侦查笔录来进行的。如果侦查机关没有制作笔录或者笔录记载不清楚、不全面,实物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将受到质疑。如《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来源不明的送检材料所作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等。
2.对侦查行为实施过程的合法性起证明作用。侦查笔录客观全面地记录了侦查行为的实施时间、地点、过程、参与人员和使用的方法或手段等。这些记录可以向参与侦查活动之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再现侦查行为的实施过程,使其对侦查行为实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出判断。侦查笔录对侦查过程合法性的证明,既是对其他证据收集程序合法的证明,也是对笔录证据自身证明力的保证。
3.对言词证据的证明力起印证作用。侦查笔录所固定和保全的证据信息可以印证言词证据所反映的证据信息的真实性或相关性。在这一意义上,笔录证据虽然很少能够直接证明犯罪事实或者量刑情节,但是它们却可以被用来佐证言词证据以及其他实物证据的证明力。[2]例如,勘验笔录所记载的犯罪现场情况,经常被用来佐证被告人供述的作案过程;辨认笔录所记录的辨认结果,往往可以用来验证被害人和证人所陈述的涉案人、物、场所的关联性;侦查实验笔录所记录的模拟试验结果,有时可以成为验证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和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依据;提取、扣押笔录以及清单所记载的物品、文件等,则可以被用来印证关于涉案物品特征、数量的陈述的真实性,等等。
三、侦查笔录的现状
侦查笔录是侦查活动的最主要的记录形式,也是审查实物证据来源与收集方法和程序的最主要、最直接的途径。但是,在实践中侦查笔录记载内容的不全面、不细致、不准确、不规范等弊病,不仅使得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以及辩护人无法从侦查笔录中获取到准确的证据信息,而且使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1.记载上的遗漏。例如,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查封、扣押清单没有载明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没有记载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的说明,电子证据的固定、提取形式各异,随意截取等。侦查笔录作为固定证据信息的重要手段,其对侦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实物证据相关信息的遗漏,使得法院无法判断实物证据的真实来源,也无从查明实物证据收集、提取过程的完整性、客观性。
2.相关人员签名的缺失。法律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制作笔录时,应当由参与侦查活动的相关人员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对于拒绝签名、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笔录签名制度是相关人员确认或核对笔录记载是否属实的重要保证,也是对侦查工作是否合法的唯一监督程序,事关相关证据有无进入诉讼活动的资格问题。因此,侦查笔录是否有相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既是对笔录类证据进行审查的关键内容,也是审查其他证据收集程序和方式是否合法的重要内容。
3.内容泛形式化。目前,一些侦查人员对侦查笔录中“过程和结果”一栏的记载基本上是用寥寥数语草率应付。例如,搜查笔录中既没有记载搜查前是否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也没有记载搜查时是否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等程序性事项,而是仅仅记载了搜查所获得的证据。提取笔录中,鲜有对物品个体特征的文字描述,也没有对所提取物证的保管方式、移交过程进行说明。又如,关于辨认笔录的“过程”仅仅是记载了“由侦查人员说明要求后,由辨认人开始辨认,条件良好,光线充足”,对感知条件和辨认条件都没有描述;对辨认活动结果的描述基本上是“经过辨认人对照片进行仔细的审查,辨认人指出第某某号为作案人或物品等”。如此形式化的笔录难以全面反映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让人质疑侦查活动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
四、与侦查笔录类证据有关的程序性机制
1.辩护方的全面阅卷权。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笔录作为案卷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方在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便有权获取所有侦查笔录,并从侦查笔录中确认侦查取证行为是否合法。与此同时,辩护人还可以就有关笔录类证据与被告人进行核实,以便更有效地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2.侦查人员向检察机关说明情况。《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三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及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存在疑问的,可以要求侦查人员提供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必要时也可以询问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及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人员和见证人并制作笔录附卷,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进行技术鉴定。”依此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侦查笔录存在疑问,可以要求侦查人员提供制作情况,或者询问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
3.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庭审中,侦查笔录是由公诉人以当庭宣读的方式向法庭出示,法庭一般是通过书面方式对笔录证据进行质证。但是,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如果发现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侦查人员就会被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4.“瑕疵”证据的附条件排除规则。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在审查侦查笔录类证据过程中,发现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该侦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就是说,“问题笔录”被视为“瑕疵证据”,允许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在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情况下,瑕疵笔录类证据将面临被排除的后果。这是法律出于对证据排除的慎重考虑,以尽可能地保留这些“瑕疵证据”的证据资格。但是,在实践中,当侦查笔录出现所谓形式上的瑕疵问题,并非补正或合理解释能轻易解决。哪些问题允许补正?哪些问题能够接受解释?如何补正才算完善?如何解释才算合理?这些问题都是对笔录类证据最终能否被采纳和采信的重大考验。
五、侦查笔录类证据规范化的构想
所谓侦查笔录类证据规范化,是指对笔录证据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如侦查主体、侦查程序、笔录制作技术等,进行必要的指引、约束和限制,使笔录类证据的形成合乎一定的规则和标准,确保笔录类证据具有应有的证据资格。
(一)从加强侦查主体建设入手,提升侦查员的取证能力
1.转变侦查观念。由查明事实的侦查观向证明事实的侦查观转变。“查”明和“证”明,一字之差,其差别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用通俗的话讲,查明是让自己明白,证明是让别人明白。很多情况下,侦查人员实施侦查行为的目的是收集证据,发现犯罪嫌疑人,破获案件。但是,如何将收集证据的过程与结果固定和保全下来作为定案的根据,却没有成为侦查人员着重考虑的问题。一些侦查人员仅仅是将制作笔录作为侦查活动的一个步骤而已,缺乏对侦查笔录的实体证明作用的认识,甚至在制作笔录时会存在敷衍了事,走过场的情况。因此,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转变侦查观念,把侦查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证明案件事实上,即在查明案件事实之后,用法律认可的证据去证明所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客观发生的事实。
2.增强工作责任心。对于侦查笔录类证据本身而言,存在问题的侦查笔录在大多数情形下会被视为“瑕疵证据”,在既无法补正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将会被排除。上文提到的侦查笔录记录错误、内容遗漏、签名缺失等问题,说到底还是侦查人员的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的。因此,在依法实施侦查行为的前提下,侦查人员必须强化工作责任心,注重工作细节,规范制作侦查笔录,确保侦查笔录的证据能力。
(二)以规范侦查行为为起点,保证笔录类证据的合法性
在侦查笔录概念中,包含两个基本范畴:一是侦查行为;二是笔录。侦查行为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不仅是制作侦查行为笔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直接决定侦查笔录记载的内容。侦查行为是否规范和合法,决定了侦查笔录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证据有无证据能力。因此,规范侦查笔录类证据,应当从规范侦查行为开始。
1.程序合法。首先,侦查行为应当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按法律要求进行审批。有些侦查行为的启动需要审批,如搜查、侦查实验、扣押、查封等;有些侦查行为在需要强制实施时才要求审批,如强制检查等。法律规定要求审批的侦查行为,只有在获得合法授权时,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实施侦查行为的主体要合法。侦查行为必须由侦查人员主持或者实施。针对特殊对象,还应由特定主体实施,例如,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三,实施侦查行为的过程要合法。例如,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进行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对查封、扣押的财物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查封、扣押财物、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查封、扣押清单,等等。第四,实施侦查行为时应当及时制作笔录。制作笔录是实施侦查行为的最后步骤,也是侦查行为程序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制作笔录要求即时性,即应当在侦查行为实施的同时或者结束后立即制作,不允许事后凭借回忆予以制作,以保证侦查笔录的客观真实性。
2.客观全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实施侦查行为的目的是收集证据、查清犯罪事实,查找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纳入侦查视线的若干侦查对象,既需要有罪证据认定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也需要无罪证据排除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嫌疑对象。因此,侦查机关在实施侦查行为时,为了保证对案件事实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准确认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
(三)以规范笔录制作为核心,保证笔录类证据的有效性
1.细化笔录体式,为制作侦查笔录提供指引。法律对于侦查笔录的规定,仅限于规定实施侦查行为应当制作笔录,应当由哪些参与人员签名或盖章。事实上,不同笔录有不同的记载要求。例如,对于笔录中“过程和结果”的内容,辨认笔录与搜查笔录的记载要求不一样,勘验笔录与侦查实验笔录也不一样。对于各种侦查笔录应当怎样记录或者必须记录哪些内容才能充分发挥其证明力,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相关规定过于粗放,缺乏有效指引,是造成笔录内容过于粗糙的原因之一。为了充分发挥侦查笔录的诉讼证明作用,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应当进一步完善各类侦查笔录的制作要求,细化各类侦查笔录应当记载的内容,便于侦查人员在实践中统一操作。美国学者理查德·塞弗施泰因在《刑事侦查学》一书中警告说:“做笔记的人应当铭记,在处理犯罪案件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书面记录可能是惟一能够帮助回忆的材料。笔记必须十分详细,以满足这样的需要。”[3]
2.对侦查活动实施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增强笔录的客观真实性。侦查笔录在诉讼证明中的意义,是通过制作笔录的方式将在诉讼过程中的某种侦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保全下来,使之成为对某种侦查活动的永久性记录,在时过境迁后,仍然可以通过笔录记载的内容帮助诉讼参与者回忆或者再现当时过程和结果。正如日本学者钢川正雄所说,“勘查无论怎样周密细致,如果不能将其结果正确表现在笔录上,也是没有意义的。笔录的使命就是为在日后看到它的第三者,特别是检察官、审判官面前能再现勘查时的情况,像直接见到活生生的现场一样容易被理解、被认识,从而充分发挥其作为证据的价值”。[4]传统的侦查笔录主要以文字记载方式为主。然而,文字记载的客观性,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记载人的感知判断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因素的制约。随着人类记录方式和手段的发展,侦查机关应当充分利用录音或录像的方式作为侦查笔录的辅助记录方式。法律以强制规定的方式,要求侦查讯问活动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于其他侦查活动,由侦查人员以必要性为原则,选择是否实施侦查活动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应当尽可能地使用录音或录像方式固定侦查取证过程,利用音视频资料动态、形象地反映侦查活动全过程的优势,弥补侦查笔录文字记录的不足之处,保证侦查笔录内容的客观真实性。
(四)建立执法责任追究机制,强化执行制度的约束力
侦查笔录是一类影响证据的证据,当其他证据证明能力与证明力,受到侦查笔录内容缺失或者形式欠规范的影响而被质疑或被排除时,落实到主办侦查员身上,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没有责任便没有约束。因此,侦查机关要加强内部执法监督,及时发现侦查取证中的问题,对于执法过程中有明显过错导致收集的证据无效或者被排除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以此强化侦查人员严格执行制度的约束力。
[1] 何家弘.刑事审判认证指南[M].法律出版社,2002:312.
[2] 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9.
[3] 乔耶·尼克尔,约翰·费希尔.犯罪案件侦破[M].贾宗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41.
[4] 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180.
Humble Comment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Investigative Records Concerning Evidence
Hu Lan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8, China)
Identification, forensic experiment records and so on have been added into the evidence categories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nacted in 2012, thus establishing the legal evidence status concerning identification,forensic experiment, search, seal, holding, evidence lifting records.This is a great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vidence system reformation.On the one hand, it has perfected and enriched the legal evidence categories and provided a new effective channel for judicial agencies to confirm case facts.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made new requirements for investigative agencies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and standardize their record making.As such,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investigative records,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investigative record making, research into the record-making procedure mechanism and probe into its standardization.
Investigative Behavior; Investigative Record; Evidence; Standardization
D915.3
A
1008-5750(2013)06-0048-(05)
10.3969/j.issn.1008-5750.2013.06.008
2013-09-18
陈 汇
胡兰(1983- ),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警务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南省常宁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