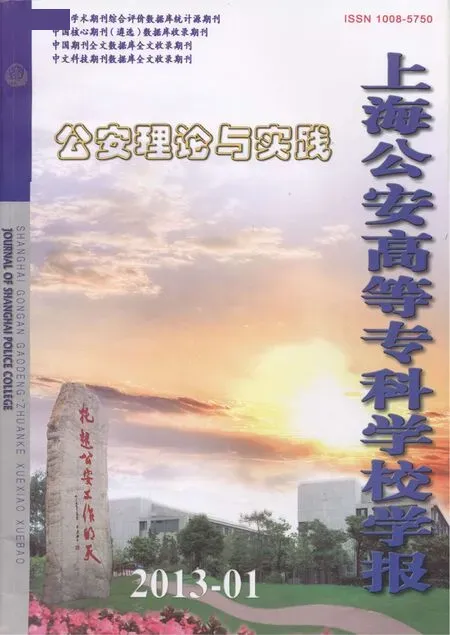英国警察自由裁量之作用及改革①
马德世,莫 燕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上海 200002;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 200070)
英国作为现代警察的发源地,在最初赋予警察职责时并没有严格的自由裁量概念。随着社会法制的进步和人权意识的增强,警察的自由裁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地承受需要节制与受限的呼声,但如何确切地规范自由裁量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调整体系,各国都没有成熟的经验或可资借鉴的立法例。英国近些年在警察自由裁量问题上正在进行深入探索,这对于研究规制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法理问题,指导我国现代警务机制建设或许有所裨益。
一、历史背景
1829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创建了“新首都警察”,他强调警察需要拥有智谋、自我拘束与克制性情的品质以及避免表现专横行为的能力。虽然中上层社会用非常尊重的眼光来看待警察,但如果警察碰到“下层大众”时,这种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当今这个警察的“黄金时代”,明显存在大量惯常性的执法错误与执法不当,但是警察作为国家自豪的象征,一直维系着提供慈善服务的神话。对于警察诸多的不利评价,从很大层面上讲,可能就是基于警察高度的自由裁量而导致的。对于一线警察最突出的问题是,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和责任与权力相伴,而执法错误又会被公众与媒体的恭顺本质所掩盖。
当前,情况已有了许多改变。自由裁量仍旧是一线警察日常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真正有价值的一个方面。然而,现在与之相伴的是更加严格的运行控制。要评价这是否确实会对当前的警察产生真正影响,就必须先考察与警察作出决定息息相关的工作性质。
二、警察自由裁量的性质
作为日常工作的基础,警察每天都要连续不断地在各项行动的诸多路径中作出选择,而低层警察更乐于获得高度的自治,因为自由裁量对于他们成功完成任务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刑事司法体系的“看门人”,警察处于准司法角色,他会选择潜在犯罪者,确定罪行并施加惩罚。在确定谁将进入刑事司法体系过程中,他们在客观上决定了法院审理的案件数。多数公众需要警察集中关注那些不应当发生以及那些需要迅速做出反应的事情。事实上,可能没有任何人类问题不能够实际成为警察合法的业务工作。警察权力源于一种原始的授权,警察在合法的范围内享有如何使用、何时使用法律与自由裁量的权利。
警察自由裁量的运行可以“调和法律的生硬”。如果在任何情形下都严格援引法律,那么不仅执法服务会因缺乏人力资源而崩溃,而且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也将无法承受负荷,有犯罪记录的人数必然剧增。因为仅仅实施了轻微犯罪行为而采取零容忍方式将如此众多的人打上“罪犯”的标记,可能会导致异端的不当扩张,进而将产生更加严重、长期、全面的犯罪问题。机械式的执法反对给予警察根据情形采取公正、适当的行为的机会。因此,自由裁量不仅合理而且必需。
然而,在现实中,它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理论层面上,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应当受到警察同等的考虑和对待。然而,对自由裁量权负面作用的考察表明,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事实上已经导致了罪犯、被害人范围的畸宽畸窄。对于罪犯而言,警察被认为是“创制”了这一群体,他们将该群体看作管控的特定对象,即“警察所有物”。英国学者博克斯曾提出“谁是警察自由裁量负面作用的主要承受者”这一问题,他认为多数执法行为主要针对于被社会排挤的人,他们常常是年轻人、穷人和黑人。警察寻求采取警力“差别配置”政策(将警力集中于目标居住区)以及“类别怀疑”(通常只怀疑全体人口中的有限部分)。这种缺乏统一性的警务方式,可能会在受到这样对待的接受终端那里产生一种不公正的感觉。警察行使自由裁量权可能因此产生并延续恶性循环,在该循环中,选择性判断会激起目标群体的负面反应,而目标群体的反应行为,将使警察进一步坚定最初的信念,即他们应当成为警务目标。
当然,在确定警察拥有广泛的裁量权范围即实施拦截和搜查等行为时,目标群体的行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可资证明的是,警察以上述方式对待黑人,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圣保罗、托克斯提斯和布瑞克斯顿地区的暴乱。虽然斯卡曼爵士认识到了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负面作用,并在关于布瑞克斯顿暴乱的报告中批评了消极裁量策略,从而导致警察权力在这一领域已有所削弱,但有证据表明,警察对黑人的侵扰仍在继续。
可以说,警务程序的改变可能会带来警察自由裁量权许多出乎意料的变革。这在众所周知的降格处理程序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种新的、非烙印式程序(例如对青少年采取警告而非逮捕)不仅可应用于对待那些已经被起诉的人,还可应用于那些还未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人。
三、警察文化之影响
如果警察的偏见和歧视会导致针对目标群体的执法过当,那么这种情形可能会因以破案率形式表现的强制性压力而加剧。很明显,为了警务利益,警察自由裁量将牺牲公共利益。政府以“公共安全”和减少犯罪恐慌为借口,要求警察清理街面上的可见犯罪,而放弃查处似乎更加严重且对社会破坏更大的犯罪。警察在操作中,一方面在放纵白领犯罪(例如欺诈,几乎没有为自由裁量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将轻微犯罪与反社会行为(基于它们具有很高曝光度,极易受制于警察自由裁量)设定为管控目标。这必然带来公众对警察自由裁量作用的疑问。
另一类犯罪是家庭暴力。警察对此不作为,基于家庭暴力系私人事件的理念而变得合理化。不干涉主义的处理方式意味着警察很少启动刑事程序,这直接导致此类受害人不愿举报。女权主义者及相关运动团体认为应当将这些问题暴露在公众的审视下,以激励改进处理家庭暴力的警务政策和思维方式。当前,犯罪被视为“警察的业务”。然而,仍然有可能,一定比例的犯罪被降低等级或被作为“非犯罪”处理。相似的情况在降格处理种族骚乱和暴力犯罪等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研究表明,直到最近,特别是在《斯蒂芬·劳伦斯调查》出炉之前,警察都不认为这些犯罪是严重的。
四、改革探索
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伴随着腐败、渎职、审判不公问题的出现,社会上产生了对警察自由裁量作用的质疑。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立法措施的演化与更迭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警察权力与责任的控制上。1962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回应了当时涉及警察权滥用问题的一系列丑闻。该委员会建议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即首先通过警察局长更加有效的监督,最终成功控制一线警察。然而,警察文化是一种非常具有对抗性的现象,它能够借助层级制度轻易规避自上而下控制一线警察的企图,因而情况并未发生改变。
1981年,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即菲利普斯委员会)报告将注意力转向低级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具体措施是要求警察记录施用裁量权的理由。该委员会改革的顶峰是建议制定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虽然这部法律认为警察仅拥有一项统一的拦截与搜查权,但同时它也试图拓展对犯罪嫌疑人的宽泛防卫权。《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宣称拦截必须基于“合理怀疑”才能够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搜查的理由必须被记录下来,如果公众愿意可以对其进行审查。很明显,《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其实施细则已经影响了警察如何解释他们的自由裁量,而不仅仅是他们施用裁量权的行为方式。但值得怀疑的是,警察是否能够记录所有的拦截行为,且他们的记录是否总是准确的。
《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因其话语的模梭两可性而倍受批评。诸如“如果切实可行”及“合理的怀疑”这些术语不甚明晰,导致警察具有相当大自行解释的空间。如果《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要更加有效,也许必然要使公民能够充分理解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依赖警察向他们传递这方面信息。《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施行之后,警察权继续在没有相关防卫措施的情况下持续膨胀,直至伯明翰·西克斯案件发生后,政府才开始于1993年寻求建立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重拾警察权和防控措施问题。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赋权警察能够在不需同意的情况下提取DNA样本,从而进一步展现了一个清晰的立法趋势,即在没有发展相应防控措施的情况下赋予更多的警察权。
另一系列改革,虽然不直接与控制一线警察自由裁量权相关,但也必然对其产生影响,因为这些改革旨在解决针对警察的投诉问题。应对针对警察投诉的程序法最初是由1964年《警察法》确立的。此后,1976年《警察法》和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等法律都倾向于将调查投诉的职责由警方转移给独立实体。最近的2001年《警察改革法案》建议建立一个新的警察投诉独立委员会。然而,这仍然不可能是一种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机制。因为不论谁来调查警察,他们都会碰到警察自由裁量权力运行可见度低的问题,故而难以支持投诉主张。
以上论述,似乎都在暗示旨在控制一线警察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改革鲜有成效。因为基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主观性质,它已被证明很难监督或控制。有人建议法律从法律规定与工作规范之间切入,继续对警察施加微小的道义强制。这导致许多人相信改革要真正起作用,必须将精力集中于一线警察的工作规范,使警察更加清楚地理解权力运行标准进而据此作出决定。从警察内部改变文化的策略,就要对此文化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警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有证据表明,由于警务工作的性质,当面对执法限制时,警察会产生孤立与怀疑公众的感觉,并伴随有挫折感与无权的失落。我们很难归纳警察文化的各种因素或建立在其上的固有性质。但始终如一的事实是,各种文化因素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也是警察感到最大威胁之所在。因此,任何通过改变警务文化而试图继续改变裁量权施用问题的尝试,必定会削弱生成并维系这一文化的警政实务的张力。这要求我们在讨论警察自由裁量权改革时,必须审视警察与公众的关系。
五、未来改革方向
警察权力与公众对警察支持程度之间以及公众的支持与他们为警察提供情报要求根除犯罪的自愿性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然而,警察可能会因过度或过少使用自由裁量权而弱化与公众的关系。因此,改革的呼声也同样集中于回归社区警务体系的要求之上。这一体系可能会降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因为公众会首先创造警察在某一事件发生时到场的理由。
但是,这一建议也存在不足之处,因为它仍要求警察在施用自由裁量权时,必须确定哪一类报警需要回应,进而判定哪些公众的需求优先于其他人。此外,必须记住警察的效率仍在以逮捕来衡量评价,将自由裁量权用于寻求非正式的解决方法以及预防恣意逮捕,那么社区警务的最佳作用便会隐而不见。如果倡导施行社区警务控制警察自由裁量权,必须清楚地考虑如何遵循各种指示以确定要求警察到场的问题。
这就是说,要成功地施行社区警务改革模式可能存在更加无法克服的障碍。当今的后现代社会不同于皮尔时代,它以分裂、多元、多样为特征,同质性和合意性更少,它是重叠、短暂并经常分离的。它暗示着排斥不断增长,而包容多数。社会增长的部分激发了犯罪率的上升,而这又产生对控制策略的需求,进而减轻对增长的排斥。因此,我们有必要回答这一问题,即通过社区警务的改革是否总是可行的。
“警务”这一术语可能不再仅仅意寓公共治安。2001年《警察改革法案》建议引入邻里守护与相互辅助,并且寓示随着警察作用与职责的重新配置,很快就能够拥有多元警务提供者。这使许多人会去反思将来是否仍将警察视为纯粹的“捕盗者”,以及社区是否要对社区警务负责。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从长期来看,自由裁量权会被缩减,它将从警察个人手上剥夺而嵌入知性体系。分裂的社会概念和警务提供者的多元化为针对施行警察裁量权的成功改革提出了更大的质疑。在一个等级的、破碎的社会,警务活动似乎从来不可能产生平等的作用。
对于警察自由裁量权改革的努力仍停留在这一假设之上,即刑事司法体系最初的产生是为了侦查和惩罚犯罪行为。然而,这一假设可能受到挑战。许多人相信当前的实践反映出包容白领罪犯、排挤穷人即社会上最无权和贫穷群体这一过程。某些最具破坏力的罪犯被以最人道的方式对待,而这一体系的优先选择和对无权者的控制凌驾于司法、法律规则以及被害人之上。执法过程的运作在于隐藏有权者对无权者的犯罪,揭露无权者对每一个人的犯罪。那些社会的被害人被当作社会的敌人,所以最终他们被贴上了标签,并因此保留了运用在他们身上的国家权力。
由于犯罪和失范行为已经有所增长,警察强制力亦随之增长。现在被贴上了“警察所有物”标签的庞大下层阶级,将会产生更多的不法行为。然而,如果这些仅仅是问题的表象,那么旨在改变自由裁量权实务的改革将会彻底失去意义。在提出新的警察自由裁量权改革策略之前,应当考虑是否“存在比国家所揭露的更多的犯罪和犯罪者”。被政府社会化了的所有公民以政府的视角看待犯罪和犯罪者。在考虑警察自由裁量权时,有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应当受制于没有(并不可能)被同等施用的一线警察权对于自由的干涉。对于那些在社会上作决定的人而言,很容易为了社会利益决定牺牲犯罪嫌疑人的自由。因此,与其问英国社会如何改革警察自由裁量权,也许还不如问对这种权力被用于维持现存不平等与从属结构的研究还能走多远。
如果研究者推断这种权力被广泛地用于这一目的,那么也许改革警察自由裁量权注定要失败。毕竟,当中产阶段受到威胁时,自由领域的主要进步是否能得以保障必然是富有争议的。从一种更少怀疑的立场出发,改革的终极产品不会成功地使警察回到他们作为受人敬爱的国家骄傲象征的那种状态。在后现代社会里,警察不能够起到神圣图腾的作用。然而,对将来警察自由裁量权改革更加具有破坏力的是,现实中的警察不知不觉地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而存在,去保护社会的不平等。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任何一种伪改革注定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