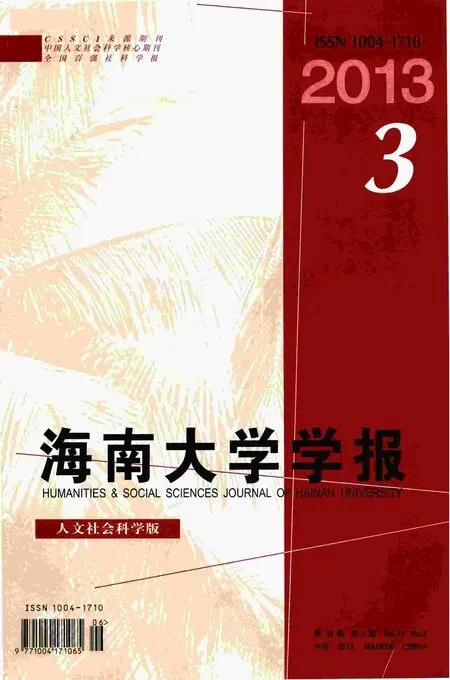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文学内涵发微
孙宗英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不仅以古文大家闻名后世,更是我国金石学史上的开山鼻祖。他自云“性顓而嗜古”,其后半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大力收集前代金石铭文,成煌煌巨著《集古录》一千卷。对此欧阳修十分看重,把它与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及“吾一翁”一起构成了流传后世的“六一居士”之名。后因友人建议,“不若举取其要,著为一书,谓可传久”[1]2420,又撰跋尾四百余篇,编为十卷。但历经北宋末年的兵燹战火,《集古录》早已零落散佚,所幸《跋尾》十卷因附文集得以保存至今,使我们得以窥见欧阳修所集金石铭文之一斑。因《集古录》的散佚,《跋尾》所具有的高度学术价值便格外凸显,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正如欧阳修所云:“得与史传相参验,证见史家阙失甚多”[1]2420。学界对于《跋尾》在金石学、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价值阐发颇多,相关研究成果甚多。但《跋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宗师,跋文中涉及的文学材料亦非常丰富,其中不乏与古文理念及创作相关者。我们知道,在欧阳修一生中,集古活动和倡导古文复兴堪称是用力甚深、历时弥久的两件大事。那么,《跋尾》的零篇断章中蕴含着怎样的古文理念,欧阳修倾尽热情的集古活动又与其毕生着力的古文革新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二者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发生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文体的复古与变新
《集古录跋尾》中约三分之二的跋文写于欧阳修57 岁以后的晚年,因此虽多为只言片语,也皆为成熟之观念。多数跋文在记录碑刻的体例、著述、品藻之外,亦涉及文体方面的丰富内容。
翻开跋尾十卷,处处可见欧阳修集古的巨大热忱,对此倾注的大量心血。有些墓志是其求之十五年而得,如《唐窦叔蒙墓志》;有些碑刻得到时已残阙不堪,欧阳修仍如获至宝,如《唐张敬因碑》;有些碑文自己无缘目睹原石,得到友人拓片,则“惊喜失声”。由于对集古的极大热情,在长期接触古碑石刻的熏染下,欧阳修明显表现出对古器碑铭所具有的简古质实风格的喜爱和推崇,在《跋尾》中他对碑刻简古的称道比比皆是:“尝观石鼓文,爱其古质”[1]2069;“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1]2243。尤其对西汉碑刻及其映射的简质世风和质朴文风,更是大加赞赏:“汉世近古简质”[1]2111,“汉人犹质”[1]2119,“前汉文章之盛,庶几三代之纯深”[1]2108。对质朴中出现的文采彬彬现象,也颇称许:“其字画颇完,其文彬彬可喜。”[1]1136
这种崇尚简古质实的文体观念是影响欧阳修碑志文乃至是整个古文理论及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认为,欧阳修古文创作的发轫期始于天圣九年(1031年)至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时①参见《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而不可忽视的是,欧阳修正式的集古活动虽始于庆历年间河北转运使任上,但其对古碑的浓厚兴趣却早在天圣四年(1026年)赴京参加科考之时已显露出来②参见欧阳修《后汉樊常侍碑》:“天圣四年举进士,赴尚书礼部,见此碑立道左,下马读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后三十年,始得而入《集录》。”,当时欧阳修刚刚20 岁。而且在跋《唐孔子庙堂碑》中,欧阳修还清楚地记得“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可见,欧阳修自少年时就对古碑情有独钟、兴趣盎然,且这种热爱长期以来与崇尚简古的审美趣味相辅相成。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因素固然很多,如自小倾慕韩文的经历,洛中文坛的因缘际会,古文创作成就斐然等,而其崇古集古的兴趣背景和推崇简古质实的审美心理也是重要方面,后者却鲜有研究者论及。
欧阳修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碑志文,据统计,卷数超过了文章总卷数的三分之一③见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页。,其复古主张也集中于他的碑志文理论,这与集古活动有很深的渊源。他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中提出作墓志铭的几项原则,如“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用意特深而语简”等,这些观点可以用“简而有法”和简约峻洁来统括。追求简约峻洁的文体风格往往在作法上要求止记大节。碑志文的价值除了寄托哀思之外,更重要的是追求传世久远。他通过长期收集碑刻铭文的切身经历体会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1]600,故其子欧阳棐在《集古录目记》中传达其父观点云:“夫事必简而不烦,然后能传于久远。今此千卷之书者,刻之金石,托之山崖,未尝不为无穷之计也。然必待集录而后著者,岂非以其繁而难于尽传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详者,公之志也。”欧阳修在《内殿崇班薛君墓表》中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予考古所谓贤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铭见于后世者,其言简而著。”
欧阳修对碑志文体崇尚简约的主张,既有承继刘知几“叙事之工者以简为主”[2]之处,也源于他“碑史同质”的理念。他认为碑志和史传文体在纪实传世方面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可“与史传正其阙缪”“以此见史家之妄”[1]2183。传世久远之碑志已是史传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集碑刻铭文的经历使其渐渐熏染出推崇简古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和“碑史同质”之观念一起构成欧阳修在碑志史传革新中复古的一面,坚守传统文学思想中由《春秋》一脉而传的“义法简严”之阵地。
如果欧阳修的文体主张仅有复古的一面,那么北宋文学史就会少一位星光璀璨的文章宗师,后世也无缘领略婉转摇曳、声情并茂的“六一风神”之美。欧阳修在古文上取得的斐然成就是与其勇于创革善于新变分不开的。他在坚守复古的同时,锐意变革的精神,也蕴涵于《跋尾》之中。
欧阳修虽然对于碑文在后世由简到繁的发展趋势颇有微词,但他并不是一味地固守原有体制,拒绝一切新变。如在古今立碑撰文之顺序不同的问题上,其态度就颇为通达:“盖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楼……今人立碑须镌刻成文,然后建立。盖今昔所为不同,各从其便尔。”[1]2221欧阳修也并不是呆板地泥古,并不认为一种体裁必须要具备专属于它的风貌。在《唐皇甫忠碑》的跋文中,他对台省文字表现出来的清新别致之风大加赞赏,而并不指责它违反了典雅厚重的传统风格。这也是欧阳修在复古的基础上主张变新的一个方面。
有关碑文的体制变革,欧阳修的《唐元稹修桐柏宫碑》集中地表现了自己的看法:
右唐元稹撰文并书。其题云《修桐柏宫碑》,又其文以四言为韵语,既牵声韵,有述事不能详者,则自为注以解之。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尔,古者刻石为碑,谓之碑铭、碑文之类可也。后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谓之碑文,然习俗相传,理犹可考,今特题云《修桐柏宫碑》者,甚无谓也。此在文章,诚为小瑕病,前人时有忽略,然而后之学者不可不知。自汉以来,墓碑多题云某人之碑者,此乃无害,盖目此石为某人之墓柱,非谓自题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宫碑》,则于理何稽也?
这篇跋尾,有两处颇可注意:其一是关于“为文自注”。欧阳修明确提出反对“为文自注”,而遍检欧集,确实无一处文中自注。但据此而认为欧阳修排斥自注则大错特错,欧阳修反对的是“为文自注”,并不反对“为诗自注”。实际上据笔者粗计,欧诗中自注多达125 处,有诗题注、诗句注多种样式。这些自注或解释风俗名物,疏通典章制度,或说明作诗缘起,进一步呈现诗歌创作背景,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拓展了诗歌意境的创造空间。“诗歌自注借鉴演变于史书自注,始于南北朝时期,至唐代得以持续发展。”[3]欧阳修并没有完全拒绝自注这种从史书而来的创作方式,但对于所用对象——诗文的区分却是泾渭分明的。也许在欧阳修看来,诗歌有字句格律之限,“有述事不能详者”则用自注加以疏通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文章并无字句格律等各种限制,“有述事不能详者”则说明其为文功力技巧尚不成熟,有待提高。由此可见,欧阳修内心对于文章创作的要求甚高,进行古文创作是其一生着力甚深的创举,是其念兹在兹的一项事业。同时,欧阳修认为诗文在某些创作方式的采用上还是有严格区别的。在自注问题上诗文有别,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补充对欧阳修文体观的认识。其二是关于碑文新变的尺度。欧阳修认为,元稹的《修桐柏宫碑》之题已远远背离了碑体发展的应有之义,跟碑这一名称的缘由用途及体例相去甚远。欧阳修在此要申明的主张是,碑文的新变应有理可据、循序渐进,议论发明也必须以真知灼见予人启悟,而过度背离原有发展轨道,哗众取宠、求奇取胜的凭空新变只会贻误后学。《跋尾》中类似这样的表述不在少数,如《唐韦维善政论》中批评只异其名而无其实的做法:“(杨)齐哲所撰,其实德政碑也,特异其名尔。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悟,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遂不胜其弊矣。如齐哲之文,初无高致,第易碑铭为论赞尔。”他在批判杨齐哲的同时,也捎带批判了元结、樊宗师,可见对二人的怪奇文风也颇为不满并加以否定。《跋尾》中另有几篇是专门批判元结之好奇好名与樊宗师的怪诞僻涩的④见《唐元结阳华岩铭》、《唐元结洼尊铭》、《唐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虽然欧阳修也肯定元结“独作古文”的历史功绩[1]2262,但是似乎已经被对他的批判之声淹没了。或许在撰诸篇跋文时,欧阳修又回想起嘉祐二年权知贡举时,打压怪诞僻涩的“太学体”古文、取“平淡造理”[4]之文的艰难阻力。“文体复归于正”[5]的成果得来不易,所以才会在晚年仍念念不忘加以重申。
二、文辞的尚真与求工
与文体的复古与变新相联系,欧阳修对于碑文的文辞也有自己的衡定标准,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处理好尚真与求工的关系,这在《跋尾》中亦有较多表现。
欧阳修特别强调碑文的真实性。他称赞《唐于夐神道碑》云“其文辞虽不甚雅,而书事能不没其实”。由于碑碣多为当时所立,史传记载多是后世追述,欧阳修常以碑证史,补史之阙或证史之讹,这在《跋尾》中俯拾皆是。不过欧阳修并不盲从碑志,对于碑文中讹误之处,他亦能分析辨明:“据碑言,刺奸、司命为光武时官,盖碑文之谬矣。”[1]2121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敏锐地认识到碑碣多为碑主门生故吏所立,碑文中所记勋绩功德,多有不合事实处,不能一味信以为真,在《跋尾》中他多次指出“自古碑碣称述功德,常患过实”[1]2156。对此,他选择去取的方法是“惟取其世次、官、寿、乡里为正,至于功过善恶,未尝为据”[1]2301。欧阳修认为,碑志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准确,“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1]984。他对碑志内容真实性的提倡还贯穿于自己为他人撰写的墓志中。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逝世,欧阳修受命作《范文正公神道碑》,碑中记述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之事,引起墓主家属的强烈排拒,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断然删去范、吕和解的一段文字,“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6]。欧阳修在此压力下却不为所动,毅然坚持纪实的创作原则,并阐述其纪实创作的深远意义:“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雠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词也。”[1]2474因纪实性强,“欧碑的很多内容为李焘著名的编年体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用。欧碑的主人公近四成《宋史》有传,《宋史》亦多采用欧碑的内容”[7]。
另一方面,欧阳修还非常重视碑文的文辞,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力求精工。在《跋尾》中,这种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是力避俗语,追求古雅流畅。《跋尾》中经常能看到欧阳修对碑文文辞粗浅的批评和以此为憾的感叹:“碑文辞非工,而事实无可采”[1]2305,“然患其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1]2173,而对碑文中出现的优美文辞却心动不已:“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1]2243。如果仅是为文工巧而失其事实,是欧阳修所要摒弃的。他在跋《唐卫国公李靖碑》时说:“唐初承陈、隋文章衰敝之时,作者务以浮巧为工,故多失其事实,不若史传为详。”但对于俚俗之语,怪异之事,事涉君相儒道者,亦颇有采录。如其跋《唐万回神迹记碑》云:“其事固已怪矣。玄宗英伟之主,彦伯当时名臣也,而君臣相与尊宠称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传道士骂老子云:‘佛以神怪祸福恐动世人,俾皆信向。而尔徒高谈清净,遂使我曹寂寞。’此虽鄙语,有足采也。”其二是崇尚笔力,追求老成雄健。欧阳修是著名的史家,善于以史笔作文,长期的集古活动和以金石证史的学术活动让他在某种程度上视碑史为同质,二者纪实传世的性质没有差别。这种观念使欧阳修以史之标准律以碑志,尤其是具有纪传色彩的个人之碑,欧阳修认为它们有为逝者立传的功能,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具有传世意义,笔力的轻重高低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墓主其人其事能否流传后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碑文的写作要求就不只是简单的求真求信与文辞华美,而要在更高层次上具有笔力独扛波澜老成的雄健气势。笔者举跋《唐田布碑》为例进行个案分析: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壮矣,承宣不能发于文也,盖其力不足尔。布之风烈,非得左丘明、司马迁笔不能书也。故士有不顾其死,以成后世之名者,有幸不幸,各视其所遭如何尔。今有道《史》、《汉》时事者,其人伟然甚著,而市儿俚妪犹能道之。自魏、晋以下不为无人,而其显赫不及于前者,无左丘明、司马迁之笔以起其文也。
这篇跋尾议论精警透辟,指出历史有真实与建构两种,真实的历史已随时间消亡,流传后世的皆为建构之历史,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笔力在建构历史中的作用甚为关键,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显赫之伟人须仰仗班马之巨笔才能著于后世,因此,不是史无伟人,而是如椽之笔难得。文辞的雄健、笔力的老成在这里被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跋尾》中欧阳修不止一次地感叹“士有负绝学高世之名,而不幸不传于后者,可胜数哉!可胜叹哉!”[1]2197在为历史上负绝学之士湮没感慨的同时,欧阳修非常重视碑志文的垂世价值,这是对刘勰提出的“属碑之体,资乎史才,……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8]文学理想的实践。这个观点对其门生也产生了影响,如曾巩就明确地论及“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9]。而欧阳修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自觉秉承《史》、《汉》传统,用雄健之笔发时人之“风烈”,使之流传后世。如在《桑怿传》中他即忐忑地提出希冀:“怿所为壮矣,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其所作碑志文,如《石曼卿墓表》、《黄梦升墓志铭》、《泷冈阡表》等都是传世名篇。后世论者也大多注意到了欧阳修继承太史公之处,并予以高度赞扬。明艾南英即云“试取欧阳公碑志之文及五代史论赞读之,其于太史公盖得其风度于短长肥脊之外矣”[10]。清古文家方苞更是盛称欧阳修的碑志文“摩《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11]。
三、跋文呈现的“六一风神”
欧阳修作为古文运动之起承转合之关键人物、宋文六家的领袖,其古文风格已臻炉火纯青之化境。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12]这也成为欧文风格最经典的概括,世人美其文曰“六一风神”。“六一风神”作为专用术语,屡见于近人著述当中⑤有关“六一风神”的定义及演进,可参黄一权《欧阳修散文研究》第三章专门论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167页;洪本健《略论六一风神》,《文学遗产》1996年第1 期,第61-68页;刘宁《叙事与“六一风神”:由茅坤风神观切入》,《文学遗产》,2011年第2 期,第100-107页。。吕思勉在《宋代文学》中说:“今观欧公全集,其议论之文如《朋党论》、《为君难论》、《本论》,考证之文如《辨易系辞》,皆委婉曲折,意无不达,而尤长于言情;序跋之文如《苏文氏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碑志如《泷冈阡表》。《石曼卿墓表》、《徂徕先生墓志铭》,杂记如《丰乐亭记》、《岘山亭记》等,皆感慨系之,所谓‘六一风神’也。”[13]陈衍在《石遗室论文》中说:“世称欧阳文忠公文为‘六一风神’,而莫详其所自出。……永叔文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杂记尤以丰乐亭为最完美,……一波三折,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此欧公平生擅长之技,所谓风神也。”[14]概言之,“六一风神”之特点集中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纡余委备而条达疏畅,二是急言竭论又容与闲易,三是叙事纵横而感慨系之。在《跋尾》的行文中,欧阳修随手所记的零碎篇章也如吉光片羽,使“六一风神”再次得到了传神的展现,其三个特点或综合于一则跋文之内,或散见于多则跋文之中,或集中呈现,或分别渗透。
第一个方面,纡余委备而条达疏畅。古碑题跋,虽然随物而著言,因事而生文,而欧阳修既能够婉转表达复杂的情事,随时控勒自己的笔端,以使跋文曲折变化,又能随物赋形,条达疏畅,故读其文,既觉曲径通幽,又感自然平易。笔者举《跋唐华岳题名》为例:
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讫后唐清泰二年,实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人。往往当时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侄并侍,或寮属将佐之咸在,或山人处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劳;或穷高望远,极登临之适。其富贵贫贱、欢乐忧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变多故。开元二十三年丙午,是岁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颂太平,请封禅,盖有唐极盛之时也。清泰二年乙未,废帝篡立之明年也。是岁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门,废帝自焚于洛阳,而晋高祖入立,盖五代极乱之时也。始终二百年间,或治或乱,或盛或衰。而往者、来者、先者、后者,虽穷达寿夭,参差不齐,而斯五百人者,卒归于共尽也。其姓名岁月,风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独五千仞之山石尔。故特录其题刻,每抚卷慨然,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
跋文一方面指出华山上浩瀚的题名中体现着诸多“人事百端”、“世变多故”,有很高的历史实录价值;另一方面,在对题名起讫年代的解读中,深刻地揭示出朝代兴衰,时运变迁,治世或乱世,都改变不了芸芸众生的求名之心。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题名者“归于共尽”,所题之名也并不能让这诸多“知名士”千古留名,永恒伫立于时空的只有华山“五千仞之山石尔”,把一腔寓意感慨、讽刺讥评深婉妥帖地蕴含于平和的叙述中,吞吐俯仰,含蓄蕴藉,“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15]。跋文突出题名起讫年代的典型历史代表性:“有唐极盛之时”与“五代极乱之时”,在强烈的对比中突出沉重的历史兴衰感和透彻的哲理思辨性,让人读罢不禁唏嘘感慨,掩卷沉思。如刘壎所云“寓意感慨,读之令人凄然。”[16]语言上时骈时散,充分体现散文诗化的特点,紧致又不失风韵,寓整齐于错落之中,读来有一种别致的节奏之美。前半部分六个“或”字的连用,造成一气呵成又跌宕起伏之感。后文“也”“尔”“者”等虚词的运用增添了摇曳多姿的情韵之美。叙事迂徐委备,委婉曲折,而行文则条畅明晰,富有神采。
第二个方面,急言竭论又容与闲易。古人论文,往往重意长言长,臻于容与闲易之境,若气尽语极,则难于条畅。欧阳修作文融急言竭论和容与闲易为一体,确是古今独步。笔者举《晋王献之法帖一》为例:
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敝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
这篇跋文可分四层分析:一层由自己的喜好以“想见前人之高致”;二层就法帖之体制言其一般情况“简短而已”;三层乃观王献之法帖过程及所引发的心理变化,始则“骤然惊绝”,终则“想见其人”;四层以今昔对比而见终老穷年者之可笑。就每一层而言,都是急言竭论,而合并读之则又气舒言畅,容与闲易。这既不同于《跋唐华岳题名》的深邃思辨,也不同于下举《唐韩覃幽林思》的深情追忆。它巧妙地融议论于流转的叙述中,观点鲜明,对比突出,而又使人不觉其说理生硬,如水中撒盐已化于无痕。短短二百余字看似一气点就随意成文,却圆美流转如弹丸,行云流水的叙述中传达出的是欧文的炉火纯青。茅坤云“遒丽逸宕,若携美人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17]此篇跋尾足以当以上评语。
第三个方面,叙事纵横而感慨系之。欧文动人之深处,在于叙事时寓于感慨,以成文章,读之有如秋风北至,落叶纷飞,顿觉凛然有怀,感慨万千。我们举《唐韩覃幽林思》为例:
余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因游嵩山得此诗,爱其辞翰皆不俗。后十余年,始集古金石之文,发箧得之,不胜其喜。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
这篇跋文朴实无华,但堪称“寓情于事的精妙小品”[18],扑面而来的缅怀伤感之情以足以让人动容。记述的角度没有落在韩覃《幽林思》诗本身,却笔锋一转,追忆起昔日游嵩情景。看似随意,实则为情难自已。《幽林思》诗为追忆打开一个缺口,昔日的壮游青葱岁月便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游嵩已是三十一年前的陈旧往事,然而这两次游历的时间、游伴等具体的细节仍在欧阳修脑海中真切的浮现,毫不褪色。真切的记忆背后是嵩山之游的尽兴与酣畅,是朋友知己情谊的深厚与难忘。跋文看似不厌其烦的繁琐记述游嵩的种种,字里行间却是压抑不住的感慨追思,对故去的友人,对流逝的岁月,对自己的沧桑暮年,有太多的感触情怀纷沓而至,而跋文却仅以“感物追往,不胜怆然”一句收尾,所有的感慨都收括其中,藏蕴其中,使文字充满了蓬勃的张力。如林纾所云:“欧公一生本领,无论何等文字,皆寓抚今追昔之感”,这一“追字诀”,“俯仰沉吟,有令人涵咏不能自已者”[19],便成就了欧文长于言情、议论风发的六一风神。近人李刚己云:“欧公文字凡言及朋友之死生聚散与五代之治乱兴亡,皆精采焕发,盖公平生于朋友风义最笃,于五代事迹最熟,故言之特觉亲切有味也。”[20]堪称精妙之论。再如《唐景阳井铭》,欧阳修所见时已漫漶磨灭,可识者仅十一二,而其作跋语在叙述铭文来龙去脉之后有云:“叔宝事,前史书之甚详,不必见于此。然录之以见炀帝躬自灭陈,目见叔宝事,又尝自铭以为戒如此,及身为淫乱,则又过之,岂所谓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铭文隐隐尚可读处,有云‘前车已倾,负乘将没’者,又可叹也。”对于文字磨灭殆尽的碑铭发此议论,读之使人顿生感慨。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42[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刘知几.史通通释:卷6[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8.
[3]魏娜.论中唐诗歌自注的纪实性及文献价值[J].文献,2010(2):39-50.
[4]韩琦.安阳集:卷50[M]∥文渊阁四库全书:1089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540.
[5]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二之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7:4599.
[6]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2[M].上海:上海书店,1990:4.
[7]洪本健.论欧阳修碑志文的创作[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2):5-13.
[8]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57.
[9]曾巩.曾巩集: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3.
[10]艾南英.天傭子集:卷2[M]∥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627.
[11]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4[M].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15.
[12]苏洵.嘉祐集笺注:卷12[M].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28-329.
[13]吕思勉.宋代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14.
[14]陈衍.石遗室论文:卷5[M].无锡:民生印书馆,1936:1.
[15]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31[M]∥续修四库全书:134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9.
[16]刘壎.隐居通议:卷13[M]∥文渊阁四库全书:866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24.
[17]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G]∥王水照.历代文话:2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786.
[18]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G]∥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71.
[19]林纾.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评语卷6[M].慕容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55.
[20]李刚己.古文辞约编:丰乐亭记题解[M]∥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