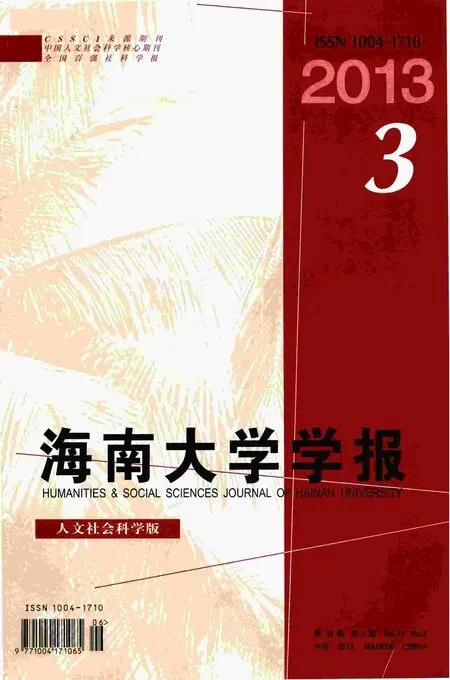设证推理的正当性及其运作——基于司法过程的考察
孙光宁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法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一、设证理论的特征:在演绎和归纳之外
在逻辑推理的种类中,设证是与演绎和归纳推论相并列的一种推理形式,其基本含义在于从一系列既定的事实和条件中获得一种假设命题(hypothesis),一旦这种作为结论的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它就能够对那些事实进行解释。从本质上说,设证理论是一种溯因推理,在已经具备结论的前提下来寻找对其最佳的解释,它与演绎和归纳的区别可以用以下逻辑图式来展现,见图1:

图1 演绎法与设证法区别图
相比于演绎和归纳,设证理论在历史上出现得较晚,主要是由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所创立。皮尔斯在论及设证法与演绎和归纳之间的区别时曾说:“设证是一个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假设的过程,……演绎证明某事是必然的(must be);归纳说明某事是实际存在的(actually);设证仅仅展示某事是很有可能的(may be)。”[1]在其后的研究中,这种独特的推理方法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并被认为是很多科学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例如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Charniak 和Mc-Dermott 在其著作中将设证视为“回溯性的离断律”(modus ponens turned backward),哲学家哈曼(Harman)则将其概括为“追求最佳解释的推论”(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2]。这样,设证就有了更为明晰的图示,见图2:

图2 设证推理图
设证的关键就是为既定的事实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明性的假设,即使最终出现了其他的假设能够更好地说明结论,那么原先的假设起码能够为更佳的结论提供正面或者反面的支持。进而言之,“不确定性”是设证理论的总体特征,它的具体表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设证针对的对象是某种假设,而该假设的真实性只是初步赋予的,在没有经过检验之前并不能在特定场景下确实地成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出现了新的假设在解释力和接受程度上优于原有的假设,那么,新的假设就能够取代原假设的地位而成为更好的推论。也就是说,各种假设之间基于解释力的不同而可以进行比较和排序,也就是说,设证推论是一种非单调逻辑(non-monotonic)。
其次,设证推理的过程具有变动性。这种变动性一方面体现在新的假设取代原假设(质变),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新的事实(或者数据)作为变量的改变能够对最初的假设进行修正(量变)。这种修正的不断进行能够确保原假设的解释力不断增强(plausibility)。
第三,设证理论具有明显的循环性特征。从总体运行过程上看,设证总是要经历假设阶段和检验阶段。随着相关事实(或数据)逐渐被检验过程吸收或者参考,原有的假设及其组成部分便会进行相应的变动。而后出现的结论也会反过来重新审视和确定原假设每个具体部分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循环的过程与解释学上的循环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部分—整体—部分的循环过程,最终尽可能地保证结论的真实性。
总之,对象、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都体现了设证推论的不确定性特征,因而,设证推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似真推理”[3]:它并不保证最终推论的绝对真实性,但是,它起码能够排除众多不能成立的假设而促成结论接近真实的最大可能性和接受性。在这里,可能性与接受性成为在整个设证过程中对假设进行确证(confirmation)的最重要的因素[4]。前者更加侧重于假设自身,例如原假设P 优于其他假设的程度、P作为假设自身的质量以及其所依据的事实(或者数据)的可靠性;后者则更多地考虑假设所面对的受众,例如要确切断定假设真伪所需成本这种实用主义的考量。
逻辑学中的设证理论有着复杂的结构图示[5],甚至有很多学者将其与贝叶斯定理的运用相联系。而法学领域,特别是司法领域的研究中,情况却有所不同。一方面,演绎和归纳已经成为重点内容,但是,单独的演绎或者单独的归纳都不能涵盖司法过程的性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司法过程的主要性质,而设证理论却没有引起相关的重视;另一方面,司法过程的实践性、操作性和程序性的特征又使得我们能够摆脱纯粹数理逻辑符号的抽象运用,能够为设证理论在司法过程中的讨论提供一定的具体时空条件,毕竟,复杂的逻辑符号运算是难以受到包括法官、当事人和社会一般公众的司法受众的欢迎的。波斯纳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法律推理’这种东西,律师和法官以实用简单的逻辑和日常思考者所使用的各种实践推理的方法来回答法律问题。”[6]。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观点,长期司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职业素养必然使得裁判者在进行推理的时候不同于日常思维,也即法律推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笔者看来,虽然设证理论并没像演绎和归纳那样成为司法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但是,它却能够从另类的层面上说明司法过程的性质和真相。
二、设证的正当性:从起点开始论证
在经过后现代法学的反思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司法领域中绝对的确定性仅仅是一种神话,而司法过程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商谈和对话的过程,不再是传统法学意义上的法官独断。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当事人(及其律师)与法官之间、事实与规范文本之间,这两对对应关系都在进行着沟通和交流,以期形成最终判决结果。虽然司法三段论受到了一些攻击,但是,就目前的司法实践以及宏观理论建构来看,三段论仍然在司法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司法三段论中所贯彻的正是演绎逻辑这一以获得必然性结论为目标的推论形式。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基本上都是依靠这种以演绎推理为核心的方式来在司法场景中提出自身的主张。这一场景可以用图3 来表示:

图3 司法三段论演绎逻辑图
也就是说,仅仅从形式上来看,当事人和法官都需要通过演绎推理来表明自身结论的“必然性”。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众多的研究成果已经揭示,司法过程最终形成的结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必然结论并不是司法过程的真正性质。换言之,如果必然性并不是司法过程的真相,那么经过检验的高度或然性就能够弥补必然性缺失后形成的真空地带。从司法运作的过程来看,根据科斯定理,如果司法资源足够充分的话,法官无需当事人的举证而自行收集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那么,法官可以直接根据案件事实作出司法判断。这种独断的结论的确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演绎推论必然性的表现。但是,司法活动的现实总是与这种理想状态有所差距,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演绎推理是无法使司法过程获得有力的支持。
从司法运作的实质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司法过程必然有一定的起点。现有的司法裁判理论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得出裁判结果,而没有对这一过程的起点予以重视。而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与预设相类似的“起点”决定着整个司法过程的走向,其地位和作用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展示。
就当事人而言,由于利益冲突和纠纷产生,因此,维护自身的主张成为其当然的选择,而这种主张往往与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是相互对立的。也就是说,维护自身的利益主张成为当事人参与司法过程的起点,这一预设的地位影响甚至决定了当事人在整个司法过程中的活动,包括运用演绎推理进行法律论证在内。如果说逻辑学中关于最初的假设如何得出的,还没有形成实证性结论的话,司法实践以及当事人利益的具体性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答案。这种情况实质上是一个设证的过程:当事人的主张相当于最初的假设(未必为真),在经过检验(司法程序的运行)之后,经过修正的假设优于任何其他的解释,那么,这一修正假设(最终司法判决结果)就很可能为真。正如卡多佐所说:“如同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一样,法律结论的有效性必须经受可能性逻辑而非必然性逻辑的检验。”[7]
从法官的角度来看,需要强调的是“法律感”的作用。由于预设的中立地位,法官不能像当事人那样预设地具有具体的结论性观点。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法官仅仅尾随于当事人之后亦步亦趋,相反,从最初接触到案件开始,法官的主观方面必然对案件形成一定的初步印象,这种初步印象中必然有对案件性质及其相应结果的初步判断。霍姆斯甚至声称:“普通法的美德之一就是先决定案件然后再确定其中的原则。通过观察其中的逻辑形式就可以得知,一旦你获得了一种部分的(minor)前提和结论,那么,必然会有更主要的(major)前提和结论,而后者正是你要准备获取并公布的。”[8]这种情况更多地是依赖于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经验等因素,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角度可以称之为“法律感”、“法感”或者“法权感”。“法律感在法律发现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律命题就是随着法律感而涌现的,它是法律论证的前奏,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法律论证的命题的质量,凭借高质量的法律感,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真命题,而低质量的法律感所发现的命题,即使经过论证也不一定有说服力。”[9]正是基于“法律感”,法官才能够形成初步的意见或结论,这就相当于设证推论中的最初假设。甚至可以说,“获致任何一项法律上发现或决定,以及判断该项发现或决定是否正当、合理,第一种可能的认识根据就是‘法权感’”[10]同样,随着司法程序的进行,在当事人不断提出各种事实及其相应主张并就此进行辩论和论证之后,法官的“原假设”也不断经受着检验和修正,最终形成最具解释力的结论(裁判结果)。同样,对于具有相似的知识结构和法律思维的律师来说,在接触到案情之后,也是一个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的过程[11]。
这样,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起点”(假设),并以此为依据来确定自己在司法过程中的行动方向,无论是进行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或者法律论证都是以这一起点为中心展开的。而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检验和修正来形成一个最具解释力的结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设证推理才是整个司法过程的真相,它为整个司法过程提供了起点,并以此为中心推动了以后的程序运行,从而在宏观上搭建了整个司法过程的框架。“设证是在每次包摄(即涵摄)之前就进行了。然而精明的法律人几乎都系敏捷而不假反思地在实施这种推论,以致这种推论并未被意识到。”[12]113这里仍然需要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假设与法官的假设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来源上,更重要的是,虽然二者能够在司法程序中形成某种对话商谈,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法官的假设,毕竟,司法权的存在赋予了法官以裁判的权力,虽然这不可能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想商谈,但是,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来说却是相当必要的。
简而言之,设证推理的过程从整体框架上还原了司法过程的整体运行状态,是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的法律推理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设证推理具有正当性,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设证推理重塑司法运行的全部过程。
三、设证的运作:程序中的肯定与否定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设证推理在实质意义上为整个司法过程设计了宏观框架,整个司法进程就是一个从提出假设(结论)到检验、修正假设(结论)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设证的运作还需要其他推理形式和相关制度的协作,特别是演绎推理。
从图3 中也可以看出,利用演绎推理的三段论是在司法程序中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法律论证的主要方式。虽然从目前研究来看,法律论证大致可以包括逻辑方法、对话方法和修辞方法[13],但是,逻辑方法是其中应用最广、同时也是最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方法。这种以演绎推理为核心的思考方式是法律思维的核心内容,从设证的角度来看,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纠正司法活动中的错误。正是借助在微观层面上共同使用的演绎推理,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才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和交流,而其中暴露在演绎推理中出现的逻辑错误也相应地成为进行争辩的焦点。
前文关于司法过程的讨论大多是以大陆法系为对象的,而即使是对于英美法系而言,设证理论也同样适用,而且相对而言,英美法系的司法过程所具有的开放性则更容易展现设证推理与其他相关推理方式和制度之间的协作关系。
从典型的普通法运行过程来看,首先是对先例的识别,这实质上是一个归纳的推理过程(包括法官和律师的共同参与),其中的规则和原则被确定之后,同样是要适用演绎推理依据事实进行判决。而现代普通法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与大陆法系的融合趋势,归纳逻辑也不再成为普通法运作的典型特征[14]。而设证同样为具体普通法的司法活动提供了整体性框架。仍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先例的存在,从设证推理的角度而言,其中的确证环节更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以上确证的环节需要与众多先例进行反复比较,从而确定各方的假设是否符合先例。这样,与先例相比较就成为普通法中确证的重要内容。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因为就法官而言,假设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法官基于对相关先例的理解而形成的经验因素,因此,再以相关先例为确证的依据和标准很容易形成同意反复,因此,即使先例能够成为确证的标准,也只能是那些在形成假设命题的过程中没有参考的标准。在笔者看来,这种怀疑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是没有必要的,毕竟,在司法程序中,通过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共同对话,即使是对于法官在形成假设命题过程中参考的先例,也同样会受到其他方面观点的影响,这实质上相当于在设证推理的确证过程中增加了新的事实(或者数据),同样能够起到检验的作用。
除了以上这种与先例对照的关注过往的确证,在普通法中还有一种注重未来的确证。在一种有价值的假设命题提出之后,在法庭中它就可以与其他假设命题相比较而进行检验。从中可以演绎出,在未来面对相似的情形时法院将如何裁判。这样,就未来结果的预测进行对比就成为检验假设命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5]。这里虽然用词是对法官行为的预测,但是其背后应当是对判决结果及其对未来社会影响的预测,从法律论证的角度来说,这种对社会影响进行预测的法律解释方法相当于麦考密克所说的“后果主义论辩”:“在那些无法根据明确的强制性规则得出判决结论的场合,或者规则本身语焉不详的场合,依靠对后果的考量作出判决实乃必要之举。但是,由于证明过程就是表明为什么判决遵循的是这项规则而不是那项规则的过程,所考虑的后果也就包括一般性裁判规则所可能导致的所有可能后果,而不仅仅是判决对某个特定当事人的特定影响。”[16]另外,由于普通法的演进更多地是依赖法官,而法官所提出的假设命题一旦超出既定的先例,那么,这种假设本身经过论证之后就能够成为先例存在,当然,也同样会经历社会现实发展的检验。很多普通法中的先例随时间逐渐被遗忘,但是,另外一些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先例却仍然能够显示其生命力,即使这样的先例在最初只是法官的一种假设命题。这种普通法的发展方式与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有着内在一致性:在原初意义上只是一种法官的“决断性虚构”,但是,经过了法律实践和社会发展的检验之后,能够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17]。
这样,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设证推理的过程总是与演绎和归纳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推理方式的共同协作才能保证司法过程的顺利进行。Downard 教授的这段话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法律假设命题的有效性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从该假设命题中可以演绎出关于法院在将来如何裁判的预测;其次,该预测可以被一系列的归纳所验证:从表面上看,量化的归纳不能用于给出关于将来案件的数理化预测,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可以用于形成一致的预测。”[18]
如果说在两大法系之间的横向对比中能够发现设证及其相关推理方式的运用,那么,就个案的审判程序及其制度来说,设证同样适用。这不仅表现在审判程序内的具体制度,例如辩论制度、交叉询问制度等等,更表现在不同的审级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十四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编第三章都规定了相应的二审程序。从设证的角度来看,对于一审程序的结论,二审程序仍然需要对其中的事实和法律部分进行检验(虽然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具体范围上略有不同)以获得终审结论。这种程序上的设计从设证的角度来看起码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方面,正如前文有所涉及的,法官的假设对于裁判结论在实质意义上具有决定作用,但是,这种决定作用却能够受到程序上的制约。例如二审程序的启动对一审判决结果进行审查,而能够启动二审程序的正是一审诉讼活动的参与者。在设证的宏观框架内,裁判权力和诉讼权利在实质和程序的不同层面上达到了相互制约。另一方面,这种程序设计同样印证了可能性与接受性是在整个设证过程中对假设进行确证的最重要的因素。就具体个案来说,可能性更侧重于裁判结论自身的质量,特别是在具有特定自由裁量范围内;而接受性更多的是考虑一审案件的参与者的情况。从极端的角度来说,即使某一一审案件的结果十分荒谬,但是只要其中的参与者并不行使诉讼权利来启动二审程序(即对结论的接受),那么,原初的假设命题也就相应地成为了似真的结论。
从设证的视角来看,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关系与审判监督程序与前两审程序的关系较为类似,都是基于某种不接受(在诉讼法规范中表述为“不服”)而再次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进行检验。当然,随着审判级别的不断上升,原有的各方假设命题都不断受到各种检验,这些不断的检验就能够尽可能地保证原初假设的真实性不断提升,最终成为“最具解释力的结论”。与之相对应的是,启动后发程序的困难也不断增大。
四、结语:作为整体性的制度
从宏观意义上来说,设证推理可以说是司法过程的整体框架。但是,这一框架也不可能离开其他的推理和相关制度。“随着演绎能力的增强,现实变得更客观,客体被分析得更充分。换句话说,在未分化的初始状态之后,当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开始分化时,这三项都得到了改进。……由这种整个所产生的运算结构揭示了它们的双重特性——既是必然的结果又是探索新发现的工具。”[19]归纳和演绎的存在使得设证的检验结论更具可能性与接受性;审判等级、交叉询问等制度则规范了设证的实践运行,第三人、鉴定人、辩护人(代理人)等多角色参与者都能够为设证推理的整体运行贡献力量,甚至严格的司法职业准入制度都能够在保证法官形成符合法律精神的假设命题时起到一定的间接作用。考夫曼也曾论及,设证法作为一种从结论出发的推论,是一种不确定的,大胆的,有风险的推论,只得出有疑问的判断,以致随时可以强调它的不确定性;在法学方法论上,人们在未来必须对设证法付出更多的关注。但是我们不能期待它成为“无可指摘的”推论,因为它无法带来这种推论[12]114-115。也就是说,任何单一的制度都无法完成任何个案的顺利裁判,只有在设证的宏观框架中保证各种推理形式和制度的整体性运作,才能尽可能地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具解释力的”判决结论,即使这一结论未必能够达到完全真实的程度。
[1]PEIRCE Charles Sanders.Collected Papers of C.S.Peirce[M].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1963,5:171.
[2]HARMAN G.Th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J].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65(12):74.
[3]李延梅,武宏志.非形式逻辑的合法性[J].求索,2004(7):53.
[4]JOSEPHSON John R,JOSEPHSON Susan G.Abductive Inference:Computation,Philosophy,Technology[M].Cambrid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1-12.
[5]BOUTILIER Craig,BECHER Ver onica.Abduction as Belief Revision[J].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6(1):154.
[6]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76.
[7]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M].董炯,彭冰,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1.
[8]HOLMES O W.Codes,and the Arrangement of Law[J].American Law Review,1870(5):4.
[9]陈金钊.从法律感到法律论证——法律方法的转向[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1):76.
[10]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99.
[11]刘彤海.律师思考与法庭辩论技巧[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64-166.
[12]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3]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张其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98.
[14]李安.归纳法在判例主义法律推理中的有效性与论证[J].法律科学,2007(2):73.
[15]DOWNARD Jeffrey Brian.The common law and the forms of reaso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2000(13):390.
[16]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M].姜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7.
[17]卢鹏.法律拟制正名[J].比较法研究,2005(1):52.
[18]MAGNANI L.Abduction,Reason,and Science,Processes of Discovery and Explanation[M].New York:Kluwer Academic/ Plenum Publishers,2001:392.
[19]皮亚杰:可能性与必然性[M].熊哲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