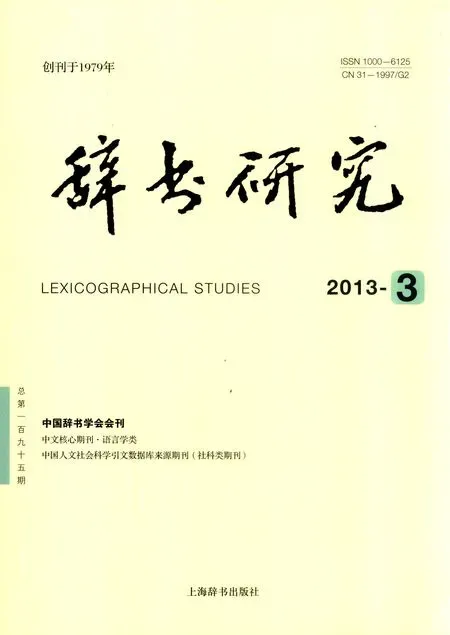戴震与两汉辞书*
徐道彬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合肥 230039)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和总结时期,作为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戴震(1724—1777,字东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对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他所倡导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1]的学术路径,引导了清代学术“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的道路。所以,有学者称“二百年来确有治学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基础,衣被学者,至今日犹有受之而未尽,则休宁戴东原先生其人也”(胡朴安1936)。
戴震自称其治学“以词通道”,所以他对《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这四部辞书极其推崇。他的《尔雅文字考》和《方言疏证》二书可谓创辟榛莽,发凡起例,引导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而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一批学者殚精竭虑,对汉代经学尤其是几部小学名著做了完备而精审的整理和注释,结出了一系列丰硕的果实。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毕沅《释名疏证》等等,都是戴震“以词通道”理论下的直接成果。因此也可以说,戴氏学术的入手功夫是从四部两汉辞书而起,而汉代辞书研究在清代的兴起,又与戴震的重视和推崇密切相关。本文以戴震与两汉辞书为题,借以考察戴氏在清代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后世辞书学研究与发展的深刻影响。
一、“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
戴震认为:“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尔雅文字考序》,《戴震全书》六)并倡言:“《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全书》六)基于这种认识与推崇,戴氏的著述中,以《尔雅》出现的频率最高。戴震曾作有《尔雅文字考》一书,自谓:“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帙,为题曰若干卷《尔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课而已。”20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省图书馆又发现了戴震的《经雅》手稿,这是一部比照《尔雅》体例,辨析草木鸟兽虫鱼而成的专著,今已收入《戴震全书》第二册中,该书分《雅记》和《经雅》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两卷:《释兽》、《释畜》;第二部分为五卷:《释鸟》、《释虫》、《释鱼》、《释草》、《释木》。主要内容是撷取古文献中动植物的名称,然后汇综先秦诸子、汉魏古注加以考辨解说,使人读一物而知古今雅俗之名、群经异同之称。如《经雅》卷二“螽”条云:“其跳之趯趯者,螽之大者也。听其声,故泛称草虫。见其形,故指云阜螽。改草虫为草螽,于义未安。蛗、蜤二字,亦字画讹阙,加虫当作蛗,斯加虫当作蟴。犹鸒斯之斯。然皆赘体,不合经义。蟴又讹而为蜤,乃蜤蜴之蜤,尤非是。”诸如此类,可见戴氏善于对古代草虫名物加以辨析,并注重经史典籍的引用,以及文字书写的规范,条贯分明,言之有据。
戴震曾准备作《尔雅注疏笺补》一书,后扬州任基振(字领从,曾任国子监丞)已先期着手,并前来请教。戴氏不仅给予任氏诸多帮助,并为之作序,序言中极力推崇《尔雅》的存古之功与训诂之用,云:“丙戌春,任君领从以所治《尔雅》示余,余读而善之。”“曩阅庄周书‘已而为知者,已而不知其然’,语意不可识。偶检《释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词。至若言近而异趣,往往虽读应《尔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释言》‘庥,荫也’,即其义。《豳诗》‘蚕月条桑’,《释木》‘桑、柳丑,条’,即其义。《小雅》‘悠悠我里’,《释故》‘悝,忧也’,即其义。说《诗》者不取《尔雅》也。外此转写讹舛,汉人传注,足为据证。如《释言》‘鬩,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传《小雅》‘兄弟鬩于墙’:‘鬩,很也。’郑康成注《曲礼》‘很毋求胜’:‘很,鬩也。’二字转注,义出《尔雅》。又‘苛,妎也’,郭氏云:‘烦苛者,多嫉妎。’康成注《内则》‘疾痛苛癢’:‘苛,疥也。’义出《尔雅》。凡此,遽数之不能终其物,用是知经之难明,《尔雅》亦不易读矣。”由是观之,戴氏不仅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对任氏加以指导,还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强调:援据《尔雅》以释群经子史,据群经以证《尔雅》,本之六书,综核条贯,确然可与论学。
戴氏的经学研究,素以贯通文字,系联经义为首要,对于去古未远的古籍犹为珍视,云:“余尝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书》六)主张以《尔雅》、《说文》以证《诗》、《书》、《礼》、《易》,“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与是仲明论学书》)。这一思想方法为“戴门后学”所继承。段玉裁的“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王引之的“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也”等等,无不根源于此。黄侃《论清儒〈尔雅〉之学》中曾有评论云:“此中诸书,以戴氏为最懿。其《尔雅文字考》自序曰:‘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音声,确然于故训之原,庶几可与于是学。’案:自戴氏后,治《尔雅》诸人,虽所得有浅深,皆循戴氏之途辙者也,展辟门户之功,亦可云伟矣。”[2]
二、研治《方言》,开创新境地
《方言》自郭璞作注之后的一千五百多年间,基本处于沉寂无闻的状态。至清代,戴震的《方言疏证》开创了方言研究的先河,其推阐语源、旁证方音之法,沾溉后学,影响至今。卢文弨云:“《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则吾友休宁戴太史东原氏之为也。义难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证明者胪而列之,正讹字二百八十一,补脱二十七,删衍字十七,自宋以来诸刻,洵无出其右者。”[3]这是对《方言疏证》学术成就的中肯评价,也是对其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的高度肯定。今人齐佩瑢也说:“《方言》之学,亦戴氏开其端,所作《方言疏证》一书,虽重在参订校补,然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核,加以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是戴氏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也。迨后有卢文弨之《重校方言》,刘台拱之《方言补校》,顾震福之《方言校补》,孙诒让之《札迻》中校郭《注》,郭庆藩之《方言校注》,然后本子始稍稍可读。注释之者,有钱绎之《方言笺疏》,广征博引,也颇能得声义贯串,以互相证发之妙。”[4]可以说《方言疏证》的问世,带动了近代以来一系列语言学问题的研究,也推动了当代学者对上古、中古及近代方言俗语的研究。
戴震治学善于独辟蹊径,他对这部非正统语言学辞书的推崇,引起了后学者对方言问题的普遍关注。他们将戴氏的这种学术思想推而广之,开辟新途,各有建树。如段玉裁效法其师以《方言》写于宋李焘《说文五音韵谱》上,撰成巨著《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一书的产生也是通过校正《方言》而来,其著作缘起和展开的路径是:《方言、广雅、小尔雅分韵》→《校正方言》→手校戴震《方言疏证》→《方言疏证补》→《广雅疏证》;[5]近代以来,丁惟汾《方言音释》、吴予天《方言注商》、章炳麟《新方言》、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等,皆秉承前贤,推进了今古方言学的研究。无论是对古语俗字的考证,还是对现代方言的调查,戴震《方言疏证》的引导和激发,功不可没。除了《方言疏证》外,戴震还有《续方言》一书,意在补苴扬雄《方言》,后见杭世骏《续方言》已出而中辍,及《方言疏证》成,此稿遂废,今仅存2卷。
《方言疏证》是对古代辞书的校勘订补和疏通证明,戴震以其渊博的学识,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文字形音义的内涵,也能兼顾词与词之间的结构意义和修辞层面上的关系,使得该书成为清代辞书的典范之作。梁启超说:“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6]杨向奎(1994:313)也说:“戴东原治哲学喜用文义分析的方法,以了解经典中的本义,开清人文法学的先河。段玉裁也注意了这种方法,王氏父子于此更有较大发展。”如此评论可谓切中肯綮,慧眼识真。戴氏认为“字书主于训诂,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论韵书中字义答秦惠田书》,《戴震全书》三);“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与是仲明论学书》)。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语言学研究,自然能够超越前贤,开拓创新。实际上,《方言疏证》中既大量地征引《尔雅》、《说文》、《释名》、《玉篇》、《广雅》等辞书原典为证据,也不乏经史诸子与《文选》等古籍为旁证,相辅相因,确然于故训之原得其根本。《方言疏证》“但开风气”,启导了清代以后语言学全面深入的探讨,引导了乾嘉时代的学术方向。如王引之《经传释词》是清代语法学著作,其中援引戴震之说很多。虽然戴震的理论高度不及后来居上的王氏父子及章黄学派,“但训诂学上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多由戴震首先提出,段、王继踵戴氏,又有所丰富发展”(郭在贻1985:201)。由此可见戴氏在训诂学领域的开拓创新精神,以及对后人在小学研究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三、指示门径,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纵观历代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最为显著者当推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该书的结撰是在其师戴震的一手指导下完成的。段氏自称:“始年二十八时,识东原戴先生于京师,好其学,师事之,遂成《六书音均表》五卷、《古文尚书撰异》卅二卷、《诗经小学》卅卷、《毛诗故训传略说》卅卷。复以向来治《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因悉心校其讹字,为之注,凡三十卷。”(《说文解字注》卷十五下)
段氏在注《说文》之前,曾将戴震以《方言》写于《说文五音韵谱》上的“分韵《说文》”稿本,携至玉屏县邸,在此基础上段氏着手注疏工作。云:“先生知训诂之学,自《尔雅》外,惟《方言》、《说文》切于治经,故傅诸分韵之《说文》,取其易检。此分写本者,乃草创之始也。分写本,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观,遂携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于洪蕊登京寓,先生索此书曰:‘分韵《说文》不足贵,欲得所分写《方言》耳。’玉裁旋入蜀,竟以道远难寄,藏至今。然假此书时,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今四十余年,于《说文》讨论成书,于《方言》亦窥阃奥,何莫非先生之觉后觉哉。”(《戴震全书》六之《戴东原年谱》)段氏遵照其师“训诂音声,相为表里”之法,用力四十余年而成此巨著。其间,若有疑难,随时问难于师,又言:“丙申之夏,并镌以赠问字者,以见予学之有师承,非苟且而已也。”段氏时刻不忘师教,努力于“切于治经”之学。而戴氏对于段氏的帮助,既有理论的指导,也有实践的示范。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云:“谐声字,半主义,半主声。《说文》九千余字,以义相统。今作《谐声表》若尽取而列之,使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则亦必传之绝作也。”(《答段若膺论韵》,《戴震全书》三)字里行间皆是循循善诱之情。段氏的“学之有师承”,也于此可见一斑。
溯其根源,戴震的学问最初就是从《说文解字》起家的,段玉裁云:“(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诂语之,意每不释。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戴震全书》六之《戴东原年谱》)可见戴氏学术实由《说文》、《尔雅》而来,终身受益,以为宝书。程瑶田曾言:“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尔雅》、《说文》二书,宝书也。”[7]戴震以汉代辞书为根基,由此而贯通学术。也曾有心为《说文》作校订,但因困于科举,累于生计,又多为他人作嫁衣,故始终未果。于是制订章程,指示门径,指导弟子段玉裁来完成此事。陈焕曾叙及此事云:“焕闻诸先生(段玉裁)曰: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取此二语而已。经与字未有不相合者,经与字有不相谋者,则转注假借为之枢也。”(《说文解字注跋》)黄侃也说:“清世自戴震创求本字之说,段玉裁注《说文》,遂壹意推求本字。”[8]可见《说文解字注》的著述意图和思想方法,皆从戴氏学术融铸而来。事实上,段注无论是在文字训释的手段上,还是六书理论的运用方面,无不体现出戴震文字学思想的特点。如大量采用转语手段和因声求义的方法说解文字,阐释经义;对“四体二用”学说全力称扬并引申阐发;全书中征引戴震之言达六十条之多。诸如此类,无不展示出段玉裁对戴震的学术继承和发展。近人马裕藻(1929)曾对此间的传承关系有论云:“(东原)在古音学上有这样的成绩,所以对于六书训诂特见甚多。此类著述除《方言疏证》已有成书外,其文集中如《尔雅文字考序》、《尔雅注疏笺补序》、《与王凤喈书》、《论韵书中字义答秦蕙田》、《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六书论序》、《六书音均表序》诸文,颇多引而未发之论。段氏之《说文解字注》、王氏之《广雅疏证》,殆无不受其沾溉。”由此也说明了学术大师的正确指导,往往造成一代学术风尚的转移。戴震在语言文字领域的巨大贡献,足以使后来者乘风而起,清代小学研究也因此而蔚然成风。
四、探求语源,以《转语》继《释名》
东汉刘熙的《释名》是一部以声训方法探求事物名称由来的语源学著作。虽然该书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在语源探求、古今词汇比较、名物制度考证,以及对后世语言学启示等方面,均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清儒对《释名》一书的批判和利用,也较前人广泛而深刻得多,戴震便是其一。
戴震的《转语》一书就是在继承和批判《释名》的基础上而成就的一部杰作。其序云:“古今言音声之书,纷然淆杂,大致去其穿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谓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说经之士,搜小学之奇觚,访六书之逸简,溯厥本始,其亦有乐乎此也。”(《转语序》,《戴震全书》六)从时代意义上来说,《转语》应当是清代古音学迅猛发展的产物,是在扬雄、刘熙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汉语语源的结果。戴氏认为字书与韵书二者不可分,无论是主于训诂的《尔雅》,还是主于字形的《说文》,以及主于音声的《释名》,其实“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所以,他认为“犹阙一卷书”就是《转语》,于是“创为是篇,用补其阙”。该书的理论要旨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这种音义互求、不限形体的方法,超越了前人,成为清代训诂学的不二法门,也正如他自己所言:“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学士茫然,莫究所以。今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转语》在《释名》的声训基础上,本着“训诂音声,相为表里”的方法,开创了比刘熙更为先进的训诂学新境地,而“各从乎声,以原其义”的思想,经过金坛段氏、高邮王氏的继承和发扬,已为今日训诂之至理,小学之纲领。
戴震不仅在理论上借鉴了刘熙注重声训的方法并加以改进,成就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法则,而且在考证经籍的实践过程中,对《释名》一书也多加利用。如《毛诗补传·皇矣》“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戴注在比较了毛《传》“耆,恶也”、《诗集传》“耆,致也”之后,取刘熙之说为正,云:“耆,读若指,《释名》云‘耆,指也’。声义本相通。‘上帝耆之’,犹言天意所属。”又如《杲溪诗经补注·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归”,戴氏比较毛《传》、郑笺和朱子《集传》后,撷取《释名》为确证,云:“刘成国《释名》云:‘髲,被也。发少者得以被助其发也。’僮僮,端直貌。祁祁,齐同貌。然则‘被之祁祁’,盖状所益之发多而不乱也,举一‘被’而将事之敬可知也。”又如《毛郑诗考正·瞻彼洛矣》“鞞琫有珌”,戴注引毛《传》、郑笺和《说文》诸说相互证发后,以《释名》为定,云:“刘熙《释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饰曰琫,下末之饰曰琕。’可据以证《说文》。”又如《考工记图》卷上《释车》之“軶谓之衡,衡下乌啄谓之軥”,戴氏引《左传》及服虔、杜预注文,以及《说文》和《小尔雅》诸说,而取《释名》以证己说。云:“《释名》:马曰乌啄下向。又马颈倾乌开口向下啄物时也。”诸如此类,所引用的《释名》之说,一方面说明《释名》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领略戴震博综群籍,稽核异同,考证求真的治学风格。虽然后世对于《释名》的评价并不高,但其去古未远的考古价值,仍不容忽视。戴氏不因人废言,对汉魏辞书与古注资料加以合理运用,也正是他“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答郑丈用牧书》,《戴震全书》六)学术精神的充分体现。
当然,四部两汉辞书因其历史的局限,都有一定的疏漏错误。戴震在研究和推崇它们的同时,对其失误之处也丝毫不加避讳。云:“《说文》所载九千余文,当小学废失之后,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戴震全书》三)“用此见汉人之书,就一书中有师承可据者,亦有失传傅会者。在好学之士善辨别其间而已。”(《经考》卷五“尔雅”条,《戴震全书》二)《说文》有偶失,《尔雅》有未臻,《方言》和《释名》也存在许多错误,关键在于好学之士善于辨别。既要善于继承与发扬前人的优秀成果,又要能够与时俱进,开拓与创新,而戴震确乎此人也。梁启超指出:一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9]戴震对《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四部辞书的重视影响了后学者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风气,促进了清代经学研究的兴盛,同时也为清代的小学类辞书如《经籍纂诂》等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总结。总而言之,四部两汉辞书成就了戴震学术,而戴震对汉代小学的研究和推崇,也促进了清代学术由小学而入经学的正确发展。
附 注
[1]戴震(清).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六).合肥:黄山书社,1995。后引戴震言辞只在文中标注篇名,不再出注。
[2]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85。
[3]卢文弨(清).重校方言序.∥抱经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4]齐佩瑢.训诂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4:240.
[5]参见华学诚.王念孙手校明本《方言》的初步研究.文史,2006:1。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2。
[7]程瑶田(清).说文引经异同叙.∥程瑶田全集(二).合肥:黄山书社,2008。
[8]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83.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4.
1.郭在贻.训诂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胡朴安.戴东原先生全集序.《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1936.
3.马裕藻.戴东原对古音学的贡献.国学季刊,1929(2).
——以一则正统十一年商人家庭阄书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