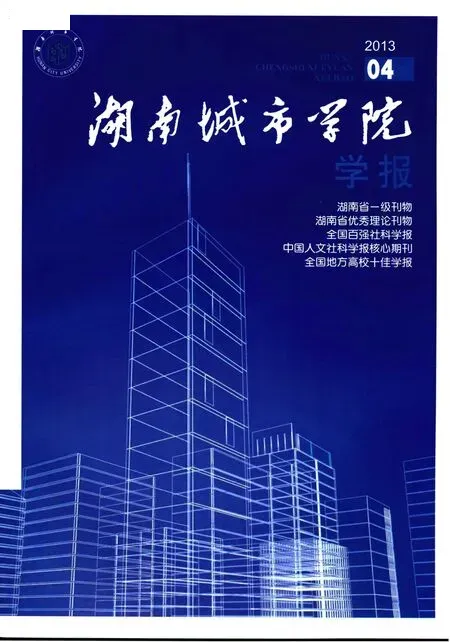民俗视野下的宝黛爱情悲剧
徐秋明
(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民俗是人俗,它包括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愿望,有着丰厚的文化蕴涵。作家往往通过对民俗事象的描述,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表现着自己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乃至深层的意识。因此,透过民俗视角解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认识的特殊视角。
《红楼梦》主要写了两大悲剧,一为以贾宝玉、林黛玉的情感为中心的爱情悲剧;一为以贾府盛衰为代表的家族悲剧。宝黛的爱情悲剧根源,历来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其中既有社会的、历史的客观因素,也有自身的主观因素。而从民俗学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解读到作家更是利用民俗事象固有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富有象征的意义表现,在反映了真实的生活情景的同时,对读者进行了暗示隐喻,使读者从更深层的文化层面了解那场悲剧的根源。
一、神话——前世今生爱情的宿命象征
《红楼梦》一开篇,就为读者讲述了两个极其浪漫的千古神话:“炼石补天”和“还泪报恩”。第一回,作者先描述了“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女娲炼石补天所剩的那块石头,灵性已通化为神瑛侍者。接着,作者又向我们介绍了西方灵河岸畔有块三生石,三生石边生长着一株绛珠草,得了神瑛侍者之甘露浇灌,受天地精华,脱草木之质,修成女体,只因未报神瑛侍者灌溉之德,五脏六腑里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遂要随神瑛侍者下世为人,把一生的眼泪都还给他,遂得脱草胎木质,化成绛珠仙子。“炼石补天”的神话和美丽的“绛珠还泪”传说,造就了一个离奇、哀怨、凄婉的“木石前盟”。但代表着爱情“木石前盟”,来之原始的灵魂之间的相通和相遇,是一种人类自我的至高追求,是理想化的“超俗之缘”,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却显得这样的软弱。
宝黛爱情诞生于神话中,而这些神话体现了人类的宿命。宝黛爱情“木石前盟”,是“超俗之缘”,代表了生命终极意义上的理想,是一种人类自我的至高追求,而这种“超俗之缘”的情感是幻化的,是尘世中难以安置,难以实现的。
纵观神话中出现的意象:玉石、小草、水,都在不同程度上带上了宿命色彩。那块补天不成的遗石,是远古“石头”崇拜的风俗。它后来幻化为宝玉脖子上那块晶莹的玉坠,随身而藏,是“护身符”。“石头”(玉)在,宝玉就聪明灵秀,“石头”(玉)不在,宝玉则浑浑噩噩、疯疯颠颠,最后归于青埂峰下。而这块顽石,需要泪水的不断浇灌才显得晶莹,泪尽玉失。黛玉的前生是一株从形体到生命力都十分弱小的绛珠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她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瑛侍者的甘露浇灌,因此对神瑛侍者具有先天的依赖性。作品中,林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便吃药,而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人篱下,居于贾府,依赖贾府的庇护为生存。水(包括泪水),代表少女的温柔纯洁,也体现女性的命运不幸之意。绛珠小草当年修成女体,“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她的愁和泪竟是如此之多,甚至于到了欲将“一生所有的眼泪还”神瑛侍者那灌溉之情的地步,谕示了林黛玉一生的愁绪。在现实层面里,林黛玉居处以竹掩映的潇湘馆,以潇湘妃子为号,这则故事取之于舜死,其妃娥皇、女英哭舜而泪化斑竹的传说,也就是暗示这段姻缘,最终黛玉泪尽而亡。
二、节日——生命的纠结暗示
岁时节日,既是岁月的交结点,也是人生的纠结点。自古以来,许多节日在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积淀着人们的观念、信仰和情感愿望。作家利用节日民俗的过程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这些民俗事象渐渐向文学意象转化,从而有了更厚实的审美观念。
在《红楼梦》全书中,我国传统最重要的节气如春节(含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在作品中都得以重点体现,此外,还有清明节、芒种节、七巧节、重阳节、立春、饯花神、小阳春、九九消寒会等。节气与《红楼梦》的主题紧密相连,春节主要以18回元宵节元妃省亲集中描写,体现了贾府的“兴”,端午节则主要写了打平安醮,中秋节则写了呈现衰败迹象的贾府过节的情景。这些节日中,有不少过程反映了宝黛爱情活动,体现了他们的情感变化,同时也暗示了他们的悲哀。
元宵节,“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这是一个浪漫而诗情的节日,是一个可以在瞬间催生爱情的节日。历代文人墨客赞美元宵花灯的诗句数不胜数,北宋欧阳修词“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描写的就是情人之间的思念之苦。最为著名的是《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堪称千古绝唱。元宵夜为有情人提供了一个传情达意的渠道,情侣们或密笺赴约,或互赠诗帕,体现的是一种纯洁的男女之情,这种感情含蓄内敛,韵味实足,可以说是中国的情人节。《红楼梦》中有六回故事中写到元宵节。小说开卷即以甄士隐的女儿英莲在元宵节被拐子拐走,伏下一幕令人感叹不已的悲哀故事。而18回中元妃省亲,黛玉的诗才初次表现,替宝玉写诗,接着展开了20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美好日子。但这时的爱情是较为脆弱的,宝玉时而表现出在宝钗和湘云之间的摇摆不定而使黛玉疑惑不安。
春天的花开花落,民间都有一定的仪式。农历中二月十二花神降临,到四月二十六饯花神活动,为花神举行“送别仪式”。作家运用这个民俗事象来塑造林黛玉。黛玉的生日是二月十二,说明林黛玉的前身是个花神;出生于春天,雨水多,预示泪多,命运的悲凉。27回的四月十六送花神节里,当大观园女儿们举行了盛大的饯花神活动中,林黛玉吟出了自身写照的哀恻的“葬花词”,预示了她爱情的夭折,命运如花一般花开花落的短暂。
端午节最早的来历据说因春夏交接,瘴气弥漫,是民间避邪驱瘟的日子。在作品的情节里,夏季本是宝黛爱情的发展时期,但他们的感情却充斥着纠葛。在29回端午节的“打平安醮”,我们看到他们情感的一波三折。清虚观打醮当中,张道士的提亲将宝玉的婚事正式提出,加剧了贾宝玉林黛玉的心理负担。同时,贾宝玉得到了几乎与史湘云一模一样的金麒麟;元春端午节的礼物,赏赐给薛宝钗的礼物与宝玉同,而黛玉则与探春等同,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一种误读——重钗轻黛,连贾宝玉都认为“传错”了。最后,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二人的爱情由此进入了误会、纠葛阶段。通过这个细节,曹雪芹已将宝黛爱情悲剧预示给了我们。正如周汝昌所论:“清虚观一个场面,岂是真为了写写打醮、看戏等事吗?完全不是,写的是宝、黛婚姻大问题。元春的‘旨意’叫打醮,却引出‘代表人’张道士,要为宝玉提亲。结果则宝、黛二人都为此而生了气,贾母也认真地着了急,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其局势之严重,为通部书所仅有。作者是特笔大书。”[1]打醮如同一个框架,装着“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冲突,装着宝、黛、钗、云的情感纠葛,装着宝黛爱情悲剧的种种预示。
作品中的中秋节落笔较多的是第75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和第76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看得出这是一个大关目,这一年中秋过的冷清悲凉。75回中,天上人间团圆的日子,向来爱好热闹的贾母一群人,只坐了半壁,下面还有半壁余空。连贾母都说道:“常日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今日就这样,太少了。……”其中,凤姐病了,宝钗回去陪母亲,后来,“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宝玉无精打采去睡了。最后黛玉和湘云“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有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联诗。月圆冷清,冷月(月缺)葬花魂,此景此诗,连一向甘于寂寞的妙玉也说“……果然太悲凉了。”天上月圆,而爱情的男主人公宝玉缺席,读者也从中阅读到悲凉的收场。
三、人生礼仪——人生悲剧的预示
人生礼仪是我们祖先按生命节律构成的礼仪程式,体现了一个人生命的关节点,成长的历程,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诞生、婚礼、丧礼这三个过程。在《红楼梦》中对这几个人生的重要仪式都在不同的角度进行叙述,通过这些叙述,既反映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也预示了宝黛爱情发展的起落。
丧礼,是《红楼梦》中体现四大家族的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志。三次盛大的丧礼,从秦可卿到贾敬、贾母,辈分一个比一个高,丧仪却一个不如一个,成了贾府渐次势尽财空的写照。在这几场丧礼中,林黛玉是处于缺席状态。
生日既有出生纪念的味道,也是成长的标志。如果说黛玉的生日是花神的诞生,饯花神活动中作《葬花词》预示其短暂的一生。22回第一次写到宝钗生日,这是她的将笄之年,是成年的标志。对一个成年的女孩子来说,一生的大事——婚姻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在宝钗十五岁的生日上,贾母对其生日的重视态度,不是对一个既有母亲、哥哥,家境富裕的客人的态度,而有对孙子宝玉的婚姻有取钗退黛之意了,预警着宝黛爱情的死亡。宝玉过生日在前八十回中提到两次,这两次生日正从两个侧面揭示了宝玉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周岁的抓周体现了他与贾政的隔阂,使他一生背上了“弑父娶母”式的情结。
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所描绘的生日,作者向我们隆重展示了与其它生日形式迥别的“群芳夜宴”图景,同时作家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宝黛爱情悲剧进行隐喻。
这次宝玉的生日,由于家长们空位,这是一次难得的青春聚会,大小上下都丢掉了一份矜持,连李纨、宝钗等都溢出了一些生命的热情,因此这可以看成是百花的盛开,也可以看成是生命的放歌,其生命的充盈正对比了大观园外生命的窒息。然而麝月掣出了那根具有象征意义的签——“开到荼花事了”直寓着“春”的离去,它象征着在森严的礼法纲常禁锢下和贾府末日来临的情势中,众花的凋零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作为核心人物宝玉在自己生日的“寿筵”上看到的却是“春”的离去、众花的凋零,所谓“反复推求了去”,“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这是他对悲剧的人生体悟的独特体验。因此“群芳夜宴”又何尝不可以看作群芳祭春呢?故鲁迅先生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2]死亡,包括生命的逝去,爱情的终结。面对痛苦而又无奈的人生,宝玉是早已做好了死亡准备的,“只愿这会子立即我死了”(57回),甚至“再不要托生为人”(36回)。他看见了“生日”背后的死亡,看到的是生命正面临的无所不在的“空”——这正是空空道人曾经历过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
婚礼,在民间,已成了一个人的成人的标志。在作品中主要描绘的是宝钗和探春的婚礼。宝钗的婚礼已经是宝黛爱情的终结,探春的婚礼是人间的骨肉分离。
从总体上看,《红楼梦》中的生日描写从生命的存在方式与死亡的特殊视角,直指着小说的悲剧意旨,人生已是悲剧,爱情以何依存。
四、信仰习俗——心灵深处的无奈
信仰习俗,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包括各种禁忌在内反映人们心理的习俗,是人类心理活动和信息上的传承,也称为心意民俗,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民众的深层意识。在《红楼梦》作品中,多处出现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等信仰。
《红楼梦》中的自然崇拜是尤其明显的。我们可以从“女娲炼石补天”、“共工触不周天”、“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等神话传说中就传递着对石头、植物、水的崇拜的信息。
木崇拜与石崇拜有相似之处,木与石都是自然界之物,又都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石与木,代表着繁殖迅速、生命力旺盛、对人类的繁衍和对生命力的保护功能,人们相信木与石都是有灵的,木与石往往紧密结合,共同构成木石崇拜的模式,体现了人类对生命与永恒的渴望。对木与石的崇拜,也体现了人类对现实的一种超越。从曹雪芹精心构思的故事当中,贾宝玉的“玉石”,黛玉的原型的“绛珠仙草”,“木石前缘”与“金石良缘”的相对,成为一组象征意味的图腾物。石头、植物、水的崇拜,有着前世今生的爱情的宿命象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石头是一种人格。中国古代文人往往以石自况、引石自喻。他们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格精神,《吕氏春秋·诚廉》中有这样的名言:“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这里石被赋予了中正不移的人格精神。相传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就以石性自比。它代表着与世俗抗争的人格风范和情操;石头是一种传统,石头的精神规定性是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玉,多由人工雕琢而成的,象征着政治秩序和社会地位,世俗的欲望。当本真的石头雕琢成人工的玉以后,它往往会被世俗社会无用被弃的。在专制君主统治下,贞刚耿介之性的石是不为世俗所容的,在世俗世界的命运是悲剧的。所以,石头是哀婉的,它代表着一代知识分子被弃的命运。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首先将女娲补天的五色石,改作顽石,“无材补天”的现实,便是这一顽石的命运。顽石之幻形贾宝石向玉的转变,宝玉憎玉爱石,既表达他对社会的反抗,对自然生命的热爱,也体现了自然在世俗的无力。所以,木石前缘在世俗的金玉良缘的较量中,也是显示了无力与悲哀。
五、社会民俗——一条持久的软控链
社会民俗是指历代传承下来的各社会集团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从社会民俗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仪式上,各种社会组织的民俗,形成了一条持久的软控链,紧紧地控制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作品中,宝黛是一种姑表关系。在汉族民间婚姻有姑表亲的对舅家的补偿婚姻或亲上加亲的习俗。但是,据既是满族人,又熟知清史的启功先生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注释序》一文中,根据满族风俗传统指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民俗根源。他说:“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叫做‘骨肉还家’更犯大忌……本书作者赋予书中的情节,又岂能例外!他以自己熟悉旗人上层社会文化生活的优势,从朝代、地名、官职、称呼、服饰、礼仪等方面,揭示曹雪芹运真实于虚幻的艺术手法。他以清代贵族家庭生活和风习,说明宝黛爱情悲剧。另外,当时还有对“隔辈人”的婚姻要尊孙子父母尤其是他母亲即王夫人的意见,“因为婆媳关系是最要紧的”。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贾母虽爱黛玉,而宝钗是王夫人姊姊的女儿,所以宝黛爱情的结局处理“完全合乎当时的生活背景,而不是专为悲剧性质硬行安排的这种情节”。启功论曹雪芹和《红楼梦》既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时也尊重当时的满族习俗。
从姓名的设置来看,林黛玉之姓林,隐喻之意很多。其一,黛玉前身为绛珠仙草,草为木质;其二,其有“林下之风”,以才女看待,又有“月明林下”,以美人尊属;其三,林遇雪(薛)则无欣欣向荣之兆,而有萧萧枯萎之嫌。林黛玉之名见于前人《题画诗》中“连光·林·黛结深翠”句,取义于晏几道《虞美人》词:“飞花自有牵情处,不向枝边坠。随风飘荡已堪愁,更伴东流水过秦楼。楼中翠·黛含春怨,闲倚栏杆遍。自弹双泪惜香红,暗恨·玉颜光景与花同。”林黛玉之名与她的身世飘零、以泪洗面、命同落花相一致。林黛玉的字是“颦颦”,这是贾宝玉与林黛玉初会时送的。林黛玉的前身为绛珠仙草,绛珠谐降珠,珠者泪也,隐喻其以泪还债也。她的别号是潇湘妃子,取自她住在密布竹子的潇湘馆内。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即以湘妃哭舜之典暗喻黛玉的爱哭性格和泪尽而逝的结局。这些名字的设置,都突出了她的悲剧性格。
从社会民俗的家族关系来看,林黛玉相对薛宝钗来说,家教较为薄弱:母亲的早逝使她从小失去母爱,也使她没有像一般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父亲请了家塾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又因她身体怯弱,课读也就不甚严格。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当然,这样一方面能保持着纯真的天性,但另一方面,又使她缺少长辈喜爱的条件:她锋芒太露,敏感、多疑的性格,没有和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以至她和贾宝玉的爱情面临绝境。
宝黛的恋爱在两个层次上与封建社会道德发生矛盾。首先,他们相互喜欢,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其次,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就是“无后”,断了宗族的“香火”。在宗法制的社会里,男人是宗族的传人,他的作为是为了立门面,续香火,传宗接代,光宗耀组。娶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服侍公婆是其次了。妇女不生孩子,就失去了自身在夫家存在的意义。这是当时社会的首要大事,林黛玉的家族单薄,自己身体先天的虚弱,能否完成贾家传宗接代的生育使命是令贾母担心的。难以完成家族延续的能力,也是难以得到长辈们的肯定。面对及及可危的贾家来说,更看重的是利益,而不是爱情,未来的儿媳妇当是需要像薛宝钗那样的管家理财式的、身体健康的人物,封建家长拆散宝玉黛玉的姻缘,选中宝钗为孙媳妇,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贾家能有健康的后代的考虑。
《红楼梦》处处体现着悲剧意识,充满悲剧气氛。宝黛的爱情是整部作品悲剧意义的核心。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通过民俗事象的选用,给读者营造了一种浓重的凄凉氛围。同时,读者更为真切的感受到在文化背景后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更为形象、深刻、直观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理解到作家的写作意图。
[1] 周汝昌. 红楼十二层[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5: 183.
[2]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