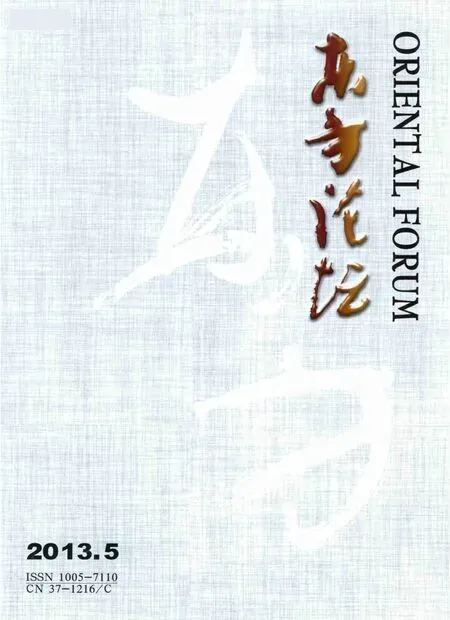论波斯细密画的伊斯兰合法性
穆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论波斯细密画的伊斯兰合法性
穆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波斯细密画以苏非神秘主义哲学思想为自己的绘画理念和理论基础,以心灵之眼即“悟眼”去觉悟所画对象的“本真”状态,被画物没有远近大小之分,也没有明暗阴影,也不表现夜色。细密画的宗旨是描绘真主创世的“蓝本”,注重被画物的普遍性与共性,因而呈现出浓厚的程式化特征。在色彩运用上,细密画以“崇高原则”为本,描绘真主眼中色彩斑斓的世界。同时,细密画画家借由俯瞰视角——被视为真主俯瞰世界的神的视角、借由苏非神秘主义中“人主合一”的学说,让自己的个体精神消融在真主的绝对精神中,从而也获得了伊斯兰合法性。由此,在反对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文化中,细密画获得了其宗教合法性,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朵艺术奇葩。
波斯细密画;空间观念;程式化;色彩运用;个人风格;伊斯兰合法性
波斯细密画兴起于蒙古人统治伊朗的伊儿汗王朝时期(1230—1380),主要作为文学作品的插图。中世纪是波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作为插图艺术的细密画,可以说是随着文学的繁荣而兴起的。细密画,顾名思义就是以笔法的精细见长,其技法明显受到中国工笔画的影响,但其精细的程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伊儿汗王朝时期,波斯全境已经伊斯兰化,从合赞汗(在位期为1295—1304年)开始,统治波斯的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然而,伊斯兰教是彻底的一神教,禁止偶像崇拜,清真图案都是植物花卉纹饰,绝少人和动物。在波斯细密画产生之前,画家和绘画艺术由于被视为偶像崇拜而受到遏制。而以人物活动题材为主的波斯细密画之所以能够为伊斯兰文化所接受,并最终成为伊斯兰艺术的一朵奇葩,与细密画所蕴涵的深刻的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哲学密切相关。
细密画兴起的时期正是苏非神秘主义在伊朗盛行的时期。苏非神秘主义从11世纪开始,逐渐成为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并对其政治、宗教、哲学、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非神秘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人主合一”,即人可以通过自我修行滤净自身的心性,在寂灭中获得个体精神与绝对精神(真主安拉)的合一,以此获得个体精神在绝对精神中的永存。而波斯细密画正是借由苏非神秘主义的途径,获得了伊斯兰的合法性。本文拟从以下五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一、绘画理念上的伊斯兰合法性
在空间观念上,细密画完全不同于欧洲绘画和中国绘画,禀具的完全是伊斯兰的宗教文化精神。首先,细密画没有定点透视法,画家的视觉焦点是流动的,画家画某处就把焦点落在某处。因此,远处的人和物与近处的人和物一样大,墙里和墙外的被画物处在同一平面,外屋和里屋的人和物处在同一平面,因此常常给人一种错觉。细密画与中国画都不表现出立体空间,但中国画有远近之分,而且中国画一般不同时表现处于不同空间的事物,而细密画酷爱表现同时处于不同空间的事物,而且没有远近里外之分。因此,细密画比中国画更具平面色彩。贝赫扎德作于1489年的《优素福逃离佐列哈的情网》(萨迪《果园》插图,藏于埃及开罗国家图书馆)很具有代表性,画中宫殿的大门、围墙、场院、一楼的房间、楼梯、二楼的外屋,最后达到二楼的里屋的场景——优素福逃离佐列哈的情网,众多不同的空间全画在了同一平面上。第二,细密画没有光影透视法,不画阴影,更不表现黑夜。贝赫扎德作于1485年的《园中苏非们的聚会》(《米尔·阿里希尔·纳瓦依长诗》插图,藏于牛津博德廉图书馆)中,众苏非身后的山坡上缀满繁花的树木明显大于位于画面前部的众苏非,我们从画顶端的一弯残月得知这次苏非们的聚会是在晚上,然而整个画面犹如白天一样清晰明亮。第三,细密画也无空气透视法,被画物体不因空气的浓淡阴晴而色调变化不同,因此远山的色调和近山的色调一样,没有远近之分。
据英国学者L.比尼恩的观点,“在西方艺术中,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侧重点在于按照自然形态去认识景物。处于自然形态中的人物和景物看起来远处的要小一些,因此它们就一定要被画得小一些。”而细密画不分远近里外是因为波斯画家认为“乞灵于自然是不妥当的。艺术之所以被称为艺术,恰恰就在于它不是自然”。由此,L.比尼恩得出结论,波斯细密画的空间表现和拒绝阴影是一种“受孩子的本能所支配的画法”[1](P79-80)。
笔者认为L.比尼恩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诚然,我们在儿童画中常常看到远近的花一样大,屋里屋外处在同一平面。但这只是表面的相似。一个心智成熟的画家是不可能以一个孩子的认识观去看待世界的。画家的认识观是由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正如丹纳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结识,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2](P41)
细密画兴起的时代正是苏非神秘主义的鼎盛时期。在认识观上,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肉眼是人认识真主(即绝对真理)的幕障,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是幻。正如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家莫拉维(即鲁米,1207—1273)所说:“那从空无中诞生的肉眼凡胎,总把存在之本质看作不存在”,“人们那只见七色光的肉眼,无法从这帷幕后把灵魂看见”。[3](P828,1042)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环境必然作用于画家的认识观。实际上,恰恰相反,从苏非神秘主义的认识观来说,细密画画的才是真正的自然形态。苏非神秘主义认为人的肉眼是人认识真主(即绝对真理)的幕障,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是幻,并不是真正的真实(即真理),真理必须用心灵之眼去认识。因此,细密画画家是用心灵之眼去描绘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非肉眼所见的事物。因此,细密画的视觉焦点是流动的,没有远近大小里外之分。因为,现实中远处的花与近处的花本来就是一样的大,色彩是一样的鲜艳美丽,只是因为肉眼的缘故错使它们“看起来”不一样大、不一样美丽;外屋的人在做这件事的同时,里屋的人在做那件事,不应该因为肉眼看不到就不去表现;山体屏蔽的只是人的肉眼,却屏蔽不了人的心灵之眼,因此在细密画中山后的人物与山前的人物活动一样一清二楚,大小比例相当;同样,人的美貌、衣着的华丽、世间的美景并不因夜色遮蔽而消失,是本来就存在的,只是肉眼受夜色遮蔽看不见而已,因此细密画拒绝表现黑夜,夜晚的人物永远如白天一样鲜艳;细密画也拒绝表现阴影,因为在苏非神秘主义中,光是绝对的,真主就是终极之光,所有的黑暗与阴影都是背光的结果,皆是虚幻。因此,细密画从不表现黑夜和阴影,夜色中的人物景色永远如白天一样鲜艳。这种心灵之眼,被称为“悟眼”。细密画描绘的正是人的心灵之眼觉悟到的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直逼事物的本真。人的这种觉悟被认为是真主在先天就赋予人的,只是被后天尘世的纷扰所蒙蔽。后天的人以肉眼所见为实,便将心灵之眼觉悟到的本真认作是人的想象。
这才是细密画空间认识观的秘密之根本所在。L.比尼恩先入为主地把欧洲绘画中“眼中的自然”认作是自然本身,从而认为细密画描绘的“不是自然”,这无疑是西方学者以欧洲绘画为写实正宗的傲慢心理的反映,同时也说明对伊朗的宗教文化缺乏了解。其实,儿童描绘的就是本来的真实,但这是一种低层次的直观认识,而细密画艺术家的认识是基于哲学层面上的认识。因此,L.比尼恩看到的只是相似的表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二、绘画实践中的伊斯兰合法性
(一)细密画程式上的普遍性与共性
在对画中人物景物的描绘上,细密画着重被画对象的普遍性和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和个性。这是因为人的肉眼只能看见个性和特殊性,看不见共性和普遍性。人的肉眼看不见“马”也看不见“人”,看见的只能是某匹具体的马、某个具体的人。人对普遍性和共性的认识是从众多个性和特殊性中概括出来的一种“类别”,是人的心灵觉悟到这种普遍性和共性而后赋之于自己的认识。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这种悟性来自真主先天的赋予,共性和普遍性只属于真主,只有造物主真主才能看见。在真主的眼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一样的。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这种普遍性或曰概念性正是真主创世的“蓝本”,而人的记忆是真主先天赋予人的一种悟性,被后天尘世的纷扰所蒙蔽。一位细密画画家在经过长期反复的训练之后,其先天的记忆被唤醒,觉悟到最具普遍意义的图像,这便是心灵的觉悟。细密画呈现的即是这种被唤醒的先天记忆,它是以“悟眼”从真主安拉的角度去呈现安拉的创世“蓝本”。尽管在人的肉眼看来,人、物每个都有自己的个体特征,彼此不相同,但为真主服务的细密画画家从来不会面对现实中某匹具体的马或某个具体的人去画“这一匹马”、“这一个人”,而是把马或人的共性特征融会于心,画出的马的确是“马”,但又不是现实中的任何一匹具体的马;画出的人物的确是“人”,但又不是现实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从而避免了陷入偶像崇拜和个人崇拜的异端中,避免了伊斯兰教最反对的东西。正如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第10章“我是一棵树”最后说:“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4]这里“意义”一词即是指普遍性或共性。细密画艺术反对通过对具体事物的仔细观察来作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宗旨。
这一点也与中国画不同,中国画虽然不讲究逼真,但讲究神似。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神似恰恰画的是个性特征。就以画人物来说,神似是抓住具体某个人最区别于其他人的根本性特征,勾勒出来,让我们觉得像某某人,所以我们才说神似某某人。而波斯细密画完全是画共性,所以完全程式化,画中所有的人大同小异,所有的马都千篇一律,完全概念化。
只画人物的普遍性与共性使得细密画成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绘画艺术,前辈大师所绘的题材、形式和技巧皆是后辈学徒亦步亦趋摹仿的典范,后辈学徒一般不敢逾矩,除非他的才能足以使他自己成为公认的大师。这种程式化的方式使得所有的画都千篇一律,大同小异,还能体现出美感来吗?答案是肯定的。当一种程式化成为一种经典就具有了其特殊的美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京剧。京剧艺术完全是程式化的,其唱腔,一招一式,脸谱等完全程式化和概念化,但京剧的美感特征是大家都公认的。细密画从某个方面说,真的有些像京剧,波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故事、经典场景,不知被各个时代的细密画画家反反复复画了多少次,大家都眼熟能详,但依然是看得如痴如醉,这就犹如京剧中的折子戏,这些折子戏的故事情节、唱词唱腔都为观众耳熟能详,一清二楚,依然还是那样让人百听不厌。细密画正是在高度程式化中体现出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
因此,细密画在对人物的描绘上,完全是概念化的,没有人物的个体特征。而国内有些学者对此完全不了解,想当然地信口开河。比如范梦在《东方美术史话》中以细密画“霍斯陆窥见席琳在湖中沐浴”为例,说:“画面中两人眼神对应产生的情感交流以及对女性人体的着意描绘,产生了相当的性魅力,这对那些生活单调乏味而又无忧无虑的宫廷贵族必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像这种表现宫廷糜烂生活的‘偷看’镜头,在细密画中还真不少。”[5](P153)这完全是用欧洲绘画中的人体画的艺术特征来描述细密画,十分错误。细密画作为一种伊斯兰文化的艺术,根本不可能有对人体的着意的描绘。笔者不知范梦先生看的是哪位画家的插图,因为原书未提及。笔者仔细观看过多位细密画画家的不同的“霍斯陆窥见席琳在湖中沐浴”图,并未感到有哪位画家在着意描绘女性人体,对裸体沐浴的席琳的描绘是十分概念化的,与西方艺术中的人体描绘迥异。
(二)细密画色彩上的崇高原则
在色彩运用上,细密画遵循“崇高原则”,认为“崇高高于显而易见的真实。”[6](P3)这个“显而易见”是指肉眼所能一目了然的现实世界中的东西。认为崇高高于人的肉眼所见的真实,肉眼所见的真实并非真正的真实,肉眼看不到的颜色,并不能说就不存在。细密画画的是真主眼中的世界,在真主的眼中,什么颜色都可能存在。这个信条使细密画艺术家打破了自然界颜色的局限,集自然界中所有的色彩美为一体,以鲜艳亮丽的色彩和大量使用金箔来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刺激,让人在目眩神迷中,产生崇高神圣之感。因此,我们在细密画中可以看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各色马儿、山丘或天空,整个画面美仑美奂,呈现出一种幻想的美、升华的美。这里说“幻想的美”完全是从我们的肉眼感知来说的。而对于细密画画家来说,并非幻想,而是一种真正的真实,因为对于细密画画家来说,颜色是被感知的,而不是被看见的,很多细密画大师在失明之后对色彩的领悟和运用往往胜于失明之前。一位细密画画家的失明,往往被认为是真主的恩赐,是进入到安拉的“高贵的夜间”,其理论依据是《古兰经》第97章“高贵”第3—4节经文:“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众天神和精神,奉他们的主的命令,为一切事务而在那夜间降临。”[7]
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红》这一章,详细地描述了“红”这种颜色被盲人画家如何感知:“如果我们用手指触摸,它感觉起来会像是铁和黄铜之间的东西。如果我们用手掌紧握,它则会发烫。如果我们品尝它,它就会像腌肉一般厚而细腻。如果我们用嘴唇轻抿,它将会充满我们的嘴。如果我们嗅闻它,它的气味会像马。如果说它闻起来像是一朵花,那它就会像雏菊,而不是红玫瑰。”[4](P228)这真是写得太精彩了。因此,针对蓝色的马、绿色的天空或紫色的山丘,人的肉眼会说,自然界中没有这种情况。细密画画家们的反驳是: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就说看不见真主。在真主的世界里,任何颜色的东西都会存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主人公之一姨父在被凶手杀害后,灵魂升空,看到了一个只有在细密画中才有的色彩斑斓的世界,看到了蓝色的马,人们相信真主的世界就是如此色彩斑斓、亮丽崇高,那里永远没有黑夜,因此,细密画中的夜色永远如白天一样鲜艳明亮。由此,细密画在色彩运用上也获得了伊斯兰的合法性。
细密画的色彩运用方式从伊朗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来说,也是承继了摩尼教绘画艺术以鲜艳眩目的色彩和大量使用金箔来体现崇高的道统。在伊朗萨珊王朝时期(224—651),摩尼教绘画艺术以鲜艳眩目的色彩、尤其是用金箔作为颜料来绘制经书的插图,以此体现经书的崇高。细密画也大量使用金箔,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开篇被杀害的就是一位细密画镀金师。
细密画主要是为文学作品作插图,不论是文学作品中的世俗题材还是宗教题材,作为插图的细密画都被要求表现崇高。对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来说,也只有鲜艳眩目的色彩才能表现出崇高的宗教之美,而只有崇高才能唤起人们热烈的向往之情,才能产生神圣之感。“崇高原则”使细密画把色彩的审美作用推到了极致,让人在目眩神迷中,产生崇高神圣之感。细密画除了描绘先知们或苏非长老们的故事的作品之外,有很多表现爱情的作品。这种爱情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宣扬的是苏非神秘主义的“神爱”。其理论依据是《古兰经》第5章“筵席”第119节经文:“真主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苏非神秘主义以对真主的神爱为通向真主的重要途径:人在对真主的爱恋中,净化灵魂和心性,使爱、爱者与被爱者达至“人主合一”的至境。苏非文学作品充满爱的激情,作为其插图的细密画也必须要表现出爱的激情,而只有鲜艳明亮的色调才能表现出这种激情。苏非神秘主义本是一种出世的宗教哲学,而细密画对它的表现却是最具世俗情爱意味的男女相爱的图画。可以说,细密画明确地以世俗之爱去喻示神圣崇高的神爱,通过世俗欲望的理想化,达到宗教的神圣、神秘和崇高。这一点在《哈菲兹诗集》的细密画插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哈菲兹的情诗及其细密画插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世俗的爱情表现宗教的虔诚,烘托出神爱的崇高。对伊朗苏非神秘主义文化缺乏了解的人,对这类爱情作品往往简单地望图生义,单纯地理解为表现世俗男女“谈情说爱”或表现“宫廷糜烂生活”的香艳之作。这无疑是轻看甚至错看了伊朗细密画的欣赏价值及其所蕴藏的宗教文化内涵。
对于世俗题材来说,“崇高原则”与细密画是作为一种宫廷艺术的背景相关。作为一种宫廷艺术,细密画要求直接为统治者服务,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因此画面必须富丽堂皇,以烘托出统治者的威严和尊贵。另一方面,古波斯帝国的辉煌一直是伊朗人民心中的骄傲和自豪,歌颂波斯古代帝王的文学作品,比如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经典,反复被不同的画家绘制插图。波斯帝国的辉煌无疑也是一种“崇高”。淡雅的色彩烘托不出“崇高”,只有斑斓艳丽的色彩才能烘托出波斯帝国一代文明古国的富足与奢华、波斯帝王们的赫赫战功和豪华的宫廷生活。冷静的色调适合表现画家的幽思和哲思,而鲜艳的色调适合表现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因此,红色是细密画最主要的颜色,红色是色彩中最热烈最厚重也是最艳丽的颜色。金色主要用于烘托整个画面的富丽堂皇。
细密画强调色彩的鲜艳、和谐、悦目,几乎没有过渡色,色彩总是一刀切,没有次变递增或递减的过程,是大红就统一的都是大红,是深绿就统一的都是深绿,因为渐变的颜色显得轻佻,不庄重,而不变的颜色显得凝重有厚度,才能彰显出崇高神圣。并且,颜色的渐变是因光影强弱变化所致,拒绝表现阴影和黑暗、以绝对光明为宗旨的细密画没有颜色渐变的立足空间。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在《红》这一章也讲到:“法兰克大师选择各种浓淡的红色,用来化各种普通的剑伤,……他们这种方法,大师们不但视之为粗鄙,更嗤之以鼻。只有软弱无知而犹疑的细密画画家才会使用不同的红色调来描绘一件红色长衫。”[4](P228)可以说,“崇高原则”使细密画把色彩的审美作用推到了极致,让人在目眩神迷中,产生崇高神圣之感。
三、细密画创作主体上的伊斯兰合法性
在细密画产生之前,在伊斯兰世界,画家一直被视为偶像崇拜者。如前所述,波斯细密画在技法上受中国工笔画的影响很深,但其精细的程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无以复加、叹为观止的地步。一位杰出的细密画大师在长年累月的精耕细作之后,因用眼过度往往失明,这被认为是真主的恩赐。细密画是画家对真主眼中的世界之美的追寻,那么画家要获得真主的视角眼光,就必须泯灭自己肉眼的视觉。前面讲到了,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肉眼是人认识真理的幕障,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是幻,真理只能用心灵之眼去觉悟。一位细密画大师在失明之后画出的作品,往往胜过其失明之前的作品,因为他已经超脱了肉眼的纷扰,达到了心灵的至境,完全凭着记忆去画。这种记忆被认为是真主先天赋予人而又被后天所蒙蔽,细密画大师经过长年的修炼,重新获得了这种记忆。一位杰出的细密画大师在自己的绘画中沉浸于真主的视角,长年的聚精会神,使画家本人的个体精神渐渐消融在了其心灵所觉悟到的绝对精神之中,进入一种寂灭状态,这时会获得一种时间停滞的永恒感。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有多处地方谈到了关于沉浸在细密画中能让时间永驻这种体验。因此,苏非神秘主义所宣扬的“人主合一”至境被细密画画家所实践。从而,之前被视为偶像崇拜者的画家借由细密画创作过程中的“人主合一”状态获得了自己伊斯兰的合法性。
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主观心灵中,是会体悟到时间停滞的永恒感,这真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体验。唯物主义者一般体会不到也不相信这种状态的存在。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存在。比如,当你专心致志地做某一件事情时,你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当你从专心致志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你才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往往会脱口而出:哟,天都黑了!或:哟,天都亮了。因此,当你处在一种专心致志的状态中,时间对于你来说是停滞的。倘若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中,那就是细密画画家们所体悟到的时间停滞的永恒感。
那么,欧洲绘画能否能带给画家时间停滞的感觉呢?不能。因为欧洲绘画采用定点透视法,格外注重光与影的效果。画家时刻关注光与影的变化,因此画家在画画时,是时时刻刻感觉到时间在流逝的。欧洲著名的印象派画家莫奈就是喜欢专门画某个时间段的景色,比如画上午十点到十半时的景色,过了十点半就不画了,第二天十点再来接着画。因为,过了十点半,在画家眼中光与影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我的名字叫红》最后所说的,法兰克画家“永远停不住时间”[4](P500)。
再从绘画视角来说,经典细密画是一种从高空往下看的俯瞰视角。《我的名字叫红》第13章讲到,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书法家伊本·沙奇尔在清真寺高高的宣礼塔上目睹了蒙古军队在巴格达烧杀抢掠、焚毁书籍的暴行,决心把蒙古军队的暴行画出来,由此开创了细密画艺术。但这只是一个传说。其实,细密画的俯视视角在伊儿汗王朝早期的细密画中并不突出。在帖木儿王朝时期(1370—1505),随着苏非神秘主义的极度兴盛,细密画的俯瞰视角才逐渐凸显出来,生活于伊儿汗王朝与帖木儿王朝之交时期的著名细密画大师祝奈德(生活于14世纪下半叶)的画作已经具有成熟的俯视视角。之后,以贝赫扎德(1450—1531)为代表的“赫拉特画派”强化了细密画的真主全知式的俯视视角,才使之成为细密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俯视视角的哲学基础:一是从真主安拉全知的观望视角出发,这是神的视角,洞悉世间的一切。真主是全知全能的,在真主的眼中,没有夜色,远处的人、物与近处的人、物没有大小的差异,山后的人、物不会被山体所屏蔽,房屋建筑也挡不住真主全知的眼睛,因此在细密画中,房屋建筑犹如被刀从中剖开,里面的人物活动一清二楚,比如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黑说:“要是能像细密画那样,把房子用刀子切成两半,我就能看到谢库瑞到底是在哪一扇百叶窗后。”[4](P147)这也是本文前面所述细密画特殊的空间表现观所承载的宗教哲学内涵。二是从人的认识观出发,苏非神秘主义认为肉眼是人认识绝对真理的幕障,只有人的心灵之眼,即悟眼,才能认识到绝对真理,才能认识到人世间的本来面目。细密画画家作为真主的仆人,履行真主的使命,为真主服务,以心灵之眼把真主眼中的事物呈现出来。因此,细密画画家以心灵之眼与安拉的全知视角融为一体,这正是苏非神秘主义理论的核心“人主合一”的境界。在这一至境中,个体精神消融在绝对精神中,以此获得个体精神的永存。由此,细密画画家借由真主安拉洞悉世间的一切的俯视视角,以及苏非神秘主义的“人主合一”学说,从绘画视角上获得了伊斯兰合法性。
四、细密画创作技法上的个人风格
如前所述,细密画注重所画人、物的普遍性,绘画本身具有浓厚的程式化特征,因此任何的创新、个人风格和签名都被视为异端。因为画家的创新与个人风格意味着擅自篡改真主眼中的景象,意味着凸显自己的创造力,把自己提到“创造者”的高度,这是对造物主真主的僭越。而签名则是把真主创造的美窃为自己所有,更是一种大逆不道。另一方面,人又绝对无法僭越真主,因此所谓的创新与风格实际上是使真主完美的造物变得不完美,出现瑕疵,因而创新与风格体现出的是人的缺陷。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细密画画家严格按照真主的视角来画,不正是把自己置于真主的地位吗?不正是表明“真主能做的我也能做”吗?不正是对真主的独一性和“创造者”地位的挑战吗?这是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第35章中借由一匹马的口吻指出的细密画的哲学悖论。其实,这样的哲学悖论在苏非神秘主义那里并不存在。因为,细密画画家在作画时是处在一种“人主合一”的状态,画家的个体精神泯灭在绝对精神中,其实质仍是真主的独一,没有画家个体精神的存在就没有二元的存在,也就不存在画家对真主的僭越。
在程式化和概念化这一大前提下,细密画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个人风格的存在呢?其实并非如此。其实,细密画技法往往带有画家自己显著的个人特征,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称之为“瑕疵”。因此,小说中奥斯曼大师才可以分辨出一幅细密画中这匹马是出自何人之手,那棵树又是哪位画师所画。若真的是完全的千篇一律,一模一样,如何能分辨?而《我的名字叫红》整部小说对凶杀案的推理,也是以画中的个人风格也就是所谓的“瑕疵”为依据来进行的。其实,当一种个人风格一旦为众人所接受,就成为后人模仿的典范,就不再是“瑕疵”,而被认作是真主眼中本来的真实状态。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很深的宗教哲学问题。这就是,任何宗教都是人创立的,神的意志是靠人去阐释的。所以,古代有先知、使者,现代有各种宗教神职人员,他们被人们视为神的意志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因此,在细密画中,当一位杰出的细密画大师的个人风格被众人所接受,也就意味着他所阐释的神眼中的事物被众人接受,他就如先知使者一般或者如宗教神职人员一般成了神的意志的代言人。
细密画在高度程式化中的个人风格,也如同中国的京剧,京剧也是在高度程式化中某位大师的唱腔风格被大家所接受,就成为后人模仿的典范,比如京剧中有梅兰芳的“梅派唱腔”,程砚秋的“程派唱腔”。细密画也是分流派的,影响较大的画派有赫拉特画派、大不里士画派、伽兹温画派、布哈拉画派、设拉子画派、伊斯法罕画派、奥斯曼画派、印度画派等。如果完全没有个人风格,就不可能有流派产生。
17世纪,细密画在欧洲绘画的冲击下,有些画师也试图变革,吸取欧洲绘画的技法(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姨夫就是主张变革的代表),这种变革特征我们从17世纪之后的细密画,尤其是“伊斯法罕画派”的人物画中可以看到。细密画艺术尽管在奥斯曼帝国淡出舞台,但在伊朗却一直顽强生存下来,这其中固然体现了伊朗文化的独立与顽强,但更体现了伊朗文化善于融会贯通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使伊朗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后,使伊斯兰教伊朗化;也正是这种特性使伊朗现代细密画在接受将绘画视角从神的俯瞰视角降低为人的平视视角的同时,强化了色彩运用的“崇高原则”和笔触的精细复繁,使伊朗现代细密画更加美轮美奂,更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强化了的“崇高原则”使细密画所承载的传统宗教文化内涵依然如故。因此,波斯细密画立足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以独特的绘画视角、空间表现、程式化特征和色彩运用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绘画艺术,而不是某种绘画艺术的附庸或分支,这可以说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一个艺术奇迹。
[1] 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M].孙乃修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莫拉维(鲁米).玛斯纳维全集[M].穆宏燕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4]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M].沈志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范梦.东方美术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6] A.M.Kevorkian,J.P.Sicre.幻想的花园——伊朗细密画七百年[M].帕尔维兹·玛尔兹邦译.德黑兰:法尔让内出版社,1998.
[7]马坚译.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潘文竹
On the Islamic Legality of the 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s
MU Hong-ya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
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s have Sufist mysticism as their concept and theory,and use the eye of the soul to perceive the"origin"of the object to be painted without regard for its distance or brightness.Their purpose is to depict the"blueprint"with which Allah created the world,paying attention to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objects to be painted and thus showing an obvious formularization.In using colors,they take the"sublime principle and depict the colorful world in the eyes of Allah.By taking abird's eye view and using the Sufist theory of"harmony between man and Allah",these painters merge the individual spirit into the absolute spirit of Allah,thus gaining the legality of Islam.
Persian miniature painting;concept of space;formularization;use of color;individual style;Islamic legality
J211.22
A
1005-7110(2013)05-0109-06
2013-06-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批准号: 11&ZD082)阶段性成果。
穆宏燕(1966- ),女,四川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波斯(伊朗)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