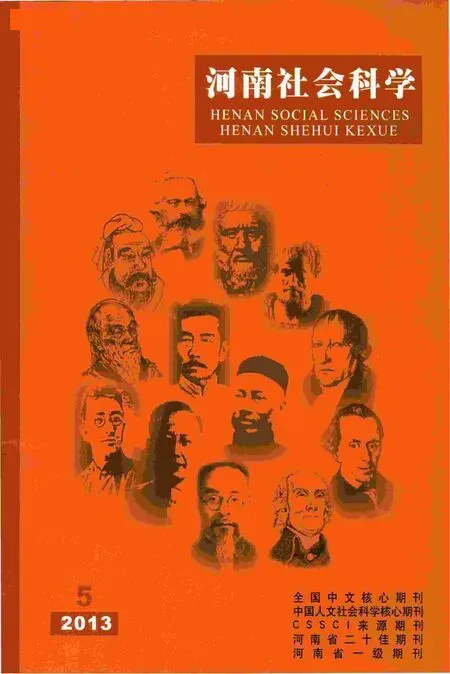最后通牒博弈对参与者的决策影响——通过设计实验研究
刘晓丽,潘天群
(1、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言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是一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两阶段动态非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一名参与者向另一名参与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提出方案的一方被称为提议者(Proposer),另一方被称为响应者(Responder)。如果响应者接受该方案,则按照方案进行分配;如果响应者不同意,则两人都将一无所获。
在标准博弈论中,假定两人是完全理性的,且这是公共知识。根据博弈论的理性人假定:提议者和响应者都是绝对理性的,追求收益最大化。提议者因为具有控制提议权的绝对优势,会尽可能提议最大化自己金额的分配方案;而同样理性的响应者知道提议者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拒绝提议者提出的任何大于0的分配。所以,最后通牒博弈理论上的唯一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解就是:响应者接受任何大于0的分配。从1982年古斯(Güth,Schmittberger and Schwarz,1982)等人设计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至今,许多实验经济学家对最后通牒博弈及其均衡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实验结果因实验设计者的实验设计差异而呈现不同,但其中的规律性也是显然的。如宾默尔(Binmore,K.,2002)说:“实验结果呈现多样化,但是提议者提出的方案很可能在50∶50附近;而对响应者而言,如果其分配的数额不少于三分之一,他将趋于接受。”[1]
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构建一个全新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以研究该博弈的情况以及参与者是如何进行思维的。笔者相信,通过具体的博弈实验,可以分析现实中的参与者是如何进行选择的,且通过展现实验数据体现的规律,可以表达出对实验方法的细致性、精巧性和惯例性的感受,进而有助于思考并研究影响他们进行决策的因素。笔者认为,具体的实验分析和研究对人们理解博弈论的理论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而对具体博弈实验的研究,看似简单,实则更有助于人们对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的理解和把握。这也正是本文的意图和价值之所在。
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其结果
(一)实验描述
我们将最后通牒博弈简化模型以试题的形式做了如下实验。实验参与人为选修“逻辑学动态”课程的本科生,文理科均有。
该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具体题目的内容为:
甲、乙两人分100元钱。规则为:甲提出方案,乙对之进行表决。如果乙接受甲的提议,则按提议进行分配;如果乙不同意,则甲和乙均将一无所有。
(1)如果你是甲,你会如何分配?
(2)如果你是乙,甲提议多少,你能接受?
请给出你的理由。
(二)实验说明
学生不知道这是一次实验。部分学生可能曾经接触过此类博弈问题,或者有一定的博弈论基础知识。学生之间有些彼此熟悉,因为这是临时的课堂考查,存在一定的交流现象。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人同时回答作为甲和乙时的选择实验,不是配对实验,所以少许交流对结果影响并不大。参加此次实验的学生,年龄、男女比例、文化背景等均相当,只是专业不同。因为该实验是一个被试扮演两个角色,所以最后有效被试为多少,博弈配对及有效数据就为多少。
(三)实验结果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根据博弈论理性人假定,理论结果应该是:只要参与者甲给参与者乙的数额非0,那么乙就不会拒绝;而甲能够预测到乙的这种推理,甲给乙的会尽量接近0。最终的实验情况如下:
共有65人参加实验,有1人只填写了名字,没有回答,还有1人的答案只做了分析,未给出选择,所以有效被试有63人,有效参考数据为63个。现以α表示参与者甲愿意分给参与者乙的数额。

表1 参与者选择数额及人数
实验数据如表1(按选择人数多寡排序。其中参与者甲的选择中有三个选择分别为:“α=30、40、60、70”,“α=40、60”,“α=30、40”。为方便分析,将其划归为相应的区间:α∈〔30,70〕、α∈〔40,60〕、α∈〔30,40〕)。
三、对本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的深度分析
(一)对参与者为甲时的结果分析
被试作为甲进行选择时,愿意分给乙的钱数最大额为75,最小额为1;选择“1”的被试有13人,占总被试人数的20.6%;选择人数最多的数额为“50”,有28人,再加上选择数额区间中间值为“50”的3人,共有31人,占总被试人数的49.2%;选择“50”的人数比选择“1”的人数多139%。
将选择金额为区间的学生答案取其区间中间值,然后将这63名被试所愿分给对方的数额进行平均,最后所有有效被试愿意分配给对方的平均数额为36;愿意分给对方的平均额36处于“1”和“50”之间,但是远远大于“1”,低于“50”。
按照区间来统计(选择结果为数额区间的,仍取区间中间值为参考值),实验结果情况如表2。

表2 被试为甲时实验结果区间分布统计
从参与者甲的选择理由看,他们都是为了合理推出对方可能拒绝的最低额。尽管推理内容和方式不尽相同,但是选择动机均为担心被拒绝,都希望给对方一定的数额以确保对方不会拒绝,从而避免一无所得。这说明“避免被拒绝”这一策略性思维的存在。同时选择数额落在区间〔0,10〕中的13名被试,选择分配给对方的数额全部为“1”。这种现象或许说明甲的理性程度足够高,并且认为乙也具有高度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往往会选择“1”。再参看区间〔11,20〕中的选择,我们发现这个区间的选择人数为1,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分析,说明参与者甲通过对参与者乙理性程度的思考,认为乙也具有高度的理性。
61以下的前六个区间,都有被试选择,可以看出参与者都会理性地分析对方的可能选择。但是选择结果的多样性则说明了参与者的理性程度不同。而有半数以上的人选择〔41,50〕,如果把在中间数额50上下浮动最小的区间〔40,60〕定为公平区间的话,那么几乎将近53.9%的被试者选择了公平分配区间内的数额,这说明公平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实验数据的证实。
除选择α=50的28人和选择α=1的13人外,其余参与者在作为甲时的选择中,所选最小的数额为15。这说明参与者甲认为低于总额的15%,对方会拒绝。其他参与者甲所给的答案也证明了他们认为参与者乙会拒绝低于15%的金额。这说明,参与者甲要么是侧重其中一种偏好,要么是综合考虑这两种偏好。
在实验数据中,有4个人分别选择了51、〔25,75〕、〔30,70〕、〔40,60〕,说明参与者甲有人会考虑给予对方的金额超出50。而除1人明确选择51之外,其他3人均选择的是区间,且最大金额为75。这说明他考虑到了对方的非理性问题,但是对对方的非理性程度或非理性因素并没有把握,以至于他给出的数额超出了50,只是超出数额不同。这可能是受对对方非理性的考虑或者是自身某种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果是出于对对方非理性的思考,那么超出的金额可能体现了对对方非理性程度的理解。超出得越多,可能认为对方非理性的程度越高。至于到底是什么因素引发的非理性,则对选择结果影响不大。这个超出的金额最多达到75,结合选择〔25,75〕的参与者给出的理由得知,他所承受的给予对方的最大金额为总数的75%。可见,没有参与者甲愿意给自己只留有25%以下的金额。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参与者在作为甲时,策略性思维和公平偏好起决定性作用。
(二)对参与者为乙时的结果分析
当被试学生作为乙进行选择时,愿意接受的最低金额为1的有7人。选择人数最多的为“α>0”,共有15人,占总被试人数的23.8%。如果宽泛地说0到1之间的所有的数额都是均衡解的话,那么选这个范围的人共用22人,占总人数的34.92%。可接受数额不低于50的有10人,占15.87%。作为乙可接受的最低金额平均为23.5%。
被试作为乙时所给出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
(1)如果参与者甲分配给自己的太少,则心理不平衡,拒绝;
(2)自己分得数额至少和甲的一样多,拒绝被利用;
(3)太不公平的话,不如拿不到;
(4)必须求一个较为公平的方法,满足自己的利益,但因为是甲提出方案,所以自己必然会吃亏,一定要将吃亏控制在一定范围。
从63个有效数据可知,被试学生作为乙时的选择几乎涵盖了从0到100的除0以外的所有数额,且这些数额被选的概率相差不大,这说明其实对于参与者乙来说,只要是大于一个适合的最低数额,他们都会接受的。这个最低限额从数据中可知为23.5%,即总数的23.5%,也就是说,低于23.5%,大部分参与者乙将会拒绝。
上述数据及其分析显示出参与者乙大多数会将>0或≥1作为最低可接受值,可见参与者乙也是理性的策略者。而α>0和α=1时参与者乙能接受的比例则表明了参与者乙的理性程度不一。
选择30与50之间的人数比例很大,结合参与者乙所给出的理由可知,除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绝对理性的偏好之外,乙更为注重“公平”。这里的“公平”,可能是由心理不平衡、自尊引发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因素引发的,“公平”偏好的确是在本次博弈实验中对乙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结合理由(4)、选择最低接受金额为50的人数比例以及接受金额不超过50的人数比例来看,大部分的被试学生或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自己所拥有的否决权,给对方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是接受额差异说明了参与者在作为乙时并非都是追求最大化受益者,一些人还存在着其他的偏好。从63名有效被试给出的选择答案几乎全部都是跨距很大的数额区间可以看出,被试在作为乙时,知道自己拥有否决权,但是对参与者甲的先发优势来说,这只是约束,关键还是看甲如何分配,只要对方给的金额不至于太低,自己的否决权约束就已经起作用了,一般不会拒绝,这种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的关系,正好从实验中被试的选择情况可以看出,即参与者甲的选择明确,而参与者乙的选择不明确。
概括来说,上述分析再次证实了参与者乙具有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但是存在其他的偏好,比如公平。且在参与者乙中,公平偏好更为明显和重要。
(三)实验结果综合分析
综合对甲和乙的分析,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参与者乙不接受接近于0的比例很大,参与者甲也会考虑参与者乙的这种选择。因为参与者甲和乙都会存在理性程度和偏好的不同,且双方都会考虑到对方的理性和偏好,所以,实验结果和理论解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多样性。且双方大都追求“分配公平”,根据参与者甲的理由,参与者甲几乎均是担心被拒绝。这显示出该实验中参与者追求公平的动机为策略性思考,是否存在真正的利他主义不详。而参与者乙尽管理由几乎均为公平因素,但响应者对公平的诉求比提议者要强,故这并不足以说明该实验中存在利他主义。
尽管实验显示参与者是理性策略者,但是结果却多样化,这再次显示出参与者理性程度差异的必然性问题。如果参与者动机是策略的,那么这里的理性有限不能支持“参与者并非追求收益最大化”这一论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参与者依然是“在追求收益最大化”。这种有限理性只能说明正是参与者存在程度和偏好上的差异,才导致了结果差异。但由此并不能质疑“理性人是追求最大化收益者”。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参与者双方地位不均等,这是由双方的权力性质造成的。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差异,甲、乙选择数额明显不同。甲的选择明确,乙的选择不明确。参与者乙之间选择的不同,更多的是体现在最低接受数额上,往往是只要大于最低数额就可以。因为甲的选择是“最多给多少”,而乙的选择则是“最少多少能接受”,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解决最后通牒博弈的关键正是乙的这个最低限额。双方能够避免一无所得的关键不是绝对理性分析,而是如何推测乙的最低接受额。本实验中获得的最低数额为23.5%。可见,在最后通牒博弈中避免乙拒绝的最低数额为总金额的20%~30%。而参与者甲往往能给出的最高额在总金额的50%左右。同时实验结果也说明了最后通牒博弈在现实情境中,如果参与者双方能够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博弈是可以达到均衡的。只是这个均衡处于实验结果的特定范围内,而非理论均衡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结果并不符合理论均衡值,说明参与者远非完全均衡假定的自利。文中实验说明公平是除理性外另一核心的选择偏好。但是公平这一概念自身却存在着来源和动机的不同。本文中的实验则验证了参与者“策略性公平”这一点。最后通牒博弈尽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核心因素还是“理性”和“公平”。尽管多数参与者会遵循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参与者会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
对于上述分析,有三点说明:
第一,该博弈不是实际金钱分配博弈情形,而是假想情形,所分配的金钱是假想的金钱,不是实际货币。因为金钱奖金的刺激不大。有很多学者认为奖金数额跟实验结果有很大关系,并且奖金效应在很多实验研究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尽管也有学者证明这种效应微乎其微,但是由于本实验只是假想的货币,所以肯定会对参与者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该实验的实验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关系未“遮蔽”。双方彼此为师生关系,受试者知道这是一道测试题,故多少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揣测老师的测试目的、意图,从而影响选择。因为在实验者“遮蔽”未满足的情况下,实验对象很有可能愿意“帮助”实验者实现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很有可能学生会猜想,既然老师将这个问题正式地作为试题进行测试,很有可能答案并非那么简单。因而他们在完成实验中会加入更多对老师意图的猜测,这超出了参与者自身的信念范围,可能不是受试者自身的信念。
第三,每个参与者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提议者又是响应者。参与者分别扮演甲和乙双重角色,极有可能会出现作为甲和乙时的思想上的逻辑不一致,这一点本文未作分析。
国内的一些学者对博弈实验及它的学术意义给予高度关注,也做了相关实验。各种实验结果说明尽管博弈论中理性假定存在问题,但是它依然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是参与者理性有限,同时又具有其他的选择偏好而已。文中的实验结果也可以支持这一点。这并不说明博弈论的无效。正如凯莫勒在《行为博弈》中写的:“博弈论的意义是预测人们做什么并给他们提出建议,还是别的什么?学者们的回答是,上述都不正确——它仅是‘解析性的’,是一个关于具有不同程度理性的参与者如何行动的这一数学问题的答案集合。如果人们不按理论的规则行动,他们的行动并不能证明数学有错误,就像发现出纳员找错零钱不能证明算术有错误一样。”[2]
[1]Ken.Binmore.A Backward Induction Experi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2,(104):48—88.
[2]科林·凯莫勒.行为博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