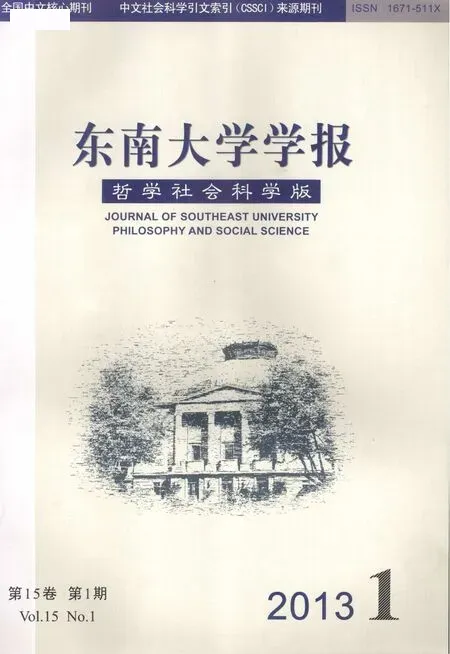趣:艺术生命之元素——从严羽的“兴趣”说到袁宏道的“真趣”论
姜耕玉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少有专门对“趣”的论述,或者说,“趣”没有像“韵味”、“意境”之类形成艺术传统的特定审美范畴。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韵味、意境等,体现了东方文化崇尚含蓄的特点。中国诗画把“生气”视为艺术生命的标志,这是以古代哲学的“气”的范畴为支撑,南齐谢赫的《绘画六法》,把“气 韵 生 动”列 为 “第 一”[1]17。 古 典 诗 人、画家也有对“趣”的艺术追求,但其趣都融于韵味或气韵之中,化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梅花》)式的韵致。这就是散见于诗论、画论中的“情趣”、“意趣”、“逸趣”等。然而,南宋诗家严羽的“兴趣”说,尤其是明代革新家袁宏道提倡“真趣”的观点,虽然涉及文字不多,却是对“趣”的本体论述,见解独到深刻,似被一些研究文章所遮蔽或忽视。
趣,是一种生气和灵机,也是黑格尔所说“心灵中起灌注生气作用”[2]37的基本因素之一。自古诗文之道有理、事、情、景四字,但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写出“趣”字,不能单单停留在使诗文增色的修辞层面上,而且,要从形象的艺术生命元素的深层上来理解。趣,使艺术形象闪现灼灼的生命光彩。在艺术创构中,生命之趣,不仅是艺术真实的元素,同时又是艺术的审美形态。严羽所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说,基本上体现了这两个层次。而一些论者,在从诗人的艺术构思来理解严羽这段著名论述时,大体都是从词、理、意、兴的统一与意境的空灵两方面,加以阐释。这样理解与阐释,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对,只是由于避开或隐去了“趣”字,而使解释宽泛。其实,在《诗辩》的上文谈“诗之法”时,把“兴趣”列为五法之一,与“体制”、“格力”、“气象”、“音节”,相齐并论。笔者认为,理解严羽的“兴趣”说,不可不发掘其“趣”的内涵,这样才能够展示其理论的独特价值。
严羽从诗的起兴出发,以“吟咏情性”,反对和克服当时诗歌受理学影响的弊端。诗歌只有因情性而发,才有表现趣的可能。他明确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3]807诗人对别材、别趣的发现与抒写,与书本道理无关。他甚至还说:“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对“理”与“言”的彻底颠覆,可谓惊世骇俗,而令一般诗家不可企及,这种颠覆本身,却是一种大胆的建构,为宋末以后诗歌洞开了一条新路。严羽的这一观点,包含着艺术形象或诗人的想象,不是语言所能够表达的。严羽反对“理”与“言”,旨在“吟咏情性”,获得诗意形象表现的自由。别趣,既是诗人的情性的花朵,又是诗的想象与创构中智性的花朵。
严沧浪所论“兴趣”的重旨,在于对诗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妙处”的追求。对于“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的比喻,如果仅仅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方面去理解,是不够的。这一观点,前人已经提过。譬如影响较大的,唐代司空图在《诗品》中,不仅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推为《含蓄》一品首句,还有“超以象外”之说。司空图在论及戴容州所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时,还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 景,岂容 易 可 谈 哉?”[4]316严 羽岂不正是论述司空图认为不容易谈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非但如此,他那微妙至深的形象比喻,还凸现了一个趣字,一种虚幻的音、色、相之趣,给人以审美愉悦。中国诗人的心灵之趣,尽在自然宇宙之境,太虚云片,寒塘鹤影,莫不是精神世界的符号。这种形而上的审美趣味,反映着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风尚。严羽的这一喻证,十分精到地阐释了他所推崇的形而上的审美趣味的诗境。
诗歌要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妙处”,需得力于诗人的“妙悟”。刘勰曾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 谓 之 器。”形 器 易 写,“神 道 难 摹”[5]608。严羽提倡的“妙悟”,是中国诗人进入形而上之道的诗性体验的独特方式。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界,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严羽将诗的品位高低,归于“悟”的深浅,称盛唐诸公得于“透彻之悟”。诗境通于禅境,诗人借助于禅道的直觉智慧,可以潜入个体体验的深层状态,获得透彻之悟的真境、灵境。所谓禅道不可道破,“涅槃妙心,实相无相”,表明悟觉形象的微妙莫测而不可言传。禅宗传教所采用的“不立文字”、“拈花微笑”,便是一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意会的方式。诗人、艺术家借助于“拈花微笑”式的艺术传达方式,其至深至妙的透彻之悟、不可言传的心灵之趣,就有活脱脱地和盘托出的可能。“拈花微笑”并非不要文字,而是寻求一种不为言语所累、潜然贯通的诗意方式。唯如是,才有严羽所推崇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上”的境界的可能。譬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因诗人妙悟的博大圆融与浑整洒脱的诗意传达,构成了旨趣静深、超旷空灵的意境。宗白华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6]156所谓“空中之音,相中 之 色,水中 之 月,镜 中之像”的境界,是诗人心灵体验微妙至深的博大境界,往往是在超越物我界限、超越时空时的“直觉悟见”、“瞬间凝聚”。
如果说严羽的“兴趣”说,还主要表现在对诗的品位与境界的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形上的审美趣味,这与神韵、逸致、灵境相融相通,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追求与文化风尚。这样,“趣”也被文人化、诗化,不能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那么至明代,袁宏道对“趣”的张扬与独到深入的描述,则企图在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中,使诗和文学回归人的本真。这种“真趣”论,不仅是对文人雅趣中玄虚倾向的反拨,也对明代兴起的市井俗文学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袁宏道的“真趣”论,是他所提出的“独抒性灵”的观点的延伸。他说:“真人真作,故作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7]。趣,是人的天性、灵性的体现。只有“任性而发”,才能调动起性灵之趣,并使之得以展示。李贽在提出“童心”说时,也有过“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8]之语。这般从人的本性上,张扬表现“趣”,大有将“趣”视为“童心”、“真心”、“真情”之标志。而千余年来,只是“童心”说、“性灵”说,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趣”的论述,却很少引起学界的注意。虽然论述很少,且是在札记中涉及,但其观点却使人耳目一新,令当时文人振聋发聩。本文从艺术构成的本质上理解“趣”,袁宏道的“真趣”论,具有独立范畴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趣”的审美认同。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语,唯会心者知之。”这与严羽所称“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相一致,都认为“趣”独得妙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难得的高级的审美形态。但两人对“趣”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袁宏道一方面尊重“会心者”,即对趣的微妙感悟,包括对不同趣美的价值取向的肯定;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当时文人中“慕趣”、“求趣”的“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的倾向,认为这种脱离世俗与人的神情的趣,只是“趣之皮毛”。他由此提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
袁宏道所论“趣”的核心价值,在于追寻了“趣”的发生的源头,从返归自然、返归人的本真方面,对“趣”作了深入论述。所谓“趣得之自然者深”,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从趣的表现形态看,趣美的生命在于自然;二是从趣的内质或构成看,趣,依附着人的本性之真,只有发自人的天性、“性灵”之趣,自由绽放之趣,才会充满生命力,带着生命本色烂漫伸展。袁宏道强调趣的自然性,企图使文学创作走出复古派和理学的阴影。
知识、官品往往是对“趣”的束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年长官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9]。袁宏道这一看法,切中古今时弊,深刻道出了文人失去真趣的社会思想原因。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10]134文人学士愈是读书识理,反 而愈失去童心、率真,甚至变得利禄熏心。言不从心,身不由己,官样文章,毫无生趣;或使假言、假文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学问与智慧,由此成了束缚和扼杀童心与性灵之趣的精神杀手。袁宏道的这一看法,虽与严羽关于诗有别趣,与理无关的观点,同出一辙,却针砭时弊,显示批判的锋芒,把病端剖析得透彻之至。
袁宏道推崇“童子”与“山林之人”之趣,具有彻底卸掉思想文化重负、砸烂精神枷锁的意义。“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目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这即是“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袁宏道称道“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9],是指童子之趣。这可以理解为皈依人之初的本真意义上的趣,具有纯粹的原生态的特征。成年之后,年岁越大,往往因变得世故和城府而失去或遮蔽了人生固有的趣。山林之人却是个例外。他们基本上处于世外,目不识丁,安贫寡欲,没有背上任何精神负担,因而,他们还拥有人生的乐趣。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人类只要远离社会思想与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同样有“近趣”的可能性。而本文更有兴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山林之人”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保持自身的本真之趣?从“童子”到“山林之人”,都是“虽不求趣而趣近之”。这即是说,趣,不是刻意可求,只要保持一颗童心,不背上思想文化的重负,就有“近趣”的可能。趣,就包孕于童心之中。人类并非要回到童年,也不可能回到童年,而是要在不停地去蔽中拥有和保持童心之真、之趣,这是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之所在。
趣,有俗趣与雅趣之分,文人视野中的野趣,可谓雅趣的变奏。我们称“趣”具有审美价值,也是指文化意义上的“趣”。一方面,我们要摆脱文化重负,回到人的本真之源去找回真趣,另一方面,趣,又不可避免地反映着人的个性与文化素养。袁宏道所说“性灵”,大概是指人先天的灵性与后天的灵性的合一,而后天的灵性,就折射着人的素质和智性。他主张“淡”,意在淡中求真趣。他既称“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又说“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11]。趣,得之自然,任乎情性,表现为淡的不可造性;而付诸艺术形式,需要通过艺术创造赋予淡以质感,加大其表现力,“大都入之愈深,则其言愈质,言之愈质,则其传愈远”[12],这又表现为淡的可造性。元代画家、书法家米芾在评论北宋巨然的山水画的“平淡天真”时,称之为“老年平淡趣高”[13]231。如此“天真”之“淡”中见“大趣”、“高趣”,折射着画家的胸襟高远。又如以“逸品”著称的倪瓒作品,草草简淡之笔中逸趣横生,却是一种任乎情性、纵笔自如的高浑大趣之境。这都可以视为袁宏道所谓性灵之“淡”不可造与文中之“淡”无不可造的有力例证。
严羽的“兴趣”说,也推崇“淡”。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侧重于“淡”的形式创造论。“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这一审美标准,表现了对以虚为实,以无为有的艺术追求,可谓将淡的形式创造发挥到了极致。老子说:“淡兮,其若海。”[10]117景外之景,相外之色,韵外之致,境外之境,如此虚幻之美,是一种浑大之美,具有极大的包蕴性。这种以老庄、禅宗的哲学为依托的艺术思想,颇能展示形而上的东方艺术精神。
古代诗人、艺术家讲求淡泊胸襟,在《诗品》中,“落花无言,人淡如菊”[14]18,是对淡泊心境的深度描述,成为《典雅》一品的范式。这种隐逸、出世之淡,已经成为古代诗画艺术所普遍追求的一种审美趣味。发人深思的是,袁宏道所说“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强调“真性灵”之淡,不可造,是不是要执意与“假性灵”之淡,划清界限?文化传统或者对某种文化的崇尚,如果日渐变为对自身心灵的束缚,致使失去本真,性灵也就有伪。袁宏道的“真趣”论,从对人的本真、对自然的张扬方面,可以说,激活了严羽的“兴趣”说。这一文学主张,不同于庄禅的返本归真,而是走向世俗、追求人的生命真实,体现了穿越时空的艺术精神。它对于文学创作所发生的作用,一是对作家创造主体本身,一是对艺术形象的创造。
作家创作的灵感和艺术生命,总是表现在对心灵之真的感悟与不断追问,对人性和性灵之趣的依恋与发现。“山林之人”已经离我们远去,而如何保持“山林之人”式的无拘无缚、自在自由的心灵,却是拥有灵趣、发挥艺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应该说,提倡个性解放、使个人的天性得到自由的发展的现代文学精神,与袁宏道的“性灵”、“真趣”的观点,也可以说一脉相承。摆脱旧的束缚,又会落入新的束缚。袁宏道所说“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的现象,依然没有绝种。返归自然、返归本真,已经注入现代哲学精神,成为反对人的异化的精神旗帜。袁宏道称道的皈依人之初的本真意义上的趣,即“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已经被现代艺术思想所点燃与照亮。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童心、童子之趣,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新鲜话题。
趣,作为心灵本真的自由显影,是艺术形象创造中个性表现的基本内容之一。袁宏道说:“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15]明清小说在文字描写的口语化中,十分重视对人物个性刻画与讲故事过程中趣的氛围的渲染。尤其是清代言情小说,对人物的情性、情趣的发掘,成了心灵逼真的表现。譬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称大观园是“女孩子天真烂漫的混沌世界”,着力展示了少女们的丰富情趣和活泼快乐的天性。曹雪芹的好友明义有评诗云:“怡红院里斗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天气不寒还不暖,曈昽日影入帘多。”[16]11这首诗最早透露《红楼梦》成书时所展现的青娥红粉争艳斗俏、情趣盎然的场面。小说中描写大观园女儿们斗俏取笑的形式,表现为雅谑。雅谑,也是谐谑,“更多的是愉快和机智的放肆”[17]93这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女孩子的天真烂漫和灵秀之气。曹雪芹对大观园少女们的天性灵趣的尊重和发掘,无疑增强了她们最后被毁灭的悲剧价值。再如,蒲松龄的短篇小说《婴宁》,全篇有26处写婴宁的笑,有遇面捻花含笑,有倚树孜孜憨笑,有初见微笑,有户外嗤嗤笑声,有客前忍笑,有叱叱咤咤,放纵大笑,还有与王生相见时,她且行且笑,边说边笑,乃至“笑极不能俯仰”。种种笑姿,发乎情性,出乎自然,是这位少女在不同场合里真实情态。小说中这样写道,她“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显然是对婴宁纯真灿烂的笑的美的认同。笑,虽为形趣,却耐人品味。按照封建社会中“淑女”标准要求“笑不露齿”,而蒲松龄写婴宁无拘无束的笑,正是在远离世俗、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桎梏中而闪现心灵的光辉。当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性格各异,即使表现“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同样可以张扬自由和真趣,关键在作家对人物的体验与认知。
至于由心灵的机智而产生的趣,包括袁宏道所说“谐谑”,包括运用借喻、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而产生的情趣、谐趣、机趣等,只要是人的本性与性灵的自由抒发,同样属于“任性而发”的“真趣”范畴。譬如,王实甫《西廂记》中红娘善于周旋、成人之美的倚门卖俏、调笑谑语,则是她心灵的智慧的表现。金圣叹称红娘“如从天心月窟雕缕出来”[18]74,这种“灵襟”、“慧口”,更藉助于她的灵性的发挥。与西方幽默、滑稽相比,红娘的调笑谑语,属于自然清纯的一类。幽默、滑稽,“摹仿偶然的事件以及情况、性格的荒谬可笑”[19]41,在更大程度上制造笑或喜剧的效果,但同样依赖于作家、艺术家的“真心”。
]
[1] 谢赫.古画品录[M]//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严羽.沧浪诗话[M]//中国历代诗话选,长沙:岳麓书社,1985.
[4] 司空图.与极浦书[M]//中国美学史资料挥编.
[5] 刘勰.文心雕龙·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 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M].
[8] 李贽.容与堂本《水浒传》回评[M].
[9]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陈正甫会心集[M].
[10]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呙氏家绳集[M].
[12]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卷三·行李园存稿引[M].
[13] 伍蠡甫.中国名画鉴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14] 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M].济南:齐鲁出版社,1982.
[15]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二十七·听朱生说水浒传[M].
[16] 一粟.红楼梦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8]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9]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赫斯列特.英国的喜剧作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