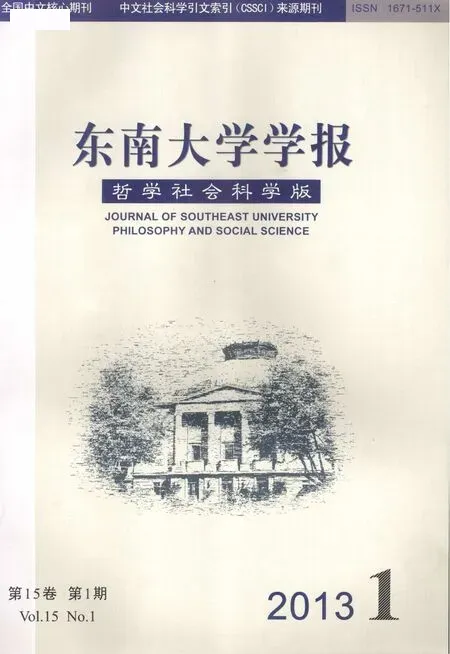《水浒传》忠义伦理的悲剧精神
宋 铮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6;沈阳师范大学 戏剧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水浒传》问世以来流布广泛,近年又被多次翻拍成影视片①据统计,近年《水浒传》影视剧的版本主要有:1972年张彻等执导同名电影《水浒传》;1976年BBC版《水浒传》;1983年山东版《水浒传》;1998年央视版《水浒传》;2011年鞠觉亮版《水浒传》等。。编撰者出于争取收视率、票房的考虑,借助新兴媒介的视听传达优势,对其中的打戏、情戏煞费苦心,特别是近期的几部水浒剧已几乎将其打造成为商业化的武侠情爱戏,而对其思想性方面的挖掘却很欠缺。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其价值肯定不局限于侠情,其精神意蕴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和阐释。且目前的创作倾向也滋生出很多负面效应。它既误导了观众对于作品的理解,扭曲了作者的叙事意图,更掩盖了原著的精神价值。比如,观众看完《水浒传》后还会留有疑问,为何才貌文武都不出众的宋江却能被推举为梁山头领?为何众人在梁山泊春风得意之时非要亟待接受朝廷招安不可?为何宋江在临死前还要毒死追随者李逵?改编者应当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我们认为,对《水浒传》特别是宋江的评判应当超越武侠、男女、权谋等传统批评意识,特别是要打破“投降派”、“造反派”等政治框框。更应当从其思想意蕴特别是伦理意识层面展开分析。悲剧就是要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眼看梁山好汉的豪情壮志被无情吞噬,英雄末路的夕阳悲歌必能唤起有识者的警醒和共鸣。而武戏、情戏不过是其中精神意蕴的装饰和铺垫。《水浒传》其实是一部具有浓重史诗意蕴的忠义伦理悲剧。其悲剧冲突的形式在于宋江等梁山好汉对忠义伦理的践行及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以及由此造成的强烈的悲剧精神情感体验。其精神价值不仅在于对正史“忠义传”引发的英雄入史情绪的深刻反省,更在于对封建忠义的伦理悖论的批判揭露。对忠义伦理的实质认识不足的梁山好汉的忠义实践历经烦忧、事败身死,换回的却是无尽的悲怆。其悲剧精神最终在带有浓厚仪式性、狂热化的宗教式的显圣叙事及其精神情感中达到了和谐圆融的境界。很显然,《水浒传》的悲剧形式和情感境界都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民族性格。
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展开具体分析:一是从叙事结构入手,分析《水浒传》的忠义伦理构架,指出宋江能够成为梁山首领的伦理因素;二是分析忠义伦理的逻辑悖论及其悲剧性。揭示梁山好汉践行忠义伦理必然遭致失败的命运。重点是指出宋江等人以忠义为标榜,却不得不破坏忠义而引发的精神危机。三是分析忠义伦理、“忠义传”的实质,诠释《水浒传》忠义伦理悲剧的史诗意蕴。即忠义伦理并非儒学、理学所标榜的形上整体,而是忠、义两个伦理系统的辩证否定。同时,“忠义传”其实是忠义伦理的愚夫派对,是封建统治者操控世人思想的两道符咒,正史“忠义传”的流布不仅让世人更加难以明辨忠义伦理的悖论实质,反而鼓舞出强烈的英雄入史的终极预期,它们共同导演了宋江等人的悲剧结局,这也使《水浒传》流露出浓厚的悲剧史诗意蕴。四是分析《水浒传》悲剧精神的情感圆成。即苦恼感、悲怆感、宗教感依次递进,最终达到和谐圆融境界的精神情感逻辑。
一、《水浒传》忠义伦理的叙事布局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水泊梁山的正堂高悬的牌匾亦名曰“忠义堂”。可见忠义在《水浒传》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它正是梁山泊对内凝聚战斗力,对外展开武装斗争的思想武器。而且,忠义也是作者所要传达和反省的伦理意识形式。一直有人质疑,为何宋江才貌文武并不出众,却能够坐到梁山第一把交椅。即使在晁盖死前,宋江在梁山内外的影响力也几乎超过晁盖。所以有“宋江上梁山,架空了晁盖”一说。为何?这完全可以用忠义伦理意识的叙事布局来加以阐释。
第一,从宋江个人的伦理意识来看。“智取生辰纲”一节,他甘冒生命危险通风报信且私放晁盖等人。后又于乌龙院误杀阎婆惜,且又被刺配充军、被迫上梁山。从县衙小吏到罪犯最后沦为强盗,此间遭受的种种磨难均由义气引发。虽然他此前早有“及时雨”的义名。但从全书看,他在私放晁盖等人之前,并没有接济或结交过影响力较大的江湖人物。想必也都是一些小人物。但这次不同,他不仅出于义气徇私枉法,不惜与以徽宗皇帝、蔡京、高俅等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划清界限,还大义灭亲杀死外室阎婆惜。因此义名远播。宋江上梁山之前更多的是表义。他虽是小吏但在官场地位低微(宋江被人尊称为“呼保义”而欣然接受,其实这个职称也不过是武职52阶中的第49阶),后来又遭遇变故下狱充军,那时大谈忠君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还显得有些滑稽。上梁山后,随着个人影响力和梁山实力的加强逐步提出践行忠义的构想、策略,特别是在晁盖死后才正式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此外,他还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着手统一梁山内部思想,希望藉此实现由义到忠的过渡和跃进,为招安做好思想动员。此举迎合了封建伦理标榜的忠义原则。从而使梁山走上了由自立山头的强盗团伙向替天行道的忠义堡垒的形象转换的道路。忠义是一套由封建统治者炮制出来并极力标榜、弘扬的伦理规范。在《水浒传》中,坚决践行忠义的人物首推宋江。忠义伦理的精神力量把这个小人物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他同时也成为忠义伦理操控下的牺牲品。其才智等局限使他注定无法看清忠义伦理的实质,无法掌控扭转梁山的未来。所以,其意识和行为都极具作为忠义伦理形象的特征。
第二,从宋江等人的人物原型(历史形象)与小说形象的反差来看。梁山好汉原型的民间形象自宋代以来就开始形成褒贬赞骂等不同版本。对其评判甚至形成观点上的尖锐对立。即使在同一部书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宋江三十六赞》中,著者既对其为盗为寇口诛笔伐(比如,卢俊义“风尘太行,皮毛终坏”,解珍“左啮右噬,其毒可畏”,秦明“天心无妄,汝孽自作”,李逵“山谷之中,遇尔亦凶”);又对其效忠王室褒奖有加(比如,“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潜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端能去病,国功可成”);而嘲讽诋毁之词也是随处可见(比如,张清“箭以羽行,破敌无颇,七札难穿,如游斜何?”,杨志“圣人治世,四灵在郊。汝兽何名,走扩劳劳。”)。但是,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形象几乎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正面意义,诋毁、嘲讽之词已然不见踪影。显然,这种正面意义的获得是与其对忠、义的践行分不开的。当然,为了赋予其更多的正面价值,创作者已经对宋江等人的造反本事做了大肆地改写和弱化,甚至还将造反写成了保义尽忠。鸡鸣狗盗、打家劫舍、坑蒙拐骗、滥杀无辜等行为也被定下了瑕不掩瑜的基调。
第三,从全书的叙事结构来看。宋江私放晁盖,结果促成梁山泊迅速崛起,实现了义的武装割据。这在全书具有破题的意义;晁盖等人大闹江州劫法场,宋江上梁山小聚义则为全书的小高潮;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众英雄排座次为全书总高潮;宋江被毒身死则是全书结局。可见,《水浒传》的叙事也是以宋江践行忠义的荣辱沉浮为线索的。但是,《水浒传》的价值不仅如此。它不仅不是对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忠义伦理道德规范的注解、迎合,而是对其全面的反省和批判。而这种反省和批判正是通过对宋江等人悲剧命运的感慨喟叹和惺惺相惜揭示出来的。
二、《水浒传》的忠义伦理悖论及其悲剧性
忠义是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既是道德理念又是行为规范。可是封建统治者从未对忠义伦理的内涵及逻辑结构做过系统阐释。在他们那里,忠义伦理只是作为一种道德理念被悬置。即忠义作为一个逻辑整体的伦理道德理念具有无可争辩的形上性。封建社会里,第一个对此进行反省的著作却是《水浒传》,它以生动的笔触告诉我们,忠、义之间并非封建统治者所标榜的形上的伦理逻辑体系。相反,忠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否定的辩证关系。这一切都能够在忠义伦理的逻辑悖论中得到解答。
第一,忠义伦理在等级制度上的悖论。很显然,义具有鲜明的平等性,忠则带有浓厚的等级性。因此,由义到忠并不具有形而上的过渡性,因为它们的伦理基础迥异。历史上,无论是刘邦、李世民还是朱元璋,在得到江山之后都对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痛下杀手,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必须建立并坚决维系以他为绝对权威的等级关系。使其他兄弟之间的义的联盟解体,同时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在《水浒传》中,统治者绝对不会允许有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义的集团存在,而必须动用一切手段瓦解、消灭之。
即使是梁山内部也受到等级观影响,这使兄弟之义的平等性大打折扣。李逵、武松等人对宋江产生崇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等级地位低下(比如,宋江和武松在柴进家相遇吃酒,武松就自然而然地在末座陪酒,不敢造次)。在宋代,娼、妓、隶、卒属贱民之列,而宋江能够看得起他们,还与他们称兄道弟,这对他们来讲绝对受宠若惊,进而感激涕零。宋江本人也受等级观念影响,他一直梦想着能够实现从吏到官的身份转换。在宋代,吏与官的等级差异较大,难以过渡。所谓“一日为吏终生为吏”。而且,梁山排座次的做法本身也是等级观念的变形。除此之外,梁山上也是派系林立,如实力较强的江州集团、二龙山集团、石碣村集团不仅排挤其他好汉,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在招安的议题中爆发。这不仅造成了梁山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削弱,事实上也使兄弟一处、快活到死的愿望沦为画饼。所以,忠与义的伦理意识形态在等级观念之下是无法调和的。
第二,忠义伦理在伦理实体上的悖论。任何一种伦理范畴都应当有对应的伦理实体支撑。伦理实体是伦理范畴取得自身合理性的基本要素。梁山上大多数人无家眷,无子嗣。鲁智深出家、李逵丧母、武松杀嫂,宋江杀惜、卢俊义杀妻、林冲家破人亡。其他人也不外如是,都是一些无家可归之人。还有一些人对女人抱有不同成见,如吴用、石秀、李逵、阮氏三雄。所以,梁山作为义的群体的先天不足在于后继无人。多数人上梁山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当时的伦理秩序的失望和否定,这种否定也多表现为对其存在及立身之本即家庭观念的决绝行为、态度。但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实体。伦理实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具有其延续性。所以,伦理实体不仅需要夫妻结合,还必须以后代的降生作为存在条件。而梁山必须寻找到一条出路满足这种基本的伦理实体性、伦理延续性。对于宋江来说,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造反,由自己当皇帝;二是接受招安,认同现在的皇帝。但是,这两种办法的结果都是重新回到封建忠义伦理的轨道,都必须搁置或放弃聚义的打算(比如,宋江接宋太公上山,李逵接母亲上山,柴进接全家老小上山,王英与扈三娘结合等行为就是意在调和家庭伦理与忠义伦理的这种对立关系)。所以宋江替梁山寻找的出路也就成为对其之前聚义的否定。另外,再加上朝廷的昏庸腐败,奸臣当道,这造成了梁山兄弟既不得不反(聚义),又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反(接受招安)。所以,宋江等人难以摆脱进退维谷、必然失败的结局。
第三,忠义伦理在其践行者上的悖论。宋江是《水浒传》中忠义伦理最忠实的践行者。他在江湖上人称孝义黑三郎,说他对父母孝顺,对兄弟朋友讲义气。上梁山之后,他又提出了忠义的构想。既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又要替众兄弟着想,使大家能够衣锦还乡。虽说其出发点是要维护忠义伦理,但其行为本身却不断造成对忠义伦理的破坏。比如,私放晁盖、杀阎婆惜是枉法,篡改晁盖遗嘱是不义。宋江只能在忠与义的漩涡中徘徊挣扎。其结果不仅使梁山兄弟离散身死、他自己也被奸臣所害。宋江毒死李逵一节带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因为怕李逵在他死后造反毁了他的忠义之名,但毒死李逵本身就是对义的否定。宋江在忠与义之间必须做出取舍,这是既无奈又必然的选择,作者正是以这种方式否定宋江一贯奉行的忠义伦理。同样,梁山被招安后奉命征方腊的军事行动也是对其忠义伦理观念的嘲讽。对于梁山好汉来说,方腊就是自己的另一个结果。
就形势来看,宋江在义之上冠以忠也是形势所迫。这不仅是从壮大梁山声势所作的考虑,其实也是对梁山兄弟行为规范的一种约束。因为梁山必须得迅速扩大影响、壮大实力,忠义之名在当时能团结更多的英雄好汉。只有自己的力量强大了,才能对抗官府的围剿。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像二龙山、桃花山等山寨一样被剿灭。梁山人物身份、身世各异。其中很有一些杀人越货、打家劫舍、鸡鸣狗盗之辈。大家虽然在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但这种义明显表现出了圈子特点,缺乏普适性。宋江提出忠义构想不仅能美化梁山的道德形象,使之成为约束众人的行为规范;也能使梁山与整个社会所奉行的伦理规范接轨。但是,忠义伦理在逻辑上存在诸多悖论,难以付诸实施,充其量不过是形而上的口号而已。
三、《水浒传》忠义伦理悲剧的史诗意蕴
“忠”字最 早 见 于 《论 语》[1],“义”字 在 《荀 子》、《礼记》等先秦典籍中也已出现①先秦典籍中关于忠、义的记载有:“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荀子·大略》);“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商君书·画策》);“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众敬贵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韩非子·解老》)。但一开始并无明显区别,可以互换。汉代以后忠开始专供君主使用,义也开始具体指向乡里、夫妻、兄弟、朋友,且多指向非血缘亲情。忠义作为专属词汇(合体)出现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东汉。据考证,最早见于王充的《论衡·齐世》,“语称上世之人重义轻身,遭忠义之事,得己所当赴死之分明也,则必赴汤趋锋,死不顾恨”,正史中最早出现忠义一词的是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忠义获宠,古今所同”。从伦理意识的逻辑来看,忠是由孝衍进而来,即从孝延伸至忠的逻辑,它们都带有等级观念的色彩。义则是仁的衍化,即义延伸至仁的逻辑,带有一定的平等意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取义与成仁是可以贯通的逻辑步骤。《周易·说卦》中就已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12的说法。仁、义是圣人的“立人”之道。所以,忠、义的伦理基础和伦理逻辑迥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封建统治者大都希望将忠义作为一个整体言说,即赋予忠义伦理形而上的整一性。从这里能够看出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潜在影响。忠义的合体很明显是对忠义本意的篡改,是统治者打击反对派特别是农民起义的一道符咒。他们为了使忠义伦理获取表面的“合理性”,进而迷惑人民,推出了关羽、杨家将、岳飞等忠义典型,并将其标榜为忠义双全的典范,纷纷写进正史树碑立传,即“忠义传”。自《晋书》至《清史稿》,其间正史中均列有“忠义传”。设立“忠义传”正是封建统治者对忠义伦理的维护和肯定。“忠义传”成了践行忠义伦理的行动者的指南针和光荣榜,而忠义行动则成了走进正史即名垂青史的一块敲门砖。“忠义传”的流行是使忠义伦理从道德理念下降成行为规范的重要步骤,也是使忠义行动获得封建统治者认可的荣誉证书。宋江等人不惜一切代价践行忠义伦理,这也是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炮制的“忠义传”所引发的英雄入史预期以及入史情绪的影响。或者说,以宋江等人的才智机缘本就无法看清忠义伦理的悖论实质,再加上“忠义传”传统暗示出的忠义行为能够名垂青史的假象,宋江等人就更加难以逃离忠义伦理汇集成的理念陷阱以及舆论漩涡。在去留取舍、生死存亡关头放弃反抗、选择了逆来顺受,失去了一贯的英雄本色。结果,宁可生时身心俱焚,也一定要彪炳史册成为宋江等人的最终幻想和最后寄托。忠义伦理与“忠义传”就是造成梁山好汉悲剧命运的两个主谋。
但是,他们的愿望到头来却还是一场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反贼录”、“贰臣传”、“荡寇志”这类东西。水浒英雄们的事迹被歪曲、被埋没,最终也只能沦为野史谈资。宋江等人根本走进不了正史“忠义传”,历史上的“忠义传”中也从来就没有这类人的容身之处。“一日为贼终生为贼”的宿命早就注定。反过来看,真正的践行忠义之人不在“忠义传”之列,这难道不是对封建统治者炮制的“忠义传”的有力讽刺么?可见,作者以“忠义传”的史传形式叙事梁山好汉,其意并不仅在于为他们树碑立传,而是在于揭露忠义伦理的悖论实质和欺人本质,还在于以此戳穿封建“忠义传”的虚伪面目。当然,也是对受到这种封建教化思想影响而滋生的英雄入史情绪的深度反省。无论如何,以悲剧意识书写忠义之人的《忠义水浒传》最终成为对正史“忠义传”的反思批判之作。
忠义两难全尽人皆知,践行忠义苦不堪言也有据可查。历史上,即使关羽、杨业、岳飞等人物也都在忠义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最终也大都苦心孤诣、命运乖舛。因为忠义不仅不是形而上的可过渡的整体,相反则是一种相互否定的辩证逻辑。即忠是对义的否定,登上权力巅峰的统治者不会容忍别人跟他讲义,也不容许义的集团出现;而义是对忠的否定,以义积聚的力量必将会对统治者造成威胁。两者难以达到交融的境界,既相生又相克。事实上,历代农民起义者往往就是以义的名义凝聚力量,并以对义的摧残完成向统治者的蜕变。在封建社会,忠义只不过是统治者们夺取政权、排除异己的御人之术而已。《水浒传》正是以梁山好汉必然失败的命运揭示出正史“忠义传”的愚民本质,宣告了封建忠义伦理的破产。由于梁山好汉无法看清其本质,不得不在此中挣扎,直至心神俱灭,进而造就出一部带有史诗意蕴的伦理悲剧。
四、《水浒传》悲剧精神的情感圆成
梁山好汉因为对忠义伦理的欺人本质缺少足够的认识,同时又执着于忠义伦理的实践,由此引发了愈来愈严重的精神情感危机。按照康德的意见,悲剧本就属于一种高级的“精神情感”[2]24之囊,能够以此激发调动各种情感元素。精神是使心灵鼓舞生动的原则,是推动叙事高潮的气韵生动,更是真实生命之内充。多种层级样态的精神情感杂糅相济,达到了近乎和谐圆融的境界,使《水浒传》获得了多重的情感张力,引发了更多复杂、丰富的情感体验。
第一,苦恼感。黑格尔认为,苦恼感是“精神努力企求客观化其自身但又未能达到自身的客观化而感到的痛苦”[4]202。作为忠义伦理的信奉者,梁山好汉在践行忠义伦理的行动中逐渐发觉其与忠义伦理实体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裂痕。也就是说,梁山好汉强烈而执着的忠义实践意识与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义伦理实体(体系)之间呈现出日益对立的格局,而这种对立正是由他们对忠义伦理的践行所引发的。这是苦恼意识产生的逻辑。用宋江的话说就是“旦夕不乐”。这与主动积极的忧患意识不同,苦恼感来自于对自身存在价值及行为合理性的质疑和无奈,是被动消极的情感状态。比如,在梁山春风得意之时就苦恼于强盗之名(为义舍忠);在众英雄排好座次之后苦恼于被朝廷当强盗剿灭,既要反抗朝廷围剿,也要手下留情,为招安留条后路、做好铺垫(得义望忠);在受到朝廷招安之后又苦恼于兄弟离散(得忠而守义);宋江死前苦恼于李逵在其死后谋反而灌以毒酒(为忠舍义)。旷日持久的烦忧、日益渐浓的苦恼感是推进《水浒传》叙事的逻辑动力和重要情感线索。
第二,悲怆感。作为忠义伦理的行动者,梁山好汉不得不应对忠义伦理的悖论实质。由此在忠义之间徘徊。宋江等人误将自己标榜为忠义伦理的标的物。寄托于以自身的行动印证忠义伦理的合理性,并期待通过对忠义伦理的践行塑造自身的道德形象,并以之安身立命。然而实际上,这些人不过是忠义伦理的验证者、探索者、行动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使命更应当是以其对忠义伦理的实践检验其真理性(合理性),而不是以忠义伦理的标的物、榜样模范自居。但受到各种局限,梁山好汉无法看清忠义之间的悖论形态及其辩证关系。误将忠义理解为可以过渡的形上整体。因此,强烈的忠义形上(建构行动)意识与忠义伦理的辩证实质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宋江等人以维护忠义伦理的形上整体为最终目标的行动必将失败。尤其是在全书的后半部,忠义伦理的坚定行动者集团——梁山好汉悲怆身死,恰似呼啦啦将倾之大厦,呈现出无法挽救的崩溃趋势。金戈铁马、壮怀激烈,换来的是一抹英雄泪。旷世悲歌无人应合却足以震荡心肺。梁山好汉的不懈努力最终无法挽回彻底的失败,留给自己和世人无尽的悲怆。宋江被朝廷赐毒酒以及自己亲手毒死李逵的叙事也在事实上(即,全忠和全义两个方面)象征着梁山好汉践行忠义伦理实践的破产。
第三,宗教感。宗教情感的实质是信与爱,宗教感也是一种最高级的终极情感。宋江等人在践行忠义伦理的过程中,逐渐放弃、远离了辨别是非对错的理性思考,而是将忠义伦理提高至信仰意识的地位,即“伦理精神的宗教”。也就是说,宋江等人践行忠义伦理的行动不仅成为对其自身价值的确证,其行为更是对忠义伦理的确证和信仰形式。忠义已被上升为终极目标,再不可争辩。忠义伦理、行动不受理性操控,相反,则成为一种宗教式的精神居所。所以,《水浒传》的内在逻辑要求它必然会以宗教性的叙事收场。即“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徽宗“具宿太尉所奏,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后来宋公明累累显灵,百姓四时享祭不绝。梁山泊内,祈风得风,祷雨得雨。又在楚州蓼儿洼,亦显灵验。彼处人民,重建大殿,添设两廊,奏请赐额。妆塑神像三十六员于正殿,两廊仍塑七十二将,侍从人众。楚人行此诚心,远近祈祷,无有不应。护国保民,受万万年香火。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保安宁,士庶恭祈而赐福。至今古迹尚存。”[3]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终极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也同时蕴含强烈的反省批判精神。作者看似以此叙事来诠释宋江等人践行忠义伦理所获得的带有宗教性的理性合理性。这一方面迎合了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忠义伦理的形上建构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梁山好汉对“忠义传”及英雄入史情绪的热切期待。在历史上,岳飞之死(大鹏啄黑龙)、关羽之死(死后显灵成神)也同样被附会了一些封神、显圣的宗教解释。但是与《封神演义》等作品不同,这种宗教性叙事的出现是奠基于浓厚的苦恼感、悲怆感之上的,并以两者为主要情绪内核。因此,《水浒传》结尾的宗教感也始终洋溢着浓厚的悲剧意蕴。而这种意蕴的获得是对水浒英雄现世求索的纯粹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很明显是理念型的,而不是宗教型的。其实质是指明忠义伦理的行动者对忠义伦理的践行的彻底失败。其表象则是忠义伦理的行动者最终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成功,即封神、显圣。或者说,通过封神、显圣的叙事诠释的忠义伦理的形上合理性,恰恰是以宗教形式的理性(信仰)合理性取代其现实合理性。即,《水浒传》是以宋江等人封神、显圣的结局否定了忠义伦理的现实性。
五、结 论
梁山好汉们践行忠义伦理的行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仪式感,对忠义的执迷达到了信与爱的巅峰意境,特别是在全书的后半部更为明显。但其行动最终也构成了对封建忠义伦理以及“忠义传”虚伪性的全面否定和绝妙讽刺。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看,忠义伦理意识作为现实的、真实的、客观的精神已经动摇了其存有的根基,即精神的客观性的基础,并被提升至绝对精神即宗教精神的领域。在这个阶段,《水浒传》作为艺术作品所传达出的精神情感已然超越了对于苦恼感、悲怆感的描画和煽情的层次,而是“把现实的自我意识表述为神灵的命运”。这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原始的神灵作为普遍的环节,不是自我,也不是现实的。”其结果就是,“这也显示出直接个别性的目的的摆脱普遍秩序而获得的完全解放和直接的个别性对于普遍秩序的嘲笑”。与《水浒传》的精神意蕴互为注解,黑格尔的这个表述可以推出如下的解释:即以《水浒传》中的宗教性叙事收尾为主要标志,伦理意识超越了客观精神的问题域已然进入到绝对精神中的艺术精神领域,即“艺术的宗教属于伦理的精神”[4]254-255的艺术宗教的精神阶段。伦理意识在艺术宗教的精神阶段消解了其实体性和现实性。也就是说,艺术精神与伦理精神最终、也只能在这种带有宗教式的情感状态下达到同一。这是以一种艺术化、理想性的宗教(终极)情感取代伦理的现实性的叙事策略,就此实现了由伦理行动——伦理精神——艺术精神的情感提升。
言下之意,宋江封神、显圣的叙事只能在艺术精神的视界内取得宗教式的理性合理性,而其作为伦理行动者的现实合理性则被同时消解、否定。所以,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收尾是对《水浒传》忠义伦理现实合理性的最高级的否定形式。也无异于说,宋江等人之前践行忠义伦理的行动只不过是某种宗教狂热化的意识抽象物,把忠义伦理作为带有宗教意味的形上崇拜物,信仰对象,但在现实中并无实质意义和可操作性。梁山好汉的忠义实践事败身死,历经烦扰,得到的只是无尽的悲怆。最终却是以远离现实的宗教性、仪式性的神灵抚慰收场。从而彻底否定了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忠义伦理道德。同时,也批判了由正史“忠义传”所引发的带有宗教狂热化的英雄入史情绪。《水浒传》忠义伦理的悲剧精神在强烈的情感激荡中得以圆成。
]
[1] 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先秦时期[J].南京大学学报,1994(1).
[2]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施耐庵.水浒传[M].天都外臣序本.南京图书馆藏.
[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