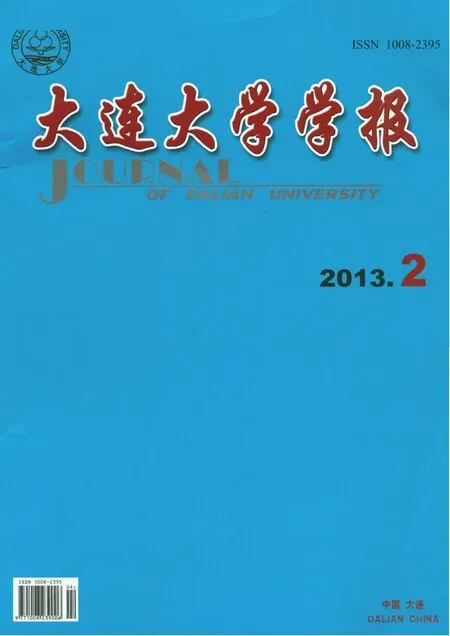山本常朝与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之生死观分析
——以《叶隐闻书》和《武士道》为中心
姜 明,张雪梅
(1.大连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2.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山本常朝与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之生死观分析
——以《叶隐闻书》和《武士道》为中心
姜 明1,张雪梅2
(1.大连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2.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武士道作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社会道德基石,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综合国内的武士道研究,大都集中在武士道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上,而关于武士道的对比研究则尚未充分。为此,试图从武士道的经典著作——《叶隐闻书》和《武士道》出发,从生死观的角度来探讨山本常朝和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思想的异同。希望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武士道的精神实质,同时对今后武士道的对比研究也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山本常朝;新渡户稻造;《叶隐闻书》;《武士道》;生死观
一、山本常朝
(一)山本常朝与《叶隐闻书》
山本常朝(1659—1719),江户时代的武士,万治二年生于佐贺。幼时,常受父亲的教诲“长成大刚者,才必有高用”、“无论如何都要成为刚者”,这些刚强的武士操守,对日后的常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岁时成为锅岛光茂(佐贺藩第二代藩主)的侍童,以后一直衷心侍奉藩主长达33年。在此期间,山本常朝师从湛然和尚和石田一鼎,分别向他们学习了佛道和儒学,《叶隐闻书》中强调的“忠于主君”、“慈悲之心”等,就源于这时期的修行。元禄十三年(1700),时年69岁的光茂逝世,常朝本想追腹自尽,以示忠诚。但因早年光茂出台追腹禁制令,命令禁止追腹,无奈之下常朝决定出家,并由此开始了隐居生活。一直都仰慕山本常朝的田代阵基在10年后(永宝七年,1710)见到了常朝,二人交谈甚深,田代将山本常朝就武士的心性修养和处世之道通过笔记集结成书,以“叶隐”为名,于享宝元年(1716)写成《叶隐闻书》,由于其体裁主要“采用语录体,成书过程和形式与儒门的《论语》相似,所以又称为《叶隐论语》或《叶隐论语摘抄》。”
全书共十一卷。卷一、卷二论武士心性;卷三至卷六言锅岛藩家族史及历史;卷七、卷八、卷九介绍锅岛藩武士的“忠勇奉公”言行;卷十涉猎他藩武士言行;卷十一补遗。
(二)山本常朝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贯穿《叶隐闻书》的一条主线,是山本常朝武士道思想的核心。山本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到“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1]
1.“死狂”——“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
“死狂”是《叶隐》武士道生死观的精髓,全文处处透露着一股山本对于死的狂气。他认为“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1]卷一,条2。武士道就是对死的狂热,即“死狂”本身。
山本常朝认为,死狂不问目的。“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的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1]卷一,条2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在此,山本常朝列举了两个例子:“长期喧哗事件①又称“深崛讨敌”、“深崛骚动”,元禄十三年(1700)春,锅岛茂久的家臣深崛右卫门和志波原武右卫门,在长崎与町年寄高木彦右卫门的同僚总内发生口角,总内被二人暴打。当夜,总内带着高木的家臣十人左右,来到深崛屋敷报仇,群殴深崛和志波二人,夺了他们的刀。闻此,深崛十六岁的儿子嘉右卫门和志波的下人立即从家乡跑到长崎,加入两人讨敌阵势,袭击高木屋敷,杀了以总内为首的多人,了其复仇的本愿。深崛和志波当场切腹,其他人撤回五岛町。事后江户幕府参与复仇的10人切腹,其他事后跑来的人流放远岛。这是一场为维护武士尊严的仇杀。”和“赤穗浪人事件②是指发生在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元禄年间赤穗藩家臣47人为主君复仇的事件。日本封建时代有一种仪式“敕使下向”,作为每年年初的惯例,先由将军派使臣上京,之后天皇派御使下京答谢。在天皇御使下京答谢之际,幕府会从大名中选派人员担任“御驰走役”(接待人员)接待御使。元禄14年3月14日,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在奉命接待朝廷御使一事上深觉受到负责仪式、典礼总指导的高家旗本吉良义央的刁难与侮辱,愤而在江户城大廊上拔刀杀伤吉良义央。此事件让将军德川纲吉在御使前蒙羞,将军怒不可遏,在尚未深究事件缘由的情况下,当即便命浅野长矩在田村右京大夫府邸即日切腹,而且断绝家名,没收领地。而另一方被浅野轻度砍伤的吉良义央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以首席家老大石内藏助为首的赤穗家臣们在无血开城后虽试图向幕府请愿,以图重振赤穗藩,但一年过后随着浅野长矩之弟浅野大学的处分裁决而确定复藩无望。于是大石内藏助于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深夜率领赤穗家臣共47人发动袭击,跃入吉良宅邸取其首级,祭奠于泉岳寺主君墓前,终为主君复仇雪耻。元禄十六年二月四日,幕府命令赤穗家臣46人切腹。”。
关于“长期喧哗事件”,山本常朝十分推崇长崎浪人的不假思索,立即报仇。山本常朝说:“武士道是行动,行动时还在用辨别力,就会落后于人[1]卷一,条10。”武士复仇,最重要的是行动,不要讲什么目标和大道理;复仇的终极意义也并不在于成败的结果,关键在是否立即做出了行动。对于赤穗武士通过长期准备的复仇,山本批评到:“浪士复仇,错在没有立断。”[1]15如果武士在准备复仇的期间,仇人突然死掉,那复仇不就不能实现了吗?“浅野殿夜讨,未于泉岳寺切腹,过分也。又,使其讨主,而讨敌之事拖延也。于内若吉良殿病死,那时将遗憾万千。”[2]山本常朝认为,真正的复仇是不需要任何准备的,即使对手上千,只要有见一个杀一个的决心,那复仇也是可以实现的。
2.“死的觉悟”——“以不断朝向死的姿态来寻找和完善生的意义”
山本常朝认为,对于武士来说,生与死是时刻相依并存的,其内涵和意义是同一的,“死之彻悟,就是每天都在死之中[1]卷一,条56。”“每朝每夕,一再思死念死决死,便常住死身,使武士道与我身为一体。”[1]卷一,条2每朝每夕,武士都需时刻思死念死,使得死身常住,才能摆脱心理上对死的恐惧,达到身体与心理自由自在的境界。山本常朝强调通过死来规划生,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生,武士在战场上,如果一味的想着要活下去,那么当他在面临死的时候会更加恐惧,然后就会害怕的胡乱挥舞刀枪,这样的话,死的几率反而会更高。因此,最后的赢家往往在战前就已经看到了死,看到了死才能活下来。“死”确实是一个令人恐惧且深刻的东西,武士在想到死的时候,无论自己曾经是多么的豪气,此刻间的分别全然消失。但是,“当你对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时,死反而会转化为生;当你想到死会常住人间时,死反而会离你而去,而你也就在那里再生了。”[1]18
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来解释,“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任何行止里面,都先天地有一个迷,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悟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也隐藏在晦暗中。”[3]每个人都存在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困境,武士所经历的濒临死亡的体验要比常人更多,因此,“死”对武士而言太过平常也极为普遍。武士只有真正领悟和把握“死”的存在,才能使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能以淡定和决然的心态自在地抉择生的道路。
3、“死的意义”——忠君奉公
山本常朝认为一切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武士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才是世间的真实。
《叶隐闻书》开篇提到四誓愿:
奉武士道者绝不迟疑;应为主君所用;孝亲;大慈大悲,方可为人。
山本认为,作为武士,首先要做到面对生死“绝不迟疑”,其次就是要效忠主君,“为主君所用”。“武士者,如不离生死,则无用。所谓万能一心,并非无心,是说离开生死,一心任事[1]卷十一,条26。”武士要效忠主君,就必须将主君的一切置于自身生命之上。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就以“死狂”的冲动来效忠主君,奉献自我,并且要感激主君给予这样的机会。山本常朝认为,能够为主君舍命就是值得信赖的家臣,“为主君舍命,当下即是,不要讲那么远的道理,最直接的道理便是舍命本身[1]卷一,条9。”
忠于主君,为主君而死,除了在战场上战死外,山本常朝还崇尚“殉死”,即在主公死后,忠义的武士会选择切腹自杀,给主公献上永远的忠诚,这种死的方式也叫做“追腹”。如果武士的忠诚和武勇不能在战场上显现出来,那么,“殉死”也可以作为向主君表达忠诚的另一种方式。山本常朝认为,“作为贴心家臣,无论主君在位还是退位,都要舍弃自身去追随。唯念主君,其他一概不问。”[1]5在锅岛藩藩主锅岛光茂去世时,山本常朝本决定为主君殉死,但由于当时幕府推行“追腹”禁制令,山本为表达对主君的忠诚,无奈剃发出家。“我想,主君虽逝,但荣誉永存,即使我独自一人,也要为增添主君的荣耀而舍命”。[1]7对主君衷心,为主君而死,既是武士的生死之道,也是武士人生意义的基础。
二、新渡户稻造
(一)新渡户稻造与《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1862—1933),生于日本岩手县盛冈市。国际政治家、农学家、教育家。父亲是南部藩士,他在幼年时曾受到过传统的武士道教育。13岁时进入东京英语学校学习,其后随后来出名的基督教大人物内村鉴三一起进入北海道农学校(即札幌农学校),之后成为了一名基督徒。1884年新渡户稻造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后又转赴德国学习。1891年回到日本,先后在札幌农学校、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任教,并出任东京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而且,他还是日本1894年至2004年间流通使用的5,000日元银行券的币面人物。《武士道》是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疗养的闲暇,直接用英文写成的。书中,作者将武士道与西方骑士道相比较,获得了西方读者的认同,被先后被翻译成德语、波兰语、俄语、挪威语等在世界各地发行,至今在世界各国的日本研究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二)新渡户稻造的“生死观”
1.坚忍——勇敢活,因为生比死更可怕
“对于真正的武士来说,急于赴死或以死求媚同样是卑怯的……蔑视死是勇敢的行为,然而在生比死更可怕的情况下,勇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4]27”。新渡户稻造认为,真正的武士应该以忍耐和正确的良心来抗御一切灾祸和困难,并且忍受它,“冲上战场被杀非常容易,最卑贱的农夫也做得到。但当活必活,当死必死,才是真正的勇。”[4]11
2.忠义——为主君去生去死
新渡户稻造认为,“忠”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德目,是武士道之魂,由“忠”的思想引发了武士对“死”的态度。作为武士,效忠主君才是武士存在的重要使命,“武士道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几位社会学家一样,认为由于国家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之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及其中的一份子而诞生出来的,因而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为它的合法的掌权者,去生去死。”[4]35因此武士“生死”的意义就在于忠君奉公、为君舍命。“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训练就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4]37
在此,新渡户稻造列举了日本历史上的最伟大人物之一菅原道真的故事。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中期的学者,因受人诬陷,被流放到偏远之地。菅原道真的敌人谋划着要把他的全家赶尽杀绝,查出他有一个未成年的幼子,被其旧臣源藏秘藏在一个寺院私塾中,于是下令让源藏限期交出幼年犯人的首级,源藏想到了用自己的孩子作为替身,来为主尽忠。我们会觉得这是个残酷的故事,父母竟然会从容并自愿地用自己无辜孩子的生命去救另外一个人的命,但是对于武士来说,“这是对义务召唤的服从”。“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5]为主君牺牲是武士绝对的“义务”,甚至在父子、夫妇亲情之上,因而在武士道中有“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的说法。
三、山本常朝和新渡户稻造生死观的异同
(一)相同点——死的美学
日本古语有“花中樱花,人中武士”。武士追求死亡的“瞬间美”,向往能够像樱花一样,在凋落的瞬间获得永恒的静谧,因此武士对于自己死的姿态以及死的是否壮美就十分关注。
1.山本常朝——带着美去死
山本常朝认为,既然武士抱有随时赴死的决心,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自己的外表便丝毫不能懈怠,武士的外在美也是武士的一种修养。
山本常朝说:“人很脆弱,随时都可能死……最好使生活趋美,带着美去死。”[1]20作为武士,死如落花一瞬,因此不能肮脏难看地去死,那么武士平素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容貌,“最好不断的照镜子”,“胭脂之粉,经常装入怀里”,倘若遭遇万一,脸色也不会一塌糊涂。“今日讨死也好,明日讨死也好,不管什么时候死,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决死心态。如果战死的时候邋遢难看,说明平素的觉悟程度就值得怀疑,也会被敌人轻视。”[1]卷一,条59“生活在五六十年代前的武士,他们每天早晨一起来就立即沐浴,然后剃净月代③江户时代,男子要剃掉从前额到头顶正中央部分的头发。来源于平安时代男子将于冠部分的头发剃光半月形。,梳理好发型,往头上喷香,修剪手足指甲,用浮石④火山石,很轻,表面粗糙不平,日本人洗澡时用来打磨污垢。打磨平滑,为了使它艳丽光鲜,再用“金色草”涂抹,在修整自己的装扮方面丝毫不敢怠惰。当然自己的武器则更是一点锈迹也没有,勤拂尘、勤打磨。对于装扮格外地用心,诚然是为了装饰外表,但这样做也体现了一种修养[1]卷一,条59。”
2.新渡户稻造——切腹
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将切腹描述成是一种具有严密规范和悠久渊源的、堪与“礼仪”相媲美的行为,认为这是武士的“完美品质”,是武士的美德之一,也可称为一种坚忍和艺术。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切腹所体现的自杀美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腹部寓意美。日本人有灵魂寓于腹部的信仰。“在我国国民的心中,这种死法会联想到最高尚的行为以及最动人的悲情的实例……美德、伟大、安详的转化力让人叹为观止,它使最丑恶的死亡形式带上崇高性,并使它带上新生命的象征……特意选择身体这个部位切开,乃是基于以这里为灵魂和爱情的归宿之处的古代解剖学的信念。”[4]45(2)宗教仪式美。首先,在切腹前,武士需要将头发梳理整齐并剃去胡须,沐浴后换上纯白色的和服(白色象征着光明和纯洁,具有道德圣洁之意)。其次,仪式一般选在装饰肃穆的寺庙中进行。新渡户稻造列举了米特福德《旧日本的故事》中的一段话,“正殿的屋顶很高,由黑色的木柱支撑着。从天棚上悬垂着金光灿灿的寺院所特有的巨大金色灯笼和其他装饰。在高高的佛坛前面地板上,安设了一个三四寸高的座席,铺着美丽的新榻榻米,摊放着红色的毛毯。”(3)视觉效果美。白色的和服、黑色的屋顶、金灿灿的灯笼、红色的毛毯,在切腹仪式中,这种颜色分明的强烈的视觉效果是武士对死亡“至美”的追求。武士将自己生命的陨落看成像樱花一样的凋零,因此,切腹的场面也应该像樱花的凋落一样绚烂美丽。
(二)不同点
1.“死狂”与勇敢活
山本常朝认为,武士最本质的生存之道就是不顾前后的、莽撞的“死狂”精神。武士在面对死亡时,其他什么都不要考虑,一心冲向死亡就可以了。新渡户稻造却认为面对生死要深思熟虑,仔细谋划,坚强忍耐,不能轻易放弃生命。“不分场合拔刀相向的人不是懦夫就是心虚之辈。”[4]55而且,新渡户强调死的目的性,即天下大义,就像我们所说的:死,有轻于鸿毛,有重如泰山;因此,死之轻重,是需要掂量的。他将儒教的伦理道德作为标准,去辨别武士的死是否有意义,并将其作为区别武士行为正邪善恶的价值标准。对此,山本常朝强调,武士在面临生死抉择时,重要的是毫不犹豫的选择死,至于是有价值的死还是无价值的死,是不需要去判断的。
2.复仇
山本常朝和新渡户稻造对死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了二者对复仇的态度。
山本常朝宣扬的是狂者的复仇,就算敌人非常强大,也要一根筋地奋勇搏杀,“武士道要求武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敢为天下先”[1]16。山本常朝非常赞赏“长崎喧哗事件”中那种当机立断的复仇精神,对其评价为“故为人褒赏为上手,不可若长崎喧哗样不假思索”[1]卷二,条51。山本常朝认为,某人被打了,却没有立即报仇,这是武士的耻辱。报仇很简单,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去杀了对方就可以雪耻了。如果想着万一复仇时不能战胜对手,就会以对手人多势众来为自己辩解,而徒然地拖延时间,最后,就只能和别人商量,甚至是不了了之。而真正的复仇,“即便对手上千,只要有见一个杀一个的决心,那报仇也是可以实现的。”[1]卷二,条51
新渡户稻造对赤穗浪人的复仇颇为赞同,武士们是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深思熟虑后才采取行动的,他们的复仇是“有道理的行动”、“有计划的行动”。新渡户强调计划和忍耐,力求最后实现复仇的目的。同时,新渡户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是“和平”,“真正的胜利在于不抵抗狂暴的敌人……不流血的胜利才是最好的胜利”。[4]56
总之,无论山本常朝还是新渡户稻造,都认为武士的生死对于武士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武士赢得功名与名誉的重要手段,是作为武士必备的修养。只是,《叶隐》的“死狂”,表现出山本常朝对死的无比迷恋,而新渡户稻造则更强调生的意义,认为生比死更可怕。这种“非理性的‘求死'和理性的‘求生'构成了武士道生死观的矛盾体。”[6]究其原因,新渡户的生死观主要来源于儒教思想,而《叶隐》则“代表了典型的日本土著思想”[7]300。
(三)《叶隐闻书》和《武士道》的影响
有什么样的生死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战争观。《叶隐闻书》和《武士道》中所强调的“无条件效忠主君及对封建领主忠贞不贰、视死如归的武士道思想,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支柱[8]”,他们将原有武士道对“主君的忠”转化为“对天皇的忠”,“以‘效忠天皇'和‘崇尚武勇'为核心,以战时‘义勇奉公'和‘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作为国民的神圣使命。”[9]“为了天皇,生命轻于鸿毛”[10]为天皇而死,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信仰。山本常朝不要理性的“死狂”精神,在二战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表现在行动上即:要么以军刀征服世界,要么以玉碎迎接死亡,并就此形成了日本侵华时期震惊世人的“南京大屠杀”与太平洋战争中青年人的“玉碎”和“自决”。日本士兵这种不珍惜自己生命,更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行为,为武士道打上了“穷兵黩武”、“野蛮血腥”的烙印。可以说,《叶隐》生死观“是日本军国主义视他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创造各种惨无人道的战术和暴行,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思想根源。”[11]
[1]山本常朝.叶隐闻书[M].李冬君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M].郭连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熊伟.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
[5]戴季陶.日本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6]国宇,张晓刚.浅谈日本武士道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M]/大连近代史研究:第9卷.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9).
[7]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张晓刚,国宇.从《叶隐》中的格言蠡测日本人的处世之道[J].文化学刊,2010(3).
[9]娄贵书.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辩护词——一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10]桥本实.武士道的精神[M].东京:明世堂,1943:370.
[11]王志.《叶隐》武士道思想简论[J].东亚历史文化,2012(7).
The Analysis of Yamamoto and Inazo Nitobe's Bushido from View of Life and Death—Based on“Hagakure”and“Bushido”
JIANG Ming1,ZHANG Xue-mei2
(1.College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2.College of Humanities,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Bushido,as the national spirit support and social moral cornerstone of Japan,has been always a hot topic both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At present,most of domestic studies on bushido are mainly concentrating in its formation,development and infuence,fewer on the comparison.This paper attempts to,based on some classic works about the bushido such as“Hagakure”and”Bushido”,discus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erences,from a perspective of life and death,between the bushido thoughts of Yamamoto and Inazo Nitobe,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bushido spirit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assistance for the fu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bushido.
Yamamoto;Inazo Nitobe;“Hagakure”;“Bushido”;View of life and death
K313
:A
:1008-2395(2013)02-0076-05
2013-02-09
姜明(1966-),男,大连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化研究;
张雪梅(1986-),女,大连大学人文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历史研究。
——读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