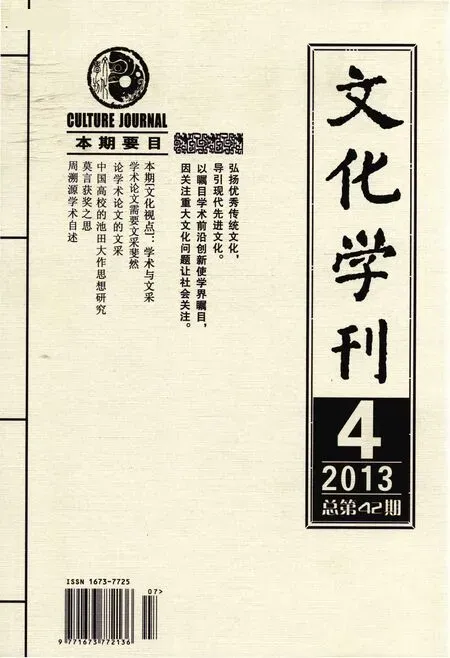民族文化谱系中的《东蒙古乐》——求索 《中国·建平 “十王会”》的前世今生
王斯语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1)
《中国·建平“十王会”》的成功发掘,并顺利登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不凡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时代价值。它,是中国北方区域文化历史考察的重大突破,是中国音乐文化形态研究的重大成果,是中华民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民族音乐存在方式的重大发现。尤为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民族文化学界、音乐史学界,长期以来翘首所望的一个重大的音乐历史形象,一个仿佛困厄于海上云雾间的重大民族音乐母题——东蒙古乐,竟由《中国·建平“十王会”》起锚,终于披波斩浪返航,并向世间披露出了久违了的那一枝桅杆,一叶风帆。
一
东蒙,此称谓始于蒙古各部实现统一后,按地理方位,分称西部蒙古、东部蒙古,简称“西蒙”、 “东蒙”。在历史学中,这个称谓前后变化较大。初时,基于地理方位,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蒙古各部的分分合合,东蒙的称谓,渐具历史意涵。
而“东蒙”的“东”,则远远始现于史前,及战国前后的北方部族的特定称谓中。最早,“东夷”的 “东”,后 “东胡”的“东”,均基于此意。
据考,“东夷”是以“鸟”—“燕”— “凤”为图腾的北方部族,约产生于夏代。其始祖可上溯至史前红山文化时期,其活动范围,由黄河东境上延至锡拉木伦河、老哈河,乃至额尔古纳河流域。中国东北的东部牛河梁史前红山文化遗址的出土,证实了中国文明的曙光,亦有北方之源。其“东夷”部族始祖的狩猎、游牧文化,在“牛河梁”的广大领域,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史前北方部族的新的经济形态。由此而衍生的精神文明,音乐文化则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东夷”及其始祖文化下延,则是与居于北境西部的“匈”族 (后被史家贬称为“匈奴”)相对的“胡”族,称为“东胡”。据考,早在商朝就有东胡的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东胡主要活动在当时的燕国(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锡拉木伦河流域。
考古学证实,东胡文化,基本上属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富河文化,而富河文化,则是哈克文化的传承,其上可溯至扎赉诺尔文化。考古表现为陶器形简单,纹饰为“之”形纹,箭镞类细石器较多。据此,可断定“东胡”应为扎赉诺尔人的后裔,而扎赉诺尔人则是世界80%蒙古人种的源头。“东胡”人的民族成份据此可以说包括现代的蒙古族。从整体上说,东胡是一个蒙古语族族群与通古斯语族族群联合的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古代民族部落国家的名称,其次才是民族的称谓。
东胡的考古遗址,在老哈河流域发现的比较集中,出土多为青铜器,其中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形制完全不同,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另外,在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人面形铜饰牌,赤峰宁城出土的青铜短剑,曲刃特点仍保存,但有刃部分已成直线型,说明东胡的早期文化逐渐受到了匈奴的影响。从出土的各国货币看,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日渐增多。从东胡墓葬看,死者头多向东,而向东崇拜实际是对太阳的崇拜。
东胡后被匈奴的冒顿单于率军攻败,一部退居乌桓山为乌桓族,一部退居鲜卑山的为鲜卑族。
乌桓、鲜卑先后占据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乌桓后被曹操大败于朝阳的柳城,喀左的白狼山。鲜卑的慕容氏则在龙山下建都龙城 (今朝阳),后世称为三燕鲜卑拓拔氏后建政于大同,又迁都洛阳,为北魏政权。据考,从鲜卑分离出去的,除慕容、拓拔,还有库莫奚、契丹、室韦等。《魏书·库莫奚传》:“其先,东胡鲜卑宇文之别种”,《北史·室韦传》: “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 (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称“蒙古室韦”。清末著名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说“蒙古语和鲜卑语相去无几”。据此,蒙古室韦亦为鲜卑后裔,后称“蒙古”一族。
通过简单的梳理,蒙古族的族源和历史脉络,就非常明晰了。由此,我们可以判明,“东蒙”的称谓,可上溯至“蒙古族”的始源期。也就是说,蒙古族被历史学确认时,后被划定的“东蒙”的地理方位,区域范围,就已经孕育出了东蒙称谓的雏形。这一判断很重要,因为从音乐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东蒙古乐”的史源理应从此时起。
“东蒙”的称谓,还有近现代的层面。清代,为统驭北境,清王朝加强了蒙古民族区域的防务,明确以驿路来划分军事、经济的区域,以张家口驿路为界,分西蒙、东蒙。由此,“东蒙”的称谓有了明确的政治意涵,且为官方所确认。后民国年间,这一称谓被沿袭下来,并在中国共产党于上世纪30年的文件中仍予以确认。抗日战争胜利后,蒙古族的上层人士,曾成立“东蒙自治政府”,首府设在兴安盟,后在承德会议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撤消该政府,成立“联合会”,由乌兰夫受命主持大政。解放初期,安波同志开辟新区的文化工作,于赤峰、建平、朝阳、阜新一线,组织收集蒙古族民歌,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东蒙民歌集》。可证,自“东部蒙古”的称谓形成起,历时数个世纪,由单纯的地理方位的称谓,渐次向具有政治意涵的方向发展,并被历史所确认。
由此来判断, “东蒙古乐”,亦不应是单纯的音乐文化的称谓,而应与东蒙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相交相契。其历史身份、社会位置、文化内涵,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
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被统称之为“礼乐文明”。礼,为政治体制及其典章,“乐”则为承载这一切的乐、舞、歌——与“礼”互为表里的文化形态。可见自远古文明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音乐文化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应该说“东蒙古乐”在“礼乐文明”中,贡献是突出的,身份是卓异的。但是,由于在中国的文化学史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唯“中国 (中原)”为“尊”,四夷皆为“蛮荒”的“误区”,把“礼乐文明”与“四夷”(包括“胡”文化)的关系视为主与仆、源与流的关系,而非共创同享的关系。这种历史的偏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建设,可以说是危害甚深。这种历史文化观,虽几经批驳,至今仍未能涤荡净尽。这在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不乏其例。例如,蒙古族的原创名曲《白翎雀》,其作曲者是硕德闾,这本是蒙古名字的汉字音译,有的“学者”却硬要“考证”为西域以外的音乐家,理由甚谬,偏见满纸。正是这样的原因,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中,“胡乐”的历史贡献和艺术光彩,不是被“边缘”化,就是被“屏弊”化。有些,至今亦未恢复其历史的“真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蒙古乐”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称道,仅在民间以“东蒙合奏”或“建平‘十王会’”流传,也就并不奇怪了。从理论层面讲, “东蒙古乐”,无论是作为历史的“存续”,还是作为蒙古族及北方其它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生态的“迁衍”,都应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存在”,其“生命”都自然具有着深遂的历史感和苍劲的现实感。《建平“十王会”》,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证。尽管《建平“十王会”》的音乐形态和存在形式,只是“东蒙古乐”的局部,但是,其乐器、曲谱、演奏方式,仍令今人看到了它的“母体”,“东蒙古乐”的妖娆多姿、美伦美涣的“音容”;亦令今人听到了它的“母体”所承续的“胡乐”——鲜卑乐、渤海乐 (包括引进的龟兹乐西凉乐)的繁音美律,余韵绕神州的“身影”。
马克思曾讲:“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已。”(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同其它的物质形式、感性形式一样,都是一种反映着对人类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认和对内在价值的追求,均是人类实践性精神的产物。就这个意义来讲,“东蒙古乐”仅仅被看作是地域音乐文化的存在,是不全面的。
“东蒙古乐”,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前奏——建政于“上都”为界,可分两个历史时期。前期,自史源至唐、宋,是“东蒙古乐”的前世——孕育期;自元建都“大都” (北京)以降,为“东蒙古乐”的今生——存续期。“东蒙古乐”的前世,陪伴东胡、鲜卑、乌桓、北魏等北方部族的诸政体,走过10余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并以“国乐”的身份,以不同名讳: “鲜卑乐”、 “渤海乐”等留光彩于史。
自“大元盛世”始,“东蒙古乐”方以区域音乐文化的身份,在不同朝代的“国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适逢元朝“开放”的历史机遇,“东蒙古乐”为主体的“国乐”,庙堂上, “宫廷”、 “雅乐”的庄重繁盛,“御苑”、“燕乐”的欢悦铺张;市井中,“勾栏”、“杂剧”的情染声腔,“瓦舍”、“玄索”的美饰妙音。这一切,都无不彰显着大元“音乐盛世”之态,凸现着大元“音乐辉煌”之貌。
明清以降,“东蒙古乐”承续、流转中,仍受到了统治者的“礼遇”,音乐界的“器重”。清王朝的“国乐”,其主体仍沿袭着“东蒙古乐”。
总之,“东蒙古乐”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中,有着不衰的生命和不凡的“谱系”。 《中国·建平“十王会”》,作为“东蒙古乐”的存续方式之一,尽管经过民间的“传承”,受过“功利”的选择,其乐器、乐曲、演奏形式表明,“东蒙古乐”的容颜未改,灵魂亦在。
二
东蒙文化,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延续久远,区域基本稳定的地域文化概念,主要原因在于其主体部位的稳固,核心区域的恒久。其中,“东蒙三河文明”占据着主导地位。所谓“东蒙三河文明”,是笔者在长期考察东蒙文化,特别是东蒙音乐文化中形成的一个概念。三河,即锡拉木伦河、老哈河、敖木伦河 (大凌河)。这三条河,流经的领域,从全国来看,范围不算广,山野田园不算阔,但是,在中国的音乐文化史中,却独放着异彩,独创着辉煌。可以说,三河穿峡过涧,一路洒下了数千年的优美音符和动人旋律,润泽着这一片天地人心,更润泽着神州的万里江山,亿兆族众。
东胡文明,据文献记载,其音乐文化首开中国吹管乐之先声。胡笳,以芦叶卷制的吹奏乐器,是先民从蒙味走向文明的道路上,从古之潢水田畔 (西拉木伦河)响起的吹奏第一声。可以说是胡笳引来东胡音乐的恢弘诗篇—— “胡笳十八拍”。而正是“胡笳十八拍”开启了“东蒙古乐”的源头。
“胡笳十八拍”据《梦辞集注·后语》,为蔡琰作。蔡琰,字文姬,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战乱中,为胡骑所获,为南匈奴左贤王妃,生二子。12年后为曹操赎回。她将这一段经历创作为音乐诗篇《胡笳十八拍》。胡笳,初为叶片卷成的吹管乐器,后衍化为三孔木管乐器,其音悲凉。“胡笳十八拍”先为“笳曲”,后与汉弦乐器——古琴和奏,衍化为 “琴曲”。“笳”与“琴”的乐曲的表达形式,在彼时是极不寻常的,为中华“管”“弦”合鸣的首创之举。据唐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说:“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衰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此诗最后一拍也说: “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此诗所记,为“胡笳十八拍”的另一版本,意是此曲为追怀蔡文姬所作,而非蔡文姬本人所作。不过从“胡笳十八拍”的原辞判断,无离伤之痛彻肺腑者,是万不能抒此呼天抢地之悲切,爱子恋夫之深情的。同时,不是汉族出身且文才斐然之音乐家蔡文姬,又怎能以一个非胡人的口吻状写胡人的生活和感受?诸如“夜闻陇水兮声呜咽”、 “草尽水竭兮举马皆徙”(第六拍),其胡人特有的生趣是“鼙鼓喧兮从夜达明”(第三拍)击鼓狂欢,又唱又跳,通霄达旦……。不过,刘商所说的此曲先为“笳曲”,后经“董生”之手翻成琴曲确有史笔。董生,即郭沫若先生笔下的董祀 (话剧《蔡文姬》)后由曹操作媒,蔡文姬再嫁的丈夫。
据考六朝时,已有《胡笳调》《胡笳曲》流传,唐、宋以来, 《胡笳十八拍》遂成流传湛甚广的“琴曲”,后成一部“大曲”。其“曲”,转引进宫廷“雅乐”,又被转引入“杂剧”曲牌。如此一来,这部“胡乐”,便成了诸乐的重要“母曲”。特别是,作为“东蒙古乐”的前世,在三河文明中,“胡笳十八拍”始终扮演了音乐文化“活水”之“源头”的角色。也正是在三河文明中,“胡笳十八拍”成了“东蒙古乐”的“母亲”,后来的流变,终未改变这一“母亲”的容颜,更未脱却这一血脉的基因。
这,在中华音乐文化的第一繁盛期—— “鲜卑乐”中得到“史”的回应。
鲜卑,源于“东胡”。先为“政体”,后为族属。史记,匈族强大之后,击败了“东胡”。“东胡”人,一部遁入鲜卑山,为鲜卑族,遁入乌桓山,为乌桓族。这两个部族所建的“政权”,均先后居于后世所称的“东蒙”地域。其鲜卑族,先建都龙城 (今朝阳),历经前燕,后燕,北燕 (还有南燕、西燕)王朝;后建都开平 (今大同)又迁都洛阳的北魏王朝,继又有威震西北的吐谷浑王朝。鲜卑族,继“东胡”人的祖阴,承中华各族之文脉,在广袤的北部版图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大戏。
鲜卑建政于龙城 (今朝阳)始,即着手建构“鲜卑乐”。 “鲜卑乐”是以“东胡乐”为基础,与中原王朝的音乐相揉和,改造提升为鲜卑的“宫廷音乐”。
对“鲜卑乐”的历史考察,是浩繁的工程。这里,只是撷取其几个亮点,以探“东蒙古乐”之源的基本形态及其内涵。
据考,前燕慕容平定冉闵,攻战邺城(邯郸附近),冉魏音乐为慕容所得,纳入前燕的宫廷音乐中。同时,前燕又将本民族的 (东胡乐)音乐与中原传统音乐相结合,即一方面使早期的慕容民族音乐上升为宫廷音乐,将早期的慕容民歌纳入到宫廷音乐“辇后鼓吹曲”中,另一方面,又接受承绪中原的宫廷音乐,并注入新鲜的慕容血液,形成了具有慕容民族特色的新型的宫廷音乐。
据《晋书》的《慕容盛载记》记载:慕容盛在位时,有一次“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 “‘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威天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勋道之茂,岂可与国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 (慕容)恪之功焉。”这一记载告诉后人三个问题,一是在后燕慕容宫廷中不仅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演奏传统的宫廷音乐,而且宫廷音乐中已经注入了“燕咏”这种新鲜的慕容音乐;二是这种“燕咏”不仅有如上所述吸收了原来的慕容民歌的鼓吹乐曲,而且还创作了歌颂慕容燕国帝王将相功业的宫廷雅乐——《燕颂》;三是这种《燕颂》可能已经不是单由鲜卑语创作的歌词,而是任用汉族官僚文士用汉文写成而演唱的。这一点,不仅有史实,而且北魏的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有此背景。
鲜卑“宫廷雅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鲜卑民族音乐,一是“阿干之歌”,一是“真人代歌”。 “阿干之歌”、“真人代歌”是由东胡乐中的民歌延伸为鲜卑族的民歌,其曲调已为历史尘埃所淹没,但其文献记载,却是脉络清晰。“阿干之歌”被慕容俊所建的前燕、慕容垂所建的后燕,改造成为“辇后大曲”;“真人代歌”则填新词以正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三十章,晨昏歌之。由此始有“北歌”。
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郡时,命掖廷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在“真人代歌”中,可解者六章,其中的《慕容可汗》歌和《吐谷浑》歌,即为慕容鲜卑音乐。可见,从北魏到唐代,其歌曲都源于东方的慕容鲜卑音乐。又据《乐府诗集》《横吹曲辞》序说:“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这里的“燕”指慕容燕国,“魏”指拓跋“魏国”。可知,北魏时期,鲜卑音乐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的拓跋氏、慕容氏等鲜卑各支族音乐在内的一种泛鲜卑音乐了。北朝隋唐时期所称鲜卑乐,一般就是这样泛鲜卑音乐。到了唐代,慕容音乐仍然是其宫廷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其中的“簸逻回歌”,成为唐代皇帝出行仪仗中演奏的鼓吹乐曲。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鲜卑乐——源东蒙于三河文明的音乐文化形式,对后世的“礼乐文明”,既提供了乐曲、舞曲、辞曲,又在历史的前行中凸显着音乐的魅力叠加和生命日强。同时,鲜卑音乐又以宽容的情态和旷达的心胸,令后世的各个王朝为之倾倒。在鲜卑乐的流转、发展中,不只有上文记载的“鲜卑乐”与“西凉乐”杂奏,还同舶来的“龟滋乐”结缡,呈鲜卑乐一世的新意与繁盛。
鲜卑乐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东蒙三河文明的主体是音乐文化,而音乐文化,又成为北方各族建政的“国家”象征和治国手段。因此,“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礼记·乐记》卷三十七)可见,音乐文化不只在民生的“俗”界为重,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为至尊。可以说,东胡一系的慕容鲜卑从西拉木伦河走出来,在东晋时建立的诸燕政权,不仅统治了辽西,还把政权延至河北诸地80多年。而居于东胡系的拓跋鲜卑,从兴安岭东侧走出来 (亦为东蒙地域),结束了十六国混战纷争的局面,统一北方,开创了南北朝局面,统治中国北主达两个世纪。其间,鲜卑乐作为“礼乐”,进入北方民族各王朝的“宫廷”,流布北方各族的“俗世”,可谓功绩卓异,一路辉煌。
三
如果说,以鲜卑乐为主体的北方音乐文化,是“东蒙古乐”的史源期,那大元盛世的建政,则理应为“东蒙古乐”的成熟期。
蒙古民族,是由东胡、鲜卑族系中的“蒙古室韦”而得其称谓。有史可考者,应始于《旧唐书》 《契丹国志》所记。“蒙古”意为“永恒之火”,别称“马背上的民族”。
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 (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从此,大漠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个部落而成的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
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人3次西征,先后建立横跨欧亚的四大汗国。同时,又挥师南下,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经70余年征战,击败了金、南宋,建立了元帝国。
据《元史·礼乐志》: “元之乐制,雅乐施于郊庙,宴乐,施于朝廷之燕享。雅乐之制有三:曰乐器,曰乐章,曰乐舞。宴乐之制有言二:曰乐器,曰乐仪”。又述: “隋氏以来,则以胡乐定雅乐,唐至元宗胡部……自唐历宋,大体皆然”。当然,元从立国到制乐,经历了文化的又一次大变革。
公元1252年,在金帐汗国的鼎力支持下,蒙哥在翰难河继大汗位,旋即派自已亲近的弟弟忽必烈出任漠南最高军政长官。离开漠北的忽必烈,带领人马来到漠南的金莲川草原。公元1256年,忽必烈决定在迷人的金莲川草原修建城池,命汉人刘秉忠选地造城。历3年始建成“开平府”。公元1263年,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公元1264年,升燕京为中都,后改为大都 (今北京)。这一征战、建城的过程,完成了从汉的儒文化到开放的多文化并举的“变革”,创建了世界为之瞩目的“大元盛世”。在经济上打破重农抑商的单一体制,在社会结构上走上了城乡并举,甚至推动城市经济繁荣的轨道,在文艺上打破“文以载道”的戒条,大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
所以元的“乐制”,以胡乐为基础,以承绪鲜卑乐血脉为主导,兼容“汉乐”与“西乐”,开创了音乐的一代辉煌,亦造就了以上都、大都为轴心,吸呐多元音乐文化精华的“东蒙古乐”的旷世繁荣。
这里仅读两点,以窥“全豹”。一是大曲《白翎雀》的创作。《白翎雀》,又称《白翎鹊》 《答刺》 《倒刺》,文献记载,白翎雀者,国朝教场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缓,终则急躁繁促,殊无有余不尽之音,窃尝病焉。后见陈云峤先生云,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世皇因命伶人硕德闾制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未有怨怒哀嫠之音乎。时谱已传矣,故至今卒莫能改。会稽张思廉宪作歌以咏之曰,“真人一统开正朔,马上鞮鞍手亲作,教坊国手硕德阅,传得开基太平乐……”。
白翎雀,为草原留鸟,只在燕山迤北的地区栖息,即“刺勒川”和“上都路”迤东的“辽阳路”(三河领域)等处。
以“白翎雀”的形象为题材而创作的大曲,苍凉而不乏热烈,雄放而略具哀怨的旋律,通过歌词,充分展示“马背上的民族”由游牧而农耕,仍眷恋故土,深念山河的奔放、深挚的情感。曲子开头,充分而娴熟地利用铮铮诉弦的表现手法,写得十分舒展柔和,一些段落还采用拟声手法,谱写白翎雀的雌雄和鸣,嘤嘤倾诉;曲终节奏急促,板式变化频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它的雄武、刚烈,为擒“敌”护草原而搏击长空,翻飞腾跃,鸟瞰大地,翱翔天宇的姿势的情态、忠贞的心地……。其中,尤为令人心动的是那“孤嫠怨悲之音”,凸显出了“白翎雀”深悟人生、情通人世的感怀。从而,此曲很快在东蒙广袤的草原、田野流传开来。元世祖忽必烈极为欣赏,定为国乐、大乐。于是“白翎雀”成了元“上都”的象征,当然也被视作孛尔只斤氏王朝经济文化繁荣的标志。元末以降,“白翎雀”曲每每引起人们对“胜国”的怀念。“白翎雀,乐极哀……八十一年生草莱鼎湖龙去何时回?”至明中叶,“白翎雀”仍是普遍喜爱的乐曲:“今年五月汉兵来,气吞瀚海声如雷。声如雷,敌可却,壮士齐唱白翎雀” (见唐之淳《愚士集》卷一《沙场曲》)。
至清,“白翎雀飞山雪寒,谱入琵琶马上弹。沙鸥鸂鶒春江上,芦草青青水满滩。”(王士祯《精华录》卷六) “一曲清高白翎雀,窗前蜡泪已成堆” (田雯《古欢堂集》《白翎雀歌辞》)。
总之,元代一曲《白翎雀》铸成后世诸华章。可以说, “白翎雀”曲、辞,是承绪“胡乐”的“母曲”而创作,又可以说,以“东蒙古乐”的“母曲”,开启了明、清的创新和演奏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