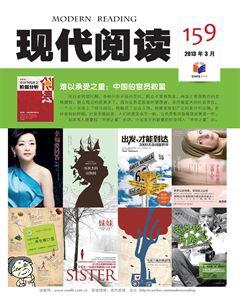逝去的辅仁大学
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按照苏联模式教育体系,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在这场“院系调整”中,由天主教人士创办的北京辅仁大学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名撤销。这一年与“辅仁”一同消失的“教会大学”,还有著名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10余所学校。
无解的问题
1948年秋,国共战事正酣,政治斗争的痕迹亦出现在辅仁大学的校园里。次年6月30日,罗马天主教廷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来到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拜访了其主要负责人周扬。此时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芮歌尼试图从周扬口中探听一下,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对于辅仁这所教会大学的态度。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处理是否已有新的法令?”周扬答:“一般地说,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学校,这件事实本身就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在这段具有“定调”色彩的答复中,周扬提出了一个所有教会学校都面临的敏感问题。
辅仁大学发端于1912年,当年9月,中国天主教两大领袖——马相伯、英敛之联袂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教廷派人来华,创办一所大学。1921年12月,教皇发出在华开办大学的谕令。依教廷的本意,他们自然希望这所学校能成为传播天主教的阵地。但事与愿违,“五四”之后,随着民族主义高涨,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都特别强调,教会学校须由中国人管理,并不得以宣传宗教为目的。
对于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抵触,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阶、习俗、仪式方面都更加严格的天主教会,此时却展现出了十分圆融的姿态。如创办初期,辅仁大学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宗教内容仅在哲学系课程中有所涉及。辅仁大学凭借着其“本土化”,与执政者保持了较为良好的互动。
不过,当新时代来临,过去的经验已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
芮歌尼对周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能否视为选修课程?”
周扬的答复是:“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
芮歌尼追问:“关于唯物史观一类的学说是否也当做选课?”
周扬说:“社会科学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应当列为大学必修课。”
政治的影子
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里,辅仁大学是以一副“闭门读书”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严进严出”是辅仁大学的一大特色。
根据辅仁大学教务处规定,一年有4次严格的考试,随堂小考更是不计其数。课堂风纪也抓得极严,没来听课的学生均被记录在案。
尽管教学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确可以提供真正的学问。辅大自建校以来,始终竭力设法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任教。沈兼士、刘半农、萨本铁、范文澜、启功等学者都曾在这所学校留下踪影。
在这种环境下走出的学生,日后大都成为了在社会各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当中包括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文物大师朱家溍等。
然而,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专门对“闭门读书”的教育予以批判:“决不能重蹈过去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覆辙,忽视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
为此,北平解放之后,学校已经开始对专业和课程设置进行局部调整。《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思想课首当其冲,成为各系必修课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课程,则被视为“培养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1950年春,学校又规定,当年的毕业生“凡未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者,或修而不及格者,均应根据实际情况补修补考。”
1949年秋季的“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入学试题”,还特别增加了“政治常识试题”部分。一共20道简答题,题目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什么阶级可以革命?哪个阶级领导革命?”等等。
接管辅仁
1950年7月,罗马天主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致信陈垣,提出来年教会拨给的经费将按月份付,一年14.4万美元,并且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一个新的董事会将要由教会选任;第二,教会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同时提出解聘5名教师的要求。这也意味着,教会与学校的矛盾,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
自1949年1月北平解放之后,教会越来越体会到众矢之的的滋味。解放军入城后不到一个月,由中共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教员会,便向校长陈垣和教会代表芮歌尼明确提出,“今后的教育宗旨及措施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精神”。
教会对此做出了让步,除了在人事上减少教士比例,还相继取消了《公教学》、《公教史》等几门课程。芮歌尼还曾专门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进行了沟通。
随着学校政治活动增多,教会显然已经失去了信心。导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5名教员的解聘问题,据芮歌尼方面的说法,这5个人都是从事“极端反教会”行为的人。
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的骤然紧张,也导致中国加快了清除英、美文化的步子。芮歌尼与校方的正面冲突,可谓撞到了枪口上。
收到来信后,陈垣和校务委员会直接请示教育部,随即对芮歌尼的要求予以驳回。
7月27日,芮歌尼又一次致信陈垣,表示可以放弃人事聘任否决权,但依旧坚持解聘5名教员,但再次遭到拒绝。芮歌尼遂正式通知校方:“自本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陈垣与教会在过去很长的岁月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33年,美、德两国的“圣言会”掌管了辅仁大学的事务。凭着德国人的出面,在抗战期间,未迁校的辅仁大学不但可以不悬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课本,还吸纳了不少无处可去的知名学者执教,声势大涨,这是陈垣与教会合作的一段黄金时期。
1950年10月10日,为彻底解决辅仁大学问题,教育部经政务院批准,宣布将辅仁大学收回自办,并任命陈垣为校长。以此为契机,我国接收外资津贴学校的序幕也就此拉开,到当年年底,全国接办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达20所。
辅仁的消逝
1952年,院系调整正式被提上日程。3月,北京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的计划,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5月,北京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院系调整小组正式建立。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二者集中力量,在师生中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显然,这两个运动,为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期间,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的自我检讨,他表示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这种全面的自我否定,被《人民日报》称赞为“诚恳老实,肯暴露自己的思想,检讨较深刻”。
《人民日报》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辅仁大学一些教职员工的“思想问题”,例如,“教育系主任欧阳湘,讲教师的修养以‘仪容、声音、情绪、品格、学识为5大标准。讲中学教育方针时,竟讲了美国的和蒋匪的而不讲人民政府的中学教育方针。”
对于在运动中表现不好的学生,学校惩罚严厉。1952年7月,校方专门开会讨论了贸易专修科的牛长民、佟辽两人的问题。牛长民“三反时有时不来,有时中途退席回家……污蔑马列主义,说‘马列主义是根据孔夫子来的”;佟辽“抗拒三反,时常不来,拒绝小组讨论”,“没交代问题,他说‘我没有问题”等等。经合议,校方决定对此二人予以开除。
经历了几次思想“洗澡”的师生,对于接下来进行的院系调整,即便是涉及人事变动这样的敏感问题,大都也能表示服从组织。
在教学调整中,最大的特点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各科按教研室构制、沿用苏联教学大纲。1948级教育系学生、辅仁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振稼回忆,当时“教育部有(苏联)顾问,学校有(苏联)顾问组,还有一个头儿,校长要听这个头儿的。”
一些专业也在这次调整中被腰斩。例如以英语为主的西语学系,高年级学生并入北京大学,留下来的低年级的学生全部改学俄文。
这样,到了1952年9月,除经济、哲学等系外,辅仁大学已全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曾经显赫一时的辅仁大学自此在大陆消失。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1960年,天主教廷在台湾实现辅仁大学复校,迄今已经半个世纪。
(摘自《中国周刊》 作者:周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