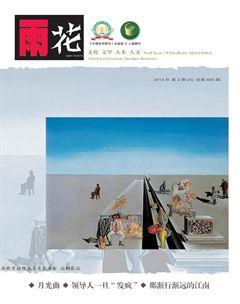苦苦的老家(外二篇)
罗箫
有天那个工作员来我家吃派饭,爹把高粱面窝头和高粱面稀饭端上桌,转身又端来半碟细盐。工作员哭笑不得,讪着脸要抄我爹碗里的凉拌猪毛菜。我爹紧忙把小黑盔子菜碗藏身后,说,你不让种菜,哪儿来的菜?这是给猪羊骡马牛驴吃的东西……
童年,每到开春,我就巴望着榆钱快些缀满枝杈,捋下来淘洗干净,加盐水拌些白面或玉米面,可以做出很好吃的蒸菜。榆叶煮出的饭发黏,如果淋几滴小磨香油,或撒些芝麻盐,简直是美味。我是说如果,那会儿没钱买香油,芝麻盐也是十年后在责任田里种几垄芝麻才能吃到。
牛马驴骡也爱吃榆钱,可它们吃不到嫩榆钱,人还争不停呢,哪有牲畜尝鲜的份儿?除非那些东西枯黄了,从树上自动落下来,有人归拢一下,筛筛,倒进石槽,加水拌拌,料棒梆梆敲几声,它们居然吃得津津有味。
记得有一年春三月,绿茸茸的柳豆冒出来时,姐姐带我和二弟去堤南坝头下捋青,那里有好大一片小柳树,是村里三年前响应植树造林号召栽的。我和弟弟负责用木钩把小柳树扒弯,姐姐哧哧哧哧两手交替着捋柳芽柳豆,她腰间系着一个粗布包单,边塞边摁,摁到实在盛不下了才回家。把柳芽柳豆煮熟,淘洗两遍捉净水,放醋,拌蒜汁,味道发苦,上顿吃了下顿还想吃。
进入四月,槐花坠弯树枝,招引无数蜜蜂从早到晚嘤嘤嗡嗡哼唱不止。地头、渠岸、堤坡与河套里好多灰叶菜马齿菜猪毛菜扫帚榆米谷菜等等正鲜嫩着,所有做工回来的人都会顺手薅一些。槐花嘟噜打蛋,一个枝杈就能捋下一竹篮,洗净用开水烫一下,加盐掺在面粉或玉米面里蒸两大笼菜团,够一家人吃几天了。
姐姐八岁就会揪野菜了,爹娘和爷爷为此乐呵呵的,他们仨人挣工分,年底算账只够换取人均一百多斤的口粮,有野菜源源不断进家,饭锅里就不那么清汤寡水了。即使在寒冬腊月,我家也有野菜吃,那些烫半熟然后晒干的野菜装满六个柳编大筐,足以支撑次年青黄不接的那段时间。
娘能把野菜做出几种花样:炒,烫熟凉拌,煮菜饭,蒸菜团,腌野菜梗,泡野菜叶。有回我家死了一只老母鸡,娘把爹剥好洗净的老母鸡剁成桃核似的碎块,连同盐和作料一起扔开水锅里炖。鸡块将炖熟时,扔进大半盆已经切好的苦苦菜,继续炖。真好吃,原本苦得烧嗓眼的苦苦菜也变香了。
有天傍黑娘指使我去常红村给姥姥家送干野菜,姥姥姥爷和舅舅妗子乐得眉眼儿里都是笑。姥姥家都是大人,没有闲人专门揪野菜,更稀罕干野菜。常红村和我们常西村和我们楼杨公社其他村一样,队里都没有菜园,那时上边不让种菜,说是要“以粮为纲”,种菜是变相搞资本主义,我们一队偷偷种了几畦子菜,被公社派来的包村工作员发现,勒令拔掉改种高粱,甚至有几块地里拃把高的玉米苗统统让拔掉,一律种高粱,说高粱耐旱、产量高。我爹脾气倔,有天那个工作员来我家吃派饭,爹把高粱面窝头和高粱面稀饭端上桌,转身又端来半碟细盐。工作员哭笑不得,讪着脸要抄我爹碗里的凉拌猪毛菜。我爹紧忙把小黑盔子菜碗藏身后,说,你不让种菜,哪儿来的菜?这是给猪羊骡马牛驴吃的东西……之后,那位工作员再也不来我家吃派饭了。
有一种野菜叫锯齿菜,很难吃。爷爷说,他当炊事班长时有年夏天住在深山里,老带领炊事班战士去山洼子揪锯齿菜,那里只有锯齿菜,找不到别的菜,不吃只有饿肚子。后来大家吃惯了,遇上炊事班抽不出人手,连长就派一个排的战士去揪锯齿菜。爷爷当过四年红军,什么苦都吃过。他说举凡野菜,都带有苦味,盐也有苦味,但吃不烦,甜东西却能吃烦。爷爷在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那年去世了,甜日子没过一天,留下的许多话,却像锯齿菜和其它野菜一样颇具回味。
三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目睹儿子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有时我难免旧事重提,儿子不耐烦地说,又是这,又是这,还有完没完了?大理论灌输不了,我使邪门旁招儿,譬如每逢假期或节日放假,我都带他回老家吃苦,就是吃野菜。回老家后,儿子只顾找儿时的伙伴玩耍了,我自个儿去地里揪野菜,不是用马齿菜蒸菜团,就是把猪毛菜煮熟剁碎加炒鸡蛋包水饺,未料儿子叫好不迭,强烈要求打包几样野菜带回城里继续享用。看来,吃苦能让人上瘾。
面糊涂
一九七一年秋,我和同村的吕大庆同在称勾国办中学上高一,学校离我们村八里路,两家均没有能力供我们住校,我俩只得跑堂上学,天不亮就起床,胡乱喂喂肚子,连跑带颠儿往学校赶,天大黑才进家。中午饭我俩都是吃自带的干粮。有些家庭经济情况好的同学扛粮食去粮站换粮条,再持粮条到学校后勤处找绰号“柳杆子”的刘会计买饭票菜票,饭票分粗、细两种,百分之二十细饭票,可以吃白馍、“面糊涂”,百分之八十粗饭票吃玉米面窝头,喝玉米面或小米稀粥。我和大庆从家挖不出粮食换粮条,也哼唧不来钱买菜票,只能就着白萝卜咸菜吃“金不换”红薯渣窝头。生红薯磨碎挤光粉芡,剩余的就是红薯渣,掺搅些高粱面或榆皮面或蒲草根面蒸出窝头来才能拿成个儿,否则一片散沙,搁学校食堂大笼里馏都没法馏,只好用手一撮一撮捏起来凉吃。
有天中午我和吕大庆几乎同时吃噎着了,跑学校食堂里去温缸舀水喝,温缸却干底净光。大庆迷糊了脸,边打嗝儿边对掌勺的炊事员说,司、司桐春,吃噎着了,给舀点、“面糊涂”、咯、中不?别怪大庆直呼其名,司桐春这人,一向不待见别人喊他司师傅,他可能听着前两个字都与“死”字同音,不吉利,又可能觉得司桐春三个字响亮好听吧,平日里无论校长副校长男女教师初高中大小学生,谁都那样称呼,司桐春乐呵呵答应着,黑红的脸膛流光溢彩。
绰号“柳杆子”的食堂管理员正就着案板吸溜“面糊涂”,见状逗趣道,小家伙,没细饭票是吧?好办,甭喊司桐春,改喊干爹,保管你天天中午有“面糊涂”喝!干、干……大庆仍在打嗝儿,“咯”的声音有些走样儿。司桐春大手一挥,别别别!咱可担当不起。说罢,麻利舀一马勺“面糊涂”,倒进了大庆的粗瓷碗,转头说,哎!“柳杆子”,二两细饭票的账,记咱名下!
“面糊涂”其实是区别于捞面条的另类面条,这是司桐春别出心裁的独家做法。一斤饭票里面只有二两细饭票,买一个馒头就用光了,吃捞面条只能盖住碗底,司桐春是大饭量,难免会替正长身体的大饭量学生娃着想,“好吃不贵,省钱耐饥”,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单说他如何制作“面糊涂”:食堂那口头号大铁锅能盛九桶水,待水烧开,撒半碗细盐,开始下面条。说下面条不准确,应该叫撒面条,因为他把擀好的面条全部切成了段,每段寸把长,撒进锅,第四节上课铃刚好响起,等锅再开,滚一会儿,扔进去一簸箕洗净剁碎的青菜叶。之后司桐春边时不时地往炉膛里添炭,拨火,边一管接一管抽旱烟,熬药一样熬个把课时,那些碎面条不糊涂成糨糊才怪,青菜叶也早滚烂了。听到下学铃响,司桐春把马勺伸进炉膛里熟油,油热到滚沸,把姜末葱花烀进去,将马勺连带里面的葱姜热油猛地哧锅里,“面糊涂”激动得直溅飞泡。学生们敲打着碗边盆底蜂拥而至,闻到的恰好是扑鼻的香味。二两细饭票换一马勺“面糊涂”,有大半海碗,比吃馍或吃捞面条挡饥不说,还灌缝,尤其那香味,弥久不散。
是个星期天,我在家吹嘘起了司桐春制作的“面糊涂”,娘比葫芦画瓢做了一顿,果然好吃。考虑到“好吃不贵,省钱耐饥”,爹有回赶称勾集,用卖箩头钱籴了二十斤白面,扛到学校找“柳杆子”换了二十斤细饭票。
之后,大庆和我一样,每天中午买“面糊涂”喝,我问他细饭票哪儿来的?大庆抿嘴不出声,只是神秘兮兮地笑。你该不会从饭票匣子里抓了一把吧?我疑惑不解地问。上周四中午开饭时,高二五排有个男生被“柳杆子”捉住了手腕。大庆急了,我啥时候手指头长过?原来,司桐春每月都给大庆几斤细饭票,他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块,因为没老婆,光棍一条,施舍得起。我问大庆,司桐春他、该不会真想收你做干儿子吧?不像!大庆挠挠脖颈说,有回我喊了声干爹,把他喊恼了,黑镇着老包脸说,胡闹!再乱喊不管你了!我问,那他图啥呢?大庆说,司桐春说、说他觉得我可怜。
白驹过隙,一晃四十年过去。有天下午我接到时任某建筑公司经理的吕大庆的女秘书一个电话,说吕头儿要为老爹祝寿,邀请我后天中午务必赶到市里“金马酒家”捧个人场。大庆爹十年前就去世了,这打哪儿又冒出个老爹?大庆曾说过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话,莫非他真去漳河南司家庄找到司桐春了?掐指算算,司桐春应该是位年近八旬的老翁了。
白地不白
春天来了,气候变暖,万物复苏。我面对着家属院内那块白地发呆。
三个月前内退后,我屡屡跑劳务市场,屡屡无果而返,原因不外乎无技术特长。我辗转反侧,一夜接着一夜失眠。儿子上学要花钱,老爹几番住院必须花钱,已经借别人好几千了。单位对内退人员只发百分之八十基本工资不说,还扣三金,我属于企业人员,工资原本就低,连扣带除,每月到手不足五百块,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有朋友好心劝我,别介这山望着那山高,好赖先找个事干着,多少有点收入,就不会失眠了。我依言而行,去火车站当起了装卸工。
这和在机关坐办公室的感觉简直有天壤之别。过去,像一滴油凫在水面,现在,像一滴水砸在土里;过去像在做客,现在像有鞭子抽着;过去是铁饭碗,现在则无所适从。最具实质的区别是,吃着碗里,必须想着锅里。换个说法就是,吃着这顿,必须想着下顿的饭钱找谁去要。当然,需要付出心血和汗水。这是个等价交换的时代,谁也得服从。
一开始当装卸工时,组长看我年过半百,有心照顾我,让我干下垛的活,抬包帮人上肩。三天后组长说你也扛包吧。我想肯定有人攀比,领一样的钱,就得干一样的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背上驮着包,一步三摇往踏板上走。一位瘦猴工友沿另一块踏板下来,下到半道停住,伸手扶了我一把说,大哥稳住了,越晃越危险,掉下去可不好玩。我大汗淋漓,汗水把眼睛都模糊了,往车厢撂包时撂得不是地方,瘦猴跟上来帮我挪好,又说,手眼并用,就撂对地方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呼喘着说,谢谢、谢谢老弟,我就不明白了,看你精瘦精瘦的,咋扛包沿踏板一步一板,脚下有根儿似的?瘦猴说,我扛包二十多年,筋骨和眼色都练硬了。一般年轻人,扛包十几二十来天,就能顺过劲儿来。我问,我呢?他说,想听实话吗?你压根儿就不是干这活儿的料!
还真让瘦猴说准了,下午我就不干了。为什么?腰岔气了。歇几天腰顺过气来我也不再去扛包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得琢磨一下自己到底是哪块料。
沉入水底的不止是石子,也有浮尘。
再看家属院内那块白地,已经不是白地了,不知何时,有许多嫩黄的草芽尖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