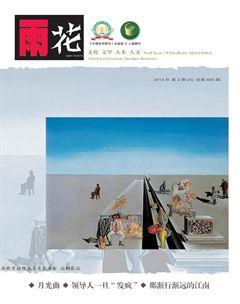月光曲
程相崧
1
月光洒下来,像无数条白色的刀子在空气里飞,刮到人的脸上,刺骨的疼。地上的雪还没有融化,银粉样的寒气散在空气里,钻进人的鼻孔,呛得人直想打喷嚏。世界是白茫茫一片,只有车轮轧过的地方显出黑色,有些肮脏。路上的行人渐渐少了,街边的店铺也多已打烊,耳边静下来了,只有几间网吧里的灯火亮着,从里面传出虚拟世界的各种声响。网吧前台阶上的雪已经被清理干净,水泥台阶在月光下显出石青色,透出坚硬的质地。一个黑色的人影正在那几个台阶上蹦上来又蹦下去,一边蹦一边冲着这边喊:
“哎,你过来啊,这样就会变得暖和。”
杜梅朝丈夫刘岩望了一眼,笑了起来。丈夫嘴巴说话的时候吐出来的热气粗大得像一个白色的手绢,说完之后,手绢便长了翅膀,呼一下飞走了,再没有影子。她的脚其实也跟丈夫的一样,冷得很。虽然穿了最大号的鞋子,里面塞了厚厚的棉花,但整个人从腰往下,都跟冰坨子一样,几乎都要没有了知觉,更不用提脚了。每天只有回到家睡觉之前,用热水泡着的时候,它们才会苏醒过来,才会感到像猫咬一样疼,继而奇痒。在这天寒地冻的晚上,像丈夫一样活动活动,腿脚或许会好受些。但相比之下,她还是愿意守着她的小车寸步不离。她怕客人以为这儿没人,耽误了生意。车上有一个燃气灶,上面有一个铁锅,刚才她还焐在上面暖手来着,但因为这么大会儿都没有客人,锅凉了,冷得像冰。在灶的旁边有一个小橱窗,里面放着鸡蛋、火腿肠、材料碗等物,旁边玻璃上写着两个红字:夹饼。
“别在那里蹦了,小心里面的人嫌你闹腾,出来赶你。”她望了丈夫一眼说。
“没事儿,”刘岩往网吧里指了指说,“里面闹得很。”
“闹吗?”女人说,“我怎么没有听到呢?”
“那你听到了什么?”他还是一边蹦一边说。
“琴声。”杜梅说。
杜梅这么一说,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耳边只有风呼呼地刮着,似乎比刚才更猛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不错,真的听到了琴声,夹在刀子一样的风里,有些缥缈,有些不真切。
“听到没?”她问丈夫。
丈夫点了点头,又呼出一团白气。
一听到这琴声,杜梅的心里便温暖了。她仿佛看到了女儿的小脸儿,仿佛看到了女儿正在明亮的灯下,专注地按动着那洁白的琴键,小手指头跳动着,像下雨时屋檐落下的水花。是的,离这儿不远,拐过一个胡同,便是一家钢琴学校,他们的女儿小红便在那里学琴。
“天太冷了,关着窗子,不然会听得更加清楚。”丈夫说,“这回听到了,是《月光曲》,贝多芬的世界名曲。”
“得了吧,你还能听出来这个?”杜梅嘲笑他。
“别小看了我,”刘岩不服气了,“女儿有这个才能,其实全是遗传了我呢。”
不错,刘岩也曾表现出过一些音乐细胞。在少年时代,他曾经喜欢上了拉手风琴,还在学校里的演出队拉过一阵子。后来县一中一个教音乐的老师听他拉了之后,便要收他为弟子。可当他欢天喜地地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爹的时候,爹却说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就不该喜欢上这个。那时候他不明白,后来才知道爹已经去百货市场悄悄问了价,一台手风琴要几十块钱哩。他是个听话的孩子,爹说不让学,他便放弃了。这些年过来,虽然并不埋怨爹,可一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感到稍稍的遗憾。学艺术花销大,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所以他们两口子自从有了这个女儿,就没打算让她学音乐,或学美术。不是不想开发培养孩子这方面的才能,是怕。
杜梅从前在酒厂上班,厂子一连几年不死不活。后来终于宣布倒闭,她便正式下岗了。那些年,家里老人有病,孩子又小,全靠丈夫在化肥厂挣的微薄工资。可老人去世之后,丈夫的化肥厂也倒闭了。从此一家三口,便挤在一套不足六十平方的小房子里,靠两个人打点儿零工过活。但是他们两口子都没料想到的是,女儿在学校音乐课上学会了弹钢琴,参加了钢琴比赛,不但获得了全校第一名,还代表学校到市里参加比赛拿了好名次。回来之后,学校里的音乐老师特意把他们两口子请到了学校,说这孩子有些天分,如果不及时开发、培养,错过时机,可就太可惜了。
两口子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狠狠心给女儿报名参加了校外的钢琴班。
钢琴学校在一栋写字楼的二楼,一楼几间门面开了一家琴行,叫爱乐琴行。每次送学生,都要穿过琴行,再上楼梯。去了几回之后,人家钢琴老师便建议他们给孩子买一台钢琴。刘岩当时牵着孩子的手,含糊其辞地应付着,最后慌不择路地逃了。
第二天送孩子去学琴,是杜梅送的。人家老师很热情,早早地就在一楼大厅迎候着了。看见杜梅和孩子来了,特意领着他们在琴行的钢琴区转了一圈儿。边转还边耐心地介绍,并不停地问孩子看中了哪一款。最后小红临上楼的时候,指着角落标价最便宜的一款,说她喜欢这个。
杜梅看了看标价,2899元,她心里不免暗叫了一声,但脸上没有显露出来。
老师笑了笑,又领着他们到了附近一台标价9000多元的琴前,说还是昨天人家张老师的儿子有眼光,上来就挑了这一台最贵的。这台虽然比其他都贵几千块钱,可音质好,孩子刚开始练,只要家庭条件允许,还是应该买一台好的。
那天晚上,两口子都没有睡着。家庭条件——他们琢磨着这个词儿,哪个家长不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家庭条件呢?他们又提到了一个陈旧的话题——如何挣钱。从外出打工到赁门面开店,最后就说到了卖夹饼。他们听人家说过,这个本钱小,还能挣钱,且不需要什么手艺,只要舍得下脸皮就行。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论证,干这个是否行得通。说实在的,这个问题两个人从前不是没有想到过,但每回都是碍于脸面,心想如果让从前的同事朋友看见了,那多丢人啊。最后每次都是打了退堂鼓。但这回不一样了,什么都是逼出来的,两人没再说什么,同时咬了咬牙,说干。
2
对于这个行当,从前他们就考察过,一般都是上午买料,下午和晚上出摊。如果一天能卖一百个夹饼,除去本钱,能挣二百来块钱。杜梅还偷偷去邻县跟人家干这个的学过技术,不但学过技术,甚至从前有一次两个人连出摊的工具都准备好了。
这回是下定了决心,说干就干。于是两天后,把女儿送去上学回来,他们便干开了。虽然看人家干得轻松,可是第一次出摊的时候,两个人真是感觉浑身难受得要命。看见亲戚朋友老远不敢抬头,见了邻居熟人也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更不用说大声吆喝,招徕顾客了。
第一次出摊回来,一天只卖出了二十个夹饼。两口子把剩下的面饼、火腿肠和碎肉收拾进冰箱,都有些受打击。刘岩躺在床上,先就又打了退堂鼓。他对杜梅说:“算了算了,这个不赚钱。”
“那啥赚钱呢?”
“赚不赚钱都不能干,丢不起这个人呢。”
杜梅就火了:“这个有啥丢人?你是偷了还是抢了?”
两口子颠来倒去说了大半个晚上,最后决定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这样一直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两个人心理上才渐渐地好起来了。不但能正视熟人,有时候还能招呼人家捎个夹饼给孩子吃了。
一开始他们把摊位摆在了一中门口,后来,晚上送孩子学琴的时候他们发现,女儿钢琴学校附近有一个网吧。每天晚上到了十一点十二点,那里还有人出来买吃的。于是,下午他们在学校门口卖一阵之后,晚上便转移到网吧门口。送女儿去了钢琴学校之后,他们便回来照看他们的生意。
除了要去菜市买东西备料,他们上午不出去摆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城管。按照大家的经验,一般上午的时候城管管得比较严。当然,就算下午和晚上,他们也是经常要跟城管打游击,几乎哪天都会被城管撵得气喘吁吁。一开始他们有些不能适应,有时候正招呼着生意,看到其他摊位的摊主拉着车子往小区里跑,往胡同里跑,他们便也一起慌不迭地抱头鼠窜。回头想想,真狼狈啊。想想那个狼狈样儿,有时候真不想干了。可看看其他摊主,好多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是那样跑。人家岁数大的都行,自己至少比他们年轻,有什么不行呢?至少比他们跑得快啊。
晚上在网吧的门口摆摊,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女儿近,接送孩子方便,而且有时候还能听到女儿的琴声。但两口子也有放心不下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不小心碰上女儿的老师。
有一次,刘岩送女儿去钢琴学校回来后不大会儿,一辆车便在摊位旁边停了下来。丈夫正要上前招呼车里钻出来的人,便被杜梅一下子按在了凳子上。刘岩不知所以,还没来得及抬起头,就看见妻子低着头,猫着腰,推着车子要走。一边推着,嘴里还一边说着:“唉,真不巧,刚卖完。”
“哪儿卖完了?”刘岩抬起头来,“还剩这么多呢。”
“你没看见?”妻子示意他小声点,“那是小红的老师。”
丈夫也吓得出了一头的冷汗,赶紧坐在那里,把头埋在了怀里。过了一会儿,车开走了,他们才又重新回到原地。
“她看见咱们没有?”女人问。
“没有,”刘岩说,“我敢打包票。”
“亏得是我,”女人说,“不然如果老师知道了咱干这个,那对咱孩子……”
两口子小声说着话,弓着腰,高兴得似乎遇到了什么好事儿。
“可惜没有记住她的车牌号码。”女人说。
“咋会没记住?”男人说着,背出了车牌号。
女人朝着男人肩膀轻轻擂了一拳,接着两个人都又笑了起来。
3
每次接送孩子的时候,刘岩和杜梅走进一楼的琴行,都会朝女儿当初看中的那台钢琴望上一眼。那台琴并不算精致,尤其在众多钢琴中间,甚至显得有些粗糙。但这么便宜的一台琴,似乎就是为他们这个家量身定做的,就是为了小红量身定做的。每次从楼上把孩子接下来,他们总是牵着孩子的手逃一样穿过一楼的展区。他们不敢看那些琴,更不敢望女儿的眼光。
干卖夹饼这个营生已经几个月了,每天晚上收摊回来,两口子都会盘算着这段时间攒下来的钱。仔细算算,扣除成本和下一步继续经营的费用,眼看着就够给女儿买一台琴的了。
“紧一紧,凑够了钱就把那台琴买下来。”杜梅说。
“那就在孩子生日的时候买吧,好让她高兴高兴。”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杜梅去接孩子的时候,一进一楼的乐行,就看见小红正倚着大厅中间的柱子,委屈得像是要哭。而几个服务员正围着她,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着。
杜梅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孩子在学完琴等着大人来接的时候,看大厅里没人,便悄悄地凑近那台钢琴,而且轻轻翻开琴盖,弄响了琴键。
“几千块钱一台,弄坏了怎么办啊。”一个服务员说。
“就算弄不坏,弄脏了还有谁买呢?”另一个服务员说。
杜梅来了之后,小红看见妈妈,心里更加委屈。知道自己惹了祸,低着头抽泣,一句话也不说。
杜梅没有理那些服务员,她蹲下身子,轻轻地摸着女儿的脸蛋,把孩子脸上的泪擦了擦说:
“不要紧孩子,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就给你买。”
杜梅说完抬起头,紧紧牵着孩子的手,一步步往外走。走的时候,胸脯似乎极力地往上挺着……
小红一边擦泪一边扯着杜梅的手说:“妈妈,我不要,我就是看一看,看一看……”
杜梅带着孩子回到摊位上,男人正在一个人忙着。这会儿正是网吧里上网的孩子出来买宵夜的时候,吃了夜宵才能玩一个通宵,不然到了下半夜肚子就会咕咕叫了。他们的摊和邻近老刘的摊都忙得不亦乐乎。小红看父母忙活着,便也帮着收钱,递东西,刚才的不快很快烟消云散了。忙了一阵之后,网吧门口安静了下来,再没有人出来买东西,时间也不早了,该收摊了。
“孩子,饿了吗?你吃一个吧。”杜梅问小红。
“妈,我不饿。”
但杜梅这次还是坚持为小红做了一个夹饼,才把火儿熄了。
邻摊的老刘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问他们:
“明天上午出不出摊?”
“城管查得严呢!”刘岩说,“上午你也敢出摊?被逮着没收了东西,可就不划算了。”
“没听说吗?明天城管里面有人结婚,他们都要去喝喜酒,所以,明天上午反而可能没人管。要出摊的话一块儿出来,到农贸市场那边,保证好卖。”
望望老刘,刘岩还有些犹豫。
“有人结婚?真的?”杜梅扯扯丈夫的衣襟,接过来说,“如果那样,谁不出摊呢!”
其实若是在从前,杜梅也不会沾这点儿小便宜。一来他们不想冒这样的风险,二来有了下午晚上的忙活,两个人也累了,第二天早上送孩子上学走了之后,都还可以囫囵一觉,补补精神。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杜梅心里却急切地想挣钱,似乎疯了一样地想挣钱。
第二天他们七点半出的摊,把孩子送到学校便推着车赶来了。他们跟老刘一起,地点是农贸市场。这天的确非常平静,没有看到一辆城管巡逻的车辆,生意也好。农贸市场到城里送菜的农人多,大多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赶上这个机会,不到两个小时,刘岩他们已经挣了两百块钱。
“老刘啊,”刘岩一边忙活一边说,“你的信息还真灵。”
“那还用说?以后跟着我,一定有油水捞!”
几个人都笑了。
“差不多了,”杜梅看看太阳,“他们去吃完了酒该回来了。”
“没事儿,他们喝了酒,还不得睡一会儿?”刘岩说,“把这些面饼卖完了再说。”
又过了一个小时,眼看着上午带出来的面饼就该卖完了。刘岩和杜梅两口子正在忙活着,这时候就听见老刘忽然喊了一声:
“跑!”
老刘别看上了岁数,可行动快。两个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老刘已经拉着车子叮叮当当地蹿出好远,钻进了一个胡同。刘岩和杜梅相互看看,他们并没有看到城管,但还是手忙脚乱地收拾起东西,跟着老刘跑了起来。等两个人一个拉着一个推着,气喘吁吁地钻进胡同,才听到城管的执法车在后面喊了起来。
“别跑了,赶紧停下,别跑了……”
刘岩心里一急,头上涔出了汗珠。他顾不得这些,拉着车子,在有些颠簸的路上拼命地朝前跑。执法车的声音更加响亮了,正在步步紧逼。过去虽然也跑过,但是城管却从来没像这次穷追不舍。朝前望望,老刘拐了几个弯儿,已经没影儿了,刘岩拉着车子,听到执法车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下一刻将发生什么,刘岩不知道。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不能让他们逮住,一定要逃脱。如果让他们逮住,一车的东西,做夹饼的材料、工具,一定都完了。刘岩这一刻真后悔刚才没有听杜梅的,及时收摊。同时又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关键时刻腿脚竟然这么慢,竟然跑不过老刘。
执法车已经超了过去,他跑不动了。
车子里下来两个穿制服的青年,脸红扑扑的,看样子是喝了酒,上来就揪住了刘岩的头发。刘岩被抓得一个趔趄,两腿一软,便跪下了。
“你跑什么,你他妈的跑什么?”
其中一个一脚踹在刘岩的胸口上,让他险些摔倒。
另一个说:“刚才那个老头是谁?是你爹吗?跑得跟兔子似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跑了就算到你的头上。”
“我不认识,那老头我不认识啊!”
“还不老实,”其中一个说,“车子扣留,下午来交罚款领车。”
“求求你们大哥,我们是小本买卖,以后再也不出来了。”刘岩说着,一下下把头磕在地上。
“少说废话,再闹你也上车。”其中一个上来揪住刘岩的衣襟,就要往车上拖。
杜梅跑了过来,用身子护住了丈夫。她嘴里喊着:“你们怎么打人?你们怎么能打人?”
“哪有人打人?”一个城管指着杜梅道,“看来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也一样跟着上车。走!不关你们个十天半月,不知道什么叫王法!”
刘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车子坚决不能让他们扣下。如果扣下,不找人疏通关系,不花上个三千两千的,不会领回来。另外,自己可以跟着他们去,但杜梅一定要留下。不然孩子没人照看不说,她小小年纪,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又不知会耽误多少功课呢。
“别拉扯她,我跟你们走。”刘岩说,“我跟你们去。”
杜梅一看也到了放学的时间了,就先去把女儿接回了家。刚才她憋了一肚子的气,一看见女儿,便渐渐消了。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小红问爸爸呢?杜梅说今天爸爸有事儿,不回来了。两个人吃了饭,送走了女儿,回到家,丈夫还是没有回来。杜梅这时候心里开始有些慌。想着那一车的东西,不知道下午和晚上还能不能正常出摊。如果不出摊,又要白白损失几百块,虽然上午卖了一些,还是不划算呢。
如坐针毡地等了两个小时,也没等来丈夫,却等来了公安局的人。杜梅说你们来干什么?来人说你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就怎么说,也不用紧张。杜梅想,去就去。上了车之后,她又感到有些想不明白,这么点事儿还惊动了公安局?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到了派出所之后,杜梅便被领到了一个小屋里。那里的人也只是了解了当时的前后情况,然后详细地做了记录,让杜梅签字画押之后,便让她回来了。回来的路上,她看到许多邻人看她的眼光都有些怪怪的,才知道这事儿已经传开了。但也没有办法,这时候还怕丢人吗?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遇到了老刘,老刘问:
“刘岩兄弟咋样?”
“估计下午就能出来。”
“弟媳妇,你还不知道,坏了,出大事儿了。我听说刘岩兄弟被逮到城管队之后,不知怎的就把两个城管给捅了。两个都送了医院,听说其中一个已经不行了。”
杜梅一听这话,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刚才派出所的人到家里来的时候,她就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没想到原来是这样。她赶紧回到派出所,证实了老刘说的话不假。人家还说你丈夫现在已经送进了拘留所,也已经跟你了解了情况,有需要你来的时候,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杜梅扶着桌面,腿抖得已经站不起来,喊着我要见刘岩,你们让我见见他!……
“不是不让你见他,现在跟犯罪嫌疑人见面,要履行法律程序。如果想跟他见面,就要请律师,让律师去跟嫌疑人见面。”
杜梅晕晕乎乎地回了家,心里拿定了主意,这事儿不能让小红知道。另外,她要请律师,要把这事儿说清楚。
杜梅接孩子吃了晚饭,晚上还是跟从前一样继续送孩子学钢琴。送走了小红之后,杜梅一个人呆在家里,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歹等到孩子放学的时候,接了孩子回来。晚上收拾好了,让孩子睡觉的时候,孩子突然问她:
“爸爸呢?怎么还没回来?”
“你爸爸有事儿要到外地去几天,很快就回来了。”
孩子将信将疑地睡着了。
第二天,杜梅便请了律师。律师进了拘留所的大门,她忐忑不安地在外面等着。一个小时之后,律师出来了。两人面对面坐下来之后,杜梅说:“见了吗?怎么说的?”
“据你丈夫说,当时他下车之后,在车库里,两个城管又开始打他。最后打得急了,他便掏出了兜里的刀子,捅了过去。”
“兜里怎么会有刀子?”
“据你丈夫交代,是城管来之前,慌乱收拾的时候塞到兜里的。但是对方坚持认为他是上车前准备好了的。”
“律师,花多少钱都行,只要能把他救出来!”杜梅跪在地上了。
“你丈夫情绪很不稳定,他只让我给你捎回来几句话:不要请律师,不要上诉,好好照顾女儿。……”
一连几天,小红都没有看到爸爸,似乎感到了一些异常。每次杜梅都不敢看女儿的眼睛,撒谎说爸爸出去给你挣钱去了。不久就要回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杜梅上了几次法庭,去了几趟派出所,不知不觉便又过了几个月。虽然她不止一次告诉女儿,爸爸就要回来了,可直到女儿生日那天,刘岩还是没有回来。杜梅送女儿去学琴,走进大厅的时候,才一下子想起了送给女儿生日礼物的诺言。她观察着女儿的动静,女儿上楼梯之前,又深深瞥了那钢琴一眼。杜梅心里一下子刀绞一样难受起来,看着女儿上了楼梯,她自己一转身,流泪了。
女儿原本已经走到楼梯上去了,这时候却又跑回来,摇着妈妈的胳膊说:“妈妈,你别哭;我不要那琴,不要!我不想要!”
5
半年后,刘岩的案子已经尘埃落定,小城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关于事情的经过,杜梅却始终没有跟女儿亲口提起过,女儿也缄口不问。孩子还是每天晚上准时去钢琴学校练琴,白天或者周末在家的时候,从他们那六十平方的小房子里,也会传出琴声。小红能弹更多好听的曲子了,什么《致爱丽丝》《秋日的私语》,都弹得非常流畅了。这天,杜梅在厨房里洗着碗,听着女儿的琴声,很满足,很幸福。听着听着,钢琴的曲调变了,变得更加熟悉,更加温柔,杜梅站在那里,一时忘了这琴声曾经在哪里听过,过了好大会儿才听出来孩子弹的是《月光曲》,贝多芬的那首世界名曲……
杜梅拿着碗,一下子愣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