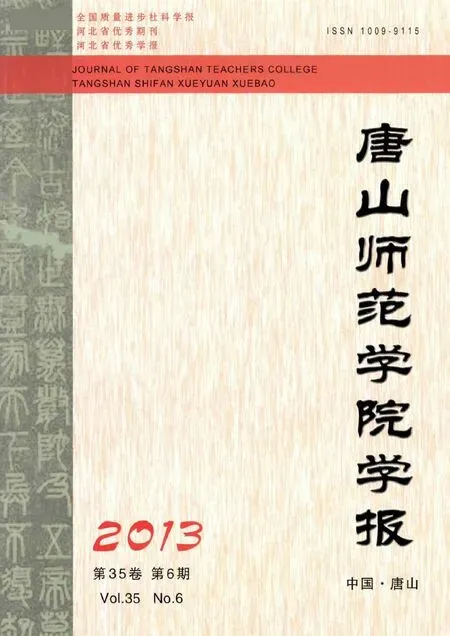现代知识分子的乡土姿态论述
汪 晴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3300)
鲁迅的文化启蒙乡土理论,以启蒙者的姿态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描绘与双重批判,超越了单纯的风土描绘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展示,勾画出了沉默的国人灵魂,对20世纪的乡土文学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是倡导具有“地域文学”倾向的的乡土文学,强调对“风土”“地域色彩”的把握。而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对于“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的重视,使之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具有某种暗合。但茅盾显然更强调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之外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尽管鲁迅、周作人、茅盾的乡土小说理论有着各自的侧重点,然而,他们却共同为20世纪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并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乡土小说的审美内涵。
一、以鲁迅为主的强调文化批判的启蒙姿态
20世纪的乡土小说主要指那种以乡村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表现东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的诗化小说或文化小说。因此,20世纪的乡土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乡土小说”这一名称最早由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指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是他自称为主观还是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克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是炫耀他的眼界。”[1]鲁迅是乡土小说最初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等取材故乡的作品都属于乡土小说。他笔下的乡村充满了浙东水乡浓郁的地方特色。那水乡土场上傍晚的小桌子和矮凳,河道上缓缓行驶的乌篷船,鲁镇祝福时祭祖的仪式,赵庄临河空地上的社戏,无不标志出特定的历史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的水乡生活气息。这些作品以冷峻的笔墨描画了旧中国农村凋敝、闭塞,农民生活的贫困和精神上的愚昧落后,展示了浙东特有的乡村文化景观。
鲁迅的乡土小说的民俗书写,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反封建和文化启蒙的时代主题。例如,《孔乙己》、《白光》通过描写乡村小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戕害;《药》《风波》《阿 Q正传》描写民众愚昧守旧的行为心态,揭示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祝福》《离婚》则批判了乡土世界封建礼教和封建观念的罪恶。鲁迅善于把民俗的描写与形象的塑造、性格刻画以及文化的批判有机地联系起来,更好地服务于批判“国民性”这一叙事主题。孔乙己的“长衫”、阿Q的“破毡帽”、祥林嫂的“白头绳”以及《社戏》《故乡》中大量的民俗场景,充分显示作家表达“现代胸臆”的审美蕴藉。“鲁迅创作视野中民俗所呈现出丰富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包含了作家主体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矛盾。正是作家复杂的文化心态,导致了现代乡土小说丰富的审美内涵。这种理性与情感‘二律背反’的叙述方式,被20、30年代乡土作家广泛采用,成为现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意味着乡土文学的成熟。”[2]
鲁迅《故乡》的归乡模式和《社戏》的童年回忆视角,给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创立了两种诗学范式。《故乡》开头的景物描写和叙述者低缓阴沉的语调营造出游子归乡的落寞心境。因为,现实中贫穷与凋敝的故乡是令人失望的,作家笔下的故乡不过是旅居他乡的游子的记忆编制罢了。“这使得文化乡土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具有了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过去和现在的时空差距,而游子的无家可归,有家难归和他乡逃离也都有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寓意。”[3,p16]而《社戏》中,小说通过“我”对城市看戏的不满,以此勾起对乡村生活的的一种怀念,暗示了叙述时间和空间的缺失,表达作者的孤独和焦虑,亦宣告了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否定。
鲁迅,毫无疑问是20世纪乡土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他高瞻远瞩的文化视角,清醒深邃的理性态度,圆润多样的艺术技巧,对二三十年代中国乡土小说流派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因此,在鲁迅的影响和示范下,新文坛兴起了以回忆故土为内容和题材的乡土小说。这些青年作家主要有许杰、王鲁彦、王任叔、许钦文、徐玉诺、台静农、彭家煌、废名、蹇先艾等。“这些来自乡村、寓居于京沪等城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和宗法制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隐含着的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4]。但是在表现乡景、乡俗、乡情上,二三十年代其他乡土小说家更倾向于单纯的展示乡村的种种陋习,并坚守着对乡俗的文化批判的单一立场。像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彭家煌的《怂恿》、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的《蚯蚓们》等,他们即使偶尔有乡情的呈现,也往往缺乏鲁迅那种文化超越意识以及对于乡土中国所隐含的民族文化的眷恋情愫。鲁迅乡土小说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复调”情感模态,在二三十年代其他乡土小说家笔下,则变成了“单调”的文化批判。
二、传承周作人的充满地域色彩的文化姿态
严家炎说过:“五四以后乡土文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倡导者是周作人。他从1921年起,就在一些文章中表示‘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认为‘风土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如果‘因反抗国家主义遂并减少乡土色彩’,那‘是觉得可惜的’。”[5,p43]可见,周作人提倡乡土文学是从民族文学建设上着眼的并且特别强调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他说道“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6]。周作人对乡土文学地方特色的推崇在于他对“土气息,泥滋味”的提倡,从地方风景、地方风俗、地方风情的角度强调了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内涵。他的乡土文学理论直接影响了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京派乡土小说文学家,也影响了孙犁、刘绍棠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并给新时期出现的地域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废名是最早师承周作人乡土理论而进行乡土小说创造的小说家。20世纪20~30年代他就写下了具有山水田园诗般的《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以及长篇小说《桥》等,以平淡、悠远的抒情笔调,开了乡土抒情小说的先河。“用一枝抒情性淡淡的笔,着力刻画幽静的农村风物,现实平和的人性之美。”[5,p211]。而沈从文接受了废名小说的影响,并成为乡土抒情小说的最杰出的代表。在创作理论上,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周作人乡土理论的具体实践者。“但由于沈从文的人生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人生感受方式,文学态度和立场的“异端性”,使他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已经占据了新文坛主导地位的鲁迅派对乡土文化批判的理性立场不同的一面。”[3,p111]他凭借自己对乡村经验的回忆和感受,抒发对乡村文化的怀念与憧憬。面对都市文明的压抑与屈辱,他产生了对美丽的乡土自然环境的怀念和对和谐无争的人世社会的憧憬,并自诩“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一把尺子,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7]。他并不注重乡村物质的进步,而关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美好人情人性的失落。这与鲁迅的理性过滤后的乡村经验与感受,注重对乡村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理性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8]无论是《边城》中的翠翠还是《长河》中的乡土人物,都具有质朴的人性美的特质。
虽然,沈从文直接师承的是废名山水田园诗般的乡土抒情小说,但在废名笔下,“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和谐,非常宁静,缺少冲突”[9]。而在沈从文笔下,则“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9],在这一方面“较似冯文炳君为宽且忧”。这就意味着,废名的乡土小说营造了桃花源式的封闭世界,内中的人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则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10]。
这又与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流派的乡土姿态不同,他们侧重于表现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三四十年代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的乡土小说则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美质的热情讴歌;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流派对待西方文化上是一种接受的姿态,那么三四十年代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乡土小说家则是以反西方文化的姿态出现的。
传承周作人充满文化乡土意味的小说家们,大大拓宽了乡土小说的审美视域。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古老的乡村更一点点地被现代物质所代替。因此他们的小说,特别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除了弥漫着温馨的牧歌情调,同时也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哀怨气息。
三、受茅盾影响的阶级意识先行的政治姿态
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政治理性视角下写出了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40年代的赵树理则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了乡村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都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
在《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中,茅盾运用现实主义精细写实手法,艺术地展示 20世纪 20~30年代中国社会宏阔的历史画面,真实地描绘了中国从大都市到小乡镇,到江南农村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必然历史命运,开创了乡土小说的新视角。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就对茅盾的乡土小说作了如下评定:“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的创作,意味着‘五四’时期所开拓的‘乡土小说’的深化和发展。作品将现实与理想融合在一起,以深刻的社会剖析的目光透视了灾难的现实,同时也充满了理想和希望,展示了大时代的变动,揭示出民众心态的变化”[11]。他的乡土小说,史诗式反映时代风云为主要内容,开辟了以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新思路。他在1932年《我的回顾》中说到:“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12]如果说,鲁迅的乡土小说是以文化批判的姿态,揭示了旧中国儿女们的愚昧与惶惑的话,那么,茅盾的乡土小说更倾向于展示新一代农民的觉醒和他们的精神追求。在茅盾看来,革命是事业,而文学只是革命的一种手段。因此,由于茅盾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理性偏好,严重地抑制了其真情实感的流露,从而使他描写的农村生活不具有真实的乡土情感。从《春蚕》《秋收》《残冬》我们可以看到,其文化内涵的逐渐递减,政治意味的逐渐浓郁。
赵树理是继鲁迅、茅盾、沈从文之后,乡土小说的又一个重要角色。他以乡村小知识分子的身份,切实地承担起了启蒙农民的历史责任,也适应了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的要求。赵树理的乡土小说创作机遇性地迎合了时代政治的需要,也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践者。但在建国后,由于农村现实环境的改变,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越来越表现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趋势。当农民立场与政治立场出现分歧的时候,作者更倾向与站在先进农民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并力图使政治内容与农民要求统一起来。因此,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农民立场和时代政治的立场的分歧越来越显得不可调和。
无论是茅盾还是赵树理,在肯定其艺术作品的对大众、对社会的积极意义下,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不同程度地有所削弱。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7.
[2] 张永.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M].上海:三联书社,2010:42.
[3] 罗关德.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八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1.
[5]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989.
[6] 周作人.民俗学论集·地方与文艺[M].北京:中华局,1980:1626.
[7]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1984:266.
[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1.
[9] 沈从文.论冯文炳[M].北京:三联书店,1984:100.
[10] 凌宇.沈从文乡土小说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3.
[11] 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339.
[12] 茅盾.茅盾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