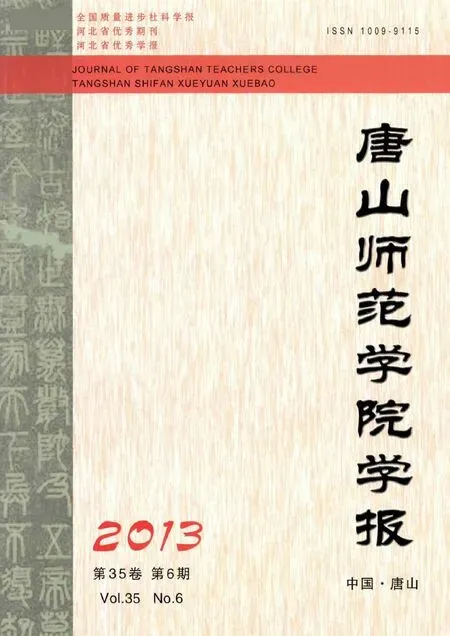丛林中的孩子
——《伊索寓言》今读
石向骞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丛林中的孩子
——《伊索寓言》今读
石向骞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伊索寓言》透射出明显的君主制制度文化背景,那些动物故事似乎呈现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伊索寓言》为各种价值因素设置了复杂的生活情境,每一种都用几个不同的故事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予以呈现。伊索愿意承认世界的微妙、社会的复杂以及人的内心需要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同时唯恐某种人为树立起来的简单化、威权化的道德律条妨害人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伊索寓言》是对泛道德主义的颠覆,它恰能契合以养成文明、理性、独立、宽容且具有强烈的权利与责任意识的公民人格为目标的现代教育。
伊索寓言;丛林世界;普世价值;泛道德化;现代教育
一
在古希腊早期作家中,荷马与伊索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两位。与吟唱长篇叙事诗的荷马不同,伊索是一个故事大王,开创了短小精悍的寓言体叙事。希罗多德、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都提到过伊索。不过历史上留下来的有关伊索生平及其作品的确切资料很少,以至有人认为伊索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今人所发现的有关伊索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中的一段文字:
罗得庇司……是色雷斯人,是萨摩斯人赫菲斯托波利斯之子雅德蒙的女奴。寓言作者伊索曾与她一同为奴。关于伊索也是雅德蒙的奴隶这一点有许多事实可资证明。其中之一就是,当德尔斐人遵奉神谕,声明如有人对伊索的被害主张赔偿,他们就会支付给他赔偿金时,最后只有雅德蒙,即已故雅德蒙的孙子前去领走了赔偿金。由此可知伊索一定曾是老雅德蒙的奴隶。[1,book2,chapter134]①
显然,希罗多德是将伊索当作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来记述的。
伊索学者乔治·费勒·汤森(George Fyler Townsend,1814-1900)在他编译的英文本《伊索寓言》中附有一篇关于伊索生平的文章,是他据法国人M.Mezeriac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来的。鉴于其珍贵的资料价值,节译如下:
伊索同希腊最著名的诗人荷马一样,其身世模糊不清。古吕底亚王国首都撒狄、希腊的萨摩斯岛、希腊人在色雷斯修建的殖民城市梅森布里亚、弗里吉亚的首府Cotiaeum等,都曾被人说成伊索的出生地。尽管不能确定上述哪一个地方应该荣膺伊索出生地这一美誉,仍有一些涉及伊索生平的事件被学者们普遍认定为史实。人们一般认为,伊索生于公元前620年,且生而为奴。他曾先后隶于两个主人,克珊托斯和雅德蒙,他们均为萨摩斯岛居民,后者因欣赏他的学识和智慧而解除了他的奴籍,给了他自由。在古希腊共和国,只有具备了自由民身份才有权参与公共事务。伊索与其后辈哲人斐多、迈尼普斯、埃皮克提图一样,都是起于卑贱,终成名流。他游历过很多国家,乐于施教,并虚心向学。其中就到过以大力赞助学人著称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统治下的撒狄。
在克洛伊索斯王的朝廷上,伊索遇见了梭伦、泰勒斯等当时的一批贤哲;他同这些人论辩,得到了国王的赏识,还讲出了一句后来成为谚语的话:“弗里吉亚人说得比谁都好。”
克洛伊索斯邀请他到撒狄定居,并委托他处理各种复杂、棘手的政务。后来,他辞去职事,访问了一些与吕底亚王国政体不同的希腊共和制城邦。他曾去过科林斯和雅典,并在那里凭着讲述充满智慧的寓言,调停两个城邦的居民与其各自的统治者佩里安德和庇西特拉图的关系。伊索之死即源于一次他奉克洛伊索斯之命出使希腊城邦。那一次,他被派往德尔斐,带去大量金币,准备分发给城里的居民。但他被人们的贪婪所激怒,便拒绝分发,把金币又带回去送还给主人。此举惹恼了德尔斐人,他们就指控他犯有渎神罪,且不顾他神圣使者的身份,公判并处死了他。伊索惨遭杀害,冤屈一直未得申雪。后来德尔斐人遭罹一连串的灾难,直至他们公开悔罪,对害死伊索做出赔偿。从此,“伊索的血债”就成了一句广泛流传的警世格言,意指天理昭彰,恶有恶报。这位伟大的寓言家也并不缺乏身后的荣耀。为了纪念他,人们在雅典立了一座他的雕像,是希腊最著名的雕刻家之一利西波斯的作品。[2,p1-2]
时至今日,有关伊索生平的史料鲜有新的发现。以上汤森氏整理的材料为伊索研究者普遍接受。
二
《伊索寓言》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在阿里斯托芬(前448-前380)的喜剧《鸟》第二场中,雅典人珀斯忒泰洛斯对由群鸟组成的歌队说鸟曾是万物之王,歌队长却表示从未听说过,他就讽刺鸟孤陋寡闻,没有查阅过伊索寓言,不知道“云雀葬父”的故事[3,p288]。柏拉图(前428-前348)在他的《对话录》之《裴洞篇》里提到,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曾在狱中将伊索寓言改写成诗②。由此可知,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已有伊索寓言集流行。公元前300年左右,雅典哲人得墨特里俄斯也编辑了一本伊索寓言集。可惜这些早期的本子未能流传下来。2世纪时,巴勃利乌斯用希腊文撰写了一本《伊索寓言》。14世纪,拜占庭的一名修道士普拉努得斯收集了约150篇伊索寓言,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后世才得以出版。从17世纪初开始,伊索寓言被广泛译介,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看到的《伊索寓言》,里面的篇目虽归于伊索名下,但它们显然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中有些故事早在伊索之前就已在流传,如“游隼与夜莺”的故事就见于公元前8-7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劳作与节令》。后人根据伊索的创作也多有改写和仿写。但无论如何,伊索总是《伊索寓言》的经典作者。
自古以来,伊索寓言一直是成人世界中人们在修辞、论辩或宣讲教义时广泛称引的实用材料。而到了现代,尤其是当下中国,它却往往被人们视为儿童读物。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适合儿童阅读的?它对儿童心性结构的培养又有何助益呢?
的确,伊索寓言篇幅短小,诙谐生动,启迪智慧,且大多以动物为主角,童趣盎然。同时,很多故事中的价值取向都能为现代社会所认同。然而,伊索描绘出的世界远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就会看到,在伊索笔下当涉及自由与奴役、公正与强权、和平与争斗、智慧与愚蠢、勇敢与怯懦、诚实与欺诈、虚荣与务实、合作与内讧、淡泊与贪婪、慈悲与伪善、怜悯与冷漠、忠信与背叛等两两相对立的价值要素时,他并非一味武断地做出倾向于前者的判断,而是经常在不同的故事中把它们置放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让它们变得复杂、模糊起来,有时竟让人难以抉择。甚至在有些故事中,聪明与狡猾(这在有关狐狸的寓言中体现得最明显)、威严与专制、英勇与凶残、老实与迂腐、隐忍与受虐(如《斗鸡和山鹑》③)、随机应变与不择手段等简直被混同了起来。伊索的世界透射出明显的君主制制度文化背景,如很多寓言表现出了对宿命、王权和奴役的无奈。伊索世界的基本信条似乎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由此,说得严重一些,伊索通过一个个动物故事,给人们呈现了一个尔虞我诈的“丛林世界”,这个世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这样一来,在以“自由、平等、民主、和平”为普世价值的现代社会框架中,伊索寓言还适合我们的孩子阅读吗?它能契合以养成文明、理性、独立、宽容且具有强烈的权利与责任意识的公民人格为标的的现代教育吗?
三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伊索寓言里缺乏维多利亚时代那些被人奉为圭臬的伦理规范[4,Cf.Introduction,ppxi-xii]。伊索寓言的原貌(或早期版本),并不像当下许多被改编成儿童读物的本子那样每个故事当中都包含有明确的道德训条,这一点与那些出于教育孩子的目的而新编的寓言比起来更加明显。现在流行的多数伊索寓言版本,每篇文未都有一条道德寓意,那显然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多有牵强。作为寓言大师,伊索却只让故事本身说话,不愿以道德面目示人。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写了一部小说体教育著作《爱弥儿》,在第二卷里讨论了寓言对孩子们的教育作用。他在分析了拉·封丹改写的几篇伊索寓言后指出,孩子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寓言的负面影响。因为出于“自爱”的天性,他们的选择差不多同寓言作者的意图是完全相反的。对于成人想纠正或防止的缺点,孩子们不仅满不在乎,而且还偏偏喜欢为非作歹,以便从别人的缺点中得到好处。比如,卢梭说,“乌鸦和狐狸”“蚂蚁和蝉”“合伙捕猎”“蚊子和狮子”“瘦狼和肥狗”这些寓言,在孩子们看来,第一个是教人卑鄙奉承,第二个是教人残忍无情,第三个是教人做事不公正,第四个是教人嘲笑挖苦,第五个是教人不
服管束[5,p128-135]。
而钱锺书在《读伊索寓言》中则这样说:“卢梭认为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象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
当。”[6,p39]
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钱锺书先生的“我认为寓言要不得”是正话反说,他真正的意思是借此揭露、讥刺社会现实中的丑陋、混乱。他所担心的并不是幻想领域的寓言对孩子们的影响,而是现实中大人们的行为以及由大人们操控的社会对孩子心灵的戕害。钱先生在文章中还对九篇伊索寓言进行了别有意味的阐发,也足以说明伊索寓言“大可看得”[6,p36]。
的确,大人们不应该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应该把社会问题归因于“坏孩子”,更不应该把孩子的“坏”归因于那些有趣的寓言。
由此看来,卢梭的担忧是一种“君子过虑”。其实大人们大可不必担心伊索会教坏了孩子,就像雅典人不必担心苏格拉底会败坏青年一样。伊索寓言不是“狼奶”④,而是自由心灵的创作。伊索的时代是古典时期思想自由的时代。当时多种政体并存:君主制、贵族制(包括寡头制)、僭主制、民主制。伊索周游列国,对各个政体应非常了解。伊索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古吕底亚王国,为克洛伊索斯王朝服务,他的寓言中的君主制制度文化背景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但他无疑对其曾游历过的雅典等希腊城邦的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情有独钟,对社会的公正、平民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倍加珍视。
如前所述,伊索为各种价值因素设置了复杂的生活情境,每一种都用几个不同的故事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予以呈现,这是他愿意承认世界的微妙、社会的复杂以及人的内心需要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同时唯恐某种人为树立起来的简单化、威权化的道德律条妨害人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但是又不难看到,伊索一方面尽量让各种价值选择接受不同生活情境的考验,同时对一些核心价值,如自由、公正,又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而明显厌弃专制暴政。例如《狼和看家狗》(101)、《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211)、《鸽子与乌鸦》(239)是讲有自由才有幸福;《狼和羔羊》(1)、《野驴和狮子》(312)、《青蛙求要国王》(51)讽刺了暴君、强权和君主政体;《猩猩和两个旅行者》(197)指斥专制国度以谎言维持统治;《狮子王国》(8)涉及对君主政体的改革,竟提到了国民大会与全民公约。此外,《树与斧子》(219)、《马和鹿》(192)等故事分明是在说,随意剥夺他者的自然权利终会使自己受害,而轻易让出自己的权利必将遭到别人的奴役。
当然,伊索的世界远为丰富多彩。那里能让我们体验到人类曾经有过或将来可能面临的几乎所有的生命情境。《橡树与宙斯》(153)、《哲学家、蚂蚁与赫耳墨斯》(145)甚至讨论了神正与人正的问题。人们该如何对待宿命、神灵、危险、骗局、名誉、金钱以及敌人与朋友、自我与他人、顺境与逆境、慈爱与溺爱呢?这个世界真的应该仅仅以人类为中心吗?所有这些问题,伊索都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答案。他一方面大力鼓励人的自由,一方面又不断提示人的有限,让人对社会环境时刻保持警惕。从一种意义上说,这不正是对精神解放的呼唤、对自由心性的吁求吗?
伊索带领我们进入各种生命情境,或温馨、美好,或无情、凶险;读了伊索,我们却有信心在经历一番精神的洗礼之后愉快地与那些情境诀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称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正常的儿童⑤。对于希腊人的正常,伊索寓言与有功焉。
四
在当下中国,弥漫着一种对儿童的道德焦虑。我们成年人唯恐孩子们学坏。于是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从家长、教师到各路媒体,不厌其烦地训示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该爱什么该恨什么,还要定期推出一两个少年道德榜样,掀起一个又一个思想品德教育高潮。可我们往往只是把那些伦理标准答案当成千真万确的知识和固定不移的“硬道理”交给他们,只决断地告诉孩子们如何行为而不告诉他们为何如此行为。我们不习惯教孩子们理性分辨,不习惯教孩子们独立思想(thinking)。我们一方面将孩子看成“缩小的成人”,一切照成人的模式去塑造他们,让他们“懂事”;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少不更事”、幼稚懵懂,认为对他们只需“灌输”,不屑与他们平等地探讨思想问题。那些深刻而美丽的思想,未经与孩子们探讨,怎么知道孩子们不懂?究竟是孩子们不懂,还是大人们自己不懂,抑或是怕孩子们懂?
看来,成人社会要孩子“懂事”,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思想启蒙,而是要他们“听话”,要他们明白不得违逆大人的意志。实际上,成人对孩子的道德焦虑源于成人对自身道德水准的缺乏信心:他们怕的是孩子们跟大人学坏。因为成人社会为孩子规定的那些道德高标连我们大人自己也做不到,甚或也没有几个人真把它们当成一回事。
于是出现了泛道德化的教育倾向。为了消除对儿童的道德焦虑,从基础教育开始,成人就开动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儿童的心性施以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同时将公共职位上的职务(责任)行为都提升为道德行为,于是人人都在“无私奉献”,人人都在无限关怀和辛勤哺育祖国的小花朵,并由此要求孩子们一定要懂得感恩。与此相应,孩子们又被告知,那些喜欢用自己的脑子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的人,那些揭了皇帝新衣的人,那些计较个人权利的人,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对和谐稳定局面不利的“坏人”或被坏人利用的人,要勇于与他们作斗争。
泛道德化的结果甚至让一头在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猪也成了象征坚强战士的“猪坚强”。有意思的是,伊索笔下的丛林世界中也不乏将动物自身的自然行为矫情为道德行为的角色。如《熊与狐狸》(26)中只吃活食的熊说他对人类最为友善,因为他对人的死尸连碰都不碰一下;《狼和马》(224)中本来不吃燕麦的狼偏说他特意把一整片地的燕麦都留给了他的好朋友马;《鹰、狸猫和野猪》(179)中的狸猫为了掠食,在鹰和野猪中间制造恐怖气氛,把二者的生活习性硬说成要加害对方的阴谋。伊索对此类角色的揭露与讽刺可谓不留情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伊索寓言是对泛道德主义的颠覆。
满街都是圣人的国度与满街都是(小大人一样的)乖孩子的国度一样可怕。何况这些乖孩子只是些能迎合标准答案的做题高手呢!
担心缺少了大人的道德训诫孩子就会学坏,无异庸人自扰。其实大人们只需尽力别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坏,剩下的尽管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找到底线好了。当然这样的前提是大人要有足够的谦卑,要把孩子当成平等的有尊严的人而不是工具。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曾劝告觉醒者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7,p130]。
这就涉及到大人们的责任了。
如果说伊索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丛林世界的话,他也是在告诉我们,在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社会,人人都是受害者。正如《蚊子与狮子》(185)、《老鼠与公牛》(295)等寓言所揭示的,在丛林中,强者与弱者都生活在恐惧中,强大如狮子、公牛也可能遭到弱小如蚊子、老鼠的不对称的暗算。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幸亏我们人类能用权利法案代替丛林法则,能让弱小者得到保护,同时让强大者在不伤害弱小的情况下得到合理发展。因此,在社会丛林中,大人们应肩起责任,驯服统治者,“把它们关进笼子里”,让狮子、灰狼不再可怕,让羊羔、兔子不再害怕,让狐狸的狡诈变成有创造性的智慧,让狮子的凶悍变成有公信力的威望。总之,大人们有责任建造一座繁茂美好的社会丛林,再踏出一条条林中路,然后放我们的孩子自由自在地栖居、行走于其间。至于孩子们是蹦蹦跳跳歪歪扭扭地走还是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地走,就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吧。相信孩子们能找到自己的底线。
这样一群丛林中的孩子才是健康的、有希望的,身处这样的丛林,才有可能长成心性结构丰盈美好的公民稚芽。
希腊人为什么是“正常的儿童”呢?因为对他们来说,上有诸神,下有法律,哪怕身在丛林。
五
泛道德化教育很容易妨碍孩子认知世界真相的自由。它缺乏内在的普适价值依据,往往左支右绌,穷于应付,最后难免露出马脚,沦落为功利主义的教唆:在家里要听话学乖,在外面要够黑够狠,只要能给老子(包括私域的老子和公域的老子)争气争光就行。
其实鲁迅先生早就揭示了道德化儒家那些“圣人之徒”对待孩子的赤裸面目:
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7,p138]
问题是一旦孩子们悟出个中玄机,看透大人们的把戏,那后果将真的很严重:他们的价值大厦将会瞬间崩解,道德信念将会一朝云散。孩子们将会因此陷入虚无的困境,觉得一切大道理都是假的。进而,他们中将会出现或者破罐破摔,放弃一切权利,乖乖地把自己交给一个可依附的强者;或者铤而走险,强食弱肉,成则王败则寇;或者索性将计就计,弄通厚黑学,玩儿转潜规则,阳奉阴违、欺软怕硬。
可见,泛道德化教育的伦理后果不外乎养成三种心性:奴性、匪性、痞性。三者可分别对应于伊索寓言中愚昧的驴子、强横的狮子和奸诈圆滑的狐狸。这是一种臣民心性结构,里面没有公民意识的栖居空间。它又极易被某种空泛、宏大的道德激情鼓动起来,从而转化为“爱国贼”式的“愤青”。当然它也渴求融入群众性的狂热中,使自己兴奋起来,以便抑制那时时袭来的虚无感。
近来竟有一班被称为中国“新左派”的人士板起“中国不高兴”的面孔,他们力挺所谓的“四月青年”“火炬一代”,寄望中华上国的新青年对内要甘受驱使、做羔羊,对外要敢不高兴、为虎狼⑥。
此外,近年还有媒体讲坛的“学术明星”向世人布道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权谋的世界,古今中外都一样,没有什么办法,有本事你也去算计别人好了;你本领不济?那就做耐压的南瓜吧,闭上眼睛让一切都过去,照样可以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因为有什么样的眼睛就有什么样的世界⑦。
鲁迅先生当年极为反感的“含泪的批评家”[7,pp403-405]也代不乏嗣。如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之后,分别被网民称为“余含泪”和“王幸福”的两位作家,就把泛道德主义的旗帜挥舞到了极致。面对灾区的孩子被地震和“豆腐渣”校舍夺去年轻的生命,他们分别含着痛心(痛心于追究校舍建筑质量的家长之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和感动(感激于“党疼国爱”)的泪水劝告道,那些遇难的孩子死得光荣,家长们对他们的死应该感到无限欣慰才是,因为他们都进了天堂,他们“纵做鬼,也幸福”⑧。
至此只能无语了。那就以钱锺书先生《读伊索寓言》中的一句话来结束吧:
小孩子该不该读寓言,全看我们成年人在造成什么一个世界、什么一个社会,给小孩子长大了来过活[6,p39]。
[注释]
① 此处译文为笔者自译。
② 参见: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9页。艾索波即伊索。
③ 参见朱馥慧、朱福云、石向骞译《伊索寓言》,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第227篇。后文所有寓言篇目均出自该译本。
④“狼奶”之喻,见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冰点周刊》。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0页。
⑥ 参见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等著《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⑦ 可参中央电视台(CCTV)第10频道“百家讲坛”栏目2006年录制播出的节目“于丹《〈论语〉心得》”。
⑧ 参见余秋雨2008-06-05的BLOG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http://yuqiuyu.blog.sohu.com/89351261.html);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齐鲁晚报》2008-06-06“青未了”副刊。
[1] Herodotus.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book 2, chapter 134)[M].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1947.
[2] Aesop. Aesop’s fables[M]. Translated by G. F. Townsend.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1886: 1-2.
[3] 阿里斯托芬.罗念生,等,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288.
[4] The Complete Fables by Aesop[M]. Translated by Olivia and Robert Templ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Temple. London: Penguin(Penguin Classics), 1998: pp xi-xii.
[5] 卢梭.李平沤,译.爱弥儿——论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8-135.
[6]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36-39.
[7]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0-405.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Kids in the Jungl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esop’s Fables
SHI Xiang-q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China)
Aesop’s Fables reflects an obvious cultural background of monarchy system, in which those animal stories seem to show a “Jungle World”. Aesop’s Fables sets up complex life situations for the value factors, each of which is present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by different stories. Aesop is willing to accept the trickiness of the world, the complexity of the social,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people’s interest demand. Aesop’s Fables is subversion for pan-moralism. It can fit exactly the goal of modern education to develop rational, independent, and tolerant citizen personality which has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esop’s Fables; Jungle World; universal values; pan-moralism; modern education
I106.8
A
1009-9115(2013)06-0009-05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6.003
2012-07-04
石向骞(1966-),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