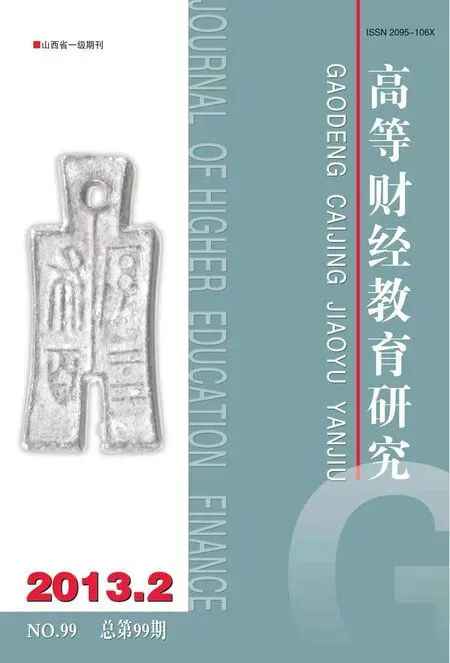文学之“虚”与翻译之“实”
——文学与翻译内在契合特质研究
杨彩霞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文学之“虚”与翻译之“实”
——文学与翻译内在契合特质研究
杨彩霞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文学是想象的艺术,翻译的核心是语言,语言交际凸显文学与翻译的契合性。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学与翻译的共性之一就是其创造性。文学与翻译的结合——文学翻译,实际上为各自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强劲的内在活力和发展空间。译者的理念对所译作品的选择、诠释和表述都会产生诸多影响,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翻译接受的美学理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评判和审视,更能彰显文学与翻译的内在同构性。文学翻译实践成为展现文学与翻译结合与汇融的现实场域。
文学翻译;契合性;同构性
一、语言交际:凸显文学与翻译的契合性
作为人类交际最为直接、外显、重要的工具,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表达感情和交流思想的方式。翻译活动是语言交际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一个人若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可以做两种选择:要么到世界各地亲身体验生活(直接经验),要么通过阅读翻译作品增加对其他文化的了解(间接经验)。美国著名学者恩格尔认为:“随着这个世界像一个熟透的橘子那样慢慢缩小起来,(无论是颇不情愿还是心存疑团)所有文化的所有民族距离都更为接近,我们有生岁月中可能说到的一句关键话就是:要么翻译,要么死亡。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可能要倚赖一个词语的及时、准确的翻译。”[1]尽管此言不无夸张成分,但也彰显出翻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充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即使这种角色在大部分情形下是隐形的,有时候看起来可能还是微不足道的。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曾经说过:翻译作品好像媒人,它们给你带来对某个轻纱半掩的美人的称赞,从而引起你很想一见其人本来面目的欲望。对于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语言汉语和英语而言,翻译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英语是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这两种语言载体各自代表着东西方两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和思维模式。
一个译者要想把一篇好文章或一部好书翻译出来,正是受到一种创作欲望的敦促。译者由其酷爱的原作引起激情,翻译时又会产生类似于作家写作时的创作欲。受原作的约束,译者既欲随心创作,又须克制自己,即应深入意境,又要善于冷静超脱,凌驾于原文之上,超越自身的附属地位。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活动一直被称为“二度创作”,有人还形象地把它比喻为“带着脚链跳舞”(英国诗人德莱顿)、“驿马”(俄国诗人普希金)、“不忠的美人”(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杨绛先生也曾把翻译形象地比喻为“一仆二主”。诗人余光中把翻译称作“有限的创作”,把创作称为“不拘的翻译”,从正反两个方面道出了翻译与创作的内在关联。他在《作者、学者、译者》一文中提出的“译者其实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没有创作的作家”,深刻揭示出翻译与创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也印证了文学与翻译内在契合的本质特性:“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2]22多做翻译可以使人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不但可以提高外语水平,丰富知识,还可以提高其母语水平,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翻译的核心是语言。因此,语言的运用不仅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首要特征,而且也是文学翻译关注的首要问题”[3]3。事实上,许多翻译家首先就是文学家,他们能以文学创作的心态看待文学翻译。
谈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自然要涉及到文学翻译中的“自然背离”(normal deviation)和“创造性背离”(creative deviation)两个方面,同时还要关涉文学翻译创造性与文学创造性的内在关联性及差异性。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翻译一部文学作品,需要对作家,对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明,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与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是翻译的前提,是翻译的指导,并贯穿翻译的全过程。不妨说,译者应当是学者。一位学者型的译者,比较容易寻得两种文明的契合点,缩小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距离,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的翻译风格,使自己的翻译靠近‘化’的最高境界”[4]93。“文学翻译不同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翻译,有其非常特别的一面,那就是翻译的对象既是一个有形可见的文字版本,又是一个意蕴深邃而模糊的艺术整体,因此,对文学翻译的探讨不能只局限于翻译理论及翻译方法的争论中,而应该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学翻译的根本前提来看待。”[5]167此外,文学翻译身份的认定也存在问题:文学翻译是创作吗?应该如何定位译者、作家和批评家的三重身份呢?文学翻译是否会削弱源文本的深刻性及隐喻性特点?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及回应,可以从不同侧面透视文学与翻译内在的契合特质,揭示文学翻译的双重角色作用。
二、文学翻译:彰显文学与翻译的同构性
文学翻译是一种特点鲜明的翻译活动。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跨越国度、超越时代,沟通人们的思想,传递人生的信息,构架文化的桥梁,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生活的力量。理想的文学翻译家应集译者、作者和学者的素质为一身,这一身份应自然而然地浑为一体,而不应显露任何的牵强附会。文学译者所从事的是一项科学性和艺术性兼并的工作,文学翻译的前提应该是文学研究,译者所进行的文本评论应该区别于学院派的学术文章,需要给予读者更多的阅读乐趣和审美享受。在中外翻译史上,把文学翻译视为创作的不乏其人,如“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就认为翻译是一种创作,不仅要与原作相媲美,而且要尽可能在表达的艺术性方面超过原作”[3]5。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认为:“21世纪是世界文学的时代,文学翻译一定要成为翻译文学,也就是说,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才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未来的文学翻译一定要提高到文学创作的地位。”[4]48文学需要翻译使其得以传播,文化需要翻译得以传承,翻译更需要文学这一丰富的载体来滋养之。文学与翻译的结合——文学翻译,实际上为各自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强劲的内在活力和发展空间,也是不同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本质且具体的体现。
文学翻译的概念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文学翻译活动,二是文学翻译作品,即翻译行为和翻译成果两个层次的意义。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与翻译文学(translation literature)的概念是不同的,翻译文学是“由翻译家转换为译入语的,主要供译入语读者群阅读的文本”[6]。翻译文学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得以存在和实现其价值,文学翻译其实正是借助于“翻译”这一方式来实现翻译文学的价值。以色列翻译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明确指出翻译文学是译入语民族文学多元系统的一部分。美国翻译和比较文学教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英国翻译理论家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视角对翻译文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国内,胡适最先提出了翻译文学问题。20世纪90年代,“谢天振等人系统地论证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提出了文学翻译是对原文‘创造性叛逆’的观点”[3]10。
文学创作需要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学产品的特质更要在文学翻译中得到鲜明再现。这就要求文学译者摆脱原文语言结构和字典释义的束缚,生动、活泼、豁达地进行换位思考和表述,因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就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将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7]。这样看来,译者的理念对作品的选择、诠释和表述都会产生诸多影响,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翻译接受的美学理念。翻译文学作品与其他类翻译有着很大的不同,文学翻译具有文学创作的一切特点,但这些特点又是原作基础之上的再现,具有创造性与约束性相结合的特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翻译学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翻译的认识有了很大拓展。“首先,从语言性质上讲,文学翻译处理的是具有想象性、审美性和高度创造性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和绝对‘对等’在文学翻译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可能有绝对忠实或完全对等的译作。其次,文学翻译必然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内,文化系统的结构、意识形态和诗学决定了文学翻译是一种‘重写’。第三,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决定了翻译是一种‘阐释’,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对原作的理解和译作的生产。因而,文学翻译作品必然是与原作相关、但却独立于原作的‘来世’生命。”[3]7可见,文学研究不仅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文学翻译的接受和批评同样具有极大的价值。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评判和审视,更突出了文学与翻译的内在同构性。
文学翻译作品具有显著的大众性特点,其在影响人们生活方面有着其他类翻译无法相比的独特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对不同的文体采用不同的标准,懂得“取舍”和“聚焦”对文学翻译尤其重要。譬如,有时译者力求保持原文的一切要素,却丧失了最重要的东西,面面俱到,等于什么也没有达到。风格是所有文学作品最为独特的部分,翻译时若没把风格体现出来,或者即便译出来,但索然无味,则这种处理恰恰违背了文学翻译的特质。文学翻译的问题不一而足,有些译者放不开,不懂得个别部分的调整并不妨碍译文的整体性,而且会保证译文完整性的实现。进一步而言,文学译本的主要参与者——作者、译者和读者要有互动作用,文学翻译活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在进行译文语篇分析时,译者的思维方式需要特别关注,译者既要横向思维,又要纵向思考;既要注意到有形方面,又要关注包括思维范式、概念差异在内的无形方面。由于语言具有力量,语言的适当使用可以达到特定目的,取得特定效果,营造特定氛围,制造特定印象。文学语言同样具有这些特质,而且较其他语言形式更为鲜明、具体,这就更彰显出语言、翻译与文学的内在同构关系。
三、翻译实践:展现文学与翻译的结合与汇融
待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客体,文学译本的主要参与者——作者、译者和读者是主体,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翻译活动的过程。文学与翻译的内在关联要求译者在选择翻译素材时,首先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和潜在影响,是否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翻译。20世纪初期,本雅明在其论文《翻译的课题》中指出,译文可译与不可译取决于译文本身有无翻译的价值;翻译不是译意思,而是译形式。因此,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翻译之前的选材对于译本最终的命运非常关键,这就要求译者认真遴选,慎重抉择,选取对社会人生具有积极意义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著名翻译家严复的选择就极其审慎,他的翻译不是信手取材,更不是避难媚俗,而是有着严格的标准:一是所译必是名著;二是译书必有命意;三是所译书的版本必是最好。另外,对于有悖于译入语文化理念、风俗传统,或有悖于现行法规的选题,完全可以弃之不译。以下实例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极好诠释:英国作家拉什迪撰写的《撒旦诗篇》,极大地伤害了穆斯林的民族感情,因而许多国家都拒绝翻译。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关注其文学性、审美性及接受性等艺术性方面,还要斟酌作品的思想性和道德内涵。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关注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翻译主体对西方文学的独特感知和认同感,会对译介对象产生一定的倾斜。文学文本中的教育性、审美性、文学性等,可以强化文学意识,提升译本档次,提高翻译质量。
确定选题之后,译者要对文学作品创作的背景、时代、生活以及作家本人的生活阅历和创作心理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在翻译过程中,要勤查工具书,多方面请教,认真琢磨字里行间的深层意义。文学作品具有多重诠释的可能性,一百位读者心目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形象,而作为带有翻译任务的特殊读者,一百位译者笔下也会产生一百个独特的哈姆雷特。因此,要想把原作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味道完整地传递出来,不仅要从语言的角度,还要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阐释。文学翻译实践的理想路径应该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即翻译作品是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并从理论的角度系统地对后者加以印证。文学作品译作的“前言”(序)、“后记”(跋)就是一种直接、系统介绍翻译实践和研究心得,其不但为译文读者提供了进入外国文学的敲门砖,也是提高译者翻译水平的好方法,同时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有据可考的实证性资料。
一旦开始文学作品的翻译,最先考虑的是原作所蕴含的各种文学元素,如体裁、主题、风格、语言和修辞等,译文必须把这些方面忠实、完整地传递出来。上文已经提到,要想生动地再现原文的内容,适当地“取舍”和“聚焦”非常重要。“取舍”的标准要看整体效果而定,文学翻译不能亦步亦趋,而要照顾到原作的内涵和意象。王国维谈到意境时说:“何以谓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也。”原文风格的传递包括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等,也就是说,语言风格既包括原文本身的措词、句法、句子长短等,还包括作者一贯的写作特点,即“个性”。修辞手法主要是指原文使用的一些写作手段,如比喻、拟人、排比、对仗、意象和象征等,还包括由此体现出来的作品总体风味,如幽默、嘲讽等。如何把这些适当地转换到译文之中,是“取舍”和“聚焦”极为关键的方面。
基于文学创作的特质,文学翻译特别需要注意体裁和风格的传达。文学翻译对风格的要求很高,翻译修饰很重要,但不一定要用最高雅的字,重要的是合适。文学家运用语言时可以说是妙笔生花,很多属于修辞的范围。这就不能一味地遵循严复翻译标准中“雅”的要求,如把唐诗译成外文也得像诗歌才行。当然,不能把戏剧译成小说,不能把政论性文章译成抒情式散文。否则,译作就是对原作的误读和亵渎,糟蹋了原作,这是翻译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避免的做法。有个比喻十分形象:“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他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杂些泥沙,那就不行了。”[2]24
事实上,文章风格的具体内容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题材(subject matter)、措词(diction)、表达(mode of expression)和色彩(color)。原则上讲,题材有正有反,措词有难有易,表达有繁有简,色彩有浓有淡。要想把风格传神地传译出来,译者首先要有识别作品独特风格的意识,然后要有表达这种风格的水平和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译者要具有与原作者同样文学功底的缘故。实际上,理想译者的文字功底甚至要超过原作者。狭义地讲,题材主要是指作品的内容与取材,并且是与风格和形式相对而言的。主题(theme)是作品的题目,即所要传递的主旨或中心思想。概言之,风格主要关涉到题材内容、语言表达、褒贬色彩等表现作品和作家个性特征的方面,“文艺作品的风格,应该是指一个作家所有作品中经常重复出现的主要思想和艺术特点的总和”[8]。温彻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r)在《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提出“雄伟”(energy)和“优美”(delicacy)的概念,认为这是风格的最高标准,即风格以雄伟为上乘,优美为次选。
文学翻译应该在最大限度内保持原作的风格,也就是说,尽量缩小作者与译者之间的风格差异,“译者在研究选择他所译介的外国作家作品的同时,也要对自己作一番研究,最为理想的是找到与自己性之所近的作家作品加以翻译,这样才能与该作家及其作品产生更多的共鸣,才能更好地再现原作者的风格。译者与作者如能心神交融,合为一体,而达到心灵上的契合,那么,翻译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9]。然而,具体到现实中,风格又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在具体操作时,需要灵活和变通,这是翻译创造性的具体体现,也对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任何一部译作的产生,都是作者与译者共同作用的产物,原作的价值只能通过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在译文语言中得到实现。
不同的译者有自己独有的译风,“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10]。这些风格会在译文中不同程度地展现出来,这也是翻译的应有之义。然而,译者的风格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二位的,都不应该与原作的风格发生冲突或者凌驾于其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压过原作的风格而使其丧失或淡化,“要妥善协调好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翻译首先要体现出原作者刻画人物及行文遣词的风格,这毋庸置疑,但不是说应该抹煞译者自己的风格,只是译者不能喧宾夺主,以译者风格代替作者风格”。从严格意义上讲,译者的风格应该是原作背后忽隐忽现的一块遮光布,是一种必需的隐形存在。“一是原作的风格在译文中应该得到再现,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变易和译者个性的介入,势必会在译文中打上译者的风格标记;二是译者风格的客观存在并不以削弱原作风格的再现可能性为前提;三是译者应该尽可能将自己的风格与原作者的风格融为一体,使译者的再创造个性转化为再现原作风格的有利因素,以追求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和谐统一。”[4]30成功的译作应凸显原作的艺术风格,又不压抑译者的自然表述风味。
在翻译实践中,文学经典的复译是极为常见的翻译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文学与翻译内在的契合性和同构性,是二者融会贯通的具体体现。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的确值得并且需要复译,这是文学创作的本质以及翻译的工具作用和碰撞的结果。文学经典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加之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原作具有不同的期待值和审美需求,而且伟大的艺术创作总具有多重诠释的视角,使得文学经典的复译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安杜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认为:“文学翻译中十分普遍的名著复译现象是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它不仅仅说明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与美学价值的世界名著对世界各民族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经久不衰的吸引力,而且也证明了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化碰撞与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同时,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译文的不同要求。”[5]88不同时代的语言、读者品位的变化等,都是进行经典复译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一些存在瑕疵的译本也可以再译,以求精益求精。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译本是完美无缺的,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此外,有些译本本身虽然没有信息理解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失误,但译者需要注意的是,译得对不等于译得好,因为文学作品的韵味和风格并非单凭准确就可传递出来。可以说,“妥帖”和“适当”是所有译品的最高标准,自然也是文学翻译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译者角色:超越与隐身的结合
英国译论家萨瓦里(Theodore Savory)在《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1957)中提出了著名的六对相互矛盾的翻译原则:“必须译出原文文字,必须译出原文意思;必须译得读起来像原作,必须译得读起来像译作;必须反映原作的风格,必须带着译者的风格;必须译成与原文同时代的作品,必须译成与译者同时代的作品;可以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不可以对原文进行增减加工;诗体必须译成散文体,诗体必须译成诗体。”这些看似悖论的表述,恰好揭示了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也带出了译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即可译性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翻译思考和策略。这是因为,对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翻译活动本质的关注,同时还关涉翻译策略的问题。无论是翻译原则的制定和遵循,还是翻译策略的实施,归根到底需要译者的出场。翻译,归根结底,是译者通过精神活动,深入体味原文的各种可能性,选择他认为准确的所指意义,用译文的形式表达出来。翻译活动正常、良性的开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在社会上的地位、角色及作用。长期以来,译者一直处于隐身地位,换言之,译者处于第二位的从属地位,从属于原作,从属于原作者,不为读者所重视。从本雅明探讨“译者的任务”,到韦努蒂思索“译者的隐身”,其关注的都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地位及角色的转变,倡导彰显译者与原作者的平等性。在强调创造性的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独立身份可以更为彰显。也就是说,译者并非幕后为作者默默奉献的人员,而是具有独立地位并对译文的翻译和接受过程产生重要作用的前台人物。
译者的价值直接体现在其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法方面,直译和意译是文学翻译中常用的技法。意译可以看作是忽略原文表层结构表达方式多样化而单纯强调语义(确切地说是信息)传达的翻译,而忠实地传达深层结构同时又兼顾表层结构风格再现才是直译。直译与意译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语言的本质要求,是翻译的必然,两者不可偏废。在王佐良看来,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紧扣局部,即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可见,在任何文体的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是不可完全分离的,直译之中有意译,意译之中见直译,这是文学翻译和译文分析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译界有句名言:“好的翻译读起来应该不像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似乎更应该达到这一目标。然而,翻译作品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摆脱异国风味,除非不是翻译而是改写。这不仅涉及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中的“异国风情”,而且涉及文字风格、风俗习惯、语言习惯、情景气氛等主要因素。有时候带点洋味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鲁迅先生就主张保存洋气,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这样写道:“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有益智,至少是知道何时何地,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保留外国情调,因为它是原作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国情调’是指另一民族的心理特点、异地风光、特殊事物等。这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十五世纪时德国翻译家阿尔勃列赫·冯·艾布在翻译时就采用改头换面的方法,用本地事物代替原作事物。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在很长时期内,在翻译时为了迎合其本国读者的“优雅情趣”,也常常删改原著,因而丧失了原著的地域性、社会历史特点及作者风格。”中国翻译史上一度也曾出现过度归化翻译的现象,林纾的文学翻译即为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的语言文采自不待言,带有强烈的文学风味。然而,林纾译文的过度中文化、异国情调的完全缺失以及大量的增删,使翻译几乎变成译者本人的文学创作。因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其创造性的把握更要有“度”。“适度”不仅是衡量世事万物的尺度,更是把握文学翻译作品的标尺。
事实上,要想成为真正的文学译者,除了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工夫外,还需要有生活体验和切身的心理感悟,能够体会到原作的精妙之处,领悟到作家丰富的精神世界,并能运用准确到位的语言妥帖地传递到译文文化之中。也就是说,译者就是“杂家”,尤其是文学翻译家,更应该通晓百物而不懈怠,因为文学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语言外形的变异,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把握住原作的精神,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精确地再现出来。阅读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享受,翻译文学作品亦是如此。译者和原作者应达到一种心灵上的感应和契合,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没有充分的人生体验,有时很难真正领悟、体味出原作的风味和意境,更何况还要把这些内容适度地移植到另一种异质文化之中。
语言层次上的反差(不规范言语与规范言语)被喻为“译者要背负的十字架”。在翻译时,译者必须把握原著中不同层次的语言特点,运用汉语中相对应的雅、俗、俚、白,真实地再现原著的这些语言特点。事实上,翻译需要有一定的“苦行精神”,译者其实就是一个经历磨难的“苦行僧”,需要具备为理想而甘愿“自我受难甚至献身”的精神,这在翻译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总之,译好一部作品,关键在于译者要会应用已有知识从原著中获得感受,并用生动、准确的语言捕捉各个形象细节,融情于景,心形传神,达到以言感人的目的。
译者要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翻译,不可因时间紧而粗制滥造,降低对翻译质量的要求。在此方面,要消除文学翻译中的一个认识误区,即尽管文学翻译需要精工细雕,但译得慢并不意味着译得好,译得快也不一定是译文质量差的代名词。同样,信息译得准确并不一定意味着译得成功,因为风格的传达不一定非常到位。因此,译文应该精心雕琢,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文中出现个别的欧化句法,有时不但难以避免,甚至是必要的。但译文不应有生硬拗口之嫌,不应有明显的欧化句式,不宜带有明显的翻译腔,不能机械地照搬辞书。文学作品读起来虽然很顺畅,但翻译起来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往往非辞典所能解决,因为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和独创性远远超出了辞书有限、固定的模式和框架。作为文学译者,不能完全或多度依赖工具书,过分夸大工具书的参考或借鉴作用,任何时候都要走出工具书,寻找适合译文语言又忠实传递原文信息的表达方式。一般而言,辞典对译者所起的作用只是抛砖引玉,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价值正是体现在能从“石”里挖掘出“玉”来。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应尽量保持异国风味和异域情调,保持文风的适度“欧化”,使译作既体现原作的风貌,又不流露生硬牵强的痕迹。准确的译文并不一定要把一切事情都说得很明白,因为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其隐约之美和含蓄之味。文学翻译之美,更在于要留有适当的空间和空白,留待读者自己去品味,表述过白或过露的作品不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作。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内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体味,而无需译者替他们把字里行间的一切都译得很直白。翻译作品给读者留一定的空间或空白是翻译的应有之义,译者无需一切都替读者着想或者低估读者的阅读能力,因为这样做恰恰丧失了文学创作的某些特质。一般来说,文字是应该明确的,但内容需明确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原作来考虑,原文含糊其词的地方,译文也应该含糊其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准确和表达到位,也是文学翻译“虚”与“实”结合的具体表现。
译者应该充分认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这一点再强调也不算过分,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译者的工作态度。尽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但翻译作品对译入语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所起的催化作用以及对译入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文学译作在开阔视野、丰富语言表达方面的作用是本国文学创作难以替代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从另一角度来看,不负责任的翻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无法衡量的,或好或坏的这些方面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译者的诚信,首先体现在对读者的高度负责,对译文的一丝不苟”。严复曾以“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形容自己对翻译的态度,这种严谨的翻译态度、审慎的选择标准以及执著的敬业精神是译者必备的素养。自觉恪守译德应该是翻译工作者的首要职业道德,国际译联把2001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定为“翻译职业道德”,译德问题对于翻译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优秀的文学译本不断出现,但文学作品的整体翻译质量仍亟待提高。从英汉互译的角度来看,翻译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使我国从翻译数量大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质量强国。如今译作如林,但精彩的译本尚不多见,有些译本还在跟着原文走。文学翻译的“适度”一直是译者所追求的目标,但对这个“度”的把握着实不易。正如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那样,“出神入化”永远是文学翻译者追求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可以说,“神似”和“化境”是文学翻译者追求的最高境界。任何语言现象的存在都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变化着的语言有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文和英文词汇中完全一一对等的情况并不多见,这其中既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也有语言形式本身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制约。英语与汉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翻译时常会遇到难以用汉语表达的句子,采取加注释的办法是很必要的。采用脚注、尾注或文中夹注的办法,确实可以解决翻译中一些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对文化信息的输入特别有益。但过多地加注释会破坏译文的完整性,同时也会给读者带来不便,打断阅读思路,降低阅读兴趣。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要解释的内容融入到译文中去,使译文本身巧妙地传达原文的风格及含义,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
翻译的过程是求大同存小异的过程,在精通两种语言、谙熟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得“意”而忘“形”是文学译者的一种特定境界。意义上的“信”和艺术形象及趣味上的“信”,虽非鱼与熊掌,但要使二者兼而有之,着实是难上加难。不过,这种挑战性正是翻译的迷人之处,也是不断吸引一代又一代翻译者投身这项伟大事业的关键因素。
[1]Engle Paul,Haualing Nieh Engle.Writing from the World:II[M].Iowa City:International Books and th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85:2.
[2]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C]//《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22.
[3]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许均,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许钧.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7]Benjamin W.The Task of Translator[C]//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00:21-22.
[8]刘隆惠.谈谈文艺作品风格的翻译问题[C]//《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165.
[9]罗选民.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67-68.
[10]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
[责任编辑:高巍]
Literary Translation ----A Display of Correspondence and Isomorphism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YANG Cai-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Literature is an art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has languages as its core.Language communication highlight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As a special form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hare a feature of characteristic creation.The marriage of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namely literary translation,actually provides inherent vitality and developmental space for both disciplines.Conceptions and ideas of translators exert tremendous influence over the selection,interpret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 works to be translated,which in turn determines to a great extent the esthetic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reception.The inner isomorphism of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s more obviously displayed in the evaluation and review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serves as a practical venue to display the marriage and merge of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correspondence;isomorphism
G642
A
2095-106X(2013)02-0048-07
2013-05-04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985工程”研究品牌计划项目“英美文学经典汉译语篇研究”(2010Z010)
杨彩霞(1968-),女,河南太康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