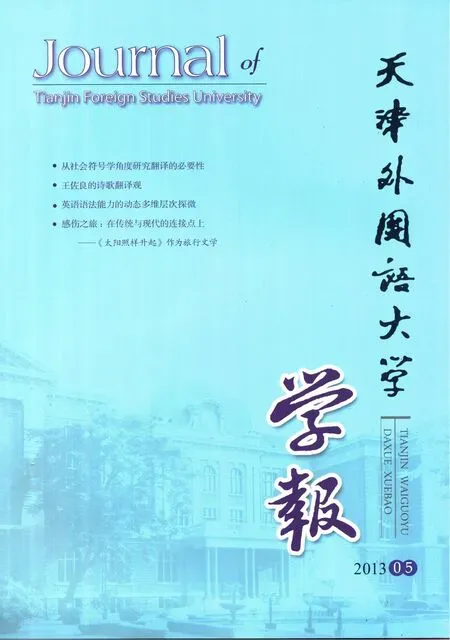王佐良的诗歌翻译观
吴文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一、引言
王佐良先生故去已经18年有余,时过境迁,王老的身影似乎已经在历史的烟尘中越走越远,逐渐模糊了。即使是在北外校园里,提及和了解他的老师和学生也已不多。很多年轻教师根本就没有见过王先生,只有耳闻罢了。唯有学校档案室里有关王先生的资料依然保留着。对于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来说,王先生却是中国20世纪翻译史上绕不过的人物,他的理论和译作仍然值得我们好好研读和学习。
二、王佐良与诗歌翻译
王佐良1916年出生于浙江上虞,1935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语系,1937年随校前往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习,1939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43年3-8月曾在昆明干海子美军炮兵训练大队担任秘书以及翻译。1946年6月,清华大学迁回北京,王佐良随之回京,在外文系任教至1947年7月。同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前往牛津大学,就读于茂登学院,师从威尔逊教授,1949年获得b.LITT学位,当年秋天回国。回国之后他首先在北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950年3月,由于国内院系调整,王佐良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去世。作为英语系的教授,他也曾担任过一些行政职务,如英语系主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1981-1984)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国文学》的主编。文革以后,王佐良先生重新焕发了学术热情。据统计,在1984-1994年的十年间,王先生就先后出版著作16部,效率惊人。最后一部著作是《中楼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那时的北外盛极一时,王先生和许国璋、吴景荣一起被称为中国的三大英语权威。
具体到文学翻译,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首批设立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点之时,王先生就成为我国第一位文学翻译博导。他在文学翻译方面既有实践又有理论,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他为人熟知的译作当属培根的《谈读书》,译文模拟培根的原文,用浅近的文言译出,在保留原文特色的基础上凸显了中文的雅致、整齐特色,脍炙人口,在翻译界被视为典范。他与外国友人合译的《雷雨》英译本也广受赞誉。1950-1951年期间,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英译工作。
作为英语文学教授,他用功最勤的还是英国诗歌方面。这与他本人的早年兴趣也密切相关。他从学生时代就写诗,诗作曾经被闻一多收入其主编的《现代诗抄》,也曾经发表过英文诗。他在北外英语系开设相关的文学课程,很多理论著作也都是围绕英国诗歌展开的,如《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1991)、《英诗的境界》(1991)、《英国诗史》(1993)等。涉及翻译和比较文学的著作有《风格和风格的背后》(1987)、《翻译:思考与试笔》(1989)、《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1991)、《论诗的翻译》(1992)、《语言之间的恩怨》(1998)、《文学间的契合》(2005)等。亲自翻译的诗歌选集有《英国诗文选译集》(1980)、《彭斯诗选》(1985)、《苏格兰诗选》(1986)等。
孙致礼(1996:106)曾经把王佐良的诗歌翻译归纳为以诗译诗,尽量求似,不拘细节,着眼全局。而陈亚明(2004:458)则把他的诗歌翻译观分类为:(1)选题;(2)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解诗歌;(3)追求本质的翻译;(4)文化意识;(5)诗人译诗;(6)坚信诗歌可译。这些都是对王佐良诗歌翻译很好的概括。也有个别学者,如王秉钦就曾经批评王佐良的翻译观点都是分散在一些散文、杂论中,总是零零散散,没有系统性。要更进一步了解王佐良的诗歌翻译观,从零散的评论中总结出一些要点,我们需要结合他的翻译实践重新审视一番。
三、王佐良的诗歌翻译观
1 崇尚直译
王佐良非常强调翻译的忠实性。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王佐良(1989:3)指出:“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翻译时要按照不同的文体确定不同的译法。传播信息的文字主要翻译意义,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注重形式,常需直译。诗歌的翻译又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要“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王佐良,1989:3)。王佐良的直译观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显露无遗。他不主张把外语中的意象简单地用中文熟语代替,认为译文应该保持新鲜,有一定的洋味。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我将永远爱你,亲爱的,
直到大海干枯水流尽。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
直到大海干枯水流尽,
太阳把岩石烧作灰尘。
他没有用中文里的“海枯石烂”,而是按照字面翻译,避免了中文读者一扫而过,而是让读者接近原文,在短暂的停顿思考中体会原作意旨。
2 以诗译诗
王佐良关于诗歌翻译的另一条准则是用诗歌的形式翻译诗歌,这也是从尽量直译的原则延伸而来。在王佐良看来,诗歌翻译应该再现原诗的精神,译者要以诗译诗。传译原文语言文字的形式非常困难,但不等于不能翻译,也不宜置形式与不顾(熊辉,2009:45)。在《英国诗文选译集》序言里王佐良(1980:2)特别强调:“此中的体会,主要一点是译诗须像诗。这就是说,要忠实传达原诗的内容、意境、情调;格律要大致如原诗(押韵的也押韵,自由诗也作自由诗),但又不必追求每行字数的一律;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保持其原有的新鲜或锐利,特别是形象要直译。”
谈到彭斯诗歌的翻译,王佐良解释了自己是如何翻译原诗格律的,即形式力求接近,诗行一样,韵脚一样,节奏一样。但他强调如果节奏都相同就会显得单调,不妨在合适的地方改变一下节奏,寻求变化。
3 译者角色
王佐良一贯主张诗人译诗,一个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很难把诗歌翻译好。在评论《戴望舒译诗集》时,王佐良(1992:19)声称“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只有写诗的人才能把握原诗的要素,才能深切体会译入语的诗风,才能根据译入语语言的变化调整译文语言,起到两种文化和文学相互交流的作用。诗人译诗能够在译诗的过程中对于诗的题材和艺术有新的体会,促进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译者也可以把自己写诗的经验用于译诗。这样两者相互启发,能提高译文质量和促进文学之间的取长补短。
在中译外和外译中的问题上,王佐良先生独到的见解也和一些国内学者截然不同。他认为,文学翻译的要求很高:“就译者个人说,他必须对于语言有足够的敏感,必须认识它的特点,层次,精华所在,弱点所在,它的过去与现在,有哪些事是它乐于做也善于做的,又有哪些是它不愿意做也做不好的,特别是它处于比较活跃、变动较多的时候更需要有清楚的认识。”(王佐良,1992:105)
鉴于此,王佐良认为,中国人从事中译外工作,尤其是文学翻译方面,除了少数久居国外的华裔之外,很难达到高要求。“这样的认识一般只有本族语者才有——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中国译者来说,他主要的工作只能是外译中。特别是在诗歌翻译方面,外文特好的人虽然也不妨偶尔一试将中国诗歌译成外文,但他的真正成就必然是在外译中。这是因为正是在诗歌中,一种语言处于最本质、最纯粹又最敏锐的状态,就连本族语者也须有修养、锻炼和敏感才能运用得好,更不必说只是在课堂上根据书本学外语的外国人了。”(同上)
他特别指出,即使是外译中,译者也应该选择那些语言风格上适合自己所长的作品来翻译,因为译者个人有风格和局限性,不可能什么都可以翻译。本族语也是博大精深的,并非一个人所能够完全掌握。王佐良对于翻译的作用、译者的所长所短都有清醒的认识。在当前中国有关部门大力提倡中译外的形势下,这种翻译思想尤其显得重要。提倡中译外未尝不可,但译文效果究竟如何,能不能被外国读者欣然接受,能不能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之前,还有很多调查研究工作要做。
4 重视文化
20世纪90年代初,奥地利女学者斯奈尔–霍恩比提出了文化转向的问题,重点是进行翻译研究时不应对文本进行脱离语境的研究,而应该把文本看作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她在评论弗米尔时说,翻译从根本上而言是跨文化传译,译者如果不能做到了解多种文化,至少也应做到了解两种文化,语言本质上是文化的一部分,研究翻译应该把文本和其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Snell-Hornby,1990:82)。王佐良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转向,但他早在1984年就写过《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两篇文章强调文化在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作用。
在王先生看来,把翻译和文化联系起来是翻译中的难题:“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对外国读者得加以解释。每个翻译者都有这类经验。”(王佐良,1989:34)虽然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同上:19)。要做一个合格的译者,必须精通或者说熟谙两种文化,本族文化不用说,外国文化需要下功夫去了解,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翻译的起点是语言,但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译者对两种文化的了解程度方面,王佐良(1989:18)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王佐良举了翻译史上大家耳熟能详的例证,即严复、林纾和鲁迅。严复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都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严复着力引介西方社会科学,就是为了拯救中国文化于水火。而他使用文言文翻译主要是投当时的士大夫之所好。“严复是一位苦心孤诣的译者,他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了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心智气候即文化情态,两相比照,才定出了他那一套独特译法。”(王佐良,1989:20)说到林纾,他虽然不懂外文,却在文学翻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使然。王佐良(1989:20)以林纾的译本之一《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1896年,上海已由一个小县城变成一个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商埠即国际都市,官僚、买办、商人、小市民们逐渐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兴趣,因此这本书以欧洲繁华都市巴黎为背景的言情小说一问世,就成了那时候的畅销书”。王佐良还提到了鲁迅的翻译。鲁迅是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他的翻译和创作和他当时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比较之后的思考密切相关。对于当时近乎蒙昧无知的国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翻译和创作都是为了唤醒大众,着眼于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中国的将来。
王先生凭借其翻译理论家的敏锐洞察力看到了译本传播效果背后的文化取舍。他指出,外国真正优秀的作品移植不过来,而二三流的作品却受到远超出本身价值所应得的欢迎,或是在本国不应该受到冷遇的作品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却能产生独特的光辉,而同一著作或作品在不同国家所引起的反响也常常不一样。在分析这两种现象时王佐良明确提出,虽然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这不仅仅是译者的眼光和能力造成的,真正的原因除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其他都是次要的。就拿拜伦和华兹华斯来说,拜伦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这和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即寻求革命和新生紧密相关。而华兹华斯的作品虽然在英国本土备受推崇,其表面淡泊、宁静而实则强烈的风格在中国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土壤,而且他的自然观在中国田园诗里也是屡见不鲜,不算奇特。
王佐良认为,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译文和译者,应该和历史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一想法的确和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比西方学者提出的更早。巴斯奈特1980年出版了《翻译研究》,然而直到2002年,在为该书第三版所作的前言当中才明确提出:“翻译不仅仅是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是文本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当中所有活动都由译者这个人物来完成。”(Bassnett,2004 :6)
以上简要介绍了王佐良的诗歌翻译观,他的翻译思想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重要的观点,比如译者要尊重读者,要了解文体学,要了解语境,要具有创造性,文学名著应该经常重译等,这些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梳理和挖掘。
四、研究王佐良翻译思想的意义
正如某些学者论述的那样,王佐良有关翻译的论文较为零散,没有大部头的系统论述,甚至个别地方还有漏洞。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王佐良翻译思想的意义。他的翻译思想承继了中国学术史散文随笔的传统,把精妙的思想撒播在篇篇美文中,仿佛零散的珍珠,虽不成系统,却也熠熠生辉。后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珍珠穿起来,梳理概括,使之成为前后贯通、一脉相承的体系。
初步研究证明,王佐良在相对较为闭塞的年代竟然也遵循着实践启迪理论、实践和理论相互生发的路径,不谋而合当中提出了和外国学者较为相近的理论观点,甚至在外国学者之前就提出了类似看法。上面提到的他对文化与翻译相互关系的重视就与外国学者斯奈尔–霍恩比的观点十分接近。他关于严复、林纾和鲁迅等的论述涉及到从译入语文化角度分析译作成功与否,谈到译入语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因素对译文接受的决定性影响,这些也与以色列当代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图里的译入语规范影响翻译策略的理论相互印证,如出一辙。他的核心翻译思想,即崇尚直译以及诗歌翻译须以诗译诗等,充分体现了尊重原作和源语文化的理念,这与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非常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佐良关于译文应该反映原作特色,传播源语文化,避开主流话语,使用生动活泼的新鲜词语等看法与当代翻译理论的主流十分契合。这表现出他非同一般的理论视野和预见性,也说明中国学者在翻译理论方面的敏锐性丝毫不比外国学者差。
研究王佐良以诗歌翻译观为代表的翻译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回顾中国翻译界的前辈大家,汲取精华,增强信心,从而实现在学术层面与世界学人对话的目的。中国不是没有翻译思想,只是欠缺整理和挖掘。立足本土文化,放眼全球,为世界翻译理论贡献中国元素,就是研究王佐良翻译思想的意义所在。
[1]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Snell-Hornby, M. Linguisi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A].In S. Bassnett & A.Lefevere(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C].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0.
[3]陈亚明.试论王佐良的诗歌译作与译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 (4): 455-458.
[4]孙致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49-1966[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
[5]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6]王佐良.论诗的翻译[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
[7]王佐良.英国诗文选译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0.
[8]熊辉.试论形式之维的诗歌误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 (2): 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