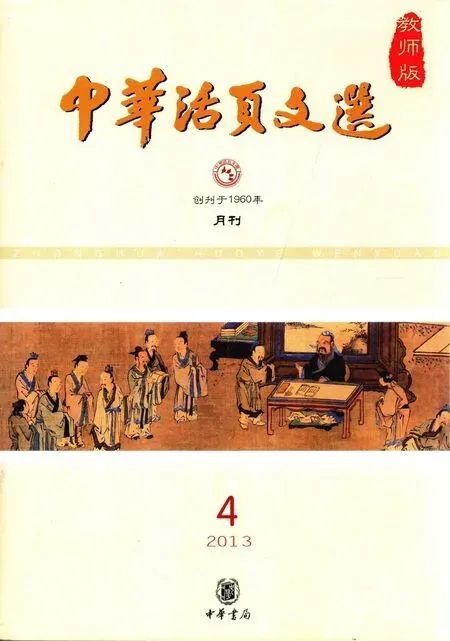构筑心灵的家园——浅论《桃花源记》的文化内涵
■ 刘久娥 曾 芬(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高级中学)
《桃花源记》作于晋亡之后,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该文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它是作者在经历了三仕三隐的人生之旅后,个人思想情结的一次升华与总结;是作者在实现了哲学归隐后告别田园、走向心灵归隐的一次尝试,是作者到达的最后一个人生驿站。
一
陶渊明一生或仕或隐,以至最终归隐的反反复复,构筑了陶渊明一生痛苦的旅程。经过汉末以来的政治、社会大动乱,儒学衰退,道家中兴,企慕隐逸之情在魏晋知识阶层已蔚然成风,远离尘嚣、逍遥自适的隐居生活成为一种人们理想的人生寄托。另外,晋朝末年,门阀士族统治占主导地位,等级制度非常森严,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对于出身没落仕宦家庭的陶渊明来说,道家的这种归隐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谓深远。然而事实上,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击壤自欢”的隐居道路,同时,他所受到的家庭影响和他那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也是不允许他一开始就选择独善其身的。
反映他早期的作品,如《杂诗》(忆我少壮时)、《拟古》(少时壮且厉)等都洋溢着他青少年时期的那种乐观分发的热情和幻想。少年壮志的陶渊明在年轻时不谙仕途,是曾经幻想做一番事业的。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理论中传统的积极入世思想在陶渊明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于是,约公元393年(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也就是陶渊明二十九岁那一年,他开始出来做了一个地方学官——州祭酒。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就是陶渊明初次入仕的全部过程。诗人的性情太刚直坦率,因而他受不了做小官的那种拘束和折磨,看不惯官场尔虞我诈、胡作非为的黑暗现象,所以他动摇了。在这个企慕隐逸之情蔚然成风的时代,陶渊明辞官归乡了,以至后来州里又召他去做主簿时,他也辞谢了,这一归隐在家就是六、七年。
可以这样说,陶渊明刚一开始并不一定是清风高洁的。作为一位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作为一位刚刚出仕不久的知识分子文人,他还是不会轻易放弃仕途的,他的身上肩负着光宗耀祖的责任,承担着兼济天下的任务。如《咏三良》(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乞食》(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所写。于是,当时局稍稍发生些变化,大约公元400年,陶渊明又一次到桓玄手下去做事。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陶渊明不久对桓玄的人格就完全失望了。桓玄只贪图个人的私利,这对于有远大抱负、性情刚直的陶渊明来说,他决不肯附为桓玄的心腹,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于是,在陶渊明的作品里出现了反映对出仕桓玄无限悔恨的“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他对自己所过的仰人鼻息的宦途生活,表现出了无限的感叹:“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现实的仕途艰辛又一次扑灭了陶渊明心目中“大济苍生”的愿望。这时,他无奈发出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感叹,表明了他不顾爵禄荣利的诱惑,决计辞官归田的愿望。大约公元401年春天,陶渊明遭逢母丧,就借此辞去官职。与此似乎相似的经历,他在刘裕幕下做过镇军参军,终因认清了统治者的面目,对现实的黑暗彻底失望后就由仕而隐,以致到后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彭泽令之后,就正式归隐了。
二
以上所述,是陶渊明一生数仕数隐的经过,是陶渊明儒家入世思想与道家出世思想相互斗争的经过。在那个黑暗的、门阀制度森严的年代,一位内心充满矛盾、徘徊、踟蹰于仕与隐之间不知何去何从的诗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寻找着生命的真谛,在那个险恶的世界里追求着自己的生活哲学,最终选择了归隐。
然而,陶渊明归田之后的生活并不是十分平静的。尽管他抱着安贫乐道、躬耕自资的理想,在归田之初曾经感到重返自然的欣慰,但是现实生活毕竟是残酷的。据陶渊明的自述,其托身之草庐“炎火屡焚如”,不止一次地遭遇火患。戊申年(公元408年)的一场大火,竟造成“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火灾之后,陶渊明的隐处片瓦不留,他不得不在船上栖身。其晚年生活则更加悲惨、贫困。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式的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带给他的绝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痛苦,更是一种超越物质之上的思想、精神的痛苦。作者始终无法摆脱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背景,隐居田园之后的生活也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好。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作者又一次产生了不满,转而追求心灵的满足。那么,陶渊明是通过何种途径来获得心灵的解脱的呢?
三
陶渊明的时代是老庄无为思想和儒家佛理糅合的玄学盛行的时代。自西晋短暂的统一后,从永嘉丧乱开始至东晋,社会处于动荡、分裂之中。这种动乱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浓厚的无常感和虚幻感,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两晋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又与老庄玄学思想相类似,一个讲“空”,一个讲“无”,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思想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更容易为陶渊明这样一位“释于精理”而又“学不称师,心好异书”且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隐逸之士所接受。就这样,当时流行的佛教性空般若学就以玄学清谈为契机进入中土。
佛教般若学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即“格义”与“六家”。“格义”就是用《老》《庄》等中国固有的名词解释佛教思想的一种方法,它认定世界万物存在的本体为“空”,为“无”。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般若经》)。它否定社会仁恒的真实性,人们所见所思维的一切对象(法相)均属虚妄。宇宙万物存在的真实本相都是空无所有,无所实存,又被称为“本无”“性空”。《道行般若经·本无品》:“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西晋,在竺法护译经中,便出现了以“空”“无”“空无”“本无”换用的情形,如《修行道地经·卷二》“察诸无及人,普见如空无”“了一切空,身如幻”。因此在文中,在以“本无”“性空”思想的性空般若学广泛传播的时代里,陶渊明受到性空佛教的影响则是极为可能的。在他归园后的诗《归园田居》中写到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则是性空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有论者指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思想出处就是《修行道地经·卷二》的“了一切空,身如幻”。另外,陶渊明的其他作品如《饮酒》《还旧居》中的“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等也是受性空般若学影响的诗句。
由此可见,当陶渊明挣扎于儒家思想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外来宗教思想——佛教就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位高洁的隐士。而且,当他无法摆脱选择道家归隐之后所带来的心灵苦难时,是这种外来的宗教给了他继续生存下来的勇气和力量。那么,陶渊明又是怎样在佛教影响下摆脱心灵苦难的呢?
四
陶渊明在晚年经历了人生似幻化的痛苦旅程,《桃花源记》在那个时代的产生,是其思想所到达的一种高度,也是一种理想与寄托。这与当时同性空般若一样流行的佛教净土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佛教史》记载:“元兴元年,在慧远倡导下,集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于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誓相提携,共登西方神界,史称此集结为‘白莲社’作为中国净土宗之始。”这里的“净土”通常指所谓“西方净土”,亦称“西方极乐”“极乐世界”“极乐净土”,它是净土宗所着力宣扬的一块毫无苦疾杂染、唯有法性之乐的“无上殊胜”的清净乐土。据佛经记载,此极乐净土位于“阎浮提”或“婆娑世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该佛本是国王,名法藏,因在世自在王如来处听佛法,决心向道,故弃主捐国,行作沙门,后于世自在王佛所发二十四愿,极乐净土,实际就是根据阿弥陀佛在因位时所发之宏愿虚构出来的一个宗教的幻境。有关“净土”的经典《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念佛三昧经》)等,早在汉末即有翻译,此后异译不断。可见有关西方净土的信仰流行很早、很广。但它能够上升到知识僧侣的信仰,并为士大夫上层奉行,则是从慧远开始的。慧远在当时影响很大,一些统治者、士大夫、隐士都与他有着密切的交往。慧远关于佛国净土的理论在《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得到明确阐述:“徒积怀远之兴,而乏困籍之资,以此永年,岂所以励其宿心哉?”这表明了慧远与刘遗民等人共同往生西方佛国的愿望。后来,刘遗民代表慧远等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共同立誓的《发愿文》中更明确表达了往生西方净土的思想。《释慧远传》中说:“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此其同志诸览,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济者也。”现世的苦难,使慧远及其崇拜者们悟解人生之无常,他们笃信佛教因果报应,他们惕惕勤勤,思愿期生净土,期待着死后转生佛国,过上美好的生活。慧远正是靠了“期往净土佛国”这一招牌,把这些崇拜者团结到了周围。由此可见,现实生活的苦难和黑暗激发了人们摆脱苦痛、向往美好世界的心愿,这种心愿是那一代受压抑的人们共同拥有的,陶渊明是其中的一位。
陶渊明当时与刘遗民、周续之并称为“浔阳三隐”,他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这种净土思想的启迪。史书上曾载陶与刘私交甚好,刘曾邀陶入社,但陶没有答应,但我们并不能以此来否定净土观对陶渊明的影响。陶的《和刘柴桑》这首是表明此事,同事也阐述了自己不入社的原因。“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去去百年外,声名同翳如。”这就是他当时的态度与思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鲜明地表现了陶不入社的原因。他虽然选择了隐居,接受了佛家“空”“无”的思想,但内心深处仍然无法摆脱儒家伦常、重友孝亲的观念,他因此而选择了与刘等同感而异归的道路。
陶渊明晚年写出的抗拒现世黑暗的桃花源,描绘了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好境界。在这块田园世界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人们生活幸福、怡然自乐,没有烦恼。以至“南阳刘子骥,闻之,欣然规往,未果”。表明这种没有痛苦与忧愁的社会,只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对来世幸福世界的一种企盼。
陶所描绘的这种理想世界,细细读之,与刘遗民等人所向往的净土佛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陶渊明归园之后,贫困交加,他无法摆脱精神与物质上的苦难,但同时又苦苦追求着摆脱苦难的途径。这种消释苦难的努力,就是在刘遗民等人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与刘等净土观念同感而又不同归的桃花源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桃花源思想是佛学净土思想在作者思想深处的变形与发展,是陶渊明在儒家伦常观念与重友孝亲观念束缚下,从心灵深处进行的一次反抗,是为了解脱现世痛苦而寄予的一种美好愿望。或许,正是有了这种希望,归园之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所带给作者的心理反差,才渐渐得以平衡,于是,陶渊明在归隐田园之后,心灵世界得到了一次升华与归隐。
如果说从入仕到归田,是作者不满现实、洁身自好所选择的哲学归隐,那么在几经风雨、感受到归园生活所无法摆脱的心灵痛苦之后所产生的心灵升华,则是超脱生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归隐,是一次心灵的归隐。《桃花源记》就是作者实现这一归隐的标志。
参考资料:
1.任继愈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3.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孙静《陶渊明的心灵世界与艺术天地》,大象出版社。
5.廖仲安、唐满先《陶渊明及其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6.王国璎《陶诗中的宦游之叹》,《文化遗产》1995年第6期。
7.丁永忠《〈归去来兮辞〉与〈归去来〉佛曲》,《文化遗产》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