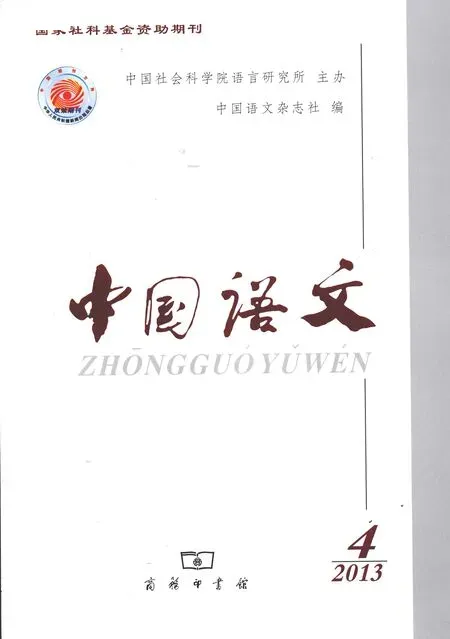对中国妇女参政问题的思考
——以后现代女权主义为视角
杨静
对中国妇女参政问题的思考
——以后现代女权主义为视角
杨静
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将“女人”等同于有生殖能力,女人基于性而有普遍性。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女人们普遍接受压迫和统一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论述。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对现代女权主义基于生理性别的对女性的划分给予了颠覆,认为生理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女人是被论述建构和后天模仿的结果。因此解构了对妇女参政问题的认识,如参政妇女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有参政的意识;除非有为妇女而参政的论述出现,否则参政妇女的结构位置不必然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位置。这些理论再次引发我们对推动妇女参政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为在政治领域中推动性别公正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后现代女权主义;妇女参政;为妇女而参政
妇女参政,顾名思义,就是妇女参与政治。一提到政治,我们常常会联想到一种传统的政治概念,即官方的机构、政府等政治行为。[1]13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着这个领域,该领域也是呈现性别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领域之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致力于在该领域中寻求和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并努力寻找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途径。
一、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基本主张
1.现代女权主义的基本主张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在于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给予两性一样的权利,因此力求法律的改革,在现有的权力关系中将女性扩充进去。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私有制、阶级压迫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因此,推翻私有制,妇女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和男性同样占有生产资料,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就可以改变。激进女权主义不同意以上说法,认为在所有的压迫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根本的压迫,先于制度和政治,主张建立一套女性不会受到贬抑的新社会秩序和妇女自己的政治文化,与男性以及社会的父权结构分离,彻底解决妇女被压迫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则认为,女性既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又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因此只有双方面都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
自由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都将妇女不平等的根源集中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制度和结构中进行分析,但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今的中国在法律制度上已经给了妇女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却在现实中仍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参政状况,为什么参政的女领导们并没有整体表现出妇女参政的意识等问题。
后现代女权主义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华,它不同于先前的女权主义理论集中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中寻找妇女受压迫的原因,而是着力于寻找压迫如何产生和建构的过程。
2.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基本主张
现代女权主义建立于父权制这个核心概念之上,而父权结构是以生物学的“性”为根基,它是父权社会结构主要物质意识形态的支持和保证。这种男女“性”差异的生物学理论,将女性和男性的本质与功能的社会定义归诸一个固定的、不会改变的自然秩序,独立于社会和文化因素之外,从而将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正常化、自然化。它将“女人”等同于有生殖能力,以本质主义的方式界定了女人,女人基于性而有普遍性。因而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女人们普遍接受压迫和统一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论述。
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克莉斯·维登(Chris Weedon)等人对现代女权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巴特勒认为不存在生理性别,只存在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并不是一个可以理解为不受文化约束的现实,“性”本身属于“性别”的范畴,是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范畴,是各种学科论述构成自然的事实,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2]对巴特勒来说,颠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是把身份概念从原因变成结果,也就是说,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体并不能决定他/她的身份,而是社会性别的论述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如果区分性别和社会性别就会落入生物决定论的圈套,将女人的范畴当成一个不变的主体,这个结果导致了与女权主义目标的背离。因此,巴特勒主张用“性别表演”取代性别与社会性别两分的概念,认为女人就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所谓“性”差异就是性别表演的结果。[3]
由于没有了性别的区分,妇女也就不具有固定的、不变的主体性,而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在论述中不断地被重新组成。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仍然将女性作为一个被描述的主体,认为有一个被压迫的女性主体客观地存在;而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想获得在历史文化中的主体身份,首先要使自身从被描述、被界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获得语言的权力。因此在后现代女权主义视野里,统一的女性不复存在,也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女权主义理论,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
后现代女权主义不仅认为女人是后天语言建构以及表演的结果,而且借用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权力观,认为女人不仅受到男人的压迫,而且自己也将男性压迫女性的论述加以内化和认同,进行自我管制、自我遵从。福柯认为,权力的压迫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4]350-351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大陆目前为什么在法律制度上规定的男女平等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为父权制度不再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制度,而是变成了看不见摸不着,隐藏在文化、观念、习俗中的一种“潜规则”,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存在于一套套的话语中,并通过语言实现对妇女主体的宰制。不仅男人接受这样的论述,甚至妇女自己也将其内化为行为准则,自己监视自己,不需要警察、监狱,只需要一个凝视,就完全地屈服。
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社会组织、社会意义、权利与个人意识的分析中的公因数是语言。[5]152-155语言不是反映了既存的社会现实,而是建构了我们的社会现实。后现代女权主义也正是从语言入手去解构现代的宏大理论。基于语言和书写的重要性,后现代女权主义鼓励妇女自己书写和发出声音,打破男性独霸的书写和话语世界、理性中心,建立自己的有别于男性的话语系统。
二、后现代女权主义视野下的妇女参政分析
1.对“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出质疑
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妇女争取政治权利平等的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妇女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然而在后现代女权主义强有力的解构下,男女平等的概念也被重新解读。
男女平等的概念中隐含着这样的一些事实,即男女平等是以男性价值规范为标准的,妇女要向这个规范看齐。妇女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仍然挣扎在不平等的“他者”的地位上,由于缺少自己的话语,追求平等也就成为拥护男性话语,这实际上强化了男性的价值和优势。就妇女参政来说,我们的参政标准是依据男性的成长规律制定的,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政策也有利于男性参政,尤其是处级以上的领导岗位选拔条件更是有利于男性;而请客、喝酒、唱歌等成为建立升迁关系网络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不利于仍以传统角色定位的妇女,妇女被选拔和推荐的机会就减少了很多。[6]198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追求了60多年的男女平等,到现在仍然没有撼动男性为中心的政治领域内男性霸权的局面。
用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男女平等”也是一套论述分析,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论述,如针对妇女参政出现的保护论、优胜劣汰论等。①1988年,面对妇女参政率出现低谷的局面,《中国妇女报》专门以“是优胜劣汰还是保证比例”为题开展了长达3个月的讨论。讨论中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规定妇女参政比例,因为女性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重负,几千年的局面造就了妇女参政能力缺乏,保证比例可以作为一项临时政策,为女性参政创造一定的条件;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规定比例的做法是政治的“恩赐”,不利于妇女公平竞争,保护上来的女性因为能力不足也很难发挥作用,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妇女参政素质的提高;另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保证比例和优胜劣汰不矛盾,规定比例有利于政治机构中妇女参政的最低比例保障,优胜劣汰的原则适用于最低比例之外妇女通过同男子竞争取得参政权利,两者可以同时实施,并逐步减少按比例保证的部分,向公平竞争过渡。选不选拔、培不培养女性领导干部,不同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论述找到不同的答案。妇女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主体性是变化和流动的。女人不仅是一种性别,而且和阶级、民族、职业、地域、年龄等交织在一起。不同的女性拥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诉求,因此当我们说男女平等时,指的是哪种女性和哪种男性平等?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参政意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妇女对妇女参政没有很大的兴趣,也无法形成一个有妇女群体意识推动的妇女参政运动。[7]
2.以生理性别本质化的“参政妇女”
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主体性是变化的、非本质的,而现实中我们看到对参政妇女的论述总是基于生物性而决定的一种不变的程式,已经假设了一个参政妇女的主体性真实地、客观地、僵硬地存在着,如,妇女的竞争意识不强,需要保护;妇女天生具有关怀特质,因此适合做副手。无论是在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在研究者或者官方的表达中,我们都得到一个刻板性的认识:或者强调参政的妇女仍然具有东方妇女的贤淑美德,能够相夫教子;或者将参政的妇女描述为不像女人,而是一个“女强人”,为事业而不顾家庭;或者猜疑参政的妇女是靠姿色上去的。这些对参政妇女“淑女症”、“假男症”、“恐夫症”的看法纯粹是基于生物性论述的结果。在这些论述的背后,其实都内含着对妇女基于生理性别的、本质性的角色定位,所以无论参政妇女怎样做,都在一种福柯所说的“全景敞式”的监视之下。
3.相互矛盾的话语同时作用在参政妇女身上,使参政妇女进退维谷
20世纪50—60年代,在“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做”的话语下,妇女们走出家门,和男人一起参加劳动和工作。因为国家没有倡导“女同志能做的事男同志也能做”,因此家务活仍旧是妇女的主要工作,从此职业女性就有了双重负担。7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无性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了80年代,国家建设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套“经济发展了,妇女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妇女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和“妇女素质低”的逻辑下,为经济发展牺牲妇女利益似乎成为理所当然,妇女下岗、参政率下降都成为这些逻辑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在政治领域中也引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原则,强调差额选举和竞争,结果却使妇女参政率从此低居不上。为了经济的发展,妇女作为“低素质的一群”,在改革的大潮中首先被改革。国家面临复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就动员妇女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国家要改革,企业要转制,就开始讨论“妇女回家”。当强调社会稳定,就宣传“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妇女在家庭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把维护家庭和谐的责任放在妇女身上,并将社会和谐的责任也转嫁到妇女的身上;当强调未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又宣传“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妇女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孩子素质的高低”,将妇女拉回到家中,把教育孩子这一社会问题的责任也暗自放到妇女身上。一方面倡导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却不以实实在在的措施推进妇女参政,今天的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相互矛盾、分裂的话语下,妇女们该何去何从呢?或者该做哪种女人呢?妇女总是被论述和演说,她们有自己的声音吗?我们看到,对妇女的压迫不仅成为一套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还被一套策略和制度安排所承载,深入妇女每天的生活中,通过媒体、周围的人以及妇女自己牢牢地监管着妇女。此时,福柯所说的“全景敞式”的凝视就是这样发挥着作用。
4.参政妇女不必然要“为妇女而参政”
既然参政妇女是一个被论述所建构的主体,因此实际上没有什么统一的“妇女”有参政的“诉求”。如果是这样,那么谁在推动参政?谁的需要?谁要参政?参政的妇女是否知道为什么参政?如果妇女们处在一种被推动参政的状态中,或者没有“为妇女而参政的意识”出现,那么仅仅提高妇女参政的比例就有点像瘸子走路,结果是参政的妇女并不能代表妇女的利益为妇女说话,她们在领导岗位上仍然依据男性的眼光和标准看待妇女同胞,歧视和排斥妇女,甚至自甘副职的位置。
很多妇女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或者某种不公平,即便在被压迫位置上的妇女也不必然会产生反压迫的意识。这里借用Laclau和Mouffe关于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s)和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的概念进行说明。结构位置①Laclau和Mouffe并没有给结构位置一个详细的定义,而是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结构位置。她们以阶级为例,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生产工具的人将可能成为工人,也就是说,由于受制于那些先于他个人意志的力量,个人被结构性地置于社会阶层之中,这些社会阶层就是结构位置。所以,个人并没有完全的选择,他们经常感到自己总是已经被放置在某种结构情境之中。是指由于受制于那些先于个人意志的力量,个人被结构性地置于社会阶层之中,这些社会阶层就是结构位置。结构位置形塑了个人的生活选择,它们把个人置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脉络里,而这个权力关系则形塑了物质资源的分配。个人只有通过政治论述才能体验到自己如何被放进社会结构里。个人对结构位置里的生活方式的回应,不仅起因于结构位置的形塑,更是因为其经历结构位置的这个主体位置。主体位置是由论述和诠释结构位置具有何种意义而来。[8]120女领导干部是一个被放置于社会阶层的结构位置,这个结构位置并不必然产生为妇女参政和解放的主体位置,只有通过一定的政治论述才可以从结构位置向主体位置转换。具体地说,现代社会没有出现一套让女领导干部“为妇女而参政”的论述,因此女领导干部无法自动地“为妇女而参政”。不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妇女参政运动只是成为妇联组织在推动的事情,而不是妇女们自己的事情。
三、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局限性和突破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后现代女权主义也不例外。当我们面对中国妇女参政历程中正在经历性别歧视这一事实的时候,后现代女权主义既给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当代妇女运动带来了诸多的困扰,对它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如“虚无”、“相对主义”等。就像哈索可(Nancy Hartsock)表达的愤怒:“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力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性、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了。”[9]103后现代女权主义颠覆性的论述使得妇女们在为自己解放的斗争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没有了不变的主体性,也就没有了统一的政治目标。如果什么都是语言论述,那么“强奸”是语言论述还是事实?如果一味坚持话语就是权利的主张,那么就会丧失面对真实的暴力时进行斗争的武器。如果一味追求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最终导致个人主义政治,那么还有女权主义政治吗?过分关注语言,会不会陷在文字游戏的泥坑里呢?过分关注身体,会不会成为自娱自乐和自怜自悯呢?女权主义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如同踩着钢丝走迷宫,里面布满了陷阱和危机。女权主义的主张同时也变成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之间相互批判的理论根据,彼此的论述除了一步步更深刻地揭示女性地位和权力斗争外,同时也成了一种拉力阻碍女性形成统一的战斗力。
如何利用后现代女权主义充满力量的一面而避免其局限性呢?澳大利亚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其与现代的批判理论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借用现代批判理论对现实进行批判,唤醒民众的意识,对意识形态霸权对人的统治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同时也借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的主体性、身份和权力的分析,对当代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实践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宏大理论和权力的一种颠覆和批判,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现代理论。后现代女权主义所提出的主张和思考让我们在主张妇女权利和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上更加注重平等,避免了一方面主张妇女解放,却导致另一方面的压迫和不平等。男女应该平等,但不是参照某一群体的标准的平等,而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两性的和谐平等。女权主义本身就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批判,它和批判理论有着相同的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关心,只是更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中的性别公正。后结构主义也提醒我们,在谈性别视角的同时不能缺失民族、国家、阶级等视角。此外,不同的妇女受到的压迫不同,当我们谈到“妇女”的时候,要注意到妇女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要打着解放妇女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对一些妇女造成压迫。
笔者认为,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权制和男权中心的社会,尽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实施了60多年的男女平等政策,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性别歧视反而以更加恶劣的形式存在着,父权制、性别歧视文化与当今商品经济愉快地联姻,在国家的机制运作中持续地起着作用。妇女参政的比例不仅没有随着国家的最低比例制规定的实施而得到改善,更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创的妇女参政局面。我们不能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熟视无睹,仍需要长期的时间、需要正义的力量、需要团结更多的妇女,去争取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包括生命权和参政权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
[1]Margaret L.Anderdsen.Thinking about Women: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x and Gender[M].Boston:Allyn and Bacon,2003.
[2]何佩群.朱迪斯·巴特勒后现代女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初探[J].学术月刊,1999,(6).
[3]张小虹.性别越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
[4]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
[5]克莉斯·维登.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M].白晓红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6]杨静.政治理想与现实冲突——女领导干部生命故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王金玲.后现代主义:中国大陆女权主义面临挑战和颠覆[J].浙江学刊,2001,(1).
[8]周嘉辰.女人与政治[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9]李银河.女权主义[M].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04.
责任编辑:董力婕
Chinese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a Postmodern Feminist Perspective
YANG Jing
The theory of postmodern feminism subverts the division of women by modern feminism based on physiological gender and asserts that physiological gender is also a kind of social construction,and that woma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and acquired imitation.It thus deconstructs the theory o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such as women in politics demonstrate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and that not all women ha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wareness.Unless there is a discourse o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structural position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hould not be necessarily shown as its subject position.All these thoughts again invite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issue of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At the same time,they can be used a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postmodern feminism;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for women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2.011
:2013-01-30
C913.68
:A
:1007-3698(2013)02-0067-05
杨 静,女,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视角的妇女问题、妇女社会工作。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