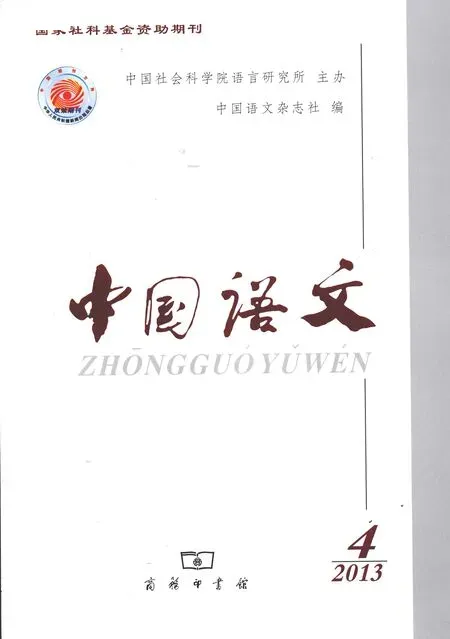美国批判的女性主义及其当代演进
周穗明
美国批判的女性主义及其当代演进
周穗明
美国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论题:多元民主、权力理论和社会性别。多元民主是批判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权力理论是批判的女性主义中的后现代主义合理因素;社会性别范畴构成了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崭新理论视角和主要演进线索。批判的女性主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直面理性与权力的内在矛盾。
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多元民主;权力;社会性别
西方批判的女性主义,即延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女性主义,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60—70年代西方新左派运动高潮中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简称SWF)的式微,批判的女性主义思潮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活跃在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大本营德国和美国。作为对第二波女性主义成败得失反思的产物,美国批判的女性主义根据1980年以后的时代变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思考和命题,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一道别样景观。因此,在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最为发达的美国,批判的女性主义与80年代以后风靡一时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并驾齐驱,引领了近30年来美国女性主义理论思潮的发展。
严格地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学术脉络的传人,当代美国的批判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是出身于西方激进运动兴盛年代的“1968年人”。这一理论思潮的几位领军人物马里恩·艾利斯·杨(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1950—)、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1947—)被誉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三位最杰出的和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家”。①参见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艾米·埃伦(Amy Allen)在2012年11月广州举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研讨会”上的报告:《权力、正义与世界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近期工作概览》(“Power,Justice,and Cosmopolitanism:An Overview of Recent Work in Feminist Critical Theory”)。她们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主张均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于西方1968年运动落潮之后。她们把后现代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创造和发展了过去3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艾利斯·杨奠立了批判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是该理论的创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本哈比汲取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差异的敏感性,同时坚持批判理论的规范诉求,是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中最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正统观点的理论家;弗雷泽突出艾利斯·杨以来对当代非正义的政治经济批判维度,强化了该理论的后社会主义激进批判方向,提出了一种后女权主义理论。
美国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论题:多元民主、权力理论和社会性别。本文通过多元民主概念剖析批判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通过权力理论解释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合理因素;通过社会性别范畴强调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崭新理论视角和主要演进线索。最后,分析了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当前问题和未来走向。
首先,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形成,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元文化主义倡导的理论与实践息息相关,与当代西方多元民主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根源出自于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强大影响。正是福柯引领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推动了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发展,构成了批判女性主义形成的重要理论动力和方法论基础。
作为著名的多元民主政治理论家,杨在其名著《正义与差异政治学》中,挑战了当代欧美语境中主流的正义理论。她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不正义来分析正义,颠覆了主流正义理论对正义的各种诠释,从而为当代民主理论奉献了新的思想资源。杨运用支配(Domination)和压迫(Oppression)这两个概念反思不正义,批评平等自由主义的分配理念不足以解释不正义和保证正义的实现,指出正义必须是消除支配结构,从而将正义上升到“自我决定”的民主制度的层面。由此,杨批评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理论忽视了商谈背景中的权力关系,故而使处境优越者的声音压倒了被压迫者的声音。[1]她提出了一种交往式的民主理论,从多元主体的交流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对话,要求为被压迫的和被边缘化的族群的交往模式留出空间。①参见Noelle McAfee.Feminist Political Philosophy,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 feminism-political/.Young.Inclusion and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2。这一理论使民主的包容性对话成为可能,也使她得以从交叉的多元文化权力的角度来重构女性主义。
本哈比与杨都力求展示一种更加开放的、包容的、甚至有些极端的平等主义的民主理论。本哈比坚定地从多元文化主义立场出发,倡导各种文化之间的讨论,支持社会变革。她不相信文化的纯洁度,批评了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构成其道德—政治普遍主义的规范内核的理想化的状态,发展出一种批判理论的更加语境化的、更加具体的版本,即交往合理性的版本。她对交往理性的重新阐释,为思考当代多元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规范方式,也为她发展出一种对性别差异敏感的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版本奠定了基础。弗雷泽批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重视文化承认而轻视经济再分配,反对把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重新解释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亚种。她构建出一个以参与均等的原则(Principle of Parity of Participation)为规范基础的三维正义结构,要求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参与均等,对现存的政治结构进行民主化改造。她批判三种理论化的非正义:经济上的分配不公、文化上的错误承认和政治上的错误代表权,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阐释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的新进展。
其次,批判的女性主义深刻的多元民主之基,是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而奠立的。引进后现代主义的、尤其是福柯的权力理论,是批判的女性主义的一项创举。众所周知,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中,权力批判与理性批判是其现代性批判的核心理念。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代理论家基本上都认为,权力是个坏东西,凸显了理性乃至现代性的根本弊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野蛮暴虐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根源,归结为启蒙理性本身,视之为理性化过程肆意发展的产物。哈贝马斯将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力量建立在对启蒙理性和支配清晰划界的基础上,极力把交往理性与权力关系的影响分割开来,充分显现出权力概念在其理论中的负面性。第三代批判理论家霍耐特把由理性推动的承认看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人类学特征,界定为一个社会中歧视和支配关系的对立面,从而展现权力与承认之间的显著差异。他同样把权力看做是人类社会生活基本形式的变形或者扭曲。三代批判理论家的权力观都没有超出传统的二元框架的、压迫性的政治概念。批判的女性主义竭力突破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固有的传统缺陷,吸收后现代主义权力观,极具批判性的正能量。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后,“权力”不断溢出其政治涵义,日益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哲学文化涵义的概念。经过尼采、弗洛伊德、阿伦特和福柯等人的阐释,“权力”的所指从主体到客体,从单向到多元,从政治到文化,从具体现象发展上升为普遍范畴。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发展出一个更具有广阔批判前景的权力理念。福柯完全颠覆了历史上的权力观。他认为,在宇宙自然和人类历史这出大戏中,权力是基础动因,是支撑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它不仅具有压制性,更具有生产性。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和场,它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弥散的,人只是权力网络中微小的个体,无论作为权力施予者还是权力受施者,无不被权力所穿透。权力意志深藏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它使我们迷恋权力,对那些支配、剥削我们的东西,反而充满了欲望。语言、知识、真理都与权力密切相关,“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肌体中去,构成社会肌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2]94
杨是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中正面接受后现代主义,特别是福柯的权力理念的佼佼者。权力是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正义与差异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杨从福柯式的权力概念出发,对正义的分配范式进行了毁灭性批判,指责这一范式导致了在分配一词之下去思考权力。杨批评这种范式仅仅把权力与能够占有和公平分配多少相联系,不去理解权力的关系属性,导致把权力简单解释为实施权力者与被施予权力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漠视“支配的结构性现象”。这种分配范式还将权力理解为一种关于权力如何被分配的相对固定的样式,而不理解福柯所指出的,“权力仅仅存在于行动之中”。①参见 Michel Foucault.Two lectures.In 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essays 1972—1977,ed Colin Gordon. New York:Pantheon,1980,p.89。最后,这种分配范式把支配理解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把争取多数人权力的权力再分配看作是对权力的矫正。[3]31-33
杨摆脱分配范式的权力概念具有深刻涵义。她从思考正义的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指责导致不正义的劣质生活的根源——由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不良价值。在她看来,决定正义与美好人生的有两种核心价值,这两种价值就是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3]37支配和压迫被她界定为这两种价值观中某一个的缺席。压迫是对自我发展的制度性的或结构性的制约,而支配就是对自我决定的制度性或结构性的制约。杨认为需要清晰区分这两个概念,因为“压迫通常包括或蕴含着支配”,“然而不是每个受到支配的人都是被压迫的”。[3]38压迫涉及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作为在文化上被蔑视的身份认同群体的成员遭受的痛苦经历,而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庞大的权力支配的大网却能支配和影响每一个人。杨认为,压迫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压迫不仅只是指单一的专制性权力,而且“指的是一些群体所遭受的广大而深重的不正义”,“是日常生活的正常进程中所产生的结果”。[3]41杨揭示了压迫在日常生活各层面的五个面孔,即:经济剥削、社会边缘化、无权、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毛细血管状的现代权力通过社会身体的全部来传播,同时具有生产性。
杨的权力理论的优点是它具有价值观的维度。这一理论不仅有着福柯的权力理论揭秘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基因密码和广泛程度的深刻性,也保持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主义的解放兴趣和规范诉求;既具有前者对多样性和差异的高度敏感,又持有后者对人文理性的坚定维护。杨把福柯的权力理论与规范的批判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权力视野,从而为全球化时代的批判的女性主义锻造了方法论武器。
再次,美国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在反思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困境和批判地借鉴以权力为核心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哈比批评了传统批判理论的性别无能,为批判的女性主义开路;杨最终发展出“社会性别”和“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为批判的女性主义奠基;弗雷泽揭露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共谋”,为批判的女性主义制定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本哈比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阶段,即遭遇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强劲挑战。她在与巴特勒的论战中,一方面汲取其多元权力观,另一方面在批评传统批判理论的性别盲点的同时,小心地维护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规范底线。本哈比努力在哈贝马斯式的批判理论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提出了一种结合了权力和批判的新的女性主义。
本哈比在接受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差异多元权力论的同时,批判它对女性概念的解构,揭示其彻底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涵义。在80年代以前,美欧女性主义理论总体上处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女性主义几乎都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女性的解放和平等。自80年代始,美欧女性主义理论在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的影响下,系统地批判了以往女性主义的性别本质主义,同时深陷身份政治学的论争之中。巴特勒的名言是:性别不是天生的,是被文化塑造的。经年累月不断重复的性别叙述使世间男女学会了自己应有的性别演示(Performance)。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固化的妇女概念,挑战传统的性别划分本身,认为对性别的强调本身就是权力和等级的产物,要求揭示定义了妇女概念的权力/真理/知识的游戏。针对风靡80年代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浪潮,本哈比接受其对历史进步的宏大元叙事和超验启蒙理性观念的批评,欣赏其内在的多元权力论和结构权力论,但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主体解构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她认为后现代主义关于“人类之死”的弱版本没什么问题,主体总是定位于多样的社会和语言实践之中;但是她反对其强版本,它把主体消解到仅仅是语言/话语的位置,因此这一论题与“女性主义的各种目标不相容”。[4]20后现代女性主义颠覆了人的概念、主体的概念,也颠覆了女性的概念。本哈比批评巴特勒的性别演示说仅仅把性别看成是表述的总和,取消了女性性别主体在排演时就已经被剥夺了的发言权,从而抹杀了关于社会性别的斗争的真义。[4]21在总体上,本哈比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盟、把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主体的彻底解构,看做是女性主义思想中更大范围地“放弃乌托邦理想”的一种表现。[4]29-30
同时,本哈比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第三代理论家的规范性视角中隐藏的现代性的女性主义理念,试图在改造和修正现代性的理性观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更具有历史性的自我意识的、交互性的、开放的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版本。对现代性及其核心理念——自主性自由的承诺,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键性特征。哈贝马斯一贯以他对现代性纲领的规范内容的顽强捍卫而著称。霍耐特也是从自主性自由的观念中推断出其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内容。他们都把自主性自由的观念视为欧洲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规范性成就,认为个人自由“构成了所有正义概念的规范性基础”。[5]38而关于自主性自由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关于历史进步的故事。因此,传统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是自主性自由这一独特的规范视角的表达,把女性主义描述为来自现代性的规范观点的发展结果,寻求这一理念在女性身上的充分实现,把女性的解放和权利看做是自主性自由的人权的延伸。本哈比批评哈贝马斯等人基于现代性的宏观批判理论解释不了女性主义的出现,缺乏性别视角。她的目的是“使道德推理的主体‘具有性别’”,“使道德论断在性别方面是敏感的,并且认识到性别的差别”。[6]8从而,“把理性和道德自我更坚决地定位在性别和共同体的语境之内”。[6]8
事实上,那种基于西方现代性的自主性自由和历史进步的女性主义,受到后现代取向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质疑。本哈比沿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民主制语境中的政治平等理论的方向,扩展了她的规范性反思,倡导一种交互的普遍主义,即普遍的尊重和平等主义的互换性原则。她通过修正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关于自主性自由、历史进步和女性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回应了后殖民的女性主义的批评。对于自主性自由的观念,本哈比从她对文化的复杂理解出发,反对欧洲现代性的这一同质性设想。她认为,“所有文化的极端的混杂性和多音性;文化……是具有多重声音的、多元层面的、去中心性的、断裂的有关行动和意义的体制。”[7]25-26她用承认西方文化的非同质性的方式认同了反帝国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观点。然而,她同时指出,新女性主义的反身性、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能力,是自主性自由的标志性特征,是从现代化的进程产生出来的。对于历史进步的观念,本哈比通过对“以技术和经济进步之名,而在这个世纪所犯下的种种罪恶的认识”,也持有后现代主义者的“对进步理想的幻灭感觉”。①参见Benhabib.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An Uneasy Alliance,in Benhabib et al,Feminist Contentions:A Philosophical Exchange.New York:Routledge,1995,p.X.。然而,她同时认为,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关于历史进步的“乌托邦的思想乃是一种实践的—道德的命令”。②同上。产生于现代性中的自主性自由的观念,仍构成了超越前现代的生活形式的一种进步。对于传统女性主义,本哈比也支持其观念,认为女性主义和其他解放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一样,是为实现现代性核心理想——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奋斗。然而,她把批判一切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文化群体的实践,视为她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责任,反对任何以所谓“文化的辩护”为借口的、对妇女的不平等的歧视和压迫。同时,让这种批评始终保持情境上的敏感性,对“他者”权力的尊重度和对质疑自身的规范性承诺的开放态度。总之,本哈比对后现代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规范理想的谨慎结合,为批判的女性主义提供了成长的新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本哈比是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和清道夫。
艾利斯·杨是批判的女性主义真正的理论奠基人。杨的理论在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中女性主义理论与批判的性别分析尤为杰出。作为一位著名的民主理论家,杨基于她对多元权力和正义的深刻理解,在建立权力关系的理论中研究社会建构,具体思考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社会性别。由此,她确定了集规范性视角和权力视角为一体的批判的女性主义的理论方位。
社会性别概念,是杨对批判的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也是这一理论的最伟大的理论成果。所谓社会性别,是指性别不仅是天然的,也不仅是文化生成的,而是一个与生物差异、文化差异相对的关于社会结构差异的概念。从这一角度看,妇女构成一个社会群体,这一群体不以共有性质和共同身份为特征,而以与基本社会结构有关的相同地位为特征。①参见I.M.Young.Gender as Seriality:Thinking about Women as a Social Collective.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3,1994,pp.713-738;I.M.Young.Lived Bodies vs.Gender:Reflection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ubjectivity.In I.M. Young.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2-26。批判不公正的性别关系,是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所在。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要从理论上阐述主体性、身份或女性经验,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社会批判,即揭露权力和压迫的关系。在理论上,杨从主体和身份的思考出发,把社会性别理解为“有生命的身体”(Iived Body)。她说:“有生命的身体是一个生理的身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行为、经验的统一理念;它是在场的身体。”②参见I.M.Young.Lived Bodies vs.Gender:Reflection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ubjectivity.In I.M.Young.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6。“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既包括身体的生物存在、文化存在,更突出了它的完整的社会结构存在。“有生命的身体”概念表明,人的主体性是被社会文化事实和他者的行为与期盼所左右的。个体被劳动与生产、权力与臣服、欲望和性行为、声望和地位的关系即社会结构所定位。每个人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些无法选择的事实关系中行动。这些是个人不能选择的。女人作为一个群体,是不同结构性因素的松散整合的产物。杨提议,我们可以将“妇女”的概念解释为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中物质与社会主体结构关系的标签。从实践角度,杨提出,性别被理解为在历史上和社会上特殊制度和过程中有生命的身体彼此之间社会地位的特殊形式,这些制度和过程对环境具有物质效果,人在此环境中行动,并在人与人之间再生产权力与特权关系。③参见I.M.Young.Lived Bodies vs.Gender:Reflection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ubjectivity.In I.M.Young.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2。
社会性别概念的确立将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与传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社会性别概念表明,性别不能简单视为生物的自然存在。杨把社会性别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它涵盖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实践、制度和习俗,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传统女性主义强调男女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构成不同的性别。它对男女的生物性持有性别本质主义的见解,即认为女性是阴柔的,是与某些特定气质、工作、欲望相联系;而男性是阳刚的,是与另一种气质、工作等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关于性别差异的本质化观点受到了各个流派的女性主义学者的全面批判,指责它毫无保留地认同异性恋规范,伪造不同种族、民族、阶级的女性的“共同经验”,其观点背后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视角。
其次,社会性别概念表明,性别并不仅意味着文化身份,而是在制度条件、个体生活可能性及其实现之间的特殊社会结构连接。杨把文化差异和结构差异区分开来。④参见I.M.Young.Inclusion and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I.M.Young.Equality of Whom?Social Groups and Judgements of Injustice.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9,1,2001,pp.1-18。她将身份理解为涉及个体的排他性概念,坚持将性别归结为社会结构而不是归结为个体身份。她认为,许多文化冲突根本不是文化上的冲突,而是出于争夺土地、资源的,或者出于参与劳动市场与决策程序的政治斗争。并非所有种族的、文化的差异都形成结构不平等。而结构差异则是指不平等的更大的框架。“结构上的社会群体这样一些人,他们同样被置于互动的和制度上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与生活前景。”[8]97杨批评多元文化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体性的文化差异,抹杀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特征。比如,由于传统的女权运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斗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女两性强弱、高下、尊卑有别的观念,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转而承认自身的女性特质,强调差异,强调女性美、女性性感和吸引力,制造了一种新的身份神话。这种话语建构不仅没有促进性别平等,相反被全球消费主义所利用,根本无力挑战现存的性别权力体系结构。对差异的迷恋、对“多样化”的拥护表面上体现了宽容,但是决定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多元话语的力量仍然是社会结构中无所不在的权力。这类“差异女权主义”的追求从根本上仍然是以男权中心主义为理论前提和参照系的。
最后,社会性别概念表明,不适宜彻底解构性别边界,女性仍然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社会群体存在。对性别的结构化理解开辟了女性解放在未来的更大空间。解构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包括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都彻底质疑性别区分,不再执著于任何固定的身份认同,要求根本颠覆女性概念。后现代取向的理论用权力理论对妇女的解构意味着把女性概念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性别分野是权力和等级的产物,从而直接导致了社会性别概念的形成。然而解构女性概念本身终成当代的一种陈词滥调。杨仍然相信,决定性别关系的基础社会结构是规范异性恋的结构,该结构定义了身体的含义,通过强调家庭内分工和“公”、“私”劳动之间的区别去组织劳动的性别分工,是一种性别的权力体系结构。①参见I.M.Young.Gender as Seriality:Thinking about Women as a Social Collective.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3,1994;I.M.Young.Lived Bodies vs.Gender:Reflection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Subjectivity.In I.M.Young.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尽管这些结构的规范异性恋的形式不变,但其内容是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杨的社会性别概念明显包括了有生命的、有性别的女性身体,同时,突出地强调妇女是一个社会结构群体,而社会结构形成了性别的服从与压迫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杨的社会性别分析不同于巴特勒,而更接近于马克思。
从社会性别理论出发,杨通过进一步分析性别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三条基本轴线——性别分工、规范异性恋和社会性别等级权利,运用其支配与压迫的范畴系统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性别支配与压迫结构的这一系统解释,也推进了女性主义思潮与对结构非正义的更广泛的批判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女性主义视角下表述正义社会的起点。
南希·弗雷泽站在杨的肩膀上,更积极地推动了批判理论面向后现代主义的变革,将批判的女性主义的研究推向全球层面。
首先,弗雷泽反思第二波女性主义(SWF)的历史成就和理论困境,揭露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共谋”。弗雷泽批判地总结了第二波女性主义40年发展史,评价了该运动的整体轨迹和历史意义。她说明,SWF起源于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运动内部,是对战后时期国家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深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激进挑战。SWF最大的贡献,是它在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中,提供了分析性别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清晰的维度,支持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改造的政治方案。SWF打造了一场划时代的文化革命,但是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尚未转变为结构上、制度上的转变。相反,第二波女性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演进过程走向了悲剧性的命运,被弗雷泽称为“理性的狡计”:它的某些理想和后福特主义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的要求之间产生了令人困惑的趋同性,无意中为“新资本主义精神”补充了一个关键因素。新自由主义调节理论家们用1968年革命的口气,提出了一种新资本主义,其中严格的组织层级将让位于水平化的团队和灵活的网络,因此将解放个人的创造力。1968年充满解放的精神——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自我塑造的个人——被转化为硅谷和谷歌气质的“新资本主义精神”;沃尔玛、小额贷款等“灵活性”、“小型化”生产方式使女性大量涌入了全球的劳动市场,妇女解放的梦想被利用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引擎。由第二波女性主义启动的那些文化变化,已服务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改造合法化。这一后果直接与女性主义关于正义社会的想象背道而驰。在新资本主义剥削的环境需要加强对政治经济的关注时,女性主义者恰好在这一瞬间将文化批判绝对化,不关注再分配而关注承认。这样,新自由主义利用了SWF,最终导致放弃女性主义的理想。它把向一种资本主义新形式——后福特主义的、跨国的、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转型合法化了。
其次,弗雷泽汲取后现代的权力理论,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批判立场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弗雷泽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介入本哈比与巴特勒关于现代性的著名论战。她当时的努力方向与本哈比并行,致力于将批判理论的规范性与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观相结合。但是,在这一结合中,弗雷泽表现得比本哈比更激进,要求更多地吸收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权力理论的积极因素。在这一批判中,她一方面批评福柯,认为其福柯为分析微观实践的权力理论只是一种丰富又有益的经验解释,但“在规范的意义上是含混不清的”,缺乏“把权力的可接受的形式与不可接受的形式区分开来的规范标准”[9]31、33,没有能够阐明一种合理的、新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概念;①参见Fraser.Unruly Practices:Power,Discourse,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chapters 2 and 3。另一方面,她支持了后现代女权主义关于主体批判性的核心思想。巴特勒在回应本哈比对其彻底解构了女性权力主体的指责中,提出了后结构主义对权力主体的建构性的深刻理解。②参见Seyla Benhabib et al.Feminist Contentions:A Philosophical Exchange.New York:Routledge,1995,chapter 1;and Benhabib,Situating the Self,p.46。弗雷泽虽然尊重本哈比观点在主体问题上对理性底线的坚持,但是她坚定地重申并确认了巴特勒的新论点:“原则上不能排除这样的观点,就是主体既是文化上被建构的,又是有能力进行批判的。”[6]67在弗雷泽看来,女性主义者需要“一种新的对主体的概念化,把巴特勒对建构的后结构主义的重视与本哈比对批判的批评性—理论性的强调整合起来”。[6]69
弗雷泽的激进权力观导致了她对激进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强烈支持。她指出,为了真正成为批判的批判理论,必须能够阐明那个年代,即女性主义、同性恋、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绝对重点的年代的那些斗争和希望。③参见南希.弗雷泽:《什么是批判理论的批判?哈贝马斯与性别的例子》,载于《反常规的实践:当代社会理论中的权力、话语和性别》(“Unruly Practices:Power,Discourse,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明尼阿波利斯,M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后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以及本土的女性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女性主义不是西方的产物,指责西方传统的女性主义把其他事物或其他群体指定为非现代或前现代的,是一种权力者的姿态。[10]xix借重于其权力理论,弗雷泽与杨、本哈比不约而同地讨论了后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性,通过对后殖民视角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更激进反思,倡导一种去权的、反帝国主义的批判的女性主义,基于此重构当代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宏观战略。
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和当前政治重组,可能标志着从新自由主义转向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起点,具有复兴女性主义解放承诺的前景。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战略应聚焦在四个中心点上:其一,这一远离新自由主义的可能转变,提供了恢复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解放承诺的机会。女性主义者应当反对和超越经济主义,用一个整合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三个维度的正义陈述,把女性主义批判重新连接到资本主义批判。其二,向后—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可能转变,提供了打破我们的家庭收入批判和弹性资本主义之间的伪造联系环节的机会。女性主义者必须重申男性中心主义批判,将受薪劳动去中心化,并且重新估价大多由妇女承担的、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非商品化活动,使家务劳动成为每个人的美好生活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提供了打破我们的精英主义批判和市场化之间的伪造的联系环节的机会。女性主义者现在必须重申对参与民主的支持,坚持在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反精英主义,为了正义的利益用政治去驯服市场和驾驭社会,建立一种公民赋权的政治权力新形式。其四,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提供了用一种生产方式去解决长久以来对民族国家体系的矛盾情感的机会。由于资本的跨国延伸,今天所需要的公共生产能力不可能单独定位在领土国家。女性主义者现在应当连接其他进步力量,为建立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新政治秩序发挥自己的影响。当代的非正义沿着每一轴心并存在于每一层面上,包括跨国界的非正义。[11]因此,女性的解放与多层面的民主力量的新群体相结合,矫正每一维度的非正义,实现地方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正义。上述在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反经济中心主义、反男性中心主义、反精英主义、反威斯特伐利亚主义斗争,构成了当代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战略的多重轴线。弗雷泽勾勒了全球化背景下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全景,目前正在酝酿关于全球大变革时代的“波兰尼女性主义”,为当代批判的女性主义开辟全球视野,重构宏观理论战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雷泽提出的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战略完成了杨的未竟事业。杨生前一直想发展一种社会主义的全球正义女性观。弗雷泽是批判的女性主义者中与杨的理论倾向和路径最接近的人。她们都是执著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女性主义者,都倾心于批判理论的规范追求,都关心新社会运动,关注实践批判的解放事业,具有正义关怀和非正义批判的全球性视野。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战略表明,她们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创新为新的女性反抗运动背书,努力占领在理论上、道德上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制高点。
批判的女性主义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目前仍方兴未艾,保持着强大的理论后劲。除艾利斯·杨英年早逝,本哈比、弗雷泽等人现在仍然活跃在当代西方学术前沿。她们均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主要成员。近年来,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成员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们的理论视野更为广阔,思想更为新锐。比如,弗雷泽的学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艾米·埃伦(Amy Allen)近期在其出版的部分批判的女性主义专著中,不仅在描述“我们自己的政治学”,而且对批判的女性主义遭遇的理论瓶颈、主要问题和新的理论生长点均提出了具有高度理论概括性的分析。
关于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埃伦指出,第二波女性主义提出的理性批判问题仍然是当代女性主义辩论中绝对中心的问题。如何将女性主义批判与哲学学科的核心概念——理性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是远未解决的问题。女性主义的理性诉求本身造成了理性和权力的纠结和冲突。理性和权力的矛盾仍然困扰着当代的女性主义争论。
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发展批判的女性主义的理性批判?埃伦从新一代人的视野出发,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理性批判纲领:揭示第二波女性主义批判的理性主义基础;检讨批判理论传统的理性批判的矛盾性;利用后现代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改造理性。
首先,埃伦指出,第二波女性主义坚持两性对理性的平等拥有(如波伏娃)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包容理性的女性“他者”和肯定女性价值(如女性主义哲学主流),都建立在理性对女性排斥的基础之上,根本无法挑战已被女性主义批判揭露的等级制的评价结构。它们要求女性在被排斥出理性空间的境遇中,在一个它想要否定的知识传统的空间中,重新规定自己的从属地位和自我异化。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理性的疑虑不无道理。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一个经典贡献是戳穿了理性的男性化本质,指出这种男性化的理性理想位于西方哲学的最核心部位,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贯穿着持久不衰和普遍存在的男性至上主义。她认为,理性的男性化表现在从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直到后康德的欧洲思想中,甚至深入到女性主义理论的鼻祖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工作中。西方哲学的理性理想与女性的性别服从地位具有深层联系。作为对女性的超越性和隶属性的理性定义和作为理性的“他者”的女性特质概念结合在一起,二者共同为性别服从关系背书、证明,并使之合理化。
其次,埃伦揭示了批判理论坚持女性主义的理性批判的意义及其局限性。她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同样接受了实践理性的理想,并尝试用这种理想为批判提供可靠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已经抛弃了强形而上学的传统理性概念,其理性出发点具有更大的兼容度,其批判理论已完全与同性恋、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逻辑相互交叉、广泛结合。但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仍然是基于对身体、情感、精神和审美的超越和否定;同时,他无法在不削弱其规范普遍性基础的情况下放弃对自主性、对生活世界合理化的进步主义追求,从而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悖论。霍耐特具有强伦理背景的承认理论,以其复杂理性观集成了情感、身体和精神等维度,形成了比哈贝马斯更能容纳多种特殊性(种族、阶级、性别、性与国籍)关怀、包括女性主义关怀的实践理性的规范概念。但是,他的理论仍然提出了有关现代性的规范性的很成问题的理性假定,这些假定前提很难抵御后殖民的批判。
最后,埃伦要求用后现代的批判性与批判理论相结合,在理论层面改造理性,在实践层面争取全面的平等权利和性别正义。她引用爱德华·萨义德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说明,批判理论“尽管对于支配、现代社会和经由作为批判的艺术而实现的救赎机会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创见,但是它对种族主义的理论、反帝国主义的抵抗,以及帝国中反抗的实践,却是令人震惊地沉默无言的”。[12]278埃伦明确主张彻底清理批判理论与统治、压迫和种族中心主义等关系纠缠在一起的关于理性、合理性、普遍性和规范性的概念,将权力和理性互相融合,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理论中一种无法调和的张力的方式,从而构建一种能够回应女性主义、同性恋、批判的种族与后殖民理论的、去殖民化的批判女性主义理论。她认为,批判理论必须在理论上把权力和理性之间根本的紧张状态置于其自我理解的核心地位,基于此找到将这类理性批判付诸实践的更好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批判,把女性主义推向新阶段。①参见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艾米·埃伦(Amy Allen)在2012年11月广州举办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研讨会”上的报告:《女性主义、现代性和批判理论》(“Feminism,Modernity,and Critical Theory”)。
[1]Young.Intersecting Voices:Dilemmas of Gender,Political Philosophy,and Polic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2]Michel Foucault.The Will to Knowledge: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1)[M].London:Penguin Books,1990.
[3]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4]Seyla Benhabib et al.Feminist Contentions:A Philosophical Exchange[M].New York:Routledge,1995.
[5]Axel Honneth.Das Recht der Freiheit:Grundriβ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M].Fankfurt:Surhkamp Verlag,2011.
[6]Seyla Benhabib.Situating the Self:Gender,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M].New York:Routledge,1992.
[7]Benhabib.The Claims of Culture: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Global Era[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8]I.M.Young.Inclusion and Democrac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9]Fraser.Unruly Practices:Power,Discourse,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M].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10]Dipesh Chakrabarty.Habitations of Modernity:Essays in the Wake of Subaltern Studie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11]Fraser.Scales of Justice,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12]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Vintage,1993.
责任编辑:秦 飞
American Critical Feminism and It Contemporary Evolvement
ZHOU Suiming
The theories of American Critical Feminism can be generalized into threes themes:Multi-Democracy, Power Theory and Gender.Multi-Democracy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critical feminism;Power Theory is the reasonable factor of the post-modernism in critical feminism;category of Gender constitutes the new perspective and main evolution clues of critical feminism.The current key problem of critical feminism is how to explain the inside paradox between reason and power.
critical theory;feminism;multi-democracy;power;gender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2.001
:2013-03-10
C913.68
:A
:1007-3698(2013)02-0005-09
周穗明,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政治哲学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