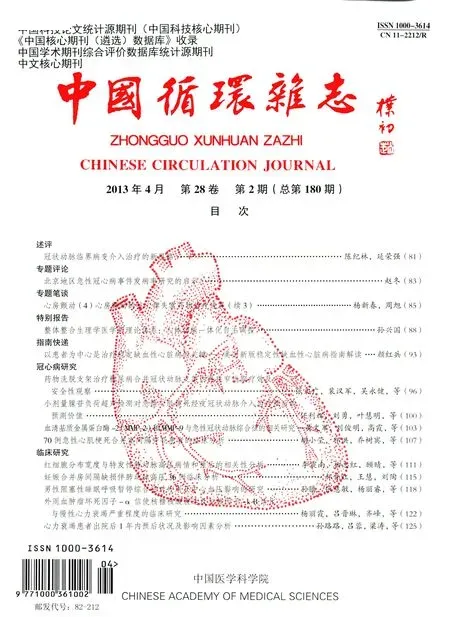冠状动脉临界病变介入治疗的新思路
陈纪林,延荣强
·述评·
冠状动脉临界病变介入治疗的新思路
陈纪林,延荣强
冠状动脉临界病变与心血管不良事件有关,合理的治疗临界病变仍然是心脏科医生的挑战。有效预测血运重建高危的临界病变,建立预测评分,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有助于提前制定有效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的治疗策略,并为冠状动脉临界病变介入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冠状动脉临界病变;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冠状动脉(冠脉)临界病变是冠脉造影目测狭窄程度在 50%~70% 的病变。冠脉狭窄程度大于 50%,无论是在动物试验还是在临床研究中,都是引起心肌缺血的界点。很多研究提示狭窄并不严重的斑块破裂或溃疡与潜在的心血管事件相关[1,2],学者 Manoharan 等[3]观察了 102 例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患者,经过血栓抽吸后,心肌梗死靶病变的平均狭窄程度为 66%。也就是说,大部分导致心肌梗死的病变为临界病变。但是因为临界病变狭窄程度不够严重,经常被延迟介入治疗干预。这些狭窄并不严重的临界病变,部分相对稳定,部分在短期内出现破裂或进展,治疗上给心脏科医生带来很大的困惑和挑战。当前冠脉介入技术成熟、成功率高、并发症低、远期预后良好,一些心脏介入医生建议介入治疗包括临界病变在内的有可能引起心肌缺血的病变。但这样无疑会增加介入手术相关并发症、潜在的支架后再狭窄和支架内血栓的风险。如何有效预测有血运重建风险的冠脉临界病变,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有助于我们提前制定有效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的治疗策略。
目前评价临界病变最常用的是血管内超声(IVUS)和血流贮备分数(FFR)。IVUS 能较准确的测量斑块性质和狭窄程度,能评价和鉴别不稳定的薄帽纤维粥样斑块。FFR 能评价临界病变的生理功能[4],DEFER 研究[5]入选 325 例无缺血证据的临界病变患者,根据 FFR 结果分为 3 组 : FFR>0.75 患者中,91 例推迟行介入治疗(延期组 ),90 例接受行介入治疗(手术组 );FFR<0. 75 的 144 例直接行介入治疗(对照组 )。延期组和手术组 2年无事件生存率相似(89% vs 83%),但明显高于对照组(78.4%,P=0.03)。研究结果提示对没有缺血证据的临界病变,FFR 能鉴别从介入治疗获益的人群。DEFER 研究 5年随访,延期组与手术组的无事件生存率相似(80% vs 73%,P=0.52)、心源性死亡和急性心肌梗死的复合终点发生率相似(3.3% vs 7.9%, P=0.21)、心绞痛缓解比率相似。研究提示,对于冠脉临界病变的患者,根据 FFR>0.75 而延期行介入治疗的方案是安全可行的。但该研究例数较少,结论的可靠性仍需更多的研究证实。
FAME 研 究[6]入选 了 1005 例 冠脉 多支 病变 患者, 随机分为 FFR 指 导的 经皮 冠脉 介入 治疗(PCI) 组(FFR ≤ 0.80 时置入药物支架,n=509)和常规冠脉造影指导的 PCI组(n=496),比较了 1 年以全因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血运重建为复合终点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研究显示 FFR 指导的 PCI显著降低了 1 年的主要心血管事件(13.2% vs 18.3%,P=0.02),但是在全因死亡(1.8% vs 3.0%,P=0.19)和心肌梗死(5.7% vs 8.7%,P=0.07)发生率没有差异。FAME-2 研究[7]是继 FAME 研究后又一个评价 FFR 指导的 PCI 在冠脉疾病中的作用。研究入选的 888 例稳定性冠脉疾病患者,均至少具有 1 处生理功能受损明显的冠脉病变(FFR ≤ 0.80),随机入组 PCI+ 最佳药物治疗组(PCI组,n=447)和单纯最佳药物治疗组(药物组,n=441),比较了术后 7 个月以全因死亡、心肌梗死和急性血运重建为复合终点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结果显示,和单纯药物组相比,PCI+ 最佳药物治疗组显著降低了以全因死亡、心肌梗死和急性血运重建为复合终点的主要心血管事件(4.3% vs 12.7%,P<0.001)。这种差异主要缘于单纯药物治疗增加了急性血运重建的发生率(11.1% vs 1.6%,P<0.001)。但值得注意的是,PCI+ 最佳药物治疗并没有降低 7 个月全因死亡(0.2% vs 0.7%,P=0.31)和心肌梗死(3.4% vs 3.2%,P=0.89)的发生率。以上两个研究均为 FFR 指导的非临界病变介入策略的研究。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 FFR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无法有效判别斑块的稳定性,无法评价斑块的进展风险;从经济学考虑,不是常规检查,增加了介入手术的复杂性;另外,FFR 指导的介入治疗在心脏性死亡等硬终点上有无获益仍然不是很清楚[6,7]。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465 例临界病变(519 处病变)患者,平均造影随访时间为 11 个月。156 例患者的 182处临界病变中,162 处进展并接收了血运重建治疗(血运重建组,152 例介入治疗,4 例搭桥)。309 例患者的 337 处临界病变没有明显进展,未接受血运重建(未血运重建组)。我们分析了临界病变进展并接受血运重建的危险因素,并相应的建立危险因素评分。缺血驱动的造影随访在血运重建组更常见(82.7% vs 48.9%,P<0.001),平均 11 个月造影随访中,血运重建组临界病变狭窄程度平均进展(24±12)%,未血运重建组平均进展 [-10,10]。血运重建组心肌梗死的发生率要高于未血运重建组(2.6% vs 0.3%, P=0.045)。血运重建组 8 例患者(5.1%)的临界病变进展为完全闭塞病变,未血运重建组临界病变无闭塞病变发生。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在入选的11个危险因素中(糖尿病、吸烟、冠心病家族史、高血压、未用他汀药物、病变部位、女性、体重指数≥ 28 kg/m2、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64 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91 mmol/L、复杂病变 ),未用他汀药物[比值比 (OR)=3.355, 95% 可信区间(CI): 1.455~7.740, P=0.005 ], 复杂病变(B2/C)(OR=2.743, 95%CI: 1.805~4.168,P<0.001), 近端病变 (OR=1.635, 95%CI: 1.056~2.533, P=0.028),和糖尿病 (OR=1.616, 95%CI: 1.058~2.470,P=0.026) 是临界病变进展并接受血运重建的独立危险因素。每个独立危险因素定义的危险评分为 1 分,我们重新分析所有 519 处临界病变,临界病变危险评分为 0 分、1 分、2 分、3 分和 4 分的接受血运重建的比例为 20.1%、25.6%、43.6%、76.7% 和 66.7%。≤ 1 分的临界病变,接受血运重建的比例为 23.3%,而≥ 2 分的临界病变接受血运重建的比例为 50.7%。
在冠脉造影后决定是否介入治疗临界病变,我们的数据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的评分对判断血运重建高危的临界病变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我们的评分中,≥ 2 分的临界病变,在 11 个月的平均随访中,50.7% 接受了血运重建。临界病变的破裂和斑块狭窄进展是导致心肌缺血症状及心脏不良事件的主要原因,冠脉介入治疗高危的临界病变,不单纯是缓解患者的症状,更重要的是减少将来临界病变导致的心血管事件。危险因素评分为≤ 1 分的临界病变,斑块破裂或进展并接受血运重建的风险较小(23.3%),建议药物保守治疗。≥ 2分的临界病变,建议强化药物治疗的同时,适时行介入治疗。
另外,临界病变是否需要介入治疗,我们还要强调血管和血管节段的重要性。我们的数据提示,近端病变是血运重建高危临界病变的预测因子,所以在重要血管如前降支的近端病变,无论有无缺血症状,其危险评分≥2分,建议行介入治疗,以减少近端病变引起的大面积心肌缺血事件。非左主干及非近端的临界病变,其危险评分≤1分,建议首选药物治疗。
[1]Arbustini E, Dal Bello B, Morbini P, et al. Plaque erosion is a major substrate for coronary thrombosis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Heart,1999,82:269-272.
[2]Burke AP, Kolodgie FD, Farb A, et al. Healed plaque ruptures and sudden coronary death: evidence that subclinical rupture has a role in plaque progression. Circulation,2001,103:934-940.
[3]Manoharan G, Ntalianis A, Muller O, et al.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ial stenoses responsible fo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Am J Cardiol, 2009,103:1183-1188.
[4]Pijls NH, Sels J-WEM. Functional measurement of coronary stenosis. J Am Coll Cardiol ,2012,59:1045-1057.
[5]Bech GJW, De Bruyne B, Pijls NH, 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ngioplasty in moderate coronary stenosis: a randomized trial. Circulation ,2001,103: 2928-2934.
[6]Tonino PA, De Bruyne B, Pijls NH, 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versus angiography for guid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N Engl J Med, 2009,360: 213-224.
[7]De Bruyne B, Pijls NH, Kalesan B, 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guided PCI versus medical therapy in stable coronary disease. N Engl J Med, 2012,367:991-1001.
2013-01-29)
(编辑:梅平)
100037 北京市,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心血管病研究所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冠心病诊治中心
陈纪林 硕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冠心病临床研究 Email: jilin.chen@263.net 通讯作者:陈纪林
R541.4
C
1000-3614(2013)02-0081-02
10.3969/j.issn.1000-3614.2013.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