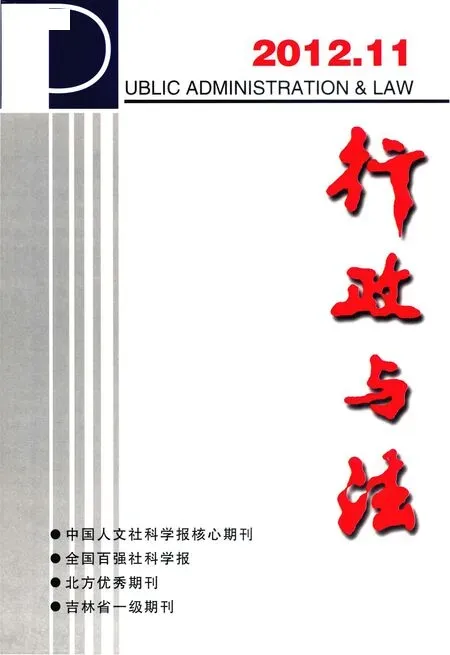环境保护与资格刑的扩张
□ 朱志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3)
环境保护与资格刑的扩张
□ 朱志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3)
资格刑通过剥夺环境犯罪人一定的资格或权利,从根本上剥夺了其再次实施环境犯罪的能力,既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特殊预防,又进一步提高了违法成本,增强了刑罚的威慑功能,从而强化了环境犯罪的一般预防。而资格刑所独具的多样性、非物质性与可恢复性等特征,也使其对于经济犯罪、环境犯罪、腐败犯罪等特殊的犯罪类型具有独特的惩戒与预防功效。因此,结合当代刑罚的发展趋势、国外立法经验及我国环境保护的需要,有必要在环境刑法中扩张资格刑的适用,以使其与财产刑、自由刑一起在法的最后保障层面构筑起保护环境的三角形支撑。
资格刑;环境保护;扩张;复权;资格的回复
一、问题的提出
备受各方关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已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完成初次审议,现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虽然该修正案草案稿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环保法律体系的不足,但令人遗憾的是,初稿中首次提出并引起各界广泛兴趣的“按日计罚”①即排污企业无法按期实现环境监管部门限期整改的要求,逾期1天将被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处罚,上不封顶。据权威人士透露,这是首次在全国性法律中列入“按日计罚”概念。因此,以初稿为蓝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法(修正案)》将来若顺利通过审议,该法将成为我国最严厉的环保立法。参见.中国最严环保法提上立法日程 首纳"按日计罚"概念[EB/OL].http://www.chinanews.com,2011-07-15.概念却未能最终纳入此次草案稿中。我们知道,同环境危害的深远性与环境治理的高耗性相比,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的柔弱大大降低了危害环境人员与单位的违法犯罪成本,从而使我国的环保法律体系在报应与预防危害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方面一直没有很好地发挥法律的应有功效。这也是专家们主张将 “按日计罚”制度纳入环保法的动因。最终出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显然在衡量各方利弊后最终放弃了过于刚性的“按日计罚”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法律制裁在报应尤其是预防危害环境行为方面进行应有的体系性的思索。
首先,我国刑法目前对环境犯罪所设定的刑罚仅包括自由刑和财产刑,对于渐受国际社会青睐的资格刑始终未能在立法上有所举动。2011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虽然对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第343条第1款“非法采矿罪”做了全面修订,但终究未能将资格刑纳入考量视野。
其次,刑法典第37条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仅适用于“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环境犯罪分子,其中“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司法建议与资格刑在报应与预防环境犯罪方面的效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现行环境法中所规定的责令停产、责令停业或关闭等措施在性质上仍为针对一般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制裁,对于达到犯罪程度的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统一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模糊性语言一带而过,而未能像当前国外的通行做法那样在附属刑法中对刑法典的概括性予以进一步明确,对其滞后性予以及时更新,从而充分发挥附属刑法在刑法体系中的补足功能。
现代刑罚理念对刑罚的发展要求是趋于轻缓化、经济化与人性化,财产刑和资格刑正是因为符合这一要求而较生命刑和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日益彰显出优势。其中,资格刑又称名誉刑、能力刑或权利刑。作为依法剥夺犯罪人一定资格或权利的刑罚,资格刑历经古罗马法中的名誉刑,中西方从古至今的耻辱刑与资格刑的演变与传承,在各国刑罚史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在理论界一直有学者以缺乏足够的威慑力、不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容易导致“刑罚过剩”等理由主张废除资格刑,但是“刑罚的选择是考虑诸多因素的结果,它们应该具有量方面大小的可感受性、本身的平等性、可成比例性、与罪行的相似性、示范性、经济性、改善性、受人欢迎,等等”。[1](p395)资格刑所独具的多样性、非物质性与可恢复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对于经济犯罪、环境犯罪、腐败犯罪等特殊的犯罪类型具有独特的惩戒与预防功效。就环境犯罪而言,资格刑通过剥夺环境犯罪人的一定资格或权利,从根本上剥夺了其再次实施环境犯罪的能力,既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特殊预防,又进一步提高了违法成本,增强了刑罚的威慑功能,从而强化了环境犯罪的一般预防。而对于被判处一定期限资格刑的环境犯罪人,在该期限届满之前,重新恢复被剥夺的资格或权利,即复权,使犯罪人有机会重新做人做事,不仅有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而且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从而为我国日益壮大的环保队伍增添更为坚定的成员。因此,结合当代刑罚的发展趋势、资格刑的自身优势、国外立法经验以及我国当前环境保护的需要,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环境刑法中扩张资格刑的适用,最终使其与财产刑、自由刑一起在法的最后保障层面构筑起保护环境的三角形支撑。
二、资格刑扩张的模式
从各国立法例看,资格刑的适用模式分为概括制与选择制。前者是指适用某种资格刑时,不加区分地将法律所列该种资格刑的全部内容均予以剥夺;后者是指刑法分则在规定各种具体犯罪时,依据本罪的具体情况规定对总则中的资格刑有选择地剥夺其部分或全部内容。根据我国刑法典第54条的规定,一旦对犯罪人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则其所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将一并被剥夺。因此目前我国刑法所确立的资格刑适用模式实为概括制。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我国刑法当前的资格刑设置始终基于阶级斗争需要而政治色彩过浓的问题,因为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中不存在死刑与无期徒刑,因此也就永远不存在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可能。但是仅就资格刑的适用模式而言,不分犯罪类型、犯罪情节、危害程度等而一并将包括选举权、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全部剥夺,这种概括制不仅使环境犯罪资格刑的适用陷入僵化,而且容易引发“刑罚过剩”,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报应与预防包括环境犯罪在内的犯罪需要了。因此,只有适用选择制,即首先在刑法总则中详细地、条款分明地罗列出资格刑的种类、适用对象,然后在刑法分则环境犯罪的相关条款中,依据各罪的具体情况对总则中的资格刑有选择地适用其部分或全部内容,才能确保所选择的资格刑内容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犯罪人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而从国外立法看,包括俄罗斯、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在确立资格刑制度时也都采取了选择制。
三、资格刑扩张的内容
从我国刑法第34条 “附加刑的种类如下:(一)罚金;(二)剥夺政治权利;(三)没收财产”和第35条“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立法就环境犯罪只设立了剥夺政治权利与驱逐出境两类资格刑。至于客观上大量存在的、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剥夺资格的处置方法,虽然游离于环境犯罪刑罚体系之外,无资格刑之名,但事实上却在发挥着资格刑的效能。这是因为“从其内容来看,它们或剥夺罪犯担任公职或剥夺罪犯从事特定职业或活动的权利;从其作用来看,起到了防止罪犯再次实施同样的犯罪行为的作用。”[2]这种立法模式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环境犯罪资格刑立法因刑种设置单一而难以应对严峻的犯罪形势之缺憾,但这种饮鸩止渴之法显然既混淆了行政处置与刑罚处罚之间的界限,也严重背离了罪刑法定精神。结合我国环境犯罪的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可以考虑将如下内容扩充进该类犯罪的资格刑体系:
第一,禁止担任特定职务。曾因实施环境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员,或者曾经在因实施环境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任职,并对该单位直接负责或者对该环境犯罪承担直接责任的人员,不得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及与环保职能相关的国家机关的职务。
第二,禁止从事特定职业。曾因实施环境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员,或者曾经在因实施环境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单位任职,并对该单位直接负责或者对该环境犯罪承担直接责任的人员,禁止其从事环境工程师、环境科学研究人员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职业。
第三,禁止从事特定活动。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对环境的保护是非常严格而且严密的。如捕鱼问题,在美国,地方法律不仅同我国一样规定了禁渔区、禁渔期及禁止使用的捕鱼工具和方法,而且要求行为人必须首先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捕鱼资格证。这对于经济欠发达和生态文明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恐怕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对于环境犯罪人,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我们可以暂时或终身禁止其从事犯罪时所涉及的与环境相关的活动,如捕鱼、狩猎、伐木、采矿等。这一资格刑的设立,对于规制以此为谋生手段、兴趣爱好或者健身方式(主指捕鱼、狩猎、采摘等)的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特别是遏制当前的滥采、滥伐、滥捕现象,将切实发挥法所一直追求的威慑作用与教育功能。
第四,剥夺荣誉。在现实中,许多实施环境犯罪的单位及其直接负责人在受到法律追究以前往往获得了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荣誉称号, 如 “××模范”、“××卫士”、“××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等。因此,在对这些单位及自然人实施环境犯罪制裁时,应同时剥夺其相关荣誉称号,以示国家对其政治上的否定性评价,从而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
第五,暂停营业。对实施环境犯罪的单位,判处其在一定期限内不准进行原有业务活动的一部分或全部,以迫使其对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行反省和整顿。
第六,限制从业。对实施环境犯罪的单位的经营活动范围尤其是与环境有关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以示惩戒。
第七,强制撤销。即对实施严重环境犯罪的单位予以强制性地注销,使其不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强制撤销与其前两项资格刑——暂停营业、限制从业,虽然就制裁内容而言类似于环境法中所规定的责令停产、责令停业或关闭等行政制裁措施,但是两方面在适用对象、适用依据、适用主体和法律制裁的性质等方面存在着严格界分。就立法技术而言,对于暂停营业、限制从业、强制撤销三项资格刑,应当同其他资格刑一样在刑法典总则中予以规定和注释,分则只是规定选取的适用种类。至于与行政法的对接问题,可以考虑在环境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像以往一样用概括性的语言做以简易交代,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实质上也是在行政刑法层面解决了某一制裁措施的行政属性与刑事属性的归属问题。或者可以考虑直接将包括这三种资格刑在内的适用于环境犯罪的资格刑类别明确而系统地在环境法的法律责任部分予以陈列。同前一种方式相比,后一种设想虽然可以充分发挥附属刑法对刑法典的援助功能,但在我国,资格刑的刑法典体系尚不明晰与健全,显然因过于超前而不具有可适性。
第八,公示宣告。基于代际正义之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以此为基点,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关注环境效益,法制建设开始重视对环境权与发展权的保护。刑法作为事后保障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在启动对实施环境犯罪的自然人和单位刑事裁量时,可以同时规定附加适用公示宣告。即法院根据案情需要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将对自然人或单位环境犯罪的判决公之于众。具体操作可以由主审法院进行,也可以由其指定或委托的法院进行。这种公示宣告资格刑的创意来源于犯罪学中的标签效应,而其设置目的在于通过名誉上的制裁来警示犯罪人和警醒意欲与单位犯罪人进行业务往来的自然人或单位,在进一步递深刑罚惩戒力度的同时更好地提升刑法的保护环境权和预防环境犯罪的功能。
四、权利的提前恢复与资格的回复
权利的提前恢复,是指对于被判处资格刑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提前恢复其丧失的部分或者全部资格或权利,即复权。其“立法设置初衷,是作为一种针对于资格刑的刑罚消灭制度,来消除资格刑可能存在刑罚过剩的弊端,并同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促进犯罪人的自我悔过进程”,[3]以早日恢复人格和回归社会。因此,我们所论及的环境犯罪资格刑的复权制度有别于前科消灭制度,后者实为刑罚后遗效果影响的消除。
当前确立资格刑制度的国家大多数都相应地规定了复权制度。如《德国刑法典》第45条b“资格和权利的恢复”中规定:“具备下列条件时,法院可恢复依第45条第1款和第2款丧失的资格,及依第45条第5款丧失的权利:⒈资格或权利丧失的期限已经经过一半的,⒉可望判刑人将来不再故意犯罪的。”[4](p16-17)《瑞士刑法典》第77条和第78条规定,被判刑人表现良好,且法院确定的或通过调解所确定的损失得到赔偿的,可以重新担任公职和恢复教养权或监护权。第79条规定,法官不担心被判刑人继续滥用职业,且法院确定的或通过调解所确定的损失得到被判刑人的赔偿的,可以撤销执行禁令。[5](p29)我国刑法典在将资格刑扩张适用于环境犯罪时,也应当相应地配置复权制度,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资格刑体系。就具体制度设计而言,应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复权的条件。从实质条件讲,只有当环境犯罪人确有悔改表现,复权后不致再次利用该资格或权利实施环境犯罪的,才可以复权;从时间条件讲,只有当资格刑执行一定期限后,才可以考虑复权。
二是复权的程序。从现有立法例看,复权的程序包括依犯罪人申请裁决和依职权裁决两种。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可规定由环境犯罪人提出复权申请或者由资格刑的执行部门提出复权建议,最终由法院裁量是否复权。
三是复权的撤销。为保证不适当的复权得以及时纠正,我国刑法可借鉴意大利等国的复权撤销制度,规定环境犯罪人复权以后,如果利用该资格或权利再次实施环境犯罪的,法院有权撤销复权。
而资格的回复是资格刑执行完毕后的当然法律后果,是指资格刑执行完毕后,受刑人被剥夺资格之恢复。我国刑法中尚无资格回复制度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四种方式:一是当然恢复,即在资格刑执行完毕后,犯罪人自行恢复丧失的资格或权利。二是宣布恢复。如1979年《公安部关于管制、拘役、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监视居住的具体执行办法的通知》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立即向本人和有关群众宣布解除管制,附加剥夺权利的,还应当同时宣布恢复政治权利。三是有条件恢复。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军官犯罪可以附加判处剥夺军衔,服刑期满,继续在军队服役的,根据需要和有关法律规定授予军衔。四是不予恢复。如对于犯罪的外国人附加判处驱逐出境的,不再恢复其在中国居住的资格;对于退役的犯罪军人附加判处剥夺军衔的,不再恢复其原有的军衔。[6]明确资格刑的回复制度,有利于积极消除资格刑的负面影响,进而促使环境犯罪分子早日回归社会。
陈兴良教授曾言:“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7](p10)邱兴隆教授也指出:刑罚有如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有益于社会的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于社会的消极影响。借助刑罚本身不可能完全阻止犯罪的发生,更不可能消除犯罪现象。因此,以有限的刑罚对付无限的犯罪,是国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而科学、有效的刑罚体制应该是功能最大、消极作用最小且严厉性程度最轻的刑罚体制。[8](p214-224)在我国,重刑仍然占据整个刑罚体系的主流,这不仅与当前的世界潮流相违背,而且重刑过多容易禁锢社会的活力和人们的创造力,长此以往将会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资格刑作为刑罚体系中的一种,其轻缓、经济、人道,辅之于主刑将对当前环境犯罪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然正如培根所言:“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9](p1)资格刑制度作为我国刑事立法中一块尘封已久的区域,①从19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八)》,十余年间,我国刑事立法未对资格刑制度做任何修订。它能否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在打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方面的效能均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但正如前文所述,结合当代刑罚的发展趋势、资格刑的自身优势、国外立法经验以及我国当前环境保护的需要,资格刑在包括环境犯罪在内的我国刑法中的扩张只是个时间问题。
[1](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M].李贵方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李荣.我国刑罚体系外资格刑的整合[J].法学论坛,2007,(02):67.
[3]于志刚.复权制度适用问题研究[J].法学,2002,(02):35.
[4]德国刑法典[M].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5]瑞士联邦刑法典[M].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6]李海滢,麻锐.腐败犯罪控制视野下的资格刑研究[J].法学杂志,2009,(07):52.
[7]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M].法律出版社,2003.
[9](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张雅光)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xpansion of Qualification Penalty
Zhu Zhifeng
Through deprivation of a certain qualification and right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s,qualification penalty can basically deprive ability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crime again,not only to implement special prevention effectively,but also to strengthen general prevention through improving illegal cost and deterrent function of punishment.Owing to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non-material and recoverability,qualification penalty has special warning and prevention effect towards economic crime,environmental crime,corruption crime and so on.Therefore,combined with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penalty,legislative experien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nee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application of qualification penalty in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and finally make it,together with property penalty and freedom penalty,construct triangle support of protecting environment at last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qualification penalty;environment protection;expansion;restoration of rights;return of qualification
D924.13
A
1007-8207(2012)11-0114-04
2012-09-20
朱志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学、知识产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