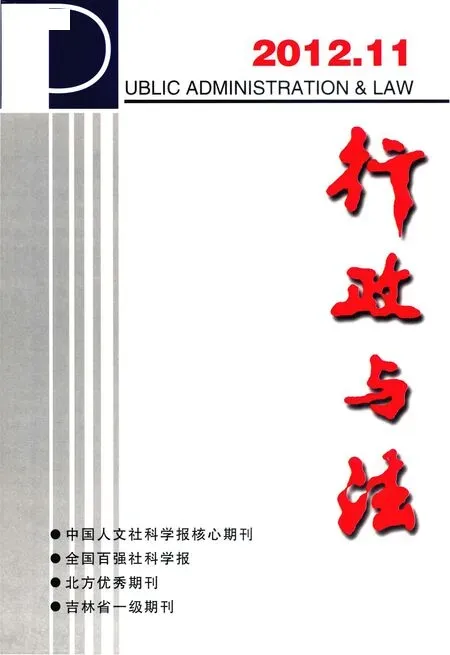论法律信任
□ 刘国华,公丕潜
(⒈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⒉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论法律信任
□ 刘国华1,公丕潜2
(⒈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⒉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法学界对于法律信仰的讨论日渐沉寂,而对法律信任的言说方兴未艾。本文在对法律信任与法律信仰进行界分的基础上,着重对法律信任的内涵、特征与功能进行了阐述。指出法律信任是一种制度型信任、程序型信任、价值认同型信任与内含制度化不信任的信任形态。法律信任具有主体普遍性、客体复合性、价值共识性、理性选择性等特征。同时其具有法治观念凝聚功能、法律行为激励功能、法律价值整合功能与法治秩序建构等功能。
法律信仰;法律信任;特征分析;功能阐释
一、法律信任与法律信仰的厘定
在对法律信任问题进行研究之前,有必要对与信任相关的易混淆概念进行辨析,尤其是对信任与信仰的辨析。
(一)信任与信仰的辨析
信任与信仰是一对极易混淆的概念,但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信仰原本是描述人类宗教情感的概念,表达的是对属于彼岸世界的事物或情境的向往。”[1]《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伦理学原理》中把信仰界定为“信仰是指人们对某事某物某人的极度信服、仰慕和崇敬、崇拜的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把信仰定义为“对某种理论、思想、学说的心悦诚服,并从内心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现代汉语词典》把信仰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的榜样或指南针”。综观上述几个信仰的定义可以发现,信仰本质上是相信其正确,甚至宁愿相信其正确,不在于其是否真实,信仰表征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假定,一种崇高的追求,一种精神的寄托。信仰一般具有先验性、神圣性与不可质疑性等特征。而信任是相信而敢于托付,其多具有经验性、世俗性、理性选择性等特征。
(二)法律信仰与法律信任的辨析
法律信仰在中国已经流行多年,法学界也接受了法律信仰的命题。许多学者从自身的知识背景与理论旨趣的角度对法律信仰命题进行了理论阐释。但对于“什么是法律信仰”似乎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法律信仰命题来源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演讲集,尤其是那圣谕般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2](p3)箴言是不容置疑的。相较于法律信仰研究的如火如荼,法律信任的声音很是微弱。但法律因其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和工具主义色彩,人们对法律只能是理性选择后的信任与不信任,而不能是毫无怀疑的盲目信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学界出现一些法律信仰论的功能替代理论,例如法律信任论、[3]法律接受论、[4]法治认同论[5]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法律信仰命题,为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与法治实践拓宽了视界。
笔者认为,中国式法律信仰命题的错误在于:
⒈法律信仰命题始于中国学者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视域下信仰危机的误读。伯尔曼是在西方社会法律信任严重丧失和宗教信仰丧失殆尽的双重危机之下来谈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法律与宗教共享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普遍性。这四种要素赋予法律价值以神圣性,并且因此而强化了民众的法律感情。法律则赋予宗教以社会性。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6](p12-13)他主张通过法律与宗教的复合来克服这种整体性危机,即“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维度,宗教赋予法律以精神、方向和法律博得尊重所需的神圣。”[7](p4)伯尔曼提倡法律信仰的本意在于批判现代西方法律过于现代化、程序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浓重的弊端,致使西方社会面临一场“全部文化精神”崩溃的可能。伯尔曼希望重新强调法律的“意义”向度,重树人们对法律与宗教的神圣性来克服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而我国并无法律与宗教联姻的共生共荣传统。因此,我国学者倡导法律信仰更多的是在启蒙民众的法治观念。
⒉法律信仰命题的流行折射出中国法学问题意识的缺失。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的流行虽然表达了中国人对迅速实现法治理想的激情期待。但在没有弄清楚法律信仰的内涵、语境、功能的情况之下的口号式盲目研究,不免会忽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真问题。因此法律信仰在中国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法学研究过程中中国问题的缺位。杜宴林从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的理论高度,对法律信仰命题的论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判反思法律信仰等流行“主义”的理论进路。他强调“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既不能做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也不能唯‘主义’至上”。“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就是强调法学研究根植于当下中国的现实社会,以当下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真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任何中国的法学研究都不应脱离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8]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的流行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后果,恰恰是因为法律信仰论者缺乏中国问题意识,误把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认作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造成的。因此在法学研究的过程中务必树立中国问题意识,唯有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才可能是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基于对中国问题深刻把握而建构的法治才是适合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法治。笔者认为,对法律信任问题的研究可以弥补因过度提倡法律信仰而产生的中国问题意识缺失的弊病。
二、法律信任的内涵界定及特征分析
(一)法律信任的概念与内涵
结合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把法律信任界定为:法律信任是指社会主体在对法律所承载的保障人权、限制权力等公平正义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基于以往对法律运行有效性的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制度给予其保障权利的制度性承诺而形成的合理预期,并在这种预期的指引下相信其他社会主体也共享该法律价值规范并与其在法律行为模式下互动而形成法治秩序的一系列社会行动。
⒈法律信任是制度型信任。与人际信任是基于熟悉、情感、血缘而直接产生的方式不同,法律信任是一种社会主体对法律制度所承载价值共同认可的一种间接的媒介信任关系形态。“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9](p3)由于人具有自私利己的本性,如果没有制度背后的惩罚机制作为后盾,人们的行为会时常偏离制度所预先设定的轨道,因此“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生缺陷。”[10](p6)制度信任是因为人们相信制度本身具有公正性的制度伦理,相信人们的行为会被制度塑造和规范,而且有充分的理由预期生活于同一制度框架内的他人的行为模式。[11]法律信任是一种底线型信任,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失去对法律的最基本信任。如果社会成员失去对作为维持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法律的信任,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倒退到霍布斯所言的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野蛮自然状态。可以说,法律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就是信任。在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法律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保障人权、限制权力、定纷止争、协调行为、型构社会秩序的功能。
⒉法律信任是程序型信任。因为“信任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它基于过去的判断,却在未来中见证结果。”[12]所以法律信任是一种具有过程性、动态性、可持续性的信任形态,它是指向未来的,或者说是以未来为定向的,由此观之,法律信任是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条纽带。什托姆普卡在论述系统信任的过程中指出,“对于机构的信任的一个有趣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程序信任。它是给予制度化的惯例或程序的信任,这基于如下信念:如果程序被遵守,它们将产生最好的结果。”[13](p59)法律的运行过程也就是法律信任得以建立或者丧失的过程,而且法律信任是一个不断调整和自我修复的动态过程。在法律运行的某一环节的法律不信任,可以通过事后的补救措施得以恢复民众对法律的信任。而法律具有通过程序运行的外在特质,通过法律程序而进行法律活动是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应有之义。因此,法律信任是一种过程导向型信任、程序性信任。
⒊法律信任是价值认同型信任。“一个共同体内共有的基本价值支持着社会凝聚力并激励人们在制度的框架内行动。”[14](p37)法律信任是社会主体之间基于对法律制度所蕴含价值共识基础上的认同型信任。保障权利与权力制约则是现代法治所蕴含的的基本精神,而制约权力的目的也在于保障权利。因此权利是现代法律之精义。正如L·亨金所言,“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5](p1)社会主体之所以信任法律,是因为法律具有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民主宪政功能。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众从内心认同法律所承载的价值,自愿地按法律要求的行为模式行动,而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则是激励民众信任法律的内在动力。如果法律失去保障权利的功能,脱变为压制蚕食权利的工具,那么民众肯定会丧失对法律的信任,那时法律将形同虚设。
⒋法律信任是一种内含制度化不信任的信任形态。法律信任并不非表征社会理性人对法律的毫无保留的信任或信赖,而是一种内含制度化不信任的信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信任的基础正是制度化的不信任。正如民主制度需要一个非民主的司法审查制度一样,法律信任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幽暗意识”与权力的工具性怀疑前提之下的一种机制。在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中,政治信任的建立主要归功于民主制度设计中的制度化不信任机制。巴伯在总结美国民主宪政发展的经验后,认为“在美国历史的一开始,对政治家和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就已经是美国公众思想意识的一部分。”[16](p68)制度化的不信任恰恰是为施予信任的人以保护,而给背叛信任的人设定惩罚措施的一种功能化的矫正机制。所以,什托姆普卡在论述了信任与不信任的辩证法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制度化不信任越多,自发信任越多”。[17](p187)法律信任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维度,也必然遵循信任与不信任的辩证法。制度化不信任机制主要通过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建构良好秩序来达到对现代政治制度的信任。[18]法律信任的建构大致也遵循同样的路径。因此,建构法律信任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不信任机制或者法律信任保障、监督机制的建立。
(二)法律信任的特征分析
⒈主体普遍性。法律信任主体是所有承认法律的合法性,并在法律要求的行为模式指引下活动的一切主体,即把法律当做生活方式的人,一切通过法律而追求良善生活的人。这里的主体应当是社会理性人,[19](p22-23)即兼具社会人与经济理性人的特质为一身的人。法律信任的主体不仅仅包括广大社会理性人,更应该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一切涉法行为均对民众的守法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作为以法律为业的人,他们对法律持一种“内在观点”而信任程度自然要高于持“外在观点”普通民众。在某些时候他们应该保持宗教般虔诚信仰的态度来捍卫法律的尊严。换言之,法律人积极信任遵守捍卫法律的行为会给其他民众信任法律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
⒉客体复合性。与人际信任客体的单一性特征不同,法律信任的客体则具有复合性。法律信任的客体既包括了像法律条文和关系到法律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立法、执法、司法机构等抽象性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还涉及具体从事法律活动的专业人员的具体性存在。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与民众直接接触的是作为法律抽象性存在物载体的具体法律人,因此民众对法律人的信任相较于对抽象性存在的信任更加直接具体。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人的行为模式承载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同时作为法律信任客体之一的法律,也包括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人们对这两种法律的信任程度和赋信理由也是不尽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国家制定法视为“外在制度型”[20]信任,而把民间习惯法视为“内在制度型”信任。人们对国家制定法的信任是基于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承认与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而对民间习惯法的信任多是基于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共享伦理习惯道德的尊重与认同。在某些情境中,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会损害人们对法律的信任,会阻滞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⒊理性选择性。法律信任作为信任的一种类型,其与风险相伴而生。社会理性人选择法律作为信任对象,其所依靠的证据就是法律过去运行的有效性和法律权威性,基于对法律能够保障其权利实现其利益的制度性承诺。正如波斯纳所言:“服从法律更多的是一个利益刺激问题,而不是敬重和尊重的问题”。[21](p294)因此,社会主体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来衡量守法的利益所得与违法的成本付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判断信任还是不信任法律。当然这种判断不仅是看一时的收益,而是要看暂时的违法行为能否造成长期的利益损失。如果从长远眼光来看,暂时的违法行为取得的收益小于未来的收益,那么信任法律是可欲的。因为现代社会复杂性程度很高,人们的价值观呈多元化,各种利益纠纷不断,法律作为社会运行的有效性框架机制,对于简化社会复杂性,为社会主体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法律信任是社会理性人进行理性选择的产物。
⒋价值共识性。社会主体之所以信任法律,按照法律要求的行为模式规划、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是因为社会主体认同尊重法律所承载的秩序、自由、正义、人权等价值,即社会主体之间共享法律价值规范。“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其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表达和维护团结。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中,信任是创立和维护团结的一个综合性机制。”[22](p68)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之所以敢于和陌生人进行交易,委托陌生人给我们看病,享用陌生人给我们提供的美味佳肴,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共享该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信任他人是基于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假设,即他人与你共有一些基本价值。”[23](p2)而所有这些信任的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功能化的保障机制在发挥作用,那就是对法律制度保障我们权利的信心与信任。
三、法律信任的功能阐释
法学界对法律信任功能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有论者把法律信任的功能归结为 “培养社会成员对于法律的信心,提高法律运行的效率,其他制度信任建构的重要媒介”。[24](p110)欧运祥认为,法律信任除以上基本功能外,尚具有以下两大功能:一是陌生人社会的保障;二是法理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25](p111-113)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笔者把法律信任的功能归纳为法治观念凝聚功能、法律行为激励功能、法律价值整合功能和法治秩序建构功能。
(一)法律信任的法治观念凝聚功能
法律和法治都是与人的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的概念。任何法律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法律所实现价值理想的期许。而法律信任则是实现这种法治理想的内在驱动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失效或无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权威的失落,而法律信任正是法律权威的直接来源。法律信任的建立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体会依据其与法律交往的经历来理性选择加深或者减弱对法律的信任。如果社会主体积累的是正面的有益经验,那么他们会强化对法律的认识并加深对法治的认同。如果他们与法律交往的过程中得到的是负面的失败经验,他们会选择放弃或减弱对法律的信任。这种减弱的信任或者不信任也是法治观念的积累过程,因为这种对法律的不信任恰恰表明法律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果立法机关及时修改法律或者司法机关运用自由裁量权来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势做出公正判决,这些经验都会增进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任。在社会主体参与法律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主体的法治观念被潜移默化地塑造起来。因此,法律信任具有整合法律观念,凝聚法治共识,张扬法律所蕴含的自由、秩序、正义和人权等价值的作用。法律信任的法治观念凝聚功能的发挥不仅需要法律适用机关准确而客观地通过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和熟练运用法律方法来确立法律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更需要社会主体积极自主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
(二)法律信任的法律行为激励功能
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激励功能是法律制度的最基本功能之一。[26](p77)法律是通过分配权利和设置义务的方式来指引人们的行为,调处社会关系的,并且是在权利与义务的互动中运行的。[27](p147)法律的最高境界在于,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或规范,实现“非强制性”的法律激励,[28]也就是运用法律隐而不发的强制力“迫使”社会主体自愿地调整其行为与法律的要求保持一致。法律激励功能的发挥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法律只能通过利益诱导,而不能强制人们选择社会所希望的行动。而法律信任就是一种通过非强制的机制实现法律调整进而形成秩序的机制。法律信任恰恰具有时间差序性、诱导性、劝诱性等特点,它可以弥补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以劝导性的柔性形式调节人的社会行为。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其激励效应。法律信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激励社会主体理性选择法律所期望的行为模式的作用。法律制度具有能动激励、互动激励、自我激励等激励类型。所谓法律制度的能动激励是指法律制度对行为人能动性的激励。“能动激励”同时意味着个体行为动力的多元化、行为向量的分散化,即表现为激励因素方面的“多元激励”和激励方式方面的“不定向激励”。[29]法律信任也具有激励社会主体按法律要求的行为模式行动的能动激励功能、法律信任主体与法律信任客体之间互动的双向激励功能和诱导法律信任主体自觉按照法律要求的行为模式创造性地行动的自我激励功能。因此,法律信任激励功能的发挥必然会激励社会主体积极地朝着法治国家的理想迈进。
(三)法律信任的法律价值整合功能
法律信任在认识论上坚持有限理性论,克服知识和观念上的独断论。它破除对政治权力的迷信,保障其批判法律正当性的自由,并且确立基本的法律价值,使之成为评判现实法的参照系。[30]法律信任本身就是社会主体值得欲求的法律价值。法律信任之所以具有整合功能,是因为信任存在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关系中,它通过增进社会价值认同、社会理性沟通、公民有效参与和社会合作,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来促进社会的整合。[31]具体而言,法律信任通过为国家权力提供合法性依据来实现国家权力整合;通过确立价值多元化及价值共识来促进社会价值整合;通过解决社会纠纷而达到社会功能整合;通过塑造社会共同记忆而促进社会理想整合。[32]法律信任通过降低社会复杂性而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降低交往成本。克服国家权力运作的任意性而提高运作效率,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因此法律信任在驯化国家权力、协调行为、整合价值、稳定预期、形成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呈多元化态势,各种利益纷争不断,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急需法律发挥其价值整合功能来协调价值冲突、化解矛盾纠纷。此时,法律信任正是充当着缓和社会冲突、整合社会价值矛盾、使法律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功能。
(四)法律信任的法治秩序建构功能
法治秩序的建构固然需要法律制度等硬件设施,但更需要法治观念等软件机制来驱动与支撑。而法律信任则是驱动法治秩序建构的内在精神力量。“法律文化是法治的重要支柱,只有在理性的法律文化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现代法治的大厦”。[33](p155)因为法治的存续兴衰,不仅要依靠法律制度架构,而且还需要依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型法治文化。而法律信任则是这种新型法治文化中的应有之义。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脱域、制度失序、人格失范等社会问题造成社会转型时期的震荡。而法律信任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普遍信任形态,其具有整合社会价值、协调社会关系、型构社会秩序的功能。“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4](p114)法律信任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形塑与控制,为法治秩序的建构贡献力量。
[1]刘焯.“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J].法学,2006,(06):87.
[2][6](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马新福,杨清望.法律信任初论[J].河北法学,2006,(08);李勇.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J].东岳论丛,2009,(08);郭哲,刘琛.法律信任在中国——以比较的视角[J].学术论坛,2010,(01).
[4]叶立周.法律接受引论[J].公民与法(法学版),2010,(06);胡平仁.法律接受初论[J].行政与法,2001,(02);秦志凯,韦伟.论立法与法律接受[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10).
[5]刘立明.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李春明,王金祥.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
[7](美)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M].姚建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8]杜宴林.论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争论为分析线索[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05):155.
[9][14](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
[10](美)托马斯·潘恩.常识[M].何实译.华夏出版社,2004.
[11]宋少鹏.论政治信任的结构[J].行政与法,2008,(08):26.
[12]薛洁.信任:民主的心理基础[J].江苏社会科学,2006,(06):79.
[13][17](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
[15](美)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吴玉章,李林译.知识出版社,1997.
[16][22](美)伯纳德·巴伯.信任——信任的逻辑与局限[M].牟斌,李红,范瑞平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18]上官酒瑞.现代政治信任建构的根本原理——兼论制度化不信任的功能与限度[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110.
[19]张缨.信任、契约及其规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0]董才生.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04).
[2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3](美)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M].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4][25]欧运祥.法律的信任——法理型权威的道德基础[M].法律出版社,2010.
[26]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7]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8]陈彩虹.法律:一种激励机制[J].书屋,2005,(05):64.
[29]丰霏.法律激励的理想形态[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01):143.
[30][32]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J].法律科学,2003,(05):74-79.
[31]雷鸣.信任的政治功能[J].甘肃理论学刊,2005,(03):22.
[33]毕玉谦.司法公信力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34]郑也夫.信任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秀艳)
On the Trust of Law
Liu Guohua,Gong Piqian
The discussion of law belief is not fierce gradually in the law circle,but the discourse of the trust of law has been just unfolding.On the basis of to demarcate the trust of law and legal belief,the trust of law's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is emphasized.It points out that the trust of law is a kind of trust form which is institution-based trust,program type trust,value identity type trust and Inclus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distrust.The trust of law posses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ubject universality,object compound,value consensus,rational selective and so on.Otherwise,The trust of law holds cohesion function with conception of the rule of law,legal acts excitation function,the legal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func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order construction.
legal faith;the trust of law;Characteristic analysis;the function explanation
D920.0
A
1007-8207(2012)11-0118-05
2012-09-11
刘国华 (1964—),女,山东即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商法;公丕潜(1984—),男,黑龙江宁安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法律信任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D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