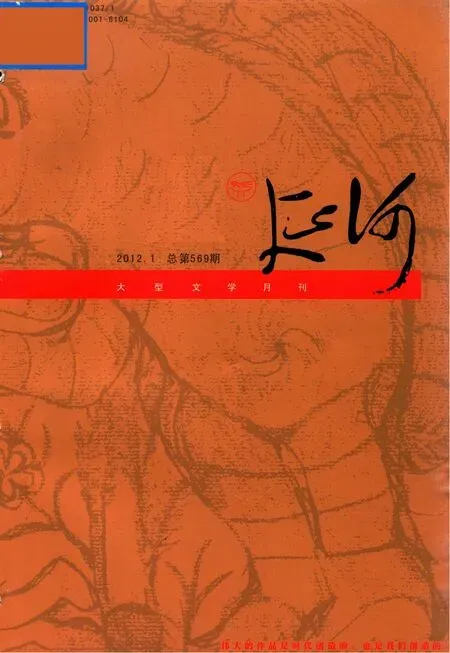“破碎的偶像”系列随笔
宋小云
中国人的性与爱
一
《风俗通》有一则传说: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传说是人面蛇身,创造了人类)抟黄土做人。剧务(工作繁忙),力不暇供(没有多余的力量来供应需要),乃引(牵、拉)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縆(绳)人也。在这则神话传说中,隐藏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性或性别观念。在中国的这则神话里,女娲造人的素材是黄土(抟黄土做人)。同样,在西方的《圣经》里,上帝也用尘土造人[1]。在这两则神话里,人似乎都是由土而来。大概是由于古人逐渐意识到大地孕育万物的现象,认为人诞生的根源不在人自身的生育繁衍,而是基于某种更为深层的大地的力:生命在本质上是土地的一部分,人对大地的依恋导致了最朴素的人与土地同构的看法——人是由土做成,也是由土而来。由此,《易经》才会有《象》曰:地势坤(土地),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生育万物,承载万物,因此坤卦与乾卦一样,是《周易》总论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中,土地是“生育万物”的承载者,人在其本质上同万物一样,是由土地繁衍生息,而非人自身的种族繁衍,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认知。
“坤”(阴)虽然有生殖的力,但却离不开“乾”(乾)的“抱合”。于是,在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阴阳生万物的说法似乎更深得人心。在中国的古人看来,阴阳两极的原则不仅存在于动植物中,而且存在于普遍的宇宙中。如天属阳,地属阴;太阳属阳,而月亮属阴;山属阳,而水属阴;男性属阳,而女性属阴。在古典哲学发展的脉络中,属阴的事物或属阳的事物在人的关照中似乎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之间的本质是可以互渗的。譬如人们习惯把女人和水放在一起来言说爱情。《诗经》里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关雎》)——《诗经》中美好的爱情总是发生在水边,在女子的一颦一笑之间,古老的生殖欲望便在水的映照中表露无疑。又譬如人们也习惯把天空和男人放在一起来言说力量。《易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里,君子通过参透天的刚健品格来与自身的精神内质达到同一。因此,人们从古到今有意无意地为“阴”与“阳”规定了不同的特征及属性。
二
阴阳虽有不同,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是彼此渗透、互为一体的[2]。老子曾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在万事万物的深层次的生命律动中,阴与阳总是共同消长。孤阴和独阳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倾近于孤阴或独阳的事物总是有死亡的意味深蕴其中。因此朱熹才说:“阳中之阴,阴中之阳,互藏其根之意”(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七)。同样,男人和女人在阴阳方面也并非泾渭分明,任何女人都有男人的一面,阳的一面;任何男人也都有女人的一面,阴的一面。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巴赞洛夫与别尔嘉耶夫同时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不但是有性别的存在物,而且是雌雄同体的存在物[3]。在柏拉图《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提及原初的人本来是圆的,有一对完整的生殖器,他们是天地间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完人,后因挑战诸神,被宙斯一劈两半[4]。“爱欲”就在找寻另一半的渴望中产生了。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借女祭司第俄提玛之口探究爱欲的本质。爱欲就是欲求自己完整的趋向,追逐并拥有善好的东西,其根本的内驱力是一种渴望整全、占有美善的欲望。苏格拉底不无深刻地告诉我们,这种欲望只有在美中才能产生,也可以说美是一切善好事物的子宫。整全的欲望只有通过在美中孕育,生产才能实现。在最高的自然法则中,雌性动物的孕育是最完美的创造,它的完成方式是凭借身体的生殖而达到原初自然创造的善的目的。而苏格拉底所真正意指的是灵魂的孕育:灵魂的生殖则是通过美的子宫而得到孕育。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进一步为我们设置了爱欲的阶梯,为了达到这种爱欲的境界,一个人必须要有类似第俄提玛这类人的引导才能从心灵上达到这种爱的境界:先从那些蕴含美的事物开始,以美本身作为阶梯,顺着这些善好的事物逐渐向上攀爬,犹如梯子,一阶一阶,从一个事物、两个事物上升到所有美的事物,再从美的事物上升到对美的品性的操持,由美的操持上升到对美的本质的把握,最后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认识那美本身的逻各斯,最终认识美之所是。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这里的美之所是即美之本体,它是超越时间范畴的存在,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和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永恒不灭。
因此,《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24)耶稣的真正用意可能与苏格拉底一样,爱欲首先必须从身体开始。在爱欲永无止境的阶梯上,身体是第一环,也就是说性是一切爱欲的肇始。“没有阿佛洛狄忒[5],就没有厄洛斯[6]。”换句话说,如果男女之间不存在性,那么也就没有爱。但是真正的爱欲绝不仅仅限于身体,身体只是爱欲的开始,但绝非终点。苏格拉底为我们设置了爱欲的阶梯,从身体开始一步一步向上攀爬,慢慢地,精神之爱也开始逐步地进入了一个人的心灵,在诸多美善女神的指引下,真理之爱也会逐渐显示她的光芒,吸引一个真正追逐美之本体的人步入其中。因此,任何否定身体的精神之爱,都必定是虚伪而又别有用心的。真理之爱或精神之爱的起点是身体。
因此,在最高自然法则之光环的照耀下,任何否定或毁灭肉欲的宗教或政党从根本上来说都非法的。一个没有经历过身体之爱的人,精神之爱或真理之爱就无从谈起。单纯的精神之爱在本质上都是精神世界里的奴役,如抛弃你自己身体的欲望,让你的精神只忠于伟大的天国之父或人民之父;又或将真理之爱等同于宗族之爱,领袖之爱。任何精神世界里的奴役总是以精神之爱作为借口,把性当做肮脏的东西,以对自然法则的根本反动作为前提,从根本上消灭人性,使其在真正意义上蜕变成专制或权威的工具。
三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上升意义上的爱欲。著名学者们将古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对性的压抑解释成古文明特有的标志,并进一步深刻地阐释说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特征……在文化肇始,上古中国人的生命意志在《诗经.郑风》的零星记载中得以昭显。“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与子偕臧[7]”——多么直白大胆而又富有生命生殖力的表述——我与你藏起来(做爱)吧。这一基于生命意志最本能的表达,却被孔子冠以“淫[8]”的恶名,涂抹到人性最初的开端上。毫无疑问,在上古人的性心理中,所有有关生殖的事情,都被赞扬抑或崇高地对待。“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辜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地官.媒氏》)这是多么盛大的祭祀活动,“司男女之无家者而会之”,生殖的过程被升华成为某种神圣的祭祀仪式。那超越一切的生命,在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尊严与神圣。这是对人,生而有之的价值的首肯。生命的生死轮回在遥远的未来与过去之间得到崇拜和供奉。对于上古人来讲,性是神圣的象征,通过至高无上的祭祀活动赋予人性以高贵和尊严,并让人在某种狂喜与战栗并存的仪式中,体会到生殖力作为生命意志最核心的力是如何在创造生命的过程中,与种族的意志合而为一。在交配、怀孕、妊娠与分娩的情境中,任何的细节都会在冷漠无边的宇宙中构成一幅动人的图景——任何时候,人都在以一种生命的创造力来拒绝宇宙的冰冷。
然而,一切还没开始,就被一位早熟者掐掉了萌芽。中国人过早地步入了所谓礼仪之邦,他们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一系列严格规定的等级序列中,女人被我们这位伟大的“早熟者”完全忽视,甚至都不在他所规定的等级序列之内,连最末的一级都没有她们相应的身影。在中国所谓的“婚姻”从来都不是男女双方的事,早期金文(婚)字形像伞下一个人张口嚎哭,耳表示“取”,嫁娶,手表示牵手,脚表示新娘出门。而“姻”子则是金文=(因,依靠)+(女)。在后来的汉语发展过程中,“婚姻”这两个字干脆抛弃了“女方”的所有所指含义,直接变成了男人们的事情。比如《尔雅》中:“婿之父为姻。又,婿之党为姻兄弟。”在这里“姻”的意思直接变成了男方的父亲,和子女反而没有任何关系。又比如《史记》中:“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这里所说的婚姻完全是两个大男人之间的事情。再后来,“婚姻伦理”关系的极端发展就产生了我们五千年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成果:太监。——这些公公们,说白了不过帝王权力极端化的牺牲品。作为皇帝,即便是在“性”的领域,也要享有绝对的支配权,保证自己权力传承的绝对“纯种”的品质。因此,阉割那些太监的不是龟头刀,而是纯粹的权力。
然而,事实上却是,在自然属性的领域中,没有比“生殖”更加体现“平等”的事实了。也可以换句话来说,性交在自然的领域内体现的是生命本身绝对平等的原则。雌和雄只要双方都愿意性交,体现的便是生命完全平等的意志。在自然界,性是一切万物最基本的权利。在性交中,一匹公马和一匹母马在自然之神的眼里地位是完全相同的,公马绝不会比母马高贵。(至于公马和母马在人的社会劳动中谁更有价值,那是人的规定,而非自然。)即便是在人的领域内,双方自愿的性交也体现了绝对平等的原则,并不例外。只不过是,性关系与权力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不相称。因此“性”永远都是权力规避的对象。——在任何国家的任何的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关于“性”禁忌的漫长历史。尤其是在极权时代,“性”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某种“禁忌”性话题,“她”要么被规制为“肮脏”、“堕落”,要么干脆被定为“非法”。任何权力在根本上是维护等级的,因此性的“平等”属性自然就是“他”的天敌。因此,皇帝的“性交”才会有那么复杂的仪式,甚至为了保证“性交”的纯粹性,权力还专门制造了太监这一奇妙的物种。帝王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遮蔽“性交”的自然平等属性,即便在“性”也要尽可能地彰显自己的无以伦比的特权,因此他必然会将自己的性事神秘化与神圣化。但是,皇帝的“那活”也仅仅是人的“那活”,即便是拥有天下女人,他的“那活”也大概只会有一根。仅就此点,“自然”的平等要比我们想象的远为深刻,即便是纯粹的“皇权”大概也会拿“她”毫无办法。
四
中国的伦理制度在人性上阉割了纯粹的两性关系。伦理用所谓的“忠诚之爱”来取代纯粹关系的“两性之爱”,这大概只能说明权力在性领域享有的支配地位。在前文我已说过,性关系就自然属性来说是天底下最能体现“平等”的关系。而权力则是天生地伴随着等级。古代的封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主流道德领域将性视为禁忌,并不是由于性本身,而是基于两个最基本的目的:
一是为了驯化,以便使臣民的肉体更方便、也更有效地为国家或者政党或者陛下服务。很简单的例子,在乡村社会,公猪基本上都是被提前阉割的对象,为的就是让他们不要在交配这件事上过分地消耗精力,从而为主人更多地提供自己的“肉体”。人也是一样,只不过阉割他们的不是刀子,而是各种名目繁多、居心叵测的道德。——性的禁忌,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臣民在肉体与思想上过分地消耗于性,从而更好地为“主子”或者“陛下”服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权阶层永远不会哪怕在道德层面上阉割自身,因此中国人的思维里,任何程度的禁忌都和等级密切相关。皇帝可以在性关系上对天下女人享有支配权,尽管“性”禁忌对皇帝而言仍然有一定的规制作用,但是相对而言在程度上要轻上很多。越是地位低下的人,性禁忌的规范内容对他(她)而言就越是繁多、从而也就越是严酷。因此,女人在封建社会中自然地“享有”比男人更为繁多的、当然也更为严酷的性禁忌的规范,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造成的。
二是为了遮蔽性关系在自然领域所体现出的平等属性。任何权力都是以强制的不平等性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与特权。然而两性关系在根本的人性属性上却是绝对的平等。即便是皇帝交配,他一次也只能进入一个女人,一次也只可能孕育一个生命。任何个体的男人在真正的性交过程中只能面对一个女人,因此自然的平等属性是任何权力都无法消灭的真实的存在。权力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遮蔽“她”,为她以道德的名义设立名目繁多的禁忌,从而让她的“平等属性”在被驯化人的视域里永远地消逝。在旧时,“洞房验贞”和男性对处女红的观念强调在其根本上都是权力介入性关系的产物。对于男人,“性禁忌”的约束力则要松上许多。即便是现代社会,男人娶一个众所周知不是处女的女人,仍然要背一定的社会道德包袱。相反,却没有人在意男人是不是处男。男人在性关系方面,显然享有权力赋予的更多的自由。
在中国,性行为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肮脏的,除却生殖的目的外,任何与性相关的行为都是一切男女讳莫如深的遮蔽性存在。——不适时的性行为甚至会亵渎神明。在鬼神常在的地方,或者在鬼神经常出没的时辰,又或者与鬼神深不可测的意志有所忤逆时,任何房事或者性行为都会被人认为是亵渎神灵。——中国人的鬼神观念确实奇怪,“鬼神”在中国的眼里并非属于与信仰等价的存在物,而是可以进行“请求”、“呼告”甚至可以用香火“贿赂”的主人。——然而,一遇到“性事”,这些“神秘鬼神”便会不讲情面、公正无私地用暴风、骤雨、地震、电闪、雷鸣、水灾、旱灾、雹灾、蝗灾、瘟疫等惩戒人类。——权力的修辞即便是在“神鬼”领域,也丝毫不放松用某种“高贵谎言”控制肉体。有人就旧时民间或者官方的性禁忌做过统计,如果完全遵守禁忌法则,中国的男人们一年内只有两天可以合法地“性交”。怪不得中国的男人们从古到今都喜欢在背地里搞事,并发展出如此辉煌优秀的权谋传统,大概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可以正大光明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少罢。
即便是到了现在,性禁忌仍然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不显山不露水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人是首先作为劳动力而被社会考量的,尤其进入工业社会,人将很难再次成为“人”了,人的本质变成了劳动力的附属属性。因此,性禁忌则会以另一种方式强有力的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现状。一个现代人,要想在现代工业社会立足,他必须首先强化自己的劳动能力。在强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过程中,他必须尽可能地推迟结婚,推迟自己的生育期,以便更好地在这个社会中谋生与立足。事实的情况是,晚婚与晚育在科学上来讲,其实没有任何依据。但它却变成了当代性禁忌的一个普遍的信条。在现代社会,人们对性交似乎并不在意,但对生育与结婚却在不经意间附加了很多额外的禁忌。太多的因素决定一个人必须晚婚或者晚育,比如中国式的教育就可以耗掉一个人几乎全部的青春年华,大部分人在大学毕业的最初几年里,不得不先在焦头烂额的就业市场厮混几年,然后不知不觉地就成了大龄青年,不晚婚也得晚婚。至于生孩子,大概许多人在中国独特的人口环境里,不得不等到三四十岁以后了。如果真是那样,晚婚、晚育的楷模们大概真就有点悲剧英雄的味道了。
五
就实质来说,性禁忌才是中国古代伦理社会的核心内容。因此,中国千年悠长的伦理历史,在其精神结构上来讲就是一部乱伦史。我曾在《孔子问题》中提出,中国人的伦理之爱,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乱伦之爱。(分析详见《孔子问题,在此不赘述。)每个家庭伦理的内部结构其实都是被微型化了的皇权结构。经过更为细致的考察,我发现所以的权力都只提倡一种形式的“爱”:这种爱大概就是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津津乐道的“忠”罢。所谓的“忠”无非就是对一种皇权模式的无原则的“爱”。在自然的两性关系中,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变态的爱,只有人才会想着用一种“爱”完全支配另一种“爱”,甚至不惜祭奠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因此,“忠”永远不是真正的爱欲,“他”几乎无原则地服从一种奴役性的情感,为一种邪恶的等级制度树立道德标准。于是,个人在权力的规制下,完全地消失了。在“忠诚之爱”的淫威下,个人对世界的爱、对生命的爱都会被权力放逐。生命“自然”的激情也随之被消耗殆尽,因此生命的原创力与生殖力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慢慢退隐。
从古到今,“忠诚”的外表下,隐匿着的是当权者并不高明的治人诡计。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原初的人为了克服恐惧,因而服从自己想象出来的、远高于人类自身的神灵。献祭人自身的肉体,大概就是对神之爱最高的表达。待到阶级社会产生之后,族群社会中,地位特殊的人就取代了神的位置,或者更准确的说出现了代神立言的人,普通人献祭的对象由神转向了人,因此“忠诚之爱”就顺理成章地被格外地强化。“国家”在制度的细节与纹理中,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忠诚之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在“道德”层面上给予“忠诚之人”无与伦比的荣誉。——大概没有比“忠诚”更有效的驯化工具了,在“忠诚”的表象下,不过是无能之辈寻求权力庇护的一种生存手段;或者说是为了坐稳奴隶、混口饭吃的重要策略;或者干脆以某种“忠诚”来换取进入利益阶层的资本,从而更方便使用特权纵恶如流。如果说必要的“忠诚之爱”可以保证城邦或者国家的稳定性,那么中国人所说的“忠诚之爱”大概只能是“吃谁的饭,办谁的事了。”自然地,奴才吃的是狗饭,大概也就只能办狗事了。——从古到今的中国人,没有基本的、超越自身利益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正义观念,唯各种各样的主人马首是瞻。——于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文化大概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么条绝对的、中国式的真理:任何时候都不问原则,只讲关系。因此,中国人的所谓的孝道当然也不过是家庭内部微型皇权的另一种更为隐秘的表述。儿子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忠诚于父亲,妻子也应该不问条件地忠诚于丈夫,而不论这个所谓的父亲或丈夫是否残暴是否正义。只有低等人的忤逆大概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
没有对公理和正义的爱,只讲忠诚。因此,中国人在漫长的千年封建历史中,才能显示出如此深厚的奴隶品质。然而在古希腊情况似乎完全不一样,毫无疑问“忠诚”也是希腊城邦看重的品质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邦民主制的健康发展。但是,希腊人的“忠诚之爱”绝不指向单一的主体,更不会指向那些宣称代表了国家的个人或团体,而指向了城邦共同的利益。希腊人清楚地意识到两性之爱,是一切爱欲的出发点。没有两性之爱,所谓的忠诚之爱或者勇气之爱都是扯谈。因此,希腊城邦在性节制这方面,并没有指定人人都应当无条件服从的律法形式。性节制在希腊的城邦里有着十分明显的针对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只针对那些想追求让自身具有尽可能美的或者具有善好形式的人。它是某种行为风格的追求,而非禁忌或者律法。
然而,上古的中国人远没有希腊人那样幸运,将类似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生命意志,上升到一种悲剧艺术。尼采说:“纵欲狂欢的心理作为一种弥漫的生命力和力量感,甚至痛苦在此之中也作为兴奋剂起效,这赋予我理解悲剧性情感的钥匙[9]。”一个民族的悲剧心理正是整个民族力量感的源泉,“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级的类型的牺牲中为自己的不可枯竭而欣喜万分[10]。”可是,一切还没开始,就被一位早熟者掐掉了萌芽。“生殖作为神圣的道路”一再被各种繁复的说教与仪式否定,通向爱欲的自由之路还没有开始就已结束。——于是,千年的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年逾古稀的妓女,受尽各种专制与强权的凌辱,步履蹒跚地来到了现代。——她早就丧失了生殖能力,然而依然被现代人一次又一次地浓妆艳抹地推向前台……
[1]《圣经.创世纪》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2]彼此渗透、互为一体并非指的是矛盾学说中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所侧重的是“斗争”,而中国人的阴阳观念则侧重的是“和为贵“。
[3]可参考别而嘉耶夫《美是自由的呼吸.论基督教的人学和人》中的相关说法,何强、王利刚选编,山东友谊出版社。
[4]阿里斯托芬原话为:他说,人本来是圆的,后来被阿波罗和宙斯砍成了一半,于是就有了寻找另一半之说.那时人的性别有两种:男,女,双性人<男女混合体>.男女性人被砍开后,都在寻找另一半,相聚后合为一体,修复人的自然,即成了现在所谓的"同性恋".追逐恋爱的过程即是恢复人性原本自然的过程。(柏拉图《会饮》)
[5]阿弗洛狄忒(Aphrodite), 她是希腊神话奥林匹斯主神之一,爱与美神。在奥林匹斯众神中,她是火与工匠之神赫准斯托斯的妻子,但她多次与别人相好:与战神阿瑞斯私通,生下5个子女;与赫耳墨斯生子;与英雄安喀塞斯生下埃涅阿斯。由于她是埃涅阿斯之母,故被视为尤里乌斯皇祖的女始祖,所以罗马皇帝都自称是她的子孙。罗马帝国兴起后,在罗马她和当地丰产及植物女神维纳斯(Venus)融合,成为丰收和爱情女神。在荷马时代,她常与时序三女神(Hours)、美惠三女神(Graces)及儿子小爱神厄罗斯相随。
[6]厄洛斯是小爱神,他的罗马名称丘比特更为人熟知。他是阿瑞斯和阿芙罗狄蒂的儿子,是一位小奥林波斯山神。他的形象是一个裸体的小男孩,有一对闪闪发光的翅膀。他带着弓箭漫游。他恶作剧地射出令人震颤的神箭,唤起爱的激情。给自然界带来生机,授予万物繁衍的能力。这位可爱而又淘气的小精灵有两种神箭:加快爱情产生的金头神箭和中止爱情的铅头神箭。另外,他还有一束照亮心灵的火炬。
[7]臧的意思有两种说法:一是同藏,隐匿之意;二是善好之意。本文采用一说。二说明显带有卫道的色彩。
[8]《论语·卫灵公》“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9]可参考尼采《偶像黄昏.我感谢古人什么》中相关说法。
[1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