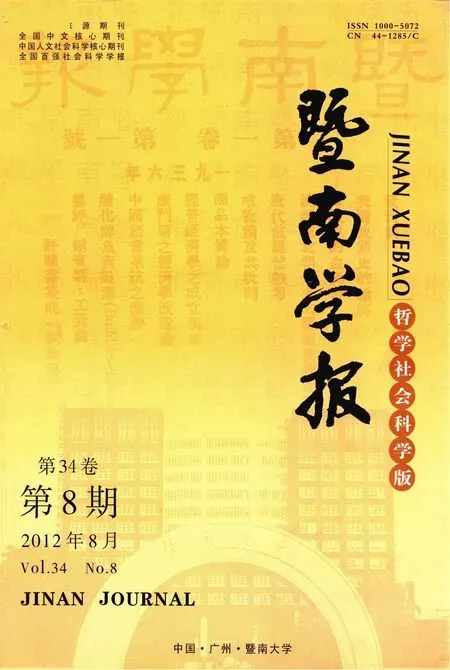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戴祝君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一、引言
“文化”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季羡林先生[1]151曾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文化热”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流行,当时就有一些极端意见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和尖锐对立是不可超越和克服的。今天世界的纷争虽不完全是由文化冲突引起,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目前的文学文化界,文化和谐与冲突成为热点,翻译评论界也不例外。也难怪,语言文字的差异造成的翻译困难一般摆在明处,容易引起重视,而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困难却往往如水中的暗礁,导致翻船。王佐良[2]34认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解释清楚。孙致礼[3]62也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本文试图从阐释学视角,以《红楼梦》翻译为例,探讨翻译过程中因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因素对文化因素的不同处理而出现的误读和错译现象。
二、文本阐释、误读与错译
“误读”首先假定了一个“正确的”解读,它不仅是理论推导的产物,同时也作为一种标准。凡是与“正确的解读”不同的,都是“误读”。孙致礼[4]356-359提出“‘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并要求译者“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理想。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传递至少需要两个步骤:首先是正确地理解原语中的文化,然后是把正确的理解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有时候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理解。
伽达默尔[5]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阐释学的三个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转引自张德让[6]23-25)。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理解,而理解总是以理解者的认知能力和视野为前提。尽管阐释学理论的出发点不是针对翻译而来,但是,众所周知,任何翻译都是从对原文的理解开始的,读者的接受也是从对译文的理解开始的。因此,阐释学理论对跨文化翻译同样适用。正如张隆溪[7]15所言,“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总是受到我们自身眼界和视野的限定”,因而“不是纯粹‘客观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其实,无论是作者、译者还是读者,都只能从自己特定的视野去理解各种事物。但是,干扰作者、译者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的因素有很多:小而言之,有他个人的经历、性格、教育、修养等等;大而言之,则有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置身其中的民族文化传统、思维习惯等等。同一个文本,不同读者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同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不同观众有不同看法。即使译者很好地理解了原文,有时在表达过程中也难免会生成新的含义,让读者产生误解。译者的文学功底,译者的政治、宗教立场,译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等都会对译者的表达产生或左或右的影响。同样,读者的文学功底、政治宗教立场、社会意识形态等也会左右他对同一译本的不同理解。绝对的中立或完全的透明是不可能的。
因此,让·贝西耶[8]143说,文化误读的真实性是肯定的,因为文化间存在差异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文化误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解读或调和文化相异性。译者只能在精通双语的同时,学习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面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不少学者把文化误读分为两类: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如杨松芳[9]176)。笔者认为,如果误读是一种事实,就不存在有意无意之别。从阐释学视角来看,误读只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即,合理的误读与不合理的误读。合理的误读主要是由于作者或译者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或者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而产生的。不合理的误读主要是由于译者或读者:1.对原语或者译语文化不甚了解;2.个人偏见或者过于自负;3.表达的失误。一般而言,不合理的误读就是一种错译。
(一)读者不同解读而产生误解
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误读的产生,来自于每个个体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同一个文本或者短语,因为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理解。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与自己的理解相异即是误读。作者在其作品中,无疑有自己的文化立场。读者(包括译者)读该作品时,也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立场。他的立场也许与作者的立场一致,也许与作者的立场冲突。译者不仅仅是读者,而且是译文的创作者。他的文化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理解问题,而且往往会影响其译作的读者。许钧[10]66指出,每一个有使命感的译者,都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而这一立场的确立,无疑直接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心态和翻译方法。译者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使者,他所面临的,有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面对这两种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原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译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立场上(同上)。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大家熟悉的《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站在中国(原语)文化立场上,而后者站在英国(译语)文化立场上。许多学者比较过两译本,这里仅举一例说明。
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这么一段话:“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10]1334文中“花”“柳”是对“妓女”的委婉称呼,汉语里还有“寻花问柳”、“花柳病”等说法。“眠花卧柳”被霍克斯[11]437译为“frequented the budding groves”,而杨宪益和戴乃迭[10]1335译为“fond of the company of singsong girls”。一般人都认为后者完整地表达了该词的意义,“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原词语的文化内涵”,而前者“显然是没有把握“花”“柳”两字的内涵意义“[13]175。霍克斯真的不懂“寻花问柳”的真实涵义吗?
试看另一个例子。在第68回,尤二姐和王熙凤相见时,王熙凤说她多次劝贾琏洁身自好,“别在外眠花宿柳”[10]2036。霍克斯的译文是not to go sleeping out“under the willows”(you know what I mean)both for his health’s sake[14]333。乍一看,译文是按照中文字面来翻译的,但是补充的一句you know what I mean(你知道我的意思)表明霍克斯完全明白“眠花宿柳”的意思,只是为了保持与原文一样的委婉:家丑不可外扬,妻子王熙凤不可能直接说贾琏嫖娼。因此,杨宪益夫妇“眠花宿柳”直接翻译成“to take good care of his health and keep away from brothels”[10]2037反而显得与原文风格不符。“远离妓院”(keep away from brothels)与“眠花宿柳”比起来,虽然更容易理解,但是实在是有点太粗俗。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le Proust)的著名小说《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第二卷《在少女身旁》(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按字面意思,英译当是 In The Shadow Of Young Girls In Flower,但是 C.K.Scott Moncrieff将之译为Within a Budding Grove[15]。笔者推断,霍克斯可能参考了此译文。因此,到底是译者错译了原文,还是读者误读了译文,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难有定论。
由此可见,有些误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误读,只是译者和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出发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而已。其实,《红楼梦》这两种译本都拥有各自的读者,如杨宪益所言,“喜欢他(霍克斯)的译本的人多一些,当然,也有人喜欢我们的译本”[16]159
(二)译者错解原意而导致错译
错译同样假定了一个正确的翻译。任何译者翻译某些词、某些短语或者句子,其译文可能只有一种,那么,与此不同的翻译都是错译,比如人名、地名的回译,行业通用规范用语等等。除此之外,某些翻译,独立地看也许是对的,但若置之于一定的语境中,却可能是错的。柯平[17]176曾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错译的原因,即“言内因素、言外因素以及译者有意或无意尊奉的翻译原则”。笔者认为,柯平所提到因“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而导致的错译,有些应该是归为“误读”一类,如“欠额翻译(翻译不足)”和“超额翻译(翻译过头)”。至于因译者的翻译原则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翻译,就更不能算是错译了。
大凡一个译者,不是本国文精通,就是外文精通,两样同等好的不多,像杨宪益夫妇那种中西合璧的情况毕竟太少。因此,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时难免看错原文而浑然不知。如思果[18]43所言:“英国汉学家 David Hawkes译的《红楼梦》英文好极,中国人不论英文写得有多好,也休想能跟他比,可是他看错原文的地方竟然不少,中国的学者大都可以指出。”翻译之难在于文化的不同。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动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附加在文字上的“超语言信息”——文化信息——具有民族性和群体共享性,在本族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但相对于异质文化而言却风马牛不相及。在不同的语言文本的转换中,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不可避免地部分失落,而另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则不可避免地大量进入,从而引起信息的变异与误读。对于具有一定语言功底的译者来说,翻译中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涵义。因此,译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中西方文化素养和翻译经验。有时候,翻译经验、成就可以使译者变得谦虚谨慎,有时候却相反,可以麻痹译者的理性思维,使他变得过于自信、自负,自以为不会出错,反而出了一般译者不会出的差错。只是有的译者不声不响,免得难为情;有的译者老实,自己提出错译、误译,并与读者商讨。这样的例子很多,一般读者都能指出不少。即使傅雷这样的翻译大家,也难免偶尔出现错译。他说,“误译的事,有时即译者本人亦觉得莫名其妙。例如近译《贝姨》,书印出后,忽发现原文的蓝衣服译作绿衣服,不但正文错了,译者附注也跟着错了。这种文字上的色盲,真使译者为之大惊失‘色’”[19]69。同样,霍克斯在《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朗,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就出现明显错译。
原文: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11]109
译文1:At next day’s session a group of well–known associates of the wanted man were brought in and subjected by Yu-cun to careful questioning.[20]117
译文2:The next day a number of suspects were summoned to court and Yucun cross - examined them carefully.[11]109
原文中“有名人犯”如何理解?是指“有名有姓的人犯”还是“臭名昭著的人犯”?霍克斯将“有名”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出名、知名”,故而将“有名人犯”译为“well-known associates”(见译文1),有人认为这是“误读误译”,此处“有名”应做“有名有姓”理解(管兴忠 马会娟[21]73)。其实两者都不对。如洪涛[22]290所言,“研读译文必须关注语篇的连贯性(coherence),而不宜只是孤立解读译文中的单词或词组。”看第四回,既然贾雨村是在状纸上“勾取”,那些“人犯”当然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人犯如何“勾取”、捉拿并询问呢?贾雨村初来乍到应天府,连本地的“护官符”都没有,当地的达官贵人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谁是“臭名昭著的人犯”呢?杨宪益简单地译为suspects(见译文2),避免了犯这类错误。但是,“有名犯人”到底如何理解?至今没有一个定论。裴效维[23]54校注的《红楼梦全解本》中将“有名人犯”理解为“列名于案件的人犯”,笔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还有一种解释是:
其实,这句话,体现了中文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简约性”,其实,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到了次日坐堂,贾雨村勾取了在状纸上列出的犯人名字,详加审问……”,“有名”是“列在状纸上的犯人名”的意思,也就是说,“有”是虚的,“有名人犯”=“犯人名”。这是中文里面一个特定的用法。( 裴钰[24]64-65)
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恐怕有待国学大师来解答。裴钰[24]65认为,“需要把隐含的意思一并翻译出来,才是正确的”。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无论裴钰做不做翻译,都应该知道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柯平[16]184曾对误解与错解作了区分:“错解原意时,译者自己对原文的理解是错误的;而使生误解时,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传达中不自觉地扭曲了原意,使读者对原文产生不正确的理解。”因此,以上的例子都应该归结于“错解原意”。中国译者在从事外译汉时常会出现“错解原意”的情况,而在从事汉译外时则往往会出现“使生误解”的情况;外国译者则恰恰相反。
三、结语
一方面,我们承认译者在阐释过程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译者主观性的过度张扬。错译无疑是应该避免的。但是,文化误读是一种复杂的翻译现象,出现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着语言、文化、心理、艺术传达等方面的“隔”,译者在审美理解和艺术表达上的误读是难免的。每一个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翻译只能限于自己的理解,但个人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同样,每一个读者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他对译作的评价也只能基于自己的理解。可以说,任何译作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误译的成分,只是有的误译(如文化与心理方面的误译)不易被察觉而已。对文化的不同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解读者的态度是认真的,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合理的解读,如今被证明是误读;今天正确的或者合理的解读在未来译者或读者的眼里也许同样是误读。传统观念把误读看得很重,往往把误读同翻译态度与翻译能力联系起来,或者把误读作为否定译者及其译作的依据。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是对文学翻译的本质与艺术规律的误解。世界文化史是各民族思想感情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历史。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翻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译文更接近“庐山真面目”。当然,在没有得到“正确的”阅读之前,你的误读若能引起一部分读者对原语文化的兴趣,吸引他们来学外文,读原作,真的起到了像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媒”的作用,那将是另一番风景了。文化差异会造成误读是事实,但误读并不能使翻译成为不可能。相反,几千年来的翻译都是在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误读与误译中前进的。文学翻译中因为文化原因所形成的误读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翻译。不管怎么说,作为文化活动的翻译还是必要且有利的。广而言之,任何阅读活动都是翻译,都是一种读者对作者文本加上本人前理解的再度阐释,在此过程中,变形与误读的现象在所难免。而且,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误读,才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如果强求要达到作者本人的原意,只准有一种解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学批评和翻译批评,这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1]季羡林著,季羡林研究所编.季羡林谈翻译[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2]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孙致礼.文化与翻译[C]∥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Gadamer,H.G..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The Continum Publishing Co.,1975.
[6]张德让.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1,(7).
[7]张隆溪.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J].复旦学报,2007,(5).
[8]让·贝西耶(法).小说误读与文化素材[C]∥乐黛云,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杨松芳.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J].社会科学家,2006,(6).
[10]许钧.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
[11]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中英对照本)[M].杨宪益,戴乃迭,译.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2]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II)[M].London:Penguin Group,1977.
[13]姜倩,何刚强.翻译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4]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III)[M].London:Penguin Group,1980.
[15]Proust,M..Within a Budding Grove[M].Translated by Scott- Moncrieff,C.K..New York:Modern Library,1951.
[16]金圣华.认识翻译真面目[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
[17]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8]思果.译路历程[C]∥金圣华,黄国彬.困难见巧.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19]傅雷.翻译与临画[C]∥刘靖之.翻译论集(修订版).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2.
[20]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I)[M].London:Penguin Group,1973.
[21]管兴忠,马会娟.试析霍译《红楼梦》(第一卷)不足之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
[22]洪涛.《红楼梦》译论中的孤立取义现象和“西方霸权”观念——兼谈霍译本的连贯和杂合(hybridity).红楼梦学刊,2011,(6).
[23]裴效维(校注).红楼梦全解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4]裴钰.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