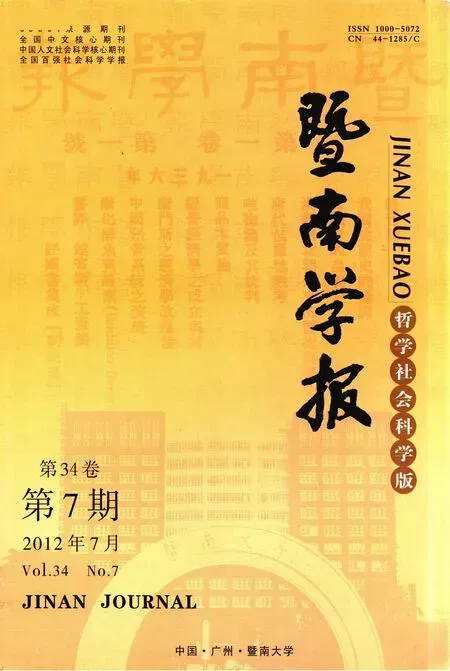明清拟话本小说中命相故事的理学观照
杨宗红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明清拟话本小说中命相故事的理学观照
杨宗红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明清拟话本小说中有很多命相故事具有丰富的理学意蕴。这些命相故事肯定命定论,但更肯定并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命相叙事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揭示命相与心相的关系,肯定心相的作用,艺术地表现了小说家对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思考以及对“致良知”的探究,是对理学的形象诠释。
命相;心相;命运;理学
命相是相术的一种,主要通过人的生辰八字及观察人体各个部分及其相关变化以确定人的富贵穷通、福祸寿夭等,故先秦时称其为“相形”,西汉则称之为“形法”、“骨法”。命相信仰在民众中广为流行,从《左传》和《国语》的记载看,春秋时命相就已经相当普遍。自宋以后,三教混同,理学关于“命”的思想对市民有深刻的影响。流行于市井坊间的拟话本小说也多载有命相这一民俗事项。据粗略统计,在头回或正话中,涉及命相的《拍案惊奇》11篇,《西湖二集》7篇,《型世言》与《喻世明言》各4篇,《二刻拍案惊奇》与《石点头》各3篇,《警世通言》2篇,《醒世恒言》、《清夜钟》、《珍珠舶》各1篇。若加上轮回转世、谪仙下凡、睡显真形和一些相关插入语,有关命相书写的就更多。明清拟话本小说命相书写虽然肯定命由天定,但因教化的需要,其重点转移到人物命运描写背后的善恶意蕴与自身努力上。小说通过命相书写,揭示命相与心相、命定与人力的关系,具有浓郁的理学特色。
一、命相书写与命定观
命相与命运相关。《辞海》释“命运”为“旧指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命运,即人对之以为无可奈何的某种必然性。”这种在广大民众中甚为流行的将命运看成是由某种客观的、外在力量掌控的,具有无法抗拒的必然性命运观,其理论基石乃是天命信仰、天人感应以及阴阳五行信仰和象数思维,它是人对自身命运进行探究的产物。
在古人看来,宇宙万物由阴阳五行组合而生,秉气不同,五行不同,则命也就有异。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道家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儒家主张要知天命。“命”也是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认为宇宙“无极而太极”[1]2,“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张载认为气聚为物,气为万物的本源“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寿夭之理,皆是所受定分。”[2]266朱熹释“天命之谓性”说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3]17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乃秉天地之正气而生,但人之气秉是有定数的,“死生有命,当初秉得气时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4]43。气之厚薄、强弱、精粗、清浊、混明等直接影响命的好坏:“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气之不可移易者。”[4]77当程朱理学成为官方之学,它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命相书之论与程朱之说在某些方面极为相似:
惟人禀阴阳之和,肖天地之状。足方兮象地于下,头圆兮似天为上。[5]159
人禀阴阳之气,肖天地之形,受五行之资,为万物之灵者也。故头象天,足象地,眼象日月,声音象雷霆,血脉象江河,骨节象金石,鼻额象山岳,毫发象草木。[5]48
人既受天地之气而生,天地之气不同,赋予人不同的相貌、气性与不同的命。《论衡·骨相篇》:“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6]36“神之清浊为形表,能定贵贱最堪论”[7]21“气乃人之本,察之见贤愚”[7]25。以此,从外形、气质、神态可看出人的寿夭祸福。在《朱子语类》中,朱熹认为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于水火,须在水火里死,合死于刀兵,须在刀兵里死。无论如何都逃不掉(卷五十九)。至于相书与理学命运观究竟是谁影响谁姑且不谈,但当理学通行,成为国家主权话语以后,相书关于命相之论则有了权威理论作支撑,命相信仰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合法性。由于相与命密切相关,小说关于命相书写的其中一种模式是:相士相某人而下断语——某人命运按照相士之言发展。这里一方面是相士相术之高,另一方面展示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如相国寺前一相士“极相得着,其门若市”,举子扣问得失,一一决来名数不爽[8]卷八;相钱镠之相士廖生,“善识天文,精通相术。白虹贯日,便知易水奸谋;宝气腾空,预辨丰城神物。决班超封侯之贵,刻邓通饿死之期。殃祥有准半神仙,占候无差高术士。”[9]廖生相钱缪“骨法非常,必当大贵”,相钟起的两个儿子“骨法皆贵”,将位极人臣,其后果然。再如:
(胡似庄相徐晞)“此位却不是吏道中人,他两颧带杀,必总兵权,骨格清奇,必登八座,虎头燕领,班超同流,鹤步熊腰,萧何一辈,依在下相,一妻到老,二子送终,寿至八旬,官为二品。目下该见喜,应生一个令郎。”[10]卷三一
(神相袁天罡相王媪)“此媪面如满月,唇若红莲,声响神清,山根不断,乃大贵之相!他日定为一品夫人。”[9]卷五
(严希几相长寿女)“……额有主骨眼有守精,鼻有梁柱,女人俱此男相。据此面部三种,以卜他具体三种,定然是个富贵女子。只嫌泪堂黑气,插入耳根,面上浮尘,亘于发际,合受贫苦一番,方得受享荣华。”[11]第六回
小说家在故事叙述时掺入的评论也表明命定论的流行。“俗话说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12]卷一“人算不如天算巧,天若加恩人不愚。”[13]人的命由天定,相也是天生的,因此命运与相貌是直接挂钩的。对此,李渔《无声戏》[14]第四回有一段议论:“相与命这两样东西,是造化生人的时节,搭配定的。半斤的字还你半斤的相貌,四两的八字还你四两的相貌,竟像天平上弹过的一般,不知怎么这等相称。若把两桩较量起来,赋形的手段,比赋命的更巧。”并引诗云:“从来形体不欺人,燕颔封侯果是真。”在同书第三回中他又说道:“凡人贵贱穷通,荣枯寿夭,总定在八字里面。这八个字,是将生未生的时节,天公老子御笔亲除的。”
在命定论下,相士的话最后都得到应验并且,小说中这些相士相人之术,都可以从一些相书如《麻衣相法》、《太清神鉴》、《玉管照神局》中找到依据。由此看来,小说家可能参阅了一些相命之书,对相命之术有一定的了解。
二、命相书写与气质之性、天命之性
古人相信天命,但并不否定人力作用,认为天虽然赋予人之命,但命运可以由自己把握。自天命而言,人之气禀得于自然界的规定,无可更改;自人而言,天命要通过人得到体现,人并非只是被动的命运承受者。所以,道家言“我命在我不在天”,人可以通过修炼得到长生。佛教因果报应论一方面肯定今生所受用的报并非天神赐予,而是自种因,自受果,显示出命运的可操控性。儒家更关注人的主体性,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作为,其道德命定论主张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尚书·伊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当人、事合于善,合于德,天赏之,反之,则罚。天赐人灾祸还是吉祥依人所行而定。荀子反对以面相取人,他在《非相》篇指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大小、善恶形相,非吉凶也。”[15]72-73王符《潜夫论·巫列》云:“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已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已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16]355决定人的祸福有两种因素,一者是“行”,指个人的行为;二者是“命”,它是由上天决定的。两者中,个人行为是主要,天命为次要。
理学家对命运更是积极。张载认为人的命运有“命”与“遇”之分。富贵贫贱乃是命,而努力之后结果不同则是“遇”与“气”,两者虽然相近,但却不同,人应知天命而尽人事①张载说道:“富贵贫贱皆命也。今有人,均为勤苦,有富贵者,有终身穷饿者,其富贵者只是幸会者也,求而有不得,则是求无益于得也。道义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张子语录上》)又说:“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犹难罪性,语气可也。同行报异,犹难语命,语遇可也。气与遇,性与命,切近矣,犹未易言也。”(《张子语录中》)。程颢说“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17]374,“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17]375理学中又一重要命题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命之性”论中,人物之性都是秉天所受,性即理,是道德理性之所在,与道一体;“气质之性”是欲望、情感之所在,它会遮蔽天命之性,只有“变化气质”才能恢复天命之性。前者自天而人,自上而下,天制约人,人从于天;后者自人而天,自下而上,人通过变化气质,达到与天一体。从天命之性而言,人秉气而生,受天地之气的影响,人的形态、气质、属性也就各有不同就气质之性而言,上天既然有道德属性,人可通过“痛下功夫”使偏塞之气复归于正,让命运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话本小说对命相的描写也反映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展示了人们“痛下功夫”的复性过程以及回归天命之性后的结果。求善要先修心,尽其心乃尽其性,天生的相敌不过后天的修为“凡人道见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见瑞而纵恣者福转为祸。见妖而骄侮者,祸必成;见妖而戒惧者,转祸为福”[16]378。不管本身命相如何,只要修德戒欲,见妖而戒惧,自然无祸有福。相法有云:“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心随相减。”心即性、即理、即气②二程、朱熹、王阳明“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都有所阐述。朱熹说:“盖本然之行,只是至善。然不以气质而论之,则莫知其有昏明开塞,刚柔强弱,故有所不备。徒论气质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则虽有昏明开塞,刚柔强弱,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尝有异故其论有所不明。须是合性与气观之,然后尽。盖性即气,气即性也。“(《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九)),心修则气变,气变则命变。有心为善,自有善相随之而生,如为恶则恶相也因之而生。《钱氏私志》载唐一行论相云:“若其人忠孝仁义,所作所为,言相相应颠沛造次,必归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言行不相应,颠沛造次必归于恶者凶人也。吉人必获五福之报,凶人必获六极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若但于风骨气色中料其前途休咎,岂能悉中也。”[5]438《西湖二集》卷二四通过周必大命运的改写揭示了人力修为在命运当中的作用。周必大“长身瘦面,脸上只得几根光骨头,嘴上并无一根髭须,身上又伶伶仃仃,就如一只高脚鹭鸶一般。”按相书,这的确不是什么富贵之相,连周必大自己也这么认为。周必大将近五十岁方举进士,初生子,才做安府和剂局门官,可以说是有其相而有其命。
似此看来,周必大必定潦倒一生。然而,周必大却以善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邻里失火,延烧数百家,以失火延烧之罪累及数十人。周必大弃一官而救之。“人果可救,我何惜一官?况舍我一顶纱帽,以救五十余人之罪,我亦情愿。”为此感动神灵:“周必大阴德通天,当为人间太平宰相,惜骨格穷酸,难登显位。”为此赐予帝王须一部。有此帝王须,骨格穷酸的周必大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
既然命运不排除“心”的作用,相逐心生,小说中关于相与命的另一模式是:相士相某人而下断语——该人做了某事——相士见其貌而重下断语。《拍案惊奇》卷二十中,刘元普年过六旬还无子女。相士相刘元普之气色,言他非但无嗣,寿亦在旦夕。后他多行善事,不但生二子,还寿至百旬。《雨花香》载,一人刻薄,相士相他百日内当死。这人在高僧指点下,广行善事,寿登百,并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上述之人因行善而改了穷酸的命运,罗隐则因一句话而由贵相变成贱相,丢掉了半朝帝王之命。《西湖二集》卷十五中,一相士相罗隐有半朝帝王之命,此时罗隐刚好借贷不着,于是言道:“可恨这些贼男女恁地奚落,若明日果有帝王之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定要把这一干人碎尸万段,方雪我今日之忿。”因此言,罗隐贵骨被换去,于是“天庭偏,地阁削。口歪斜,鼻子塌。皮肤粗,猴狲脚。吊眼睛,神气撒。远观似土地侧边站立的小鬼,近看一发像破落庙里雨淋坏滴滴点点的泥菩萨。”形貌与原来的贵相有天壤之别。形貌改了,半朝帝王之命也随之而改。相士再见罗隐时的一段话即表明了气与心、相的关系:
(相士解释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举心动念,天地皆知。汝若举一点杀心,便毒雾妖氛弥漫宇宙,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天怎么得不知道?相逐心生,心既不好,相亦随变,此是必然之理。
人秉气而生,心与气相连,理是气之理,性是气之性,心的活动影响自身之气的运行,进而影响到周围之气的流转。罗隐动一点杀心,便使“毒雾妖氛弥漫宇宙,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自然被上天知晓。《二刻拍案惊奇》卷八中,相士言丁湜气色极高,便言其当“第一人及第”该中“状元”。丁湜好赌,后再见那相士,相士大惊,言其气色大变,连中榜也不可能了。“相人功名,先观天庭气色。前日黄亮润泽,非大魁无此光景,所以相许。今变得枯焦且黑滞了,那里还望功名?”并断言丁湜做了欺心之事。丁湜悔过,才中了第六名。
这些命相书写主旨趋向对“心”的重视天心即人心,“举心动念天知道”实质是“心”知道,心是一身之主,小说家欲通过故事的形式让被遮蔽的“气质之性”重归于“天命之性”。“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于气,性命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2]23倘若不修德,则“性命于气”人只能被动听从“天”的安排,但若修德,使“德胜于气”,则“性命于德”,以“天地之性”作为道德的根据,人可以成为命运的主人。所以,周必大、刘元普以德胜,他们把握了自己的命运,罗隐与丁湜因“德”不够,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权,当他们意识到败德之害,立马改过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自己的命运。
三、命相书写与修身俟命、致良知
在小说的命运改写的故事中,除了当事人知道自己命运之后,主动修行以避害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主人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走向但仍一心“循天理”、“致良知”,最后命运发生改变,二是知道自己命运格局,但不以为意,率“性”而行,命运因而发生改写。以理学的观点看,前者属于“修身以俟命”,后者属于“致良知”。
在阳明心学看来,修身俟命是属于较低层次的,他认为“夭寿不贰其心”的目的只是要人一心为善,“夭寿不贰其心”,实际上是有“夭寿贰其心”在前,因此,“为善之心犹未能以一”,“若曰夭寿皆有命定,吾但一心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若曰俟之云者,则尚未知天命之所在。”又说“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侯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18]44。有“修身俟命”之心,则修身并非一心为善,有未知天命的成分。《喻世明言》卷九入话中有一段议论涉及到“心相”:“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贵相之人,也有做下亏心事,损了阴德,反不得好结果。又有犯着恶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积阴功,反祸为福。此是人定胜天,非相法之不灵也。”“面相不如心相准,为人须是积阴功。假饶方寸难移相,饿莩焉能享万钟?”《无声戏》第四回也有类似的话:“相貌生得好的,只人不做歹事,后来毕竟发积,粪土也会变作黄金”,“就是相貌生得不好的,只要肯作好事,一般也会发迹,饿莩也可以做得财主。”贵相人做亏心事,非顺命而行,非知命者;做善事为求好报,也是非知命者。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重要命题。阳明认为修身有阶段性,修身俟命如同婴儿襁褓阶段,存心事天属童稚之年,尽心知天属年力健壮之人。由于“身的主宰便是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良知存在于人的本心,不需向外去求。虽然良知人人有,但常常为私心物欲所蔽,只有从心上下功夫,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去尽“障碍窒塞”,恢复和发扬良知,致良知阶段已具备“修身俟命”在其中。《喻世明言》卷九中头回言裴度少年时,相士相他“纵理入口,法当饿死。”后来他拾到玉带,还了孝女,使她救了父亲。结果裴度“骨法全改,非复向日饿殍之相”,终于出将入相,大富大贵。《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一写王部郎家的小厮郑兴儿,相士衰尚宝说他犯了恶相,会妨主。王部郎将兴儿辞退,兴儿在外拾到一大包银子,将其还给了失主因这善行,郑兴儿“满而阴德纹起”,“骨相已变”,最终做到指挥使。
裴度知道自己的命运,但不以为意,只是想到“此乃他人之物,我岂可损人利己,坏了心术?”是非之心一起,便有了还带之行,知行合一,“良知”实实落落而致。郑兴儿想到自己命本该穷苦而且妨主,想到意外之财关着他人命运,关着阴鸷,故等失主来领,将一念之善落到实处。再如《无声戏》卷三中的蒋成事事不顺到“活神仙”处算命,得知命局极为不好,为了打发蒋成出门,“活神仙”胡乱将其八字给改了。蒋成“不敢欺公作弊,地方上的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做了刑厅的心腹,但“不曾做一件坏法的事,不曾得一文昧心的钱”,并扶持刑厅做好官。小说结尾作者议论道:
要晓得蒋成的命原是不好的,只为他在衙门中做了许多好事,感动天心,所以神差鬼使,教那华阳山人替他改了八字,凑着这段机缘。这就是《孟子》上“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究竟这个八字不是人改,还是天改的。又有一说,若不是蒋成自己做好事,怎能够感动天心?就说这个八字不是天改,竟是人改的也可。
阳明心学主张“如一念发在好善上,变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变实实落落去恶恶。”[18]119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将“致良知”落到实处。发于事亲,就在事亲上做功夫,发于事君,就在事君上做功夫,发于处贫贱富贵、处患难夷狄,就在处贫贱富贵、处患难夷狄上做功夫。裴度、郑兴儿、蒋成等,都知道自己命相不好,其行善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发自于本心的良知,并将这良知在日常生活中去落实,通过做功夫达到心之本体。在“致知”中,他们超越了生死忧患荣辱沉浮,充分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由于将道德作为实践的先天根据以及将良知视为宇宙万物本体,视为终极实在,道德良知成为一种信仰。这种将至善良知作为终极目标之学被范曾视为为己之学[19]。无论是成圣成王,还是因善恶报应观的影响而求善,“破心中贼”的为己之学的确可以达到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
概而言之,话本小说中有关命相、八字等民俗事项并非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受到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影响,是对宋明理学的形象阐释。命相书写以善恶报应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是“适俗”,通过“适俗”实现小说的商业追求;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即以广泛存在于民众中的信仰,引导民众破除“心中贼”,达到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而这,正是“警世”、“喻世”、“醒世”、“型世”的目的所在。
[1]周敦颐著.周濂溪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朱熹.中庸章句[C]∥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顾颉.相术集成[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7]倪岳撰.麻衣神相真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8]凌濛初.二拍刻案惊奇(卷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9]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陆人龙,编,陈庆浩,校点.型世言(卷三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1]天然痴叟,著,弦声,校点.石点头(第六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2]凌濛初.拍案惊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3]周楫纂,陈美林.西湖二集(卷二四)[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4]李渔著.无声戏[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6]王符.潜夫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7]程颢,程颐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9]一字圣典:善——范曾谈中法圣贤王阳明和笛卡尔[J].人民论坛,2010,(24).
I242.3
A
1000-5072(2012)07-0128-06
2011-04-15
杨宗红(1969—),女,湖北恩施人,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规划基金项目《民间信仰与明清话本小说的神异叙事研究》(批准号:11YJAZH11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批准号:2012M511880)。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