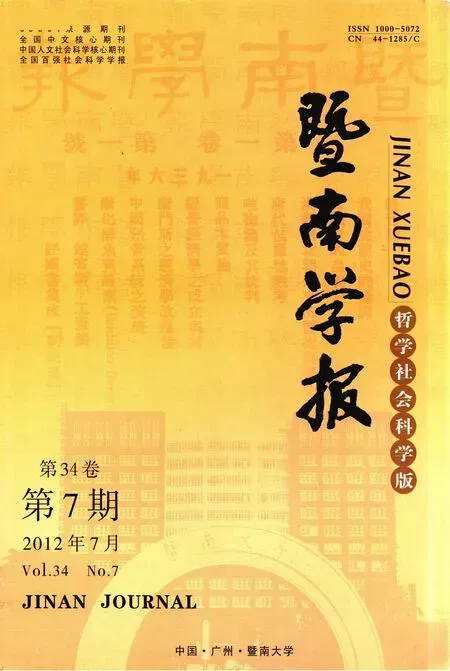国际法的历史解读——评《国际法史论》
康 丹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2)
国际法的历史解读
——评《国际法史论》
康 丹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2)
在宏观上,《国际法史论》从具体国际法史实分析到理论学说述评层层深入地展现了一幅国际法史的全景图;在微观上,它通过三条线索,尤其是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交叉研究,以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心和国际事件为中心,展示了国际法是如何在历史现实中运作并发展演变的。由此也可见国际法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国际法史论》;国际法史全景图;国际法律文件;国际事件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史的交叉研究,是晚近国际法学的重要趋势之一。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杨泽伟博士新近推出的《国际法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版,以下简称“《史论》”)堪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不但绘制了一幅国际法从远古时期的萌芽到21世纪初国际体系转型时期的历史演进的全景图,而且从不从层面对国际法进行了深刻的历史解读。
一、宏观构图:国际法史全景图
从宏观上看,《史论》不论是整体架构还是章节组成都浑然一体,从而以严密的论证结构为读者展示了国际法史的全景图。
(一)全书整体架构
从整体上看,除去绪论,《史论》正文的六章可以分解为三大块:(1)前四章分别对国际法的萌芽以及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阶段的国际法发展史进行了分析阐述;(2)第五章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预测;(3)第六章对中国国际法及国际法学史进行了整理概括。这三个部分之间是有着必然的逻辑先后顺序的:首先必须通过第一部分从古到今对国际法史进行梳理,理清了国际法发展的基础、脉络,找出了发展的规律,然后才能顺着这一脉络并借此对规律的认识来对国际法未来的发展趋势加以判断和展望,而只有认清了国际法的发展规律及其整体上的发展趋势之后,才能在这一整体背景下对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评判,进而对我们应如何对待国际法、如何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努力作出指导,即落脚于中国国际法实践以及国际法研究这两方面的具体问题上,从而使得史学的基本功能得以实现。
(二)章节组成层面
如前所述,上述三个部分各自内部又是循着一定的史学研究具体方法的思路来展开论述的。
第一部分国际法史阐释的四章的共同思路是,从史料分析到特点总结,再到编纂和学说评述。例如,第三章现代国际法首先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著者分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苏联、《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日内瓦议定书》、《洛迦诺公约》、《非战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日意法西斯的侵略与国联的制裁、《慕尼黑协定》这十个史实为主题对现代的重要的国际法事件或文件进行了个案分析,探讨了相关事件或文件在国际法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也就是本阶段国际法史的主要内容。然后在这些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著者用一节归纳总结了现代国际法三个特点:(1)集体安全制度的初步形成;(2)国际司法制度的渐趋健全;(3)中立制度的新发展。最后两节著者分别对现代国际法的编纂和现代国际法学进行了评述。可见,著者循着从具体史实分析到抽象一般规律的思路对现代国际法史进行了全面的阐释,这也是史学研究一般过程和方法在《史论》中的具体体现。类似的,除了第一章“国际法的萌芽”缺少特点总结和国际法编纂两部分之外,各章都是以这一思路来展开阐述的。
第二部分,即第五章“当代国际法发展的新趋势”,其下辖的五节内容也是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性的,可以说它充分体现了在做预测性研究时候应遵循的一般思路。为了科学地预测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前景,著者在第一节对国际社会基本结构的新变化进行了阐释,这实际上是对国际法未来生长发育的土壤进行了勘测;然后第二节对当代国际法发展的新趋势进行了总结,这些已经显现的趋势是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性起点,无论未来国际法有怎样的飞跃性发展,它都必须起步于此、脱胎于此,而绝不可能完全斩断与已有国际法发展苗头之间的联系,因此这些新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起到了决定作用的;如果说前面两节是国际法发展的实然层面状况,那么第三节关于当代国际法的应有价值和时代使命的论述,则是对当代国际法应然追求的表述,推动国际法的发展既要立足于现实,以免根基不牢发展不稳,同时也要仰望星空放眼高远,以免消极放任和方向错误;再之后第四节关于影响当代国际法新发展的三个因素(科学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分析,则是对除国际社会基本结构这一根本性大环境之外的其他客观条件的分析,这些因素虽然不一定能起主导作用,但是对国际法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快慢是有相当作用的,因而也必须重视。在对大环境、起点、目标和影响因素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就是预测性研究的一般思路)之后,著者指出了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国际法将更受重视、并将逐步摆脱强权政治的束缚。
第三部分,即第六章“中国与国际法”,是《史论》在宏观上的落脚点:认识和指导中国国际法实践和研究。这一部分从宏观上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中国国际法史和中国国际法学史当然国际法史部分又内涵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遗迹和近、现、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实践两部分。在这里,著者基本上是按照世界层面的国际法史的思路对中国国际法史进行分析阐释的——即先分析史实,再评述学说,在此基础上,本章落脚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国际法学研究的反思和评价,进而从方法论和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两方面,对今后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史论》作为学术著作最具体的现实意义之一。
综上所述,《史论》在宏观上不但以外在的恢弘笔法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宏大全面的国际法发展史的全景图,总结了国际法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进而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而且其内在的精巧论述结构也可以为读者进行学术思维的洗礼。这两方面就是《史论》在宏观上的价值所在。
二、微观雕琢:国际法研习的现实之门
相对于宏观上侧重国际法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有助于一般性学术思维培养这两方面价值而言,《史论》在微观上则是通过三条线索将国际法(学)和国际关系史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国际法研习者和实践者形成认识国际法所必须的知识体系。这三条线索是:(1)结合国际关系史来阐述国际法史;(2)以学者、学派及东西方或国别为对象类别来阐述国际法学史(国际法学说史);(3)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及学说史总结。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前两条是国际法制度史和国际法学说史(或可谓“国际法理学史”)即理论联系实际来认识国际法,第三条既可视为结合中国实践认识国际法,同时也可以视为对如何将国际法运用于中国外交实践和法学研究的探讨,即国际法在中国的实践。简言之,三条线索是多层次地将国际法理论联系实际。从内容上的这一有机结构来看,《史论》可以说是暗含了一个有机的认识结合国际关系(史)、法理学来认识国际法的知识体系。而这其中,首要的就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史的结合研究。
结合国际关系史来研究和阐释国际法并非《史论》首创,相反,众多国际法史著作或者一般国际法学著作都采用此法。而《史论》的特点在于其论述的清晰度和详细度。这样的例子贯穿全书、俯拾即是,尤其从对近代国际法的论述开始。笔者认为可以总结出如下两个模式。
(一)以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心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国际会议特别是其产生的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心的论述。例如,在论述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中,著者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中心展开论述时,其基本结构是:先简述作为该和约前奏的三十年战争概况,理清战争的实质,特别是参战各方亦即和约的缔约各方的参战目的以及战争结局;以上述国际关系史实为前提,著者再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介绍,在此读者稍加思考就能发现,此条约的内容即是上述战争目的和结局的反映,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上述两层分析为基础,再着重分析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是以上述和约内容发展出来的。如此,著者实现了从国际关系事件(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国际法律文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再到国际法发展这一脉络的梳理,这是笔者所谓的第一个模式。类似的,书中关于其他国际法律文件或者国际会议的论述,基本也采取了这一模式。
如上所述,在这一模式中,著者论述的连结点是国际会议及其所产生的国际法律文件,它们都是相关时期、一定范围内国际关系史或者国际法发展的总结: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对三十年战争的总结;《凡尔赛和约》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非战公约》是对此前战争合法性问题的总结;人权两公约是对人权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洛加诺公约》和《慕尼黑协定》是凡尔赛体系存续的转折,等等。这些国际关系史上的总结或转折性文件,同时也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
从直接推动的意义上看,一方面,这些国际会议文件中大多有着相关国际法原则、规则、制度的规定,可谓是相关国际法的条约化或者说成文法化;另一方面,采取国际会议缔结条约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本身,也是国际法实践的重要形式。而不论是相关原则、规章制度的成文法化,还是国际法实践,都直接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从间接的意义上看,这些标志着历史总结或者转折的文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例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林立的国际体系,世界从此进入了近代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史阶段——这可谓正面的作用;《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尽头,而后二战黑云压城城欲摧,而从更大的视界来看,二战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是《凡尔赛和约》不公导致的后果——这可谓负面的作用。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它们共同的效果是都推动或者标志着国际关系的质变,从而为国际法的发展翻新了土壤,萌发了国际法发展的新希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后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法新时代。
(二)以国际事件为中心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关于会议之外的国际关系事件为中心的分析。例如,针对古巴导弹危机,著者先论述了事件的大致过程,即苏联在古巴安置中程导弹被美国侦察发现,随即美国采取隔离措施,迫使苏联放弃安置计划。然后着重分析该事件中涉及的国际法问题及其影响:隔离措施的性质(集体安全措施抑或自卫权)以及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从国际事件到其中的国际法律问题,再到其对国际法的影响的模式。简言之,即对国际事件进行国际法层面的分析。
在这一模式中,国际事件成了国际法发展的催化剂:正是由于国际事件中出现了新情况新的呼声、观点——或者既存国际法规定在此面临实践的检验了——从而带来了对既存国际法规定的拷问和挑战。如上述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的隔离措施即可视为对集体安全制度和自卫权规定的挑战。类似的例子有:十月革命带来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主要既存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法的革新;二战的惨烈激起了新自然法在国际法领域的兴起;科索沃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干涉冲击了原有的关于武力使用和干涉内政的规定;伊拉克战争中预防性自卫与先发制人战略对传统的自卫权规则构成威胁,等等。在经历过了这些冲击或者挑战,相关问题的答案在相当范围内被国际社会再度认定和接受之后,既存的国际法规定或是为新的理念所取代而得以发展,或是战胜新的理念而进一步得以巩固。而无论结果如何,此过程中的论战以及实践操作均丰富了国际法的实践和理论,因而在整体上都是对国际法的发展。
总之,如上的“国际事件+国际法律文件+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和“国际事件+相关国际法律分析+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两模式的共通之处在于:其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作了结合分析,让读者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国际关系史实中的体现,而不再是孤立地对待两者。在这两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中可以归纳出议定条约、制定规则的经验,重点在于如何制定稳定、有效的规则要领;第二种模式则可以总结出运用规则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重点在于如何维持各方的平衡,从而最佳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或许还可以实现国际法所追求的某种普世价值和利益。由此,《史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法进行了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研究。而在历史维度上进行这样一种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意义是:它以历史发展为脉,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联系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将偶然性状况扩大为必然性规律的误读。同时也有着熟能生巧的效果,认真思考的读者,或可以从中总结出某些普遍性规律,从而更好地掌握之。
三、商榷之所在
尽管《史论》有着如上的诸多可取之处,但毕竟书无完书。且不说史学研究本身就存在着必须经受不同时代检验的问题,即便从通常意义上看,笔者也认为有值得商榷和可以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关于国际法史特点总结问题。笔者认为《史论》还可以在三个层面增加对国际法发展史特点的总结:第一,对国际法萌芽阶段的特点有必要总结,因为这一时期的国际法比较简单,因而能最简单明了地反映国际法到底是应何种需要而生的,进而可以从必要性的层面探寻国际法的本质;其二,对中国国际法发展史也可以进行特点归纳,这样有助于认识中国国际法实践和研究的正反两方面意义;第三,在总体上可以对国际法史四阶段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应能发掘出国际法史总体上的特点,这其实也就是抽象出国际法史的总体规律,虽然第五章关于国际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阐述或暗含了这种总体规律,但是笔者认为从阶段性特点到总体特点进行归纳,可以得出更具理论性的结论。
(二)对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史)结合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适当进一步加强对两者联系的论述,原因有二:一是此为本书最重要的特色,值得加强;二是这种研究本身就可能蕴含着极有价值的前景,甚至超越“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这一直接的效果。这一点在对第一条线索的分析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此不赘述。
(三)对于上述三条线索之间的联系可以尝试加强阐述。就前两条线索而言,笔者认为学者或流派、国别的国际法思想,或也是与一定时代的国际关系背景相联系的——尽管强弱或有不同——而这种联系正是学者或者相关实践者看待和实践国际法的纽带,即决定了国际法(学)的观点和实践中的作为——即便这种纽带可能甚至必然是多元化的,但是这种决定作用对于国际法而言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因此值得探讨;就第三条线索而言,笔者认为除了论述方式上的一致,它相对于前两者更为孤立,是否可以将前两者分析的成果更积极地运用于对我国国际法实践的评价当中去,从而得出更客观的认识?
(四)相对前两条线索而言,第三条线索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加强。这部分的论述是相对比较单薄的。比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实践的论述就只涉及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承认、国家继承、国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几个方面,而且基本上这些方面均可视为中国国际法实践中的成功之处。这里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参与国际法实践的历史相对较短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也似乎有偏颇之嫌。而通常而言,对教训的反思,有时比对经验的总结更为重要。更何况中国在近代有着长期的弱国无外交经历,新中国又经历了相当时期的极左思想误导,在这两类特殊背景下,或多或少存在着有价值的教训或者说另类的经验,笔者认为这些都值得考究。
(五)外文资料的采用方面尚有所欠缺。《史论》丰富的中英文史料和国内外学术界最新的科研成果,既增强了该书论述的论证力度,又增加了可读性。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语言的限制,德文和法文资料的采用略显不足,对苏联/俄罗斯、日本的国际法学研究也不够全面。当然,这种在个人专著中要求同时实现多种外文资料的采用和吸收,也是有相当难度的,或许只能从科研组织的层面上寻求解决。
当然,正如吕思勉先生在介绍自己读书方法时所指出的,“……这不关乎书的好坏。再好的(书),也不能把一切问题,包括无遗的,至少不能同样注重。这因为著者的学识,各有其独到之处,于此有所重,于彼必有所轻。如其各方面皆无所畸轻,则亦各方面无所畸重,其书就一无特色了。无特色之书,读之不易有所得。然有特色之书,亦只会注意于一两方面,而读者所要知道的,却不是以这一两方面为限的。这是读书之所以要用几种书互相参考的理由。”[1]324正如这段话所言,笔者这里所指出的商榷之处,有些或是著者有所侧重所致,因而此处指出,并不一定是对《史论》相关论述的否定,因此希望读者集思广益,细细揣摩以自得其意。
四、对于国际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国际法史的研究存在诸多困难
国际法史的研究具有高度专业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存在诸多困难,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提高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包括专业的国际法学和历史学知识跨学科研究技能,熟练的多语种研究能力,国内外历史资料的获取、整理能力,以及持之以恒认真审慎的治学态度。通过历史学和国际法学的专业教育,掌握娴熟的法学和史学研究技能是进行国际法史研究的基础。
(二)国际法史研究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虽然面对诸多困难,仍应进一步加强国际法史的研究。一方面,如上所述,国际法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国际法史方面的论著实在太少笔者对著名的英文学术刊物《国际法历史学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发现该刊物最近5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之中只有一篇来自中国学者(杨泽伟,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a's Confucianism in the 19th Century: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第13卷)。在专著方面,《史论》也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为数很少的国际法史著作此外,从现实需要角度看,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其外交实践亟需相关的实践经验来指导工作,以便为国家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国际法史研究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引导
鉴于国际法史研究的困难及我国国际法史研究的现状及潜力,笔者认为需要更好地组织和引导国际法史研究。具体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努力:第一,加大资金投入,增加相关研究项目的立项;第二,开展相关的研修班及学术交流活动,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扩大人才储备;第三对国际法史研究进行总体规划,比如进行国际法制度史、学说史等分类研究,古代、近现代、当代的分段研究,以及分国家进行国别国际法史研究或者分地区或者分文化类型进行国际法史研究。总之,要进一步挖掘我国国际法史研究的潜力,还需要加倍努力。
[1]吕思勉,著,张耕华,编著.大家小集:吕思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D90
C
1000-5072(2012)07-0156-05
2012-06-24
康 丹(1983—),男,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公法研究。
[责任编辑 李晶晶 责任校对 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