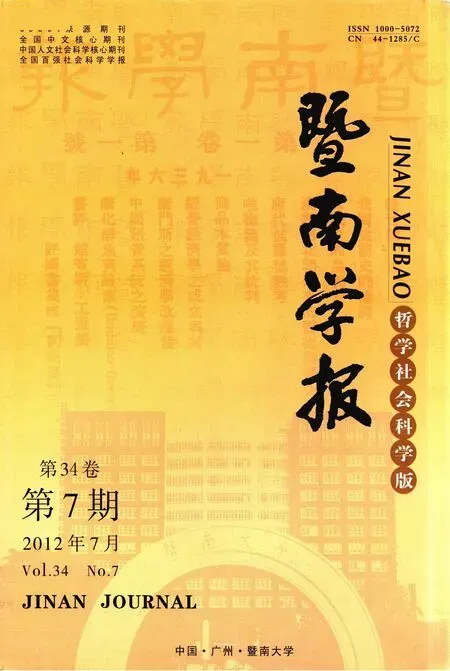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法律性质论
陈咏梅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法律性质论
陈咏梅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这是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世界第三个最大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CAFTA的全面达成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增长,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CAFTA的名称暗含着中国与东盟整体之间的协议,但由于东盟不具备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没有缔约能力,因此,CAFTA实质上是中国与东盟各个成员国间的双边协议的集合。CAFTA的这一法律性质定位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及CAFTA义务的履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CAFTA;东盟;缔约能力;法律人格;法律性质
亚洲地区已经存在许多自由贸易协议①从1998年到2006年年初,亚洲地区已经签署了15个自由贸易协定,2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过程中,还有至少16个正在计划筹备中。See David Pilling.ADB chief hits out at“noodle bowl”trade[N]Financial Times(Asia),2006 2 9.。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或ASEAN)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CAFTA)毋庸置疑已成为该区域最引人瞩目的自由贸易协议。该协议以2002年11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为发端,伴随中国与东盟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争端解决领域一系列子协议的缔结,2010年,中国-东盟已建设成为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贸区。
一、CAFTA的历史进程
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进行法律性质的探讨,首先必须了解其历史进程。CAFTA由一个《框架协议》和四个子协议构成。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建议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就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0月公布了其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为在二十一世纪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与东盟应建立全面的战略性的经济合作体系。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框架协议》②《框架协议》载东盟秘书处的官方网站www.aseansec.org/13196.htm。,为最终在2010年前与东盟的六个老成员国(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2015年前与其他四个新成员国(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奠定了基础[1]124。随后,2003年10月6日,缔约各方又在巴厘岛召开的年会上通过了《框架协议》的修改议定书①《框架协议》修改议定书载 w ww.aseansec.org/15157.htm。,对原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框架协议》对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贸易自由化的临时措施及以后的谈判议程做出了规定。在协议书中,11个缔约国(中国与东盟十国)承诺增进合作,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②参见《框架协议》第1条b项。,这意味着CAFTA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尤其重要的是,缔约各方一致同意通过以下措施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1)在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中逐步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2)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3)建立开放和竞争的投资机制,便利和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投资;(4)对东盟新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5)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中,为各缔约方提供灵活性,以解决它们各自在货物、服务和投资方面的敏感领域问题,此种灵活性应基于对等和互利的原则,经谈判和相互同意后提供;(6)建立有效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化海关程序和制定相互认证安排;(7)在各缔约方相互同意的、对深化各缔约方贸易和投资联系有补充作用的领域扩大经济合作,编制行动计划和项目以实施在商定部门/领域的合作;以及(8)建立适当的机制以有效地执行本协议③参见《框架协议》第2条。。
为使各缔约方尽早享受到任一缔约方,主要是中国所给予的优惠待遇,增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信心,《框架协议》还在中国与东盟还未就全部货物的降税安排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规定了“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 Program),就一部分产品用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幅度先行降税。“早期收获”计划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启动,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最先实施的降税计划。
四个子协议中最为突出的是货物贸易和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协议。2004年10月,中国和东盟就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取消清单及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谈判,同年11月29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老挝万象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署了两项历史性的协议,即《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④《货物贸易协议》载 w ww.aseansec.org/16646.htm。(以下简称《货物贸易协议》)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⑤《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载 w ww.aseansec.org/16635.htm。(以下简称《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是仅次于《框架协议》的CAFTA的第二个重要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从2005年7月始,中国和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开始逐步削减商品关税,到同年7月20日,仅就正常产品⑥根据《框架协议》,货物贸易产品除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其中正常产品近7000种,占整个中国-东盟贸易量的90%以上。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的区别为:正常产品的关税要削减直至取消,敏感产品的关税受到上限的约束,但不必取消关税。而言,中国和这六国间40%税目的关税已降至0~5%,截至2007年1月,60%税目的关税已降至0~5%。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间超过90%的产品实现了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2]。《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则代表了中国和东盟贸易关系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它为解决中国和各个东盟成员国间的贸易及投资争端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该协议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方式用以解决中国-东盟国家间的经济争端,以避免各成员寻求单边措施及报复性措施。在随后的2007年和2009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相继签署,分别规定了在服务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安排。
国际制度在实践中能否有效运行是衡量该制度功能的重要标准[3]41。要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能够有效运行,明确其法律性质是必要的。要厘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法律性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国际条约及其缔约者。
二、CAFTA与国际条约
(一)CAFTA的国际条约属性
对于上述已签署的协议,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协议是否是国际条约?如果是,是多边条约、区域条约抑或双边条约?我们知道,条约是现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据有关国际法学者统计,“现在,一个大国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的数目,平均每天不止一个”[4]1。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于1969年5月23日在维也纳签署,1980年1月27日生效。第2条规定:就适用本公约而言,称“条约”者,谓国家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议,无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无论其特定名称为何。也就是说,一项协议要成为条约,其应当是国家间的书面的且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协议。该规定将条约的主体仅限于国家,随着国际社会实践的发展,这已远远不能满足在国际社会中被承认为国际法主体的国际组织参与条约缔结的现实需要。因此,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1986年《维也纳公约》)②《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于1986年4月21日在维也纳通过,但至今仍未生效。将缔结条约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公约规定:“条约”指(1)一个或更多国家和一个或更多国际组织间,或(2)国际组织相互间以书面缔结并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协议……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的解释,“以国际法为准”意味着根据国际法创设义务的意图[5]12。由此可知,无论国家还是国际组织都能够缔结国际条约并进而创设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义务。
具体而言,CAFTA,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作为一项规定缔约各方贸易、投资方面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律文件,其毫无疑问地当属于国际法所称之“条约”。至于其缔约主体,则仅从字面上看,中国和东盟这一国际组织是CAFTA的两个缔约方,然而,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这一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中国是CAFTA的缔约一方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东盟这一国际组织能否成为CAFTA缔约方则值得商榷。因为尽管国际组织是条约的主体之一,能够缔结条约或协议,但其缔约能力与国家不同。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每一个国家都有缔约能力。与之相反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有缔约能力。国际组织的缔约能力是有限的,其只能在特定条件和特定的范围内缔结条约成为条约的主体,不同的国际组织其缔约能力的范围甚至其是否具备缔约能力均有所不同。因此,要对东盟这一组织是否为CAFTA的缔约方做出准确判断,首先应对国际组织的缔约能力进行研究,并进而认定东盟这一组织是否具备条约的缔约能力。
(二)国际组织的缔约能力
国际组织的缔约能力是指国际组织具有以自己的主体资格与国家、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法主体达成具有国际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简言之,也就是国际组织以自己的主体资格与同为国际法主体的他方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6]37。作为现代国际生活中促成各国合作的一种有效的法律形式,国际组织的缔约能力与该组织是否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密切相关[7]7。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马尔科姆·N·肖在其撰写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一个国际组织是否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取决于该组织的性质、其实际拥有的职权及其在具体活动中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尤为重要的因素包括该组织与国家及其他组织交往并签订条约的能力,以及法律的授权。这些因素在国际法上被称为“法律人格的要件”(the indicia of personality)[8]241。
国家是国际法最初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主体,其法律人格来源于把独立(或主权)和平等视为国家最基本特征的国际社会体系[8]189-193。因此,国家具有完全的法律人格,缔结条约是其行使国家主权的一种方式,缔约能力是国家所固有的天然主权的一部分。因而,从理论上讲,只要不违背国际强行法的规定,国家行使该种权力就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国际组织则不同,国际组织仅仅是一种拟制的法律人格者,其法律人格是不完全的、是派生的,其各项具体权能,包括缔约能力在内,均具有派生性,这种派生性决定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及缔约能力是有限的。国际组织人格的取得首先取决于建立该组织的法律文件之规定,正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所言,如果国家试图赋予国际组织以法律人格,则该组织的组织文件中就应有相关规定,并且这种规定对该组织的法律人格具有决定性作用[8]1187-1188。然而,有必要注意到,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虽然组织文件毫无疑问是某一国际组织缔约能力最重要的来源,但组织文件中缺乏法律人格和缔约能力的明确规定并不必然导致该国际组织丧失缔约能力。国际法院在其意见中还认为:在任何法律体系中,各法律主体在它们的性质上或在权利范围上不一定相同,而它们的性质是取决于社会需要的[9]178。国际法院进而指出,诸如联合国一类的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其组织文件所明示或默示规定的以及在实践中加以发展的其自身的宗旨和职能[9]178。一言以蔽之,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和职权并不必然来源于组织文件,即使组织文件中没有相关规定,这些法律特征也可通过其他条约、组织成立后的活动、成员方直接或间接的授权以及法庭对法律人格和职权是实现该组织宗旨所不可或缺的认可而加以证明。
(三)东盟的国际法律人格
普遍观点认为,CAFTA,或者说至少CAFTA的《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这一区域组织的区域性协议。然而,这种观点若是经过对国际法及东盟本身的法律与政策文件进行严密分析则不得不引人质疑。
由于东盟松散的组织结构及其法律人格的未决性,且根据该组织的法律文件对该组织职权的规定,东盟无法成为一项国际条约(如CAFTA)的缔约方。东盟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因此其法律人格和职权主要由其组织文件决定。东盟是1967年8月8日根据五个原始成员国间签订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①《 宣言》文本载www.aseansec.org/1629.htm,五个成员国家分别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成立的,该《宣言》又称《曼谷宣言》,是建立东盟这一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根本条约。《宣言》包括五个主要条款,规定了若干合作的基本原则。虽然缺乏具体规定,但该《宣言》列举了联盟成立的宗旨和目的,并且为执行这些宗旨建立了一套制度,因此《宣言》仍被认为超出了仅仅是对“合作意愿的宣告”[10]34,成员方随后的行动,包括为逐渐增强东盟的组织特性而签订的一系列政治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表明了东盟是一个拥有若干职权的国际组织②1967年《宣言》以后签订的主要政治协定包括1971年11月在吉隆坡签署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1976年2月24日在巴厘岛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1992年7月22日在马尼拉签署的《东盟关于南中国海宣言》,1995年12月15日在曼谷签署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1997年12月15日在吉隆坡公布的《东盟2020展望》以及2003年10月7日在巴厘岛签署的《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亦称《第二巴厘宣言》)。。然而这些组织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东盟的法律人格,也没有涉及它的缔约能力。
东盟前秘书长Rodolfo C.Severino将该组织的使命归纳为:1967年,东盟的创立者们意图使东盟成为东南亚所有国家为共同利益自愿合作,并以经济、社会和文化和平发展为首要目的的联盟[11]。然而,他进一步指出,实现这些目的并不意味着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东盟组织机构,东盟不是也无意要建立一个独立于各成员的超国家机构。它没有具有立法权的区域性议会或部长级会议,没有执行权,也没有司法系统[11]。华盛顿东西方研究中心主任穆提亚·阿拉加帕随后指出,现有东盟制度和安排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2]22-24:第一,东盟缺乏一个统一的决策机制。它目前主要充当一个对话平台的角色,实质上该组织并没有中央决策机构;第二,协商一致的决策方法适用于所有事项、所有层面,这极大地减少了东盟内部成员国合作的效率;第三,东盟极其强调的轮换原则弱化了秘书长的作用,东盟秘书长往往被各国的政府首脑边缘化;第四,东盟的组织结构集中反映了各成员国的利益及国家代表权,与之相对应,东盟这一团体利益的代表权却没有相关规定;第五,东盟依赖的基础只是一个政治体系,而没有司法制度。
总之,东盟创立者的本意是将其设计成一个结构松散的组织,以顺应该区域的文化环境为由,为成员的某些行为提供运作的空间,尤其是在人们认为区域合作和团结一致至关重要之时,东盟的存在可以让各成员因具备这样一个组织而很有面子[12]22。更为关键的是,创立东盟并不是为了使其成为一个权力机构,而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间的区域联盟,在这个层面上,东盟仅仅是一个各成员国进行合作的平台机构,而不是一个国家共同体[10]29。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推动区域和国家间的和平、进步和安全,这些目标通过建立一个社会共同体更易实现,而不是一个法律共同体[10]29。因此,东盟成员国无意也不愿使东盟这一组织具备独立的、完全的国际法律人格,具备缔结条约的能力。然而,仅据此就判断东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及缔约能力仍然为时过早。
如前所述,即使组织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可以从该组织的职权、宗旨及其活动中推断而来。但从东盟的对外交往活动来看,东盟也无法援引该规定而获得法律人格。在晚近数年间,东盟与很多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对话关系,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盟,并且,外国国家和地区正在逐渐倾向于把东盟当作一个共同的整体来处理[10]37。然而,东盟却没有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好国际法上的“认可”原则,相反,它似乎在进行“法律人格的选择性活动”(selective exercise of legal personality)。近年间,许多与外国签订的重要协议都由东盟十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分别签字,而不是由东盟作为一个组织代表所有国家签字,这些协议包括与中国、印度、日本三国分别签署的《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框架协议》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修改议定书》,后者将允许上述三国作为非东盟国家分别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之相反的是,涉及某一特定领域事项的协议则相对而言被视为不太重要
因而可以由东盟的秘书长签字,例如,《中国农业部和东盟秘书处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就是在2002年11月2日由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齐景发与时任东盟秘书长的Rodolfo C.Severino共同签署。另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协议则是《中国政府和东盟成员国政府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协议亦由时任东盟秘书长的Ong Keng Yong与中方代表于2004年1月10签署。如上所述的“法律人格的选择性活动”无法充分支持东盟具备国际法律人格及缔约能力这一结论。从前文所述的两个谅解备忘录的名称可以看出,东盟秘书长的代表权很有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安排,而不是有权机关的常规活动
即便退一步说,假设东盟这些“法律人格的选择性活动”能被国际社会认可,并据以认定东盟具有法律人格、具备缔约能力,那么这实际上反而印证了一个事实,即东盟成员国与外国签署的那些“重要协议”,包括与中国、印度及日本的框架协议,并不是这些国家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组织签署的,因为事实上这些协议在签署时不是由东盟这一组织代表成员国签字,而是所有东盟成员国与该外国分别签字署名的。因此,无论上述哪种情况,CAFTA都不是中国与东盟这一独立实体之间的双边协议。
三、CAFTA法律性质定位
CAFTA协议看似中国与东盟这一区域性组织之间的协议或中国与东盟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更为准确的说法则是CAFTA是中国与各个东盟成员国间签订的双边协议的集合。
这一观点可被《框架协议》的文本及权利/义务结构所证实。《框架协议》文本及其他附件的规定表明,中国的义务,如“早期收获”计划项下的义务,都是针对各个国家个体的,并且,虽然规定有时采用“东盟各成员国”这一术语,把其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但此种用法只是出于方便的考虑。理由如下:在《框架协议》的序言部分,CAFTA的缔约方宣称,《框架协议》由以下主体签署: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与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以下将其整体简称为“东盟”或“东盟各成员国”,单独一国简称“东盟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①参见《框架协议》序言,第1段。可以注意到,在此处,十个东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名字都作为缔约方出现在《框架协议》中。在《框架协议》的最后部分,只有11个国家的首脑在协议上签字,而没有东盟代表的签字。
序言的第三段在写到成员方期望通过《框架协议》所达到的目标时,将“中国与东盟”整体称为“各缔约方”,单独提及东盟一成员国或中国时称为“一缔约方”②参见《框架协议》序言,第3段。。毫无疑问,所用这些表达都表明了各缔约方的目的是使这11个主权国家成为《框架协议》的缔约方。
《框架协议》的核心在于其第六条,该条规定了“早期收获”计划。不同于其他条款旨在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的机制,第六条规定了实体权利及义务。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这些义务对各缔约方均具有约束力。第六条允许东盟各成员国以优惠关税将HS编码第一章到第八章的产品出口至中国,其中主要是农产品。作为互惠,中国产品也应以优惠关税出口至东盟。但基于部分东盟成员国对某些产品实施市场准入存在困难,中国对这些国家采取了单边优惠,即允许这些国家将该部分产品作为“早期收获”计划的例外产品,不必参加先期降税。总之,各个东盟成员国都可以提交一个农产品的例外清单,豁免该部分产品的市场准入义务。此外,中国还同意对东盟成员国的130种工业品给予单边优惠,这些国家可以将一些前八章以外的产品也列为“早期收获”产品,提交一个特定产品清单,中国对清单所列产品仍然给予关税优惠待遇③东盟成员国提交的产品清单规定在《框架协议》附件2中。。享受该优惠的特定东盟成员国也应当给予中国一些优惠待遇,但是,其给予的优惠无需建立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上。
在互相给予优惠的规定上,《框架协议》最初遵循了区域主义的路径,使得《框架协议》更像是一个区域协议。这主要体现在:根据“早期收获”计划,除依《框架协议》第6条第3款(a)(ⅰ)规定的例外清单上的农产品外,各个东盟国家不应当只给予中国产品优惠待遇,还应对其他东盟国家产品给予同等的优惠。但由于菲律宾在“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前仍未与中国谈判达成一致,其拒绝签署“早期收获”协议④直至2005年4月,菲律宾才决定参与“早期收获”计划。,而马来西亚不愿将其与中国达成的“早期收获”计划惠及菲律宾,于是马来西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其只对中国提供“早期收获”计划待遇。这一措施随后通过2003年对《框架协议》进行的修订被纳入修改议定书中,这极大地改变了CAFTA关于农产品的相关规定,使其由区域主义向双边主义方向发展。修订后的《框架协议》通过对第6条第3款(b)(ⅰ)的修改强化了这种实践,新的规定为:(1)一缔约方可以根据本条单方面对其他缔约方加速降低关税和/或取消关税:(2)一个或多个东盟成员国也可以根据本条与中国开展加速降低关税和/或取消关税的谈判并达成加速降税的协议。另外,这种被减损了区域协议效力的规定也体现在《框架协议》第6条第3款(a)(ⅲ)的规定中:本协议附件2中所列的特定产品应涵盖在“早期收获”计划中,这些产品的关税减让应仅对附件2中列明的缔约方适用。这些缔约方必须就该部分产品相互提供关税减让。到目前为止,只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根据《框架协议》的第6条第3款(a)(ⅲ)提交了“特定产品”清单,这些国家,加上后来的文莱和新加坡,仅是参与“早期收获”计划的东盟成员国的半数而已,另一半的东盟成员国并不受该条款约束,无需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框架协议》只规定了若干关于谈判协商CAFTA的原则,但其对CAFTA本身的性质并未明确,这个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取决于东盟这一组织的性质。如果东盟无法直接依据组织文件的相关规定或是间接通过其实践活动证明其具备法律人格,则CAFTA不应被视为是中国与东盟这一组织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综上所述,东盟这一组织不具备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其不是CAFTA的缔约方,CAFTA是中国与东盟各个成员国签署的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集合。
四、定位CAFTA法律性质的法律后果
CAFTA不是中国与东盟这一组织签署的协议的结论将会对许多重要事项产生影响,包括该组织及其成员国各自对第三国(此处仅指中国)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当发生由该协议引发的争端时。
与国际法律人格相伴的是义务和责任问题,然而,国际组织参与的条约是否对该组织的成员国产生效力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国际法律难题。在上述1986年《维也纳公约》的谈判过程中,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约文草案。针对该问题,草案规定,满足以下条件时,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得受该组织缔结的条约之约束:(1)该组织的成员国基于组织的组成文件已经一致同意受该条约之拘束;并且(2)国际组织成员国受条约之有关条款拘束的同意已经适时通知各谈判国和谈判组织[8]859。该规定对国际贸易协议,如区域性组织签署的关税协议等具有重要价值,例如欧盟与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的协议等。正如马尔科姆·N·肖所评论的那样,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如果不是立即对其成员国产生拘束力,则该条约将毫无价值[8]859。然而,即便得到欧盟的强力支持,该草案条款在维也纳会议上仍被弃置未予通过,事实上,该条款最终被该公约第74条第3款所取代,该款规定,如果某一国际组织是某一条约的当事方,本公约各项规定不将预先判断任何基于条约下国际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而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
如今,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对其成员国的法律效力问题应“在有关国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在个案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加以解决”[8]860,这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际组织不同的是,欧盟不仅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执行社会、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共同政策的能力,还具备紧密的组织结构。在国际社会实践中,欧盟经常依据其组织文件的直接授权代表其成员国行事。另外,欧盟本身也是WTO的一个独立成员,是全球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欧盟作为一个独立参与方,代表各个成员国共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已经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社会实践①例如,可参见欧盟在“Appellate Body Report,EC—BananasⅢ”案中的实践。。
然而,东盟与欧盟并不类似。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东盟是否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还未明确,并且由于其缺乏决策机制及执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更似一个政治对话的论坛。在所有与外国国家签署的正式协议中,东盟所有主权国家的代表都必须出席并且各自签署相关协议,而不是由东盟这一组织代表代为行使各成员国的签字权利。CAFTA《框架协议》的文本及其规定的权利义务结构也证明了这一点,即《框架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直接由各缔约国享有,并且这些权利义务只在中国和各个东盟成员国间或特定情况下在各东盟成员国相互间适用。这一规定对CAFTA义务的履行及其争端解决将产生深远影响。CAFTA的缔约方,即名义上的11个国家,就承诺义务对彼此承担责任。在此意义上讲,CAFTA看似一个区域协议但实质上是一个双边协议的集合。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CAFTA主要规定了中国和各个东盟成员国间的双边权利与义务,并在特定范围内涵盖了东盟成员国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对东盟成员国而言,如果CAFTA规定的互惠待遇并不高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待遇,则CAFTA在其相互间的关系方面将显得毫无价值。
义务的双边性尤其反映在CAFTA的争端解决上。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主要解决中国和各有关东盟成员国间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东盟成员国相互间因违反协议义务而引发的争端,其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解决中国与东盟这一组织整体间的争端。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其不得不追踪每一个东盟成员国,要求履行承诺的贸易、投资等义务。对东盟而言,东盟只是主张各个成员国履行条约义务,其仅可以提供政治上的善意支持,而无法提供法律帮助,要求各个东盟成员国履行义务。根据东盟现有的组织结构,东盟一方面无权要求其成员国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负责的救济措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东盟又无法承担起对中国的义务和责任。进一步说,东盟,其本身不是CAFTA的一个缔约方,也没有权利要求中国对所有CAFTA成员履行所有CAFTA义务,除非中国在某一方面对CAFTA所有成员做了相关承诺。
五、结 语
我们从CAFTA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了CAFTA的法律性质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中国-东盟《框架协议》以及其他子协议的迅速签署代表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史上划时代的成就,从此,双方的经贸关系开始向自由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CAFTA中以法律义务形式规定的“超WTO”(WTO-Plus)关税减让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推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CAFTA这一名称虽然暗含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协议或者说中国与东盟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区域性协议,但是,事实上,这是对CAFTA法律性质的误解。由于东盟没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并且CAFTA是由各个主权国家分别签署的,因此CAFTA实际上是一个由11个成员国共同缔结的双边协议的集合。同时,CAFTA的这一法律性质也将对其法律义务的履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1]Jiangyu Wang.China'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The Law,Geopolitics,and Impact o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J].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8).
[2]中国外交部.中国—东盟合作:1991-2011[EB/OL].(2011-11-15)[2012-07-12].http:∥www.gov.cn/gzdt/2011-11/15/content_1993964.htm.
[3]孙志煜.国际制度的表达与实践——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为样本的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4]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5]Fourth Report on the Law of Treaties[R].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965,(2).
[6]万鄂湘,石磊.论国际组织缔约能力的法律依据[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
[7]梁西.国际组织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8]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9]Reparation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Advisory Opinion[R].ICJ Reports,1949.
[10]Paul J.Davidson.The Evolving Leg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M].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2002.
[11]Rodolfo C.Severino.Asia Policy Lecture:What ASEAN is and What It Stand For[R].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University of Sydney,Australia[1998-10-22].
[12]Muthiah Alagappa.Institutional Framework,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s[C]∥The 2ndASEAN Reader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4.
Analysis on the Legal Nature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HEN Yong-mei
International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By January 1,2010,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has been formed,which is the third largest free trade area in the world after the EU and NAFTA,and is the largest free trade area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has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romoting the economic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At first glance,CAFTA seems to be an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s an independent entity.Since ASEAN has no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ality as well as the treaty-making power,it is the fact that CAFTA is a collection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China and individual ASEAN members.The legal nature of ACFTA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ACFTA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d will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FTA obligations.
CAFTA;ASEAN;treaty-making power;legal personality;legal nature
D99
A
1000-5072(2012)07-0008-08
2011-09-20
陈咏梅(1969—),女,四川南充人,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重庆企业投资东盟市场法律风险与防范研究》(批准号:11SKC09)。
[责任编辑 李晶晶 责任校对 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