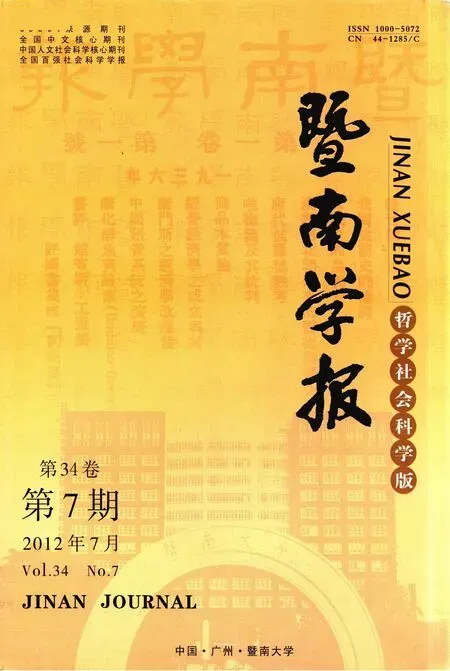论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明道意识
向 回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51)
论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明道意识
向 回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51)
《琴操》组诗创作是韩愈作为思想家自觉的修辞立言行为。此行为在表达韩愈怨恨失意之情绪及乐道守操之品格的同时,也实现了其以具体言论阐明自己道德理想并以此来影响世人的政治用途,可谓之为“诗以明道”。他之所以于古乐府中独选十首《琴操》进行摹拟创作,则是因为这些上古琴歌以音乐歌诗形式向后人透露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成型而稳定的士人人格类型,传达了仁亲爱民的政治思想,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
韩愈;琴操;本事;明道意识
一
韩愈为文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力求词必己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其诗歌创作亦复如此,多自道己意,不甘蹈袭前人。但其集中《琴操》十首却是个特例,这组以蔡邕《琴操》所载之古琴操曲名为题而创作的琴歌,完全是传统的文人拟乐府。它们创作方法相类,均先以小序言明所依本事,继之以歌辞来增衍此事;整体风格相似,均明显使用代人言情的叙述口吻,拟古色彩很浓。这显然与韩愈生平主张与行事颇多抵牾,故前人对这组作品的评价也就呈现出两个极端。誉之者极为推崇,无以复加,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谓:“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1]187讥之者则极为贬斥,如章士钊曰:“夫题如《琴操》,辞出名手,非摹古诗,即肖骚辞,非诗非骚,抑又何物?试为譬之,直兽类中之四不像耳。”[2]1173郑樵《通志·乐略》亦谓:
今观琴曲之言,正兔园之流也,但其遗声流雅,不与他乐并肩,故君子所尚焉。或曰,退之之意,不为其事而作也,为时事而作也。曰,如此所言,则白乐天之讽谕是矣。若惩古事以为言,则《隋堤柳》可以戒亡国;若指今事以为言,则《井底引银瓶》可以止淫奔,何必取异端邪说、街谈巷语以寓其意乎?同是诞言,同是饰说,伯牙何诛焉?[3]911
显而易见,这些不同态度源于不同的评论角度。严羽就乐府古题创作的角度而言,认为韩愈的创作非常得体;章士钊从纯诗歌创作入手,认为此组诗没必要作。至于郑樵,其论乐府以声为主,认为“君子之于琴瑟,取其声而写所寓焉”[3]910,而韩愈《琴操》组诗的创作,非但不重其声,其立意也多取法于本事与古辞,自然会为郑樵所诟病,讥为私塾教授学童所用的兔园册子。这两个极端的看法,均拘囿于歌辞的文字层面。但韩愈这一组诗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行为,故而单纯从乐府歌辞或诗歌创作层面对其进行评论,不深入到这一组诗的特殊创作背景,去探究作者的创作目的,根本无法对其作出正确评价,也难以真正地把握其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
二
对韩愈《琴操》十首的创作背景,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认为是韩愈“入潮以后,忧深思远,借古圣贤以自写其性情也”[2]1142-1143。后人多数也都认同这一说法。那么,这一组诗创作究竟抒写了韩愈怎样的性情呢?这就需要将《琴操》中所载各曲古辞与韩愈拟辞作下比对。
韩愈《琴操》十首中借古圣贤自写性情的因素,在许多歌辞中都有所表现。如《将归操》,相传为孔子之赵闻杀鸣犊而作,《琴操》所记该曲古辞只有“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4]25四句,透露了一种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似的情感。《孔丛子·记问篇》所记之歌辞前面比此多出了“周道衰微,礼乐陵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凤鸟不识,珍宝枭鸱。眷然顾之,惨然心悲。巾车命驾,将适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鱼。临津不济,还辕息鄹。伤予道穷,哀彼无辜”(《将归操》诗后注)[2]1144十八句,书写了夫子自知道穷的无奈。《水经注》所记之辞则与此完全不同:“狄水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将归操》诗后注)[2]1145再来看一看韩愈的拟辞: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将济兮,不得其由。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我济而悔兮,将安归尤?归兮归兮!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2]1144
相较而言,韩愈之辞与《水经注》中所载更加相合,均在借水起兴,主要体现了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处世哲学。纵观韩愈的仕宦生涯,可知其并不顺利,《进学解》中自谓是“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5]46-47。现在他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难免会产生出虑人忌害的思绪。歌辞中“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的顾虑及无与石斗、无应龙求的态度,虽是孔子口吻,未尝不是其进退失据的自我心态写照。
再如《拘幽操》,乃文王拘羑里时的忧愤之歌,《琴操》所载古辞与韩愈拟辞在所表达的情感上出入较大:
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无故桎梏,谁所宣兮。幽闭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勤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仓皇迄命,遗后昆兮。作此象变,兆在昌兮。钦承祖命,天下不丧兮。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4]28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2]1158
按,就《诗经·大雅·荡》中“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6]851诸句观之,文王并不以殷纣为圣明,《琴操》所录古辞对该曲本事的叙述也证明了这一点。再者古辞之末尚有文王训子之“钦承祖命,天下不丧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诸语,这些都可见出文王对殷纣的态度,绝不会有韩愈拟辞中“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用意。结合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正名定罪,万死犹轻”[7]617等语气观之,拟辞在想象文王拘幽之困境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在自责,是他贬居潮州时自我性情的抒写。
《残形操》一曲无古辞留存,相传曾子昼卧,梦见一狸,见其身而不见其首,故有是曲。韩愈拟辞在叙述曲调本事之余,亦道尽了心中的彷徨:
有兽维狸兮,我梦得之。其身孔明兮,而头不知。吉凶何为兮,觉坐而思。巫咸
上天兮,识者其谁。[2]1170
狸身明而头不知,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是“叹明王不作”,王元启则认为“推之事亲交友,及学问中崇德辨惑之事,无所不通。若就鲁国而论,或叹三桓僭妄,亦未可知”(《残形操》诗后注)[2]1170-1171。此二说就曲调本事而言,立论无据;就韩愈拟辞而言,亦未中肯綮。陈沆《诗比兴笺》则将韩愈此诗创作与“贾谪长沙,问吉凶于鵩鸟;屈放江南,托古筮于巫咸”(《残形操》诗后注)[2]1171之行为作比,认为其辞明示放臣之感,颇能道出韩公真实心迹。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而潮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咫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7]618,环境十分恶劣,时时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与死神为伍,以致生发出“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7]620的哀嚎。所以,借《残形操》本事中所透露出来的未知情绪,来表明自己一时的彷徨失据,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说上面分析的三首歌辞主要体现了韩愈被贬潮州时怨恨失意之情绪的话,《猗兰操》与《龟山操》则主要体现了他坚守礼义、乐道而不失其操的品格。
《猗兰操》一曰《幽兰操》,相传乃孔子伤不逢时而作,其古辞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4]26在这首古辞中,孔子因幽兰之不得其所而生发出“世人暗蔽,不知贤者”的感叹,在韩愈拟辞中,更多的却是对幽兰品格的赞美: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2]1148
在这首拟辞中,韩愈显然是在以猗兰与荠麦自比。猗兰隐幽谷而弥香,荠麦处霜雪而独茂,这是其固有之本性;君子不逢时而益自修古道,这亦是其固有之品格。歌辞虽以孔子口吻出之,但实亦是韩愈自道。它在表达对孔子居乱薄之世而仍能不失操守之品格认定的同时,也表明了自我心迹。
《龟山操》相传乃孔子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谏不从而作,其古辞云:“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4]26体现的是孔子面对季氏专政,欲诛之而不能的无奈。但韩愈拟辞在立意上显然又多了一层:
龟之氛兮,不能云雨。龟之枿兮,不中梁柱。龟之大兮,只以奄鲁。知将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归余辅。[2]1152
分析可知,拟辞虽也以龟山蔽鲁喻季氏专政,其末句“周公有鬼兮,嗟归余辅”却是拟孔子希望周公显灵助己归辅其君除奸之口吻,流露出自己矢志不渝之忠心,这同时也是表达自己渴望政治清明的愿望之辞。
三
上面所分析的几首歌辞,其创作虽不拘囿于古辞,但绝不脱离本事。它们在抒写韩愈被贬潮州时怨恨失意情绪的同时,亦体现了他坚守礼义、乐道而不失其操的品格。而这正是韩愈要借《琴操》中所载之十曲来写其性情的直接原因。在古代文人传统的情感倾向中,操为古琴曲类别之一,以操为名的琴曲,主要就是抒发作者虽内心穷苦忧愁而又能不失其操守的品格。刘向《别录》曰:“君子因雅琴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后汉书·曹褒传》注引)[8]1201桓谭《新论·琴道》曰:“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9]64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其遇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失其操者也。”[10]293所以,以《琴操》曲名为题进行创作,是韩愈被贬潮州时自我心迹的表白,也是其复杂情绪的一种释放。
但是,如果结合韩愈一生的行事与理想来看,则又可以发现其《琴操》组诗的创作还有更深层的目的。韩愈一生,以维护儒家道统为职事,这已是学界共识,不赘。《孟子·尽心上》中所提出的“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1]890-891等士人品格要求,一直都是韩愈的行事准则。在《争臣论》一文中,韩愈传达了“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12]112-113的思想;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又表达了不得意则“作唐之一经”的远大志向,这些都是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言论的最好注脚。因为在韩愈看来,君子在不得其位、不能兼济天下之时,就当修德立言,以自己的人格和言论影响他人。《琴操》组歌的创作,既是韩愈争臣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实现“作唐之一经”志向的努力方向,即通过这一组歌的创作实现自己修辞明道的目的。而韩愈所明之道,就是以历代圣贤思想与行事为核心的儒家理论。因为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等人思想行事为代表的儒家道统已经失传,①在《原道》一文中,韩愈构造了一个圣贤迭相递绪承接的儒道系统:“尧以是(按:即儒家道统)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第18页。所以韩愈才要致力于恢复之。又因为韩愈所作《琴操》十曲之本事无不承载了其一生致力于恢复的儒家道统思想精华,故其《琴操》组诗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其修辞以明道之争臣论的具体实践,具有切实的明道意识。
这里说韩愈所作《琴操》十曲之本事承载了儒家道统思想的精华,是可以逐一论明的。前文已分析的五曲歌辞,抒发了韩愈被贬潮州时的复杂心情,但其本事亦同时传达出了儒家的思想精髓。如《将归操》中孔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13]303的处世原则,是儒家思想中的士人品格规范;孔子拒入赵国以示对赵简子杀鸣犊之不齿,则又体现了一种“君子讳殇其类”的仁者情怀。再如《猗兰操》体现了孔子逢乱世而不失其操的品格规范,《龟山操》体现了孔子伤政道陵迟、闵百姓失处的忧国忧民情怀,这些也都是儒家思想中需要弘扬的士人品格规范②当然,韩愈《拘幽操》拟辞中“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痛悔语,既不合文王之意,似乎亦不合孔孟之道。因为在儒家君臣关系论中,武王谓纣为“独夫”,孟子解释武王伐纣行为是“但闻武王诛一夫纣耳,不闻弑君”,孔子则提出君君臣臣的政治思想。这些都是对君臣关系提出的一种君信臣忠、君不信则臣不忠的双向要求。君不像君,臣自然无须尽臣之义务。韩愈敢于在佞佛的唐宪宗面前骂历代佞佛之君都是短命鬼,这无疑体现了他的斗士性格,是合于儒家道统思想的。不过,儒家同时还讲究中庸之道,且唐宪宗总体来说在中唐还算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而不是一个站在儒家对立面的昏君。当韩愈因其不讲方式的直谏触怒宪宗而被贬潮州时,他难免要在君臣关系上寻求一种妥协。诚如欧阳修所云:“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虽韩文公不免此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第617页)所以,韩愈拟辞中出现这种痛悔语,与其《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正名定罪,万死犹轻”之用意一样,主要是抒写其贬居潮州时的困顿心情,与他《琴操》组诗整体用来明道并不矛盾。。至于本文尚未分析的五首作品,其本事与歌辞亦无不体现了儒家道统思想的精华,以下亦逐一分析。
《越裳操》相传为周公相成王时因越裳重九译献白雉而作,其本事体现了一种天下和平、万国和会的政治秩序,这正是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王之德,更是儒家对统治者德政的期待。该曲古辞较为简单:“於戏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4]27这显然是周公口吻之谦辞。而韩愈之辞却立足于本事,以自己的想象,传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于彼为?自周之先,其艰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后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临孔威,敢戏以侮。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2]1155-1156
于此可见,韩愈之拟辞虽也模仿周公口吻,揣摩周公心迹,其义却并不在归功文王之自谦,而是重在阐明一种贤人治国、雨施物孳的政治理想。这是周公治国的实际行为,也是韩愈理想的政治格局。
《岐山操》一曲,其创作本事历来说法大都一致,但其作者则有周太王所作、周公为太王作及周大臣所作三种说法③郑樵《通志·乐略》中还有“或云周人为文王所作”的说法,不知何据。或许“文王”为“太王”之讹。,韩愈认为是周公为太王作。《琴操》记其本事与古辞云:
《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恻隐,不忍流洫,选练珍宝犬马皮币束帛与之。狄侵不止,问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者,所以养万民也,吾将委国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无君?”遂杖策而出,窬乎梁而邑乎岐山,自伤德劣,不能化夷狄,为之所侵,喟然叹息,援琴而鼓之云:“狄戎侵兮土地移,迁邦邑兮适于岐。烝民不忧兮谁者知?嗟嗟奈何,予命遭斯!”[4]28
这里的古辞是以周太王口吻对狄戎侵略而被迫迁徙之事发出的哀叹。但韩愈拟辞之主旨并不在此: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将土我疆。民为我战,谁使死伤?彼岐有岨,我往独处。尔莫余追,无思我悲。[2]1161
《岐山操》本事传达的是周太王之仁恩恻隐、不忍众民为己死伤的民本思想,这是儒家思想中“仁”的精神,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4]212以及《孟子·尽心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5]973等以民为本的思想相合。分析可知,韩辞更多的还是传达一种希望统治者仁恩恻隐的理念,是对该曲本事中所体现出的民本精神的挖掘,这也是韩愈所固有的一种政治思想。
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为上古圣贤,其行事代表着儒家政治理论与人格修养的最高价值取向,故韩愈取这几曲制词,自然和其倡导恢复儒家道统紧密相关。而相传为伯奇所作之《履霜操》、陵牧子所作之《别鹤操》及犊(一作独)沐子所作之《雉朝飞操》,其本事则蕴涵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故这几首歌辞的拟作,也是其倡导恢复儒家道统的具体实践。据《琴操》所言,《履霜操》之本事体现了一种孝子之德: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曰:“伯奇见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为人慈仁,岂有此也?”妻曰:“试置妾空房中,君登楼而察之。”后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缀衣领。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逐,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王。宣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遂射杀后妻。[4]29-30
伯奇之事关乎孝行,而孝为儒家所大力提倡之道德内容。《论语》中有不少谈及“孝”的言论。如《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6]18“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6]27《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7]66韩愈拟作《履霜操》以吟咏其本事,正是因为该曲体现了儒家伦理所推崇的孝道。
同时,在儒家伦理道德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孟子·离娄上》。东汉赵歧注此一语时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孟子正义》卷15,第532页。。《琴操》对陵牧子《别鹤操》(韩愈集中作《别鹄操》)一曲本事的记载,体现的正是儒家伦理中的这一内容:
《别鹤操》者,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妻闻之,中夜惊起,倚户悲啸。牧子闻之,援琴鼓之云:“痛恩爱之永离,弹别鹤以舒情。”故曰《别鹤操》。后仍为夫妇。[4]30-31
陵牧子《别鹤操》主要抒发的虽是主人公别妻之悲,但于后人来说,这件事情本身则又体现了儒家道统中的人伦之厚,是合于礼教要求的。韩愈此诗有明显的议论倾向:“巢成不生子,大义当乖离。”[2]1168诗中所言之“大义”,指的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孝义。韩愈对《别鹤操》一曲本事的这种情感把握,在唐人思想意识中是很普遍的。白居易《和微之听妻弹〈别鹤操〉,因为解释其义,依韵加四句》云:“义重莫若妻,生离不如死;誓将死同穴,其奈生无子。商陵迫礼教,妇出不能止。”[18]464把陵牧子的出妻当做是礼教制度下的无奈之举。而唐佚名所撰之《灌畦暇语》①《灌畦暇语》一卷,三十二条,不著撰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书中皆自称‘老圃’,‘唐太宗’一条独称臣,称皇祖,知为唐人。‘蒲且子’一条,称‘近吴道元亦师张颠笔法’,又引韩愈诗二章,云‘后来岂复有如斯人’,则中唐以后人也。”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20,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03页。对《别鹤操》一曲本事的评价,更可以看出中晚唐时文人对陵牧子改娶一事的看法:
老圃曰:古者娶而无子,大义当出。虽然人之所以为人者,由其情隐于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匡床是同,一旦而以为胡越,宁不慨然。潘安仁初丧其偶,作为哀永逝之词,而赋悼亡之歌。夏侯湛见而叹曰:“是文生于情欤?将情生于文欤?”览之喟然,令人增伉俪之重。由是以考商陵牧子之撰,其亦可以厚人伦者矣。[19]10
于此观之,韩愈选取《别鹤操》一曲制辞而对其本事加以吟咏,显然也是因为该曲蕴涵了儒家的道德传统,有补于人伦之教化。
至于相传为独沐子所作之《雉朝飞操》②东汉扬雄《琴清英》中谓《雉朝飞》乃卫女傅母作,所言之本事与《琴操》迥异。韩愈所取为《琴操》中的说法,只是将“犊沐子”作“牧犊子”。,《琴操》对其本事亦有详细记载:
《雉朝飞操》者,齐独沐子所作也。独沐子年七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飞雉雌雄相随,感之。抚琴而歌曰:“雉朝飞,鸣相和,雌雄群游于山阿,我独何命兮未有家,时将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4]30
适时婚姻体现的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男有分,女有归”[20]582,使男女各得其所,婚姻不失其时。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序》中谓“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21]1967,韩愈在其《原道》中亦认为所谓先王之教,“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5]18。于此可见《雉朝飞操》之本事中亦包含着强烈的儒家伦理文化内涵。
分析至此,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明道意识已经了然。值得补充的是,蔡邕《琴操》所载之古琴操曲名本有十二,韩愈所取止其前十曲,将相传为伯牙所作的《水仙》、《怀陵》二操删而不用,这种曲调的取舍其实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明道意识。郑樵《通志·乐略》云:
右十二操,韩愈取十操以为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犊牧子所作,则圣贤之事也,故取之。《水仙》、《怀陵》二操,皆伯牙所作,则工技之为也,故削之。[3]910
郑樵这里所谓圣贤之事与工技之为的区别,确实是韩愈摹拟《琴操》创作时曲调取舍的直接原因。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韩愈之所以选取那些以圣贤行事为内容的琴曲进行创作,对其本事进行歌咏,正是因为这些琴曲之本事合于儒家的文化传统,体现了儒家理想的统治秩序。但《水仙》、《怀陵》二操却显然并不具备这一特征。此二操无古辞留存,《怀陵操》之本事难以详考,相传乃伯牙为子期而作。《水仙操》之本事,郑樵《通志·乐略》有详细记载:
《水仙操》。世言伯牙所作。伯牙学鼓琴于成连先生,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延望无人,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但闻海水汩没崩澌之声,山林窅寞,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终,成连刺船而还。伯牙遂妙绝天下。[3]909
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琴师,此曲本事正是关于其学琴的传说,颇有神异色彩。可对儒家道统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③《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正义》卷8,第372页。,是极力抵制这种神怪之说的,故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无补甚至有损于儒家道统,为孔子所极力抵制。于此可见,《水仙》、《怀陵》二操无论是其作者行事还是乐曲本事所传达的思想,对韩愈来说都无所取义,不足效仿,故此删而不用。这就说明,无论是歌辞内容还是曲调取舍,韩愈《琴操》组诗创作都完全体现了他的明道意识。
四
在《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韩愈指出了当时“孔丘殁已远,仁义路久荒,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22]84的儒学困境,说明他所致力于恢复的儒家道统思想精华在当时已经迷失了。可以想见,当时的许多社会现象是不合于儒家理想的仁义道德和统治秩序的。也就是说,韩愈借《琴操》组诗创作来明道的同时,它应该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匡世正俗的实际目的。这也是可以具体说明的。
中唐社会现实问题之中,藩镇割据是最大的一项急待解决的政治课题。陈寅恪《论韩愈》曰:“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23]329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描述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孽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7]619。当时的各大藩镇,往往割据一方,他们占有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不仅不交赋税,反而时常作乱,威胁朝廷。更不能容忍的是,有些藩镇甚至称王称帝,一如古之诸侯;或者自立主帅,使得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权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这显然是与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相违背的。树立大一统观念,让全国民众心向朝廷,使逆藩在道义上陷于孤立,这是韩愈一直致力的工作。其《后廿九日复上书》以“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12]162之问阐明了他心目中的大一统格局,亦反衬出当时政局的不理想。而《越裳操》本事所体现出的天下和平、万国和会的政治秩序,却正是韩愈心目中理想的大一统格局,故此曲歌辞的撰写对当时不理想的政治格局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反拨。
寺院经济的膨胀与君臣沉迷于佛老思想,是当时的又一大社会问题。就当时社会的稳定来说,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与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统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统治者的倿佛与崇老,已经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及社会经济。与韩愈同时的彭偃曾献《删汰僧道议》云:“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24]4545韩愈《送灵师》诗亦云:“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25]202于此可知当时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更为重要的是,佛教禁止婚姻,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道教亦讲求出家以修身,这对儒家的伦理观念显然是一个致命的冲击。韩愈《原道》中云:“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5]16《谢自然诗》云:“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织耕耘。下以保子孙,上以奉君亲。苟异于此道,皆为弃其身。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22]29《嗟哉董生行》亦云:“时之人夫妻相虐兄弟为仇,食君之禄,而令父母愁。”[22]80诸多言论无不表明了韩愈对当时社会家庭伦理败坏现象的忧虑。而《别鹤操》、《履霜操》与《雉朝飞操》诸曲本事正体现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故此三曲的创作对当时人道伦理失常的社会弊害,显然也是有所匡正的。
当然,韩愈《琴操》组诗对社会弊害的反映与匡正,只是它的客观效果。因为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直接原因,就是在自己被贬入潮的强力打击之下,仍要修辞立言,以实际行动继续维护儒家道统。这一组诗的创作从根本上说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一次自觉梳理,而不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即兴感发,其理性要多于感性。但这组作品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流俗的匡正也是无庸置疑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韩愈致力于维护儒家道统思想本就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是一个醇儒自觉的、具有充分实践可能性的行为。
五
通过以上歌辞与本事的逐一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韩愈被贬潮州后进行《琴操》组诗创作,在表达自己怨恨失意之情绪及乐道守操之品格的同时,也借此实现了其修辞立言、以具体言论阐明自己道德理想并以此来影响世人的政治用途。他之所以于古乐府中独选十首《琴操》进行摹拟创作,则是因为这些上古琴歌以音乐歌诗形式向后人透露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成型而稳定的士人人格类型,传达了仁亲爱民的政治思想,并且各曲之本事还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①有关琴乐与人格修养及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参见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第一章第四节《上古琴歌所蕴涵的礼乐精神》中的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90页。韩愈《琴操》组诗的创作不是一个单纯内心情感抒发的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仅仅为了发一己之愁思,借古圣贤以自写其性情。它同时还是一种著书立说、弘扬儒道的文化反思,是诗人失意之时对儒家道统精髓的自觉弘扬,也是韩愈作为一个思想家修辞以明道的具体实践。韩愈《题哀辞后》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26]304-305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亦谓其文为“贯道之器”[5]1。这里所说的虽是其古文,但以其来说明韩愈《琴操》十首的创作,亦颇在情理。以其“文以明道”的诸多古文作比,《琴操》组诗可谓之为“诗以明道”。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吉联抗,辑.琴操(两种)[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5]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8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范晔.后汉书:第3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0]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焦循.孟子正义:第 2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刘宝楠.论语正义: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廖名春,陈明.尚书正义:第7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5]焦循.孟子正义:第 2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刘宝楠.论语正义: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7]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8]顾学颉.白居易集:第2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佚名.灌畦暇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0]孙希旦.礼记集解:第2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司马迁.史记: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4]董诰,等.全唐文:第 44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第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I206.2
A
1000-5072(2012)07-0088-08
2011-04-02
向 回(1978—),男,湖南沅陵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与乐府学研究。
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奖《历代乐府诗研究》(批准号:YB20081002801)。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