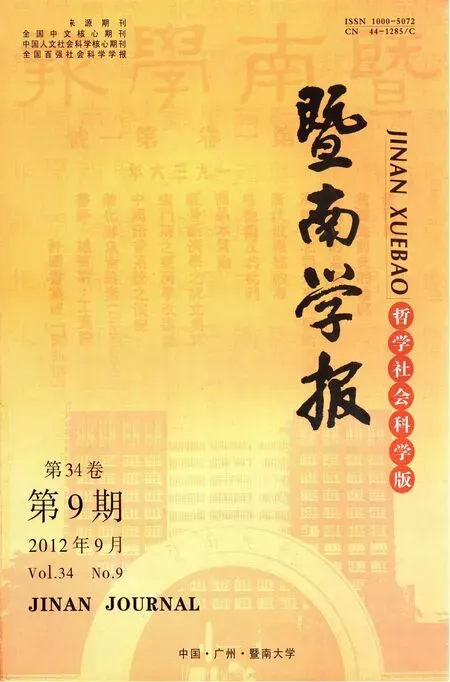内圣与外王:论牟宗三对叶适的批判
郭庆财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 041000)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和哲学大师。他一生创业垂统,志在反省中华民族之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牟先生的众多巨帙中,《心体与性体》是研讨宋代理学的经典著作,识见高峻,发覆之处甚多,甚至被认为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的伟构”[1]。在该书《综论》部分的最后一章《对于叶水心〈总述讲学大旨〉之衡定》,他将矛头指向南宋著名学者叶适,斥其学说为“实用主义”、“事务主义”、“平面颟顸之见”;更有多处措辞极为严厉,如“愚妄”“癫痫”“根性恶劣”“蛮横不讲理”等语,几近于詈骂。
牟宗三对八百年前的叶适大动肝火,其中缘由颇值得深思。叶适是永嘉学派的巨子,其主要活动时间在南宋乾道、淳熙间,其时心性之学大盛,朱熹、张栻等理学家于天理性命、太极阴阳之说反复讨论,辨析精微,蔚为一时风潮。叶适及其代表的永嘉学统向来以功利主义著称,他们从求实效、谋实功的立场出发,深厌性理学说“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识”,即玄虚迂阔,但却于事无补。和叶适一样,牟宗三对儒学传统中外王的不足也有深刻认识:“然宋明儒者,因偏重内圣一面,对于外王一面毕竟有不足。长期之不足,形成内敛之过度,其弊即显道德意识之封闭,而不能畅通于客观之事业。”[2]因此实现外王比实现内圣更加困难,牟氏一生也在致力于如何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思考。但问题仍在于内圣与外王的紧张:由内圣能否开出外王,道德与政治二者能否沟通,如何沟通;在当前环境下,应以内圣为本还是外王为本;可否逾越内圣,而直接实现外王,等等。这是牟宗三和叶适的分歧所在,也是内圣外王这一传统儒学问题论争在现代的又一次重演。内圣本于心体的道德自觉,其根本在“心”;外王则要外而从政,着力于礼仪、纪纲、器物的协调和修治,即着眼于“物”。因此,本文试图由心物关系入手,探究牟宗三对叶适外王思想的批判及其原因。
一、物与心
心物关系是古代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宋代理学的主体是内圣之学,以心性为本,注重道德自律,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曾子的守约慎独,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皆是反身逆觉的道德自省。发展至宋代,更有“性即理”“心是理,理是心”[3]的论断,以达成心、性、理的融通无碍。而且大多数理学家受到《礼记·乐记》的影响①《礼记·乐记》:“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常将“物”视为物欲的代称而隔绝之,以保持心性的清明与和平。
从南宋浙东学者开始对这一倾向进行有意识的反驳。受到浙东前辈学者薛季宣、陈傅良“道器相即”思想的影响,叶适认为名物度数即道。他指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4]还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5]。叶适认为“物”并非物欲,而是天地间一切物质存在;靠不住的不是物,而是心思。因为“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5],相对于反躬之“心思”而言,“物”才是最根本的、第一性的条件。因此,叶适对心的善恶不予深究,也不去心上做守约慎独的工夫,而将眼光集中于“物”,既然物无善恶,则应“克己以尽物”,消去主观臆想以循从物性,使万物各得其所,便可自然合道。
叶适的“物本”深为牟宗三所反感。牟宗三的哲学是接着宋明理学家讲的,尤其倾向于明道、象山、阳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路子,主张反身逆觉以证本体;且将心视为人类摆脱物化状态的关键,认为心“是吾人生命得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之真正的主宰,它指导并决定吾人行为之方向,它是吾人之真正的主体。”[6]即将心作为价值之源和精进德性生命的超越根据。人之躯壳必须有心作主,才不会是物化的行尸走肉。而叶适恰恰隔绝了心思,片面强调了人“物性”的一面,并说“人之所甚患者,以其自为物而远于物”,则人的肺腑肝胆、耳目手足也不过是物,人便简化成为形质,而没有诚悃之心来提撕润泽;其探求的道也便成了无生命的死路[6]。与叶适的隔绝心思、克己尽物相对,牟宗三认为:正因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心思不定,故须下一番“惟精惟一”的戒慎工夫,以贞定其道心[6]。道心即孟子所谓“本心”,戒慎工夫,就是像孟子所说的,应确立心之“大体”,隔绝耳目之“小体”;使心为主为本,闻见为从为末,因为“本心所发之超越而总持之妙用,能提住耳目、主宰耳目,而不为耳目所囿所拖累者也。”[6]即前者对后者具有超越和总摄的意义;而以耳目之官为主,则往往会随躯壳起念,难免为物欲所蒙蔽。
也正因为此,牟宗三不太喜欢《大学》所讲的“格物”。比如他多次提到,在理学三系②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儒学分为三系:分别是五峰、蕺山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象山、阳明系(以《论》、《孟》摄《易》、《庸》而以《论》、《孟》为主);伊川、朱子系(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中,以程伊川、朱子为代表的《大学》一系只重格物致知,心意旁落,将知识问题与成德问题混杂在一起讲,即于道德为不澈,不能显示道德的本性,因而为儒家发展中的旁出[6]。他批评的是《大学》“格物”的知识路向与反躬内省的思路不协调。根据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思路,人可以通过“反躬”,直下反之于本心性体以复天理之源。本心性体呈现即是天理之呈现,不需要通过格物方式以致其德性之知,藉以晓明天理[6]。由此看来,《大学》拈出的“格物”实在是附赘悬疣,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作为成德之教的进阶。
与之形成映照的是,叶适早就对《大学》的“格物”提出过质疑。不过在叶适看来,《大学》讲“格物”讲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不透彻:《大学》虽然提出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八条目并作了阐释,而唯独于“格物致知”阙而弗论,乃是对“物”的轻忽。他说:“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耶?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耶?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5]。《大学》对“格物致知”讲得不清楚、不透彻,尤其没有为“物”作出明确的定性,于是“意诚而非其意,心正而非其心”,也使正心诚意工夫昏昧不明。对《大学》“格物”的不同认识,恰恰反映出牟宗三与叶适心、物思想的差异。
二、叶适的“皇极一元论”
与心、物思想相关的,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政治哲学,即如何处理协调社会秩序、确立合理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也是叶适和牟宗三两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精神的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叶适哲学中的“物”本体具有广阔的涵容性,体现在社会政治哲学中,尤其与礼仪、制度、纪纲有关。我们先来看看叶适的政治哲学,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第五章一开始,即斥之为“皇极一元论”。那何谓“皇极”呢?“皇极”一词最早是《尚书·洪范》提出的。箕子答武王治理天下之问,陈洪范九畴大义,其五曰“建用皇极”,适居九类之中,后人往往因此以“九五之中”附会之。《尚书正义》中释为“大中”、“安中之善”[7],即追求均衡和谐的统治秩序。在宋代“回向三代”的政治文化风气中,叶适十分向往三代的声名文物之盛,他在为制科考试所撰写的《进卷》50篇中有《皇极》一篇,重释“皇极”这一古老的命题,藉以描述三代外王气象:
极之于天下,无不有也。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饮食嗜好,能壮能老,一身之极也;孝慈友弟,不相疾怨,养老字孤,不饥不寒,一家之极也;刑罚衰止,盗贼不作,时和岁丰,财用不匮,一国之极也;越不瘠秦,夷不谋夏,兵革寝伏,大教不爽,天下之极也,此其大凡也。至于士农工贾,族性殊异,亦各自以为极而不能相通,其间爱恶相攻,偏党相害,而失其所以为极;是故圣人作焉,执大道以冒之,使之有以为异而无以害异,是之谓皇极。[4]
而从上引叶适的“皇极”论来看,“极”是极致之意,是事物的道理,特指其最完美无缺的理想状态。它无处不在,事物各有其“极”;但是万物品性各异,各有其极而不能相通,难免“爱恶相攻”,因此须有更高的“皇极”以维系协调之。如同《周礼》中掌兽、掌山泽各有官,如周公驱虎豹犀象龙蛇,如“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8]之类,各有品节,使万物各得其所。可以说,皇极是以顺应“物”性、协调器物秩序而形成的和谐统治局面。
叶适的皇极论有两个特质:一方面,皇极的最高典范乃是远迈汉唐之上的唐虞三代。久远的三代在宋代已成为完美统治秩序的代称,它的长治久安人心凝聚、功化流行风俗醇美、官制庞大而有条不紊等等,都被人们津津乐道。另一方面,三代统治精神不在言传,而在于能实行之。《六经》的文本只是对三代统治事迹的记录,对于当下的治道并不能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汉代经学家以经学缘饰吏治,还是宋代的理学家从六经中阐发性命之理,都偏离了治道,“不验之于事”,“无考于器”[4],抽离了经所负载的致用精神,将之变成了空言。后人不应谨守空言,而应在政治庶务的践行之中求与三代声气相通。
“皇极”之道决定了“道”的传授形式,即“道统”的序列。从二程开始,为了弘扬明心见性的内圣之学,便做了建构道统的努力,到朱熹,则由《四书》中发明“道”的传授源流,精心建构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而且以曾子、子思、孟子承接道统之传。叶适反对程、朱以心性言道,他自然也会对理学家的“道统”提出质疑。叶适以为“理成功立”和“明体达用”乃是三代圣王共同遵循的精神,周公更是“道”的集大成者,开物成务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说:“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并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元凯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算数,不可违越。”[5]周公作《周礼》彰明一代典法,制定礼仪以教化天下,是治教并行的典范和继往开来的圣者。本于对三代圣贤治道的高度推崇,叶适对理学家以圣贤传心、从而塑造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做法极为不满,并对理学家常常引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传心诀”做出别样的解释,认为十六字的含义为:“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5]这里他故意无视文本,而淡化圣贤事迹中有关于性命之道的微旨①十六字“心传”乃出于《伪尚书·大禹谟》,的清代阎若璩、惠栋等人指出,《荀子·解蔽》篇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的话,梅赜用这几句话加上《论语》的“允执其中”,便凑成这四句。但是叶适并未能从文献上攻击十六字“心传”,只得作出自己独异的解释。。对于孔子在道统中的地位,叶适的看法也和理学家不同。理学家往往以为“夫子贤于尧舜远矣”①《孟子·公孙丑上》:“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程氏解之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于尧舜,语事功也。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河南程氏遗书》卷五,第76页),折射出他们以王者师自命的特点。周代礼崩乐坏,典籍散亡,孔子搜捕遗文坠典,使宗周礼乐文明能够流传。孔子虽以布衣而为天下法,但并没有得位行道,未能将六经真正施之于治。叶适的事功思想其核心在“治”道,因此对有德无位的孔子的推崇,只限于传经而已。并且以为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故此“其设教不在于是”,抹去了孔子为百世立教的圣师光环,被历代经学家和理学家尊为素王的孔子在叶适那里只是一位文献专家。据此标准,孔子之后,被理学家尊奉为道统传续者的曾子、子思与三代传统也没有必然瓜葛,都不应列入儒家道统的链条。在叶适这里,理学道统学说第一次遭到了全面的批判。
三、牟宗三的“人极说”
无可否认,叶适以三代为标榜的政治哲学构想当然美好,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三代之后礼乐崩坏,圣人不作,而且由于后世君权的专制和宰制,也使得士人难以得君行道,外王难得开出来。对这一点,牟宗三看得很清楚。他指出:
自王官失守,孔子有教无类,秦汉以后,君师殊途,亦不能合一,尽伦尽制纯寄于士人。为君者能承而受之,施而行之,已可谓尽伦尽制矣。至于尽心尽性尽理,则尤是孔孟立教后,宋明儒者之所发扬。[10]由于治教分离,君师分离,三代的统治精神已不可恢复。因此,外王的实现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时命”色彩,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并不能得位,自然也就没机会行道,因此叶适之以三代为标榜的外王说不能作为后人学习的必然法则,“是求无益于得也。”
二,叶适的“皇极一元”论,片面强调了统治者的治术,而忽略了个体精神的觉醒。叶适在《进卷》中指出:圣人之治天下“以物用不以己用”,“喜为物喜,怒为物怒,哀为物哀,乐为物乐”[4]。这也便是“诚心应物”的“皇极”精神。这和理学家程颢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思想非常相似,都是一种无所用智、随宜应变的精神。因为道在日用器物之间,默然不喻而无往非道,甚至愚夫愚妇寻常行事无不体现了道:“古者以天下之至圣而行愚夫愚妇之能行,极天下之高明而道众人之中庸。”[4]众人行事自然合道,不知所以然而然,而圣人只是顺其自然而已。这种统治境界看似自然无滞,近乎无所用心。既然“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因此他干脆放弃了由心上做工夫的努力,直接透至现实界和政治行为,隔绝了内圣之学,也放弃了包括愚夫愚妇在内的个体自觉,表现出明显“轻个人而重制度”的功利色彩[9]。
基于此,牟宗三对叶适的皇极一元论提出质疑:“岂只准言皇极,不准总人生宇宙之根本而言其极致之理耶?此正是道之究极会归之所在,道之究竟自立自见其自己之所在,而乃云因言太极而‘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何其性与人殊如此之颠倒乖戾耶?”[6]即叶适仅言皇极,而不能透至万理之会归——太极,仅从外表看王者之制度功业,而和人生、宇宙精神毫无关系。与之相对,牟宗三则提出三极共建:“太极是本,人极(仁教)是主,以皇极为末。”[6]太极,即是宇宙极致之理和最后的绝对;人极,其核心是修明仁教,使心性淳明;皇极是其广被于客观社会政治之用,即为儒家事功之道。这是对宋代理学宇宙论、心性论、经世论的继承和重新建构。三者之中,牟宗三尤其重视“人极”,认为皇极“为人极所范围而不能外”,即外王政治乃是“人极”的题中应有之义,政道、事功必统摄于心性之学,因为儒教“以道德实践为中心,虽上达天德,成圣成贤,而亦必赅摄家国天下而为一,始能得其究极之圆满。”因此“内圣之道明,则外王之道亦可得而明。”[6]虽然后来牟宗三愈发意识到内圣转出外王的艰难,在《政道与治道》等著作中对此多有修正,尤其强调外王是内圣的“致曲”表现[2],但源自宋代理学家内圣为本、外王为末的基本思路并未改变。不过,牟宗三所讲的“人极”,更在宋儒内圣之学的基础上贯注了其生命哲学精神,其根本精义乃在每一个体“生命”的觉醒,而不像叶适所谓的一任“愚夫愚妇”各行其道,对自己的生命懵懂无知,而仅成就圣王一人的事功。他说:“中国自尧舜禹汤以来,以至周文的形成,所谓历圣相承,继天立极,自始即握住‘生命’一原理,内而调护自己之生命,外而安顿万民之生命。是以其用心而言,而抒发真理,措之于政事,一是皆自一根而发。哲学从这里讲,历史文化从这里表现。”[10]内而自己,外而万民,由生命一义而内外贯通,实现“各正性命”的自由意志,以求得每个个体的自觉、挺立。这种由己及人的思路也便是儒家的“忠恕”之道,是一种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思路。
牟宗三看来,以“人极”为基础的内圣之学强调个体生命自觉,是直探本源之学;三代后可以接续“斯文”的,是富有必然性的生命精神——仁教,每个人可藉以豁醒自己的道德意识,“是求有益于得也。”此种必然的仁教精神有赖于孔子的发扬。春秋时期孔子出来“振拔了一下,另开创一个新传统。”[11]牟宗三承认尧舜三代为“道之本统”,但孔子的“仁教”寻找到了社会秩序的价值依据和心理本源,实现了“道之本统的再建”,则更为关键。仁,为生命之跃起,内在天理之呈现。此后曾子之守约慎独的工夫、孟子之尽心知性知天、周张二程之理气动静,进一步彰显了道德心灵的自觉,引出了人的精神生命之方向。因此,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直至宋明儒学家,实构成了先后一脉相承的道统。他说:“孔子之仁教确为中国文化生命中自本自根之‘直方大’而光畅之精神生命之方向之决定。继之而发展者,不唯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传是其自本自根之发皇,即使隔千余年而兴起之宋明儒学亦是其自本自根之发皇。”[6]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仁教已接触到人生的基本之处,因此比三代圣王甚至周公更伟大。牟宗三借助孔子的仁教,特别凸显了人性的深层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延续了理学家的道统说,建构起生命精神的链条。
人极和皇极的对立,体现的是个体生命精神和政治事功思想的对立。牟宗三以“人极”为核心,盛推孔子对于儒学本统之重建,致力于重新弘扬儒家“道统”;而叶适一贯尊奉三代,将之标举为治道的楷模,而对于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难免抑而下之,招致了牟宗三的严厉批评,斥责其迷失了精神生命之方向,“癫痫狂悖”,“大可哀怜”,言辞是很痛切的。
四、两种学术立场:历史哲学和历史经验主义
牟宗三对叶适政治哲学的严厉批判,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和文化背景。牟宗三一生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何梅协定、七七事变,随之抗战爆发。他蒿目时艰,以寻根的眼光来反观中国文化,往深处关注“文化的动源,文化的生命方向”,而这个动源即在各民族的心灵之中。对一个民族言,“一个民族的生命就是一个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含着一个普遍的精神实体。历史的发展即是步步彰著此精神实体。”[10]生命、理想、价值观念超越于政治之上,对历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并在现实政治之中逐渐具形。这和黑格尔以理性为最高追求的历史哲学十分相似。黑格尔坚持认为“理性支配着这个世界”,而且理性本身就是历史的目的,圆满的理性必定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具形。“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这种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结果。”[12]
与黑格尔纯思辨的、理性的“绝对精神”相似,牟宗三所致力的是从历史进程中抽绎出“生命”的线索,藉以建构自己的道德形上学。此种生命精神落实到人心,即为健行不息之“仁”道,牟宗三也称为“不容已之真几”,此乃是一切理想与价值之源。牟宗三对生命哲学的建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哲学使命感。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随着自由民主潮流遭受压迫和拘束,科学实证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泛滥,精神性和理想性逐渐丧失。功利主义、自然主义成为精神的否定,造成了自由意志的丧失。牟宗三呼吁克除物欲,反对生命的物化、僵化,以“清澈自己之生命。”[13]为此,牟宗三对物化生命、科学理智主义高度警惕,并善于作历史的反思。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大体说来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没有感应。”为此,他认为应当“常常作些民族历史文化的提醒”[14]。正是由于牟宗三这种瞻前顾后的文化关怀,素以“功利主义”著称的浙东事功学派代表叶适乃成了他批评的靶子。
叶适向三代寻求治道,所循的是历史经验主义的路子。他的思想体系虽没有程、朱那样精微深刻,并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却可以使得儒学精神获得历史的证据,可以通过历史事实的学习,通经以致用,以冀重开华夏大业。虽然说来动听,但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对古代名物制度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感性形态和客观了解,而难以融入自我生命;而且时移世异,参之于古,未必能验之于今,历史经验在当下未必真能活起来。所以叶适虽对三代充满了向往和敬畏之心,并在《廷对》中提出“臣愿陛下将兴礼乐以为出治之本,而无求乎汉唐之陋”[4],体现了对传续斯文的文化使命感和礼义之教的崇敬,但这又使他难免于迂阔,他自云:“盖唐虞夏商之事虽不可复见,而臣以诗书考之,知其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阔大迂远之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4]他言必称唐尧虞舜,悬帜甚高;但他在《上孝宗皇帝札子》中论“四难变与五不可动”,《进卷》中所具论的和买、茶盐、铨选、资格、用兵、理财等等的弊病和相应的变革措施,又只着眼于具体制度和个别问题之解决,和三代礼、乐之治的宏大精神毫无关系,因此遭到牟宗三的功利之讥:批评他为“直接之实用主义、散文之事务主义、直觉之英雄主义”[6]。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论及陈亮也用了“英雄主义、直觉主义”等词汇[2]。叶适虽鄙薄汉唐,垂青三代,而不像陈亮那样斩截地高扬汉唐的英雄才气,但由于在他那里三代梦想的虚悬和架空,使他应对国难民彝的丛脞现实时,终于难免实用主义、事功主义的气息。
小 结
传统儒家强调人的道德关怀和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且建构起“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模式。因此,儒家的真精神究竟何在,一直存在内向化与外向化的两类认识。宋明理学家从心性涵养的角度强化着儒学道德本位的思想,认为只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解决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就可以“一以贯之”地解决自然、社会、生命的所有问题,而对此路径达成的实际效果则关注不够。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儒学理想主义作用于复杂的现实能否有效,这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者所怀疑的。叶适将视线上溯至三代,直接从上古汲取外王之道的真髓,以为当下政治提供借鉴,表现出注重实效的特点,但难免精神外骛和功利色彩,而缺乏人文关怀。牟宗三顺承宋明理学家的思路并进一步正本清源,以“各正性命”为本源,旨在发扬内圣精蕴和生命精神,向前开辟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外王。立足于这一“现代化”的立场,并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原则与方向,牟宗三对叶适等提出严厉批评,典型反映了新儒学的立场和思路。
[1]刘述先.记牟宗三先生[C]∥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叶适.习学纪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何俊.南宋儒学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0]牟宗三.历史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12]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3]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14]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省察[M].台北:台湾联合报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