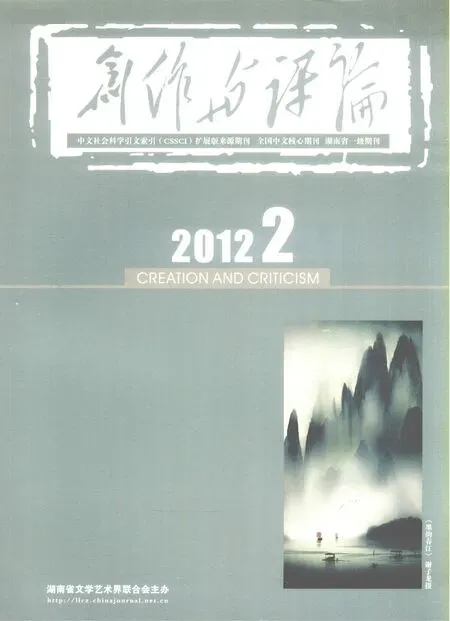希望是每个人活着的底气——何顿访谈录
■ 彭国梁
彭:何顿兄,这几年你创作可谓大丰收,大部头一本本的,让我不能不佩服,先是《黑道》,那本长篇小说结构非常好,故事特别吸引人,让我一读就放不下。去年,你出的新书《湖南骡子》,更是好评如潮,小说中语言十分讲究,我曾写过一篇读后感,《湖南骡子的诗化语言》,研讨会、评论文章,铺天盖地,全国影响很大。听说还上了“2011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四名,这种来自非官方的学术界的评定,对你这部书写百年湖南历史的《湖南骡子》,应该说是给予了十分的肯定。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创作的?
何:先说《黑道》吧,它在同类型文学作品中,被很多人视为写得很不错的小说。湖南文艺社的刘社长,在北京碰见我,对我说《黑道》这部小说,比《黑道风云》一类的小说写得好。鲁迅文学院的副院长施战军先生,是位文学评论家,对《黑道》一书十分肯定,并把《黑道》推荐给“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参与评奖,《黑道》已从全国几千部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入围,三月份将揭晓。还有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长天,也十分看好《黑道》,也是《黑道》一书的推荐者之一。据说,要两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推荐,小说才能参与评奖,这两位,我都不认识,只是在刊物或报纸上读过他们的文字,谢谢他们推荐。这是“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的组织者,通过微博发私信告诉我的。
《湖南骡子》是去年七月份出版的,但真正进入市场,是九月份。《湖南骡子》在《花城》第四期发了上卷,在《芙蓉》第五期发了下卷。书出版后,确实获得同行的很多好评,如《花城》的主编田瑛、《文学报》的朱小如先生、山西大学的王春林教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之一,《芙蓉》主编龚湘海和湖南文艺社副社长陈新文先生等,都对《湖南骡子》一书,给予了高度的好评,我不好一一列举,列举出他们说的话,显得有点自夸,甚至卖弄,还是把这些话放在心里,暖暖心吧。去年年底,研讨会一开,报纸一宣传,《湖南骡子》一书,在长沙的很多书店都变成了抢手货,几度销售已空,几度添货,书店老板看见我,对我说,《湖南骡子》销得真的好,很多读者走进来就问:老板,请问有何顿的《湖南骡子》吗?我知道,这是报纸宣传的结果。《长沙晚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晨报周刊》和《湘声报》、《今日女报》都对《湖南骡子》进行了宣传。
彭:我这次访谈,专谈你写的一系列黄家镇的中篇小说,我个人感觉你的中篇小说也写得相当好,也许你的长篇小说创作成就太大了,因此覆盖了你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在我看来,评论界的人不怎么注意你,也许是你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太下层了,下层得让评论家不好评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也许这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让他们读来陌生,就不好把握。我读来却感觉非常有意思,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思索,感到作者用心良苦,如《蒙娜丽莎的笑》、《希望》、《我的生活》和《到此为止》都与命案有关,读来冷峻,却又令人掩卷遐思,我不禁想问,你为什么爱写这些匪夷所思的凶杀案?
何:有段时间我喜欢看长沙的政法频道,政法频道里常有一些案例,看后让我思考。我把那些案例搬到了黄家镇,因为天地下没有黄家镇,如果有,只存在于我的小说里,这就避免了官司一类的麻烦。所以,看到或听到什么案子,觉得写下来可以让读者思考,就写了。像《蒙娜丽莎的笑》,写金小平杀了丁副镇长,是想告诉某些人,不要去揭某些姑娘的底,不要去毁了人家的新生活,只是没这么说。我不喜欢把主题弄得很明朗,我喜欢把思考变成人物、把内容藏在人物身上,你读了多少是多少。又如《我的生活》里,黄镇长掐死了他爱恋的姑娘,和《到此为止》里,民警指使联防队员打死吕医生,这些案子,如果写在真名实姓的城镇,那会给自己惹官司,用一个虚构的镇容纳这些人物和事件,就没人找我的不是。早几年,我经常上铜官镇、靖港镇、丁字湾镇和榔梨镇走马观花地看看,目的就是去体验镇上人的生活。有时候,我会在一个地方坐上一下午,或坐在餐厅里听镇上的人说事,当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时,我就搭话。后来混熟了,便常去,住一两天,感受下镇上人怎么过日子。黄家镇汇集了我走过的众多小镇的特点,写作时,这些走过的小镇就都会闪现在我脑中,让我突然看见一扇门打开,金小平、陈娟、杨琼或二牛、三伢子、黄刚、彭志、大毛和二毛,还有吕医生、刘姗老师、李副所长等,走出门,看我一眼,或因犯了案而慌慌张张。
比如中篇小说《蒙娜丽莎的笑》里,我写金小平杀丁副镇长,就是在某镇上吃饭时,餐馆老板与一个走来的什么人,于聊天中听到的。假如那天我没去那里,不吃那餐饭,我就听不到那个悲惨的故事。我听见了,其实就几句话,可是在我脑海里却出现了众多的浮想。回到家,就提笔写了这个中篇。小说《蒙娜丽莎的笑》发在2002年的《收获》第1期上,发表后,很多刊物都选载了。
彭:我读完你的《到此为止》后,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伤,你怎么让那个洁身自好的吕医生死在警察手上?这小说名是不是有别的隐喻?
何:你有一种莫名的感伤,这证明这篇小说就写到位了。《到此为止》是想写一个好男人,爱上了一个他感觉很好的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人,却是个有夫之妇,——女人出来寻找新的爱情,因为丈夫对她来说不新鲜了,她想出轨。这样的事,如今这个情感混乱的社会,确实不少。女人里也分等级,有高贵的,有贫贱的,有普通妇女,还有性欲旺盛的女性。吕医生不该爱刘姗老师,他爱上她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刘姗老师是李副所长的夫人,李副所长是普通民警时,追求刘姗老师,追到手了,之后,他忙于向上爬,很少关心老婆,而刘姗老师是个浪漫型女性,喜欢浪漫的生活情调,李民警却忙于公务,没时间跟她浪漫。刘姗老师就找到了纯洁的吕医生。
我从来没写过男人很纯洁。我笔下的男人都是朝三暮四的。吕医生是我唯一写的一个纯洁男人。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带大的,母亲干涉他的恋爱,把他年轻英俊潇洒时谈的一个个女朋友都吓跑了,吕医生毫无办法,因为面对他那个自私的母亲,他没办法完成他的婚姻大事,就拖到了与刘姗老师相识的那一天。当他得知刘姗老师是个已婚妇人时,他多次想逃避这场情感灾难,但面对饥渴的内心,他无法抗拒风骚、婀娜的刘姗老师,直到他和刘姗老师在新青年酒吧约会的那个晚上。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晚上。
吕医生不是被公安打死的,是被公安下面的联防队员打死的。《到此为止》确实有这种隐喻,就是这样的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我只在结尾处写了立案调查,没写调查结果,结果让读者自己去添加。有的事情,不能把故事讲满,讲满了,就没有余地了。
彭: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叫《繁华的背影》,其中写的都是在这个都市之中讨生活求生存的底层人物。你的小说创作,所关注的也都是底层人物。你对这些底层人物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何:我喜欢写底层人物,写底层人物更能体现人的本性。高层人物身上裹着很多层东西,要一一剥开,写起来累。底层人过得生猛海鲜一些,扯皮、打架、敢做敢爱,这种感觉是活力。中国十三亿人,百分之九十几是底层人士。写底层人物简单,随处可见,聊天也什么都敢说,写起来无须多动脑筋。这就是我写底层人物的原因吧。
回想起来,可能也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家人被从湖南第一师范赶了出来,赶到街道上,与街上的市民生活在一起。我们家在那条街上生活了整整十三年,直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于被澄清,我一家人才从那条街上搬走。也许正是这段不平常的生活,让我熟悉了小市民生活,且身上充斥着小市民情结吧。
彭:谈谈《蒙娜丽莎的笑》,年轻时,曾经在大城市卖过淫的金小平,赚了钱,回到黄家镇后,已经从良了,你却安排一个曾经出差到长沙的丁副镇长睡过她,认出了她,让她最后杀了丁副镇长,然后又让她消失,你这样写,是出于对金小平的同情,还是对现今生活的不满?因而让金小平远走高飞?
何:我记得该小说创作前,我曾与一个卖淫女聊过,那是十多年前,她不知道我是作家,她说她家很穷,她要供弟弟读高中,还要挣钱替父亲还债,父亲建房,欠了亲戚朋友许多钱,她只好出来打工。可是,打工来钱太慢,无法让她父亲看到希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走上了卖淫这条路。我当时觉得她是个善良的姑娘,因为她赚钱一是供弟弟读高中,二是替父亲还债务,这很了不起。我问她,将来面对丈夫,她会怎么办?她说,我把吻给我丈夫。她说她从没吻过嫖客,她要把吻留给让她愿意嫁的男人。这个姑娘就是我小说的原型金小平。我写《蒙娜丽莎的笑》时,这个姑娘就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她说话的声音、表情就跃然纸上。她回到镇上,从良了,但她没想到曾经睡过她的男人,那个丁副镇长却毁了她的生活,这让她感到绝望,因而动心杀人。我本来是要在小说中让她自首的,可是我觉得她不会自首,因为像她这种卖淫女,在生活中见多了,不甘于把自己的后半生赠给监狱,本能让她选择了逃跑。所以我没写她自首,也没写她被公安抓住。
彭:无论是底层中层还是上层,为爱情所困为婚姻所困,恐怕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注意到,你这几个中篇小说都是写底层人为情爱所困因而杀人,杀人就那么简单吗?你对他们杀人怎么看?
何:底层人杀人,有时候是意气用事,大多脑海里没装多少后果,只装着恐惧或仇恨。仇恨能让人杀人,金小平纯粹是因恨而导致她趁丁副镇长洗澡时,杀死了丁副镇长。恐惧同样能让人杀人。《希望》里二牛把老五骗到山洞里杀死,就是恐惧所为,他害怕老五把他杀死大毛的案件说出来,于是起了杀心。《我的生活》这部小说里,那个矮小、猥琐的黄耀武,最后把自己爱恋的小叶掐死,这是由爱转恨的结果。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加上对小叶的不信任,恨就变得无限大了。这都是下层人冲动起来不顾后果的结果,我在多篇文章里都提到过,后果其实就在前面,你不干,后果就永远在后面,一旦你干了坏事,杀人、强奸或偷窃,后果就转到前面来了,它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你,后果不是巫婆,不是鬼神,是法律,是监狱。我写这类小说,其实不是宣扬某些人敢于发泄愤恨,我是想让读者读到这人生的一瞬所带来的后果,看到后果,自己遇到这种事时,会想一想后果。
作家写书,重在对世人说些什么。宣传教育,从来都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正面的说服教育,一种是事例展示。我是后者,我用笔展示事例,让读者去判断。
人都为情所困,美好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少的,所以人们才拚着性命追求美好。因此,千百年来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爱情是残缺的,所以作家们便不惜大书特书,讴歌不止。往后一万年、十万年,爱情仍然是一代又一代人用生命追求或在生命中叹息的。爱情不是河流,它是条小溪,容不下那么多人沐浴,就会有人站在岸上捶胸顿足,看着他爱的人在爱河里与别人嬉闹而痛哭流涕。这是因为世界上永远存在着男人和女人,永远存在着性,除非性可以为其它东西取代,但至少目前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最美的是人,只有人,才能让人激动、痛苦、捶胸顿足,恨不得一头撞死,其它,比如山水风景、花朵、装饰品或服装,再怎么美,只会让你高兴,不会让你激动。当然,金银财宝也能让人激动,但那是另一种激动,与美无关。
彭:我还发现了你这中间的一个有趣的东西,那就是你把长沙市一些街道和宾馆什么的都搬到黄家镇去了。如下河街、迎宾路……
何:那是便于记忆,下河街、沙河街、迎宾路,长沙都有,差点把五一路都写到黄家镇了,考虑到黄家镇没那么大,载不得一条宽大的五一路横躺在黄家镇上,这才没写。这样写是便于以后写另一个小说时,一下子就能想起来。从《我的生活》,到前年发在《作家》杂志上的《到此为止》,是十年时间,如果是自己临时想的街名,恐怕早忘光了,而这些现有的街巷名,却能信手拈来。黄家镇,是众多小镇与我曾经居住过的街巷的混合体。
彭:对弱势群体我看你是又爱又恨的。你写的时候是不是心情特别复杂?《希望》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中篇,写了底层人矛盾和复杂的心理,你能谈谈《希望》的创作思想吗?
何:有些底层人把持不住自己的爱恨情仇。你看看电视报道,很多底层人,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挥刀砍人,事后,公安介入,一问,不过是一些让人发笑的芝麻绿豆事,而彼此冷静下来后都十分后悔。这是底层人太生猛了,太易冲动太不计后果了。底层人善良起来也十分善良,凶起来有点忘乎所以,骂起人来什么恶毒的脏话都可以从嘴里飙出,这是底层人物的特质。因为,他们在平常生活中没受多少约束,就不忌口,也不怕事,等到闯下大祸了,蹲监狱了,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蛮勇。
《希望》里的三伢子、二牛,老五和杨琼都是十足的底层人,老五希望能在二牛那里诈取点钱,从而搭建一间小房子给儿子搞学习。三伢子和二牛都是黄家镇的二流子,二流子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可是他们也有希望,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变好,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先是杀了镇上的小老板大毛,弄了钱,两人分了,以为太平无事,不料却被老五发现了,就又起了杀老五灭口的恶念。恶念一旦产生,就给了二牛杀人的勇气。我始终认为,杀人是需要勇气的,杀人又不是宰鸡,没有勇气,下不了那个手。杨琼是个暗娼,多年里都在照顾她那个智障的丈夫,她希望他死,只有丈夫死了,她才有重新生活的希望。她老了,客人不多了,而她的儿子却在一天天长大,她似乎无力支撑她那个衰败的家了,于是她把那个智障丈夫骗到幸福桥的护栏上坐着,趁丈夫不注意时,把丈夫推下了桥。
我在创作《希望》这个中篇时,脑子是乱的。我心里很同情杨琼,开始创作时并没有她把丈夫推下幸福桥的构思,构思是她和她丈夫走上幸福桥时产生的。好像不是我要把她丈夫推下幸福桥,是她自己要把这个拖累她多年的男人推下幸福桥。当我写到她和她丈夫走到幸福桥上时,突然我有一种她丈夫要死了的预感,于是我开始写桥,写桥下的河流。当我写到她丈夫在宴席上,遭到邻居逗弄时,她心里的恶念就更坚决了,于是就有她趁天黑,又趁无人时,把她丈夫推下幸福桥这个章节。人物有时候是牵着作家走,人物会对作家说,我要干这事,我一定要干。我写小说,很多时候,写到一半,把开始的构思又推翻了。
彭:你写了一些三陪小姐“从良”之后的故事。“从良”也要讲一个平稳过渡和软着陆吧?那么多的“三陪”从业者,她们的归宿,是神秘?是辛酸?是无奈?一万个“三陪”,便有一万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不知你对她们的命运,是否作过深层的思考?
何:三陪小姐,终究是要从良的,随着年龄的增大,也没人再叫她们三陪,还有一个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大,她们自己也有青春不再的恐惧感,就想从良,找个丈夫,安个家,生儿育女。三陪小姐走出来三陪,百分之九十是生活所迫。很多姑娘并不甘心自己被命运摆布,自己想去命运的潮流中搏一搏,能赢多少是多少,不愿意在家里窝着。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杭州来长沙的三陪小姐,聊天中她告诉我,她想干个一年、两年,赚个二三十万,再回家乡找个丈夫,开个店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她说,她们家乡,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赚了钱,然后回家乡的县城或市内租个门面,开个小店子,过一辈子。这是社会问题,已经成了很普遍的现象,如今的中国,笑贫不笑娼,观念改变了,新的观念就是专门攻击固有传统的,这种笑贫不笑娼的话,在农村和城市广为流传,流传多了,人们就接受了。
彭:《永远是十七岁》是篇写初恋成为泡影的小说,感觉这种初恋故事里有很多遗憾和无知,众所周知,初恋基本上是失败的,这篇小说里有没有你的初恋?那个黄斌是不是就是你自己?
何:《永远是十七岁》是一个定格,把一个姑娘定格在十七岁。许多人因初恋失败,因而多年后又回头去寻自己的初恋。十年前,我听一个朋友说,他去见了他的初恋,那个在他心里一直很美好的姑娘形象坍塌了,从此再也找不到了,而在他见那个姑娘前,那姑娘在他心里一直是中学时代的样子,蓄着两根羊角辫,穿着那个年代里很好看的酱油色灯芯绒衣,笑容是那么纯朴、青春、稚嫩、好看。他对我说,可是那天他见到了他的初恋,完全变了,不是那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了,变成一个感觉上很俗气的中年女人,四十岁了,十六七岁的她没有了,只能到记忆里去找了。
这给我的感慨很大,因为我也有初恋,我的初恋也和我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由于我那个朋友的提醒,我没有去见我的初恋,我怕那种感觉被毁,而只要见了面,被毁是肯定的,所以我就有了让初恋定格在《永远是十七岁》的创作冲动。我们这代人确实有很多懵懂无知的东西,这要怪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视爱情为资产阶级小情小调,不革命,因而把生理卫生课都取消了,仿佛女孩子来月经、男孩子夜梦遗精都是很肮脏的,必须从根子上剔除,其实那是既违背人性又有悖于人生理健康的,但那个年代可不管这些,说取消就取消。我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告诉我,他得了绝症,生殖器喷出了液体,液体有股难闻的腥味。当时他十五岁,说这话时满脸痛苦,好像在这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吓坏了,劝他去医院看病,以为他得了病,都不敢声张,两个人郁闷了很久,后来他告诉我,他听他们街上的一个男人说,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叫夜梦遗精。假如开了生理卫生课,这就不会让我们慌张。小说是写一种感觉,对那种初恋的美好回忆,老实说,有我一点初恋的影子,但不是全部,我不是生活在黄家镇,我也没有与我的初恋在趸船上初试云雨。
彭:你在《别人的故事》里有一段写马春燕和刘老板跳“情调舞”。这“情调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很流行的,马春燕和刘老板因跳情调舞,有了那种关系,你对女人出轨怎么看?
何: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音乐,但音乐有时候也乱性,在特定的场合,比如舞厅,当一对男女搂在一起跳“情调舞”时,男人和女人的脑海里会产生幻想。假如这个女人或这个男人,婚姻是失败的,在舞厅里充满浪漫情调的氛围下,也许就会把持不住自己。这样的故事,生活中很多。有的女人,进舞厅时,只是玩玩,一开始并没打算背叛丈夫,可是玩来玩去,就经不住丈夫之外的男人的诱惑了。在舞厅里,流行一句话,丈夫是一丈之夫,离开了那一丈,就不是丈夫了。情调舞之所以风行,是情调舞把女人搂得更近了,这一距离的缩短,丈夫就消失了。中间没有丈夫,有些事情就发生了。
不要大男子主义的只约束女人,女人就不能出轨?假如她的丈夫先她出轨了,不爱她了,她难道要把自己的青春和身体浪费掉才是好女人?那是傻女人。违背人性的话,我不说,违背传统道德的话,我敢说。传统道德大多是孔孟那里来的,而孔孟是看不起女人的,倒不是他们两人错了,而是古代人都大男子主义都错了,把女人看成生育工具,或看成纯粹发泄性欲的皮囊,这是不尊重女性。西方早在几百年前就不是这样看了。大男子主义,是不人道的。当然,我并不主张但凡女人,都去出轨,我只是不把女人出轨看成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人生就一世,关键是要对得起自己。
彭:有的父母信奉“棒子下面出孝子”,动不动就对儿女大打出手,可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棒子下面出逆子”。不知你对这棒子是如何看的?
何:上一辈人就有点法西斯,革命让他们脾气大。另外,他们生养得太多了,个个张着嘴要吃,做父母的脾气自然暴躁,动辄挥拳头。这种状态,我辈人见得多。今天,你很少还能看见大人打小孩,因为都是一个儿子或女儿,爱都爱不够,还怎么会动棒子?
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过于溺爱,不好,太讲拳头了,也不好。今天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教育也该多元化。我是没看见谁家在教育子女上动粗了。我想即使是农村,今天的教育也不会动粗。一是他们的父母不再像过去的农村父母,那个年代的农村父母,都是社员,必须听从生产队长安排农活,因而个个都是井底之蛙。如今的农民,在大城市里打工,也闯荡了一下社会,视野比上一辈农民开阔。我所下过乡的农村,只要头胎是生了儿子的,也像城市里一样,奉行只生一个,还什么棒子啊?
彭:在《我的生活》里,你写了一个小叶,她开始相信爱情,后来一次两次地被人抛弃,她便对男人失望了,便开始不把自己的身体看得那么纯洁了。她到桑拿中心当服务员,然后到发廊当洗头妹,兼做暗娼,还到洗脚城当洗脚妹。她这个人物我感觉你写得非常到位。
何:《我的生活》写于十年前,刊发于2002年《花城》第1期,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开了家洗脚按摩店,我常上他开的洗脚按摩店洗洗脚或做做按摩,自然与他店里的按摩女混熟了,她们便跟我说了小叶一类洗脚按摩女的故事。她们不喜欢她们跟你洗脚时你板着脸,她们会找你聊天,一聊天,她们就说她们的见闻,她们说话无心,我是听者有意。从我对她们的了解,她们一开始把爱情和身体是看得很神圣的,随着她们接触的一个个男青年,还有她们对有妇之夫的非分要求,她们在男女关系中躲避或寻觅,边开始琢磨人生。人,一开始是纯洁的,但进入那种染缸,爱情就变得随随便便了,变成肉体与金钱的交易,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爱情了,生活一片灰色,并非万紫千红,加上欺骗和背叛充斥在她们的眼里和耳里,自己也一步步地下滑了。
小叶这类姑娘,生活中比比皆是,她们在生活中不讲真话,她们倒不是要报复谁而隐瞒真实姓名,而是她们不愿意别人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因为她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还需要重新生活,那种生活是相夫教子生儿育女的。人都有面子观念,都在为自己设计后路。小叶她们年轻,后路虽然没想透彻,但也想给自己留着,这就是小叶她们这类女人。
彭:其实有许多的凶杀案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黄镇长和陈娟的故事。很多人的一生都是毁在自己的头脑简单上。不知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何:怨产生恨,恨产生报复。报复,那就是置人死地而后快。在犯罪未产生前,他们是不知道怕的,因为罪恶还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只是个辨不清的影子,也就没有怕。怕,是罪恶产生之后,人才知道罪恶给自己带来的后果,于是才会后悔,才会怕。这就是人!恨是人身上的一种毒瘤,要自己切除,不要让这颗毒瘤长大成形。而消除怨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消化它,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消除。怨恨又不是物质,是一种存在于大脑里的有毒的化学分子,连脑细胞都不是,别人怎么帮你消除?消化它,只有自己。
陈娟是个小骗子,她与黄镇长的纠葛是她在有意无意中骗了善良、老实的黄镇长。黄镇长是个个子矮小的男人,身高只一米五八,这样的男人,在恋爱上,当然会遇到困难。陈娟是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的姑娘,但陈娟是洗脚按摩女,没对他说真话,随口说自己姓叶,不把黄镇长的爱当回事。黄镇长却为她投入了很多感情和金钱,后来黄镇长觉得自己被这个年轻姑娘骗了,就愤怒,向陈娟索赔。陈娟却不肯,两人争吵,黄镇长已不相信她了,在她企图逃脱时,他掐死了这个姑娘。我隐约记得,这个故事是当年在洗脚按摩店听到的,关于小叶又叫陈娟这样的故事,我自己是想不出的。
彭:几年前,我曾在《小说月报》上读到过你的中篇小说《新青年酒吧》,这次重读,更加感觉你小说中,对下岗职工很关注,还能感觉你在思考下岗职工的出路什么的,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创作《新青年酒吧》这部中篇小说?
何:《新青年酒吧》当年发在《作家》杂志上,当年便被《小说月报》转载。那段时间,我很多初、高中同学都下岗了。他们是七十年代末参加工作,招工当的工人,那时候大家都以为自己这辈子永远是工人了,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有下岗的一天。八十年代时,工厂还行,进入九十年代,一些工厂相继垮了,工人自然面临下岗。一下岗,生活就困难了。我们这代人,三四十岁正是养家的年龄,可是却下岗了,在家待业。这便是我当时忽然想写我们这代人遭遇的窘境。你也知道,我们这代人都没学什么知识,文化大革命中,最反对的是走白专道路,走白专道路就是批判学生埋头学习。现在想起来过去提出的口号真是害人,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既然这样,那就当社会主义的草吧,何必成为资本主义的苗而遭老师和同学们批判呢?这样的标语,在当年不是很影响一代人吗?
谁会想到,不读书的报应会来得这么快?还只三十几岁,报应就找上门了,你当社会主义的草,那就让你当个够、当个饱!黄刚就是这样的人,没读什么书,到了民族乐器厂又当了干部,只知道画画写写,一双手没干过活,一心希望工厂好下去,当工厂倒闭时,他就只能面对倒闭的现实而愤怒了,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你要晓得,他还只四十岁啊,出门遭遇的总是囊中羞涩的窘境,他难道不义愤填膺?!现在,街上有很多麻将馆,都是下岗的职工或退休工人。假如我要找我们这代人,直接去他家附近的麻将馆找好了,当然,也不是全部,但我确实发现,他们中的某些人,只要口袋里有一点钱,就去麻将馆里打发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们活得很无聊和苦闷啊。
彭:《新青年酒吧》小说中的黄刚,有两个细节很让我感叹,一是他要去杀让他戴了绿帽子的彭镇长,带了把三角刮刀;另一个细节,他去找强奸了他女儿的飞哥要钱,而不是愤然报案,你既然写了三角刮刀,又写了黄刚的愤恨,却让他什么都没干,你怎么会这样写?
何:不是每个人拿了刀子就会杀人。很多人有很多不平,可是大家都拿着刀就去杀人,那这个世界不乱套了?法制教育和法制思想,会让一些人知难而退。黄刚本是要去杀彭镇长的,他带了三角刮刀,敲开了彭镇长的家,坐在彭镇长家里等待时机,可他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当彭镇长突然对二毛说,你帮我解决一下他的问题看后,黄刚的杀人念头就灭了。他本来就不坚决,愤怒在他心里却不在他手上。
人是被逼得没办法才会把法律置之度外,人只要脑袋还清晰,就会想别的办法解决问题。最开始,我是想让黄刚去杀彭镇长,但他杀不了彭镇长。真的是这样,不是所有的人愤怒了,感到受了侮辱就会杀人。真要那样的话,这个社会会多很多命案,因为这个社会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事。黄刚是个什么人?是个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懦弱者。我不是看不起他,他是很愤怒,但他的愤怒并没完全凝结在彭志身上。他的愤怒是针对社会,对彭志,他只是嫉妒,他是个可卑的人。我写他去找新青年酒吧的飞哥,飞哥强奸了他女儿,这总可以杀吧?于是我想安排这样的情节,但情节就是不朝着那个方向运动。他匆匆去找飞哥,用报案威胁飞哥,向飞哥索要一万元,赔偿他女儿的贞洁。还跟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这丧失了人的尊严,但对于黄刚这样的人来说,尊严已经不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了,钱才是他生活中的主题。
我在写黄刚这个人时,想写他像男子汉样维护自己的尊严,但尊严这东西始终到达不了笔下,因为这个社会,我感觉很多人都活得没尊严,尊严成了很多下岗职工和农民兄弟想要也要不到的奢侈品。我觉得,杀人既要有足够的理由,还需要足够的胆量。像黄刚这样的人,既然有退路,就不会杀人,所以,他什么都没干。我丝毫没有在小说中嘲笑他,我觉得黄刚什么都没干才是绝大多数下岗职工的特点,下岗职工是生活得很不好,是对这个社会有怨言,但不是什么人一动怒就宁可把自己置于绝境。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假如黄刚杀了人,他就不会轻松地走进常德牛肉粉店,要盖双码的牛肉粉。我开始想写他走进派出所说“我杀了人”,但,怎么写,笔头也不往那里去。
彭:你这些故事好像都与案件有关。在一篇创作谈中,在谈到如今这些年轻人的法律意识为何如此淡薄时,你好像说传统文化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四大名著中,就有两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大谈杀人放火的。可那些杀人放火者都是大英雄。问题是很多时候,那些大英雄都是在滥杀无辜。
何:生活在边缘地带里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很少看书的,在他们脑海里,装着的是义气,而义气的来源,除了生活本身,自然还有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而且,我敢说,这种影响对他们很深。水浒里,众多好汉都是杀人犯,林冲、鲁智深、李逵、武松、杨雄、史进等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逃杀人犯。今天的法律当然不会允许这些人存在,可是文学却对这些个小说中的人物,大力吹捧和颂扬,这对底层人做出那些龌龊事,自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当年我与街上的流子交朋友,请他们吃宵夜时,他们一提及那些个人物,例如鲁智深、林冲、武松,就十分神往。这就是影响,潜移默化了,当他们拔出刀时,你能说他们的脑海里就没有出现李逵、武松吗?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于那一瞬难道不正在他脑海里横行?左右他挥刀朝对手猛砍的,也许就是李逵或鲁智深的阴魂呢。事后,再痛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今天不是远古时代,没有水浒梁山供他们躲避官兵和享乐了。
传统文化里的某一些部分,对法律意识淡薄的人,或某些自私的人,简直是一种灾难,影响是十分负面的。百分之九十的罪犯,基本上都有一种这样的思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似乎是最好的自私自利的理由,这也是所谓传统文化里的精彩语句。很多犯罪分子,别的话从他耳边一闪而过,而这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却可以在他们脑海里像一面锦旗一样飘扬。早个十几二十年,我曾与某些街上的社会流子交谈过,他们几乎于有意无意中,个个对我说过这句话,而且很理直气壮。增广贤文上收集了我们古人说的很多精辟的言论,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不劝不善/钟不打不鸣”等,那么多励志的话,他们看了,跟没看一样,惟独像这样的句子,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句子却落入了他们的耳鼓,像一根根标杆样插在他们脑海里,这也是传统文化呵。
彭:说说希望。其实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希望,那就很难活下去。最起码的,饿了,就希望吃饭;冷了,就希望穿衣;然后饱了温了,就希望淫欲。再之后,便是要住得好,出门要有车;再然后呢?我希望……希望一过,是不是就叫欲望呢?
何:希望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大小不一罢了。一个人如果做了一地方大员,他的希望自然是治理好他的辖区,能让他辖区的老百姓记得他,对他歌功颂德。中国古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然,这样的官员,得有一个前提,就是真想为广大的老百姓做事。一个大老板,在希望赚更多的钱的情况下,也有其它希望,弄一个省政协常委或全国人大代表什么的,好光宗耀祖。中国人的思想,大多没脱离传统的俗套,最终都落在光宗耀祖上。我小说里的那些人,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的希望是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处境。希望和欲望,词典上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