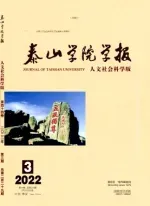“实践本体论”:切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处——在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开启中
孙成竹
(山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山东 济南 250103)
当下正在进行的哲学对话,逐渐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引向深入。这为我们从“实践本体论”切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更大可能性。“实践本体论”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责难,有学者甚至认为只有超越实践本体论之争,才能矫正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概念化、理论化的偏向。[1]然而,哲学作为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又不得不诉诸概念。这决定了“实践本体论”与马克思哲学革命阐释的某些思辨性特征。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个人”的开启和生成,使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实践本体论”日益必要。本文将主要在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开启中展开这项工作。
一、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领悟“实践本体论”的历史性契机
有这样的哲学,需要借助别种哲学才能更好地敞开自身。马克思哲学就是如此。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对“现象”及“现象学”的独特理解,开启了重新领会马克思哲学的可能。这是因为:
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意味着某种东西的别具一格的照面方式,即就其自身显现其自身。现象学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海氏现象学意味着:第一,显现者必须具有自身显现,而且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能力”;第二,以描述的方法将现象之显现展示给人看。前者的关键在于找到可以本真显现的显现者,后者则必须付诸诠释学。海德格尔找到了“此在”。惟有“此在”具有始源的显现欲求。因而,“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2](P44)。“此在”的现象学基于一种使命——探问存在的意义。在海氏看来,哲学的对象是“存在”而非存在者。而“此在”是通达存在惟一可能的存在者。就此而言,现象学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存在论的可能形式:“存在论与现象学不是两门不同的哲学学科,并列于其它属于哲学的学科。这两个名称从对象与处理方式两个方面描述哲学本身。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2](P45)
“此在”的存在结构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因为“现象学的阐释必须把源始开展活动之可能性给予此在本身,可以说必须让此在自己解释自己。在这种开展活动中,现象学阐释只是随同行进,以便从生存论上把展开的东西的现象内容上升为概念”[2](P163)。因而“此在”的本质——生存(绽出之生存)的诠释,就成为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地基。
海德格尔视黑格尔为最大形而上学家:第一,黑格尔哲学从意识出发。而意识作为非始源性存在并非哲学之最后前提。只有历史性的“此在”才配称哲学上的“现象”;第二,黑格尔的“现象”不具有“让存在”的结构,即意识只是存在者,而且是非此在式存在者。也就是说,黑格尔未曾脱离形而上学——将“存在”当作存在者的根据。
较之精神现象学,“此在”现象学具有两大优越品格:第一,“此在”是历史性存在;第二,“此在”的存在具有“让存在”的结构。这一结构只有在历史视野中才得以可能。也正是在这里,异化才是得以可能的。
海氏对胡塞尔的超越,正如他自己所言:“现象学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开山。下面的探索(指《存在与时间》一书——引者注)只有在胡塞尔奠定的地基上才是可能的。对现象学的先行概念的界说表明:从本质上说,现象学并非只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才是现实的。比现实性更高的是可能性。对现象学的领会惟在于把它作为可能性来把握。”[2](P45)这意在表明:现象学并非仅有一种,而是有多种可能形态。胡塞尔进入了艰难而深奥的意识领域,建构了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并未紧随其师在意识领地中跋山涉水,而是抽身而出,进入“此在”的存在,直指存在的意义。这样一来,他就找到了一条通往“存在”的捷径。事实上,海德格尔是通过重新诠释“存在”的意义——存在者的存在,从而使“此在”与存在挂搭起来。因此,“此在”的本质性阐释必须确保问题提法的恰当,即“我们要获得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命题,这样就可以从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方式来进行现象展示。但最为自明的答案自古流行至今,从这些答案中又派生出问题的种种提法。从将要提出的问题来看,我们若要在这种种答案和种种问题提法面前保持现象展示的优越性,此在的现象学阐释就必须始终谨防问题提法的颠倒”[2](P133)。“始终谨防问题提法的颠倒”成为海氏现象学的基本原则。通过这一原则,海德格尔开启了人道主义的新视野。
“此在”现象学敞开了通往历史之门,而“历史”无非是“此在”的敞开。此即海氏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开启之所在。必须指出,“此在”现象学并非现实历史本身,它只是为描述现实历史提供了方法。因为“此在”只是“现实的个人”的摹本,这一点保罗·蒂里希看得比较分明。他说:“海德格尔的概念表面上显出[与超历史的概念]对立的一面,即历史性的概念。但他把人从一切真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让人自己独立,把人置于人的孤立状态之中,从这全部的故事之中他创造出一个抽象概念,即历史性概念,或者说‘具有历史能力’的概念。这一概念使人成为人。但是这一观念恰好否定了与历史的一切具体联系。”[3](P57-58)无疑,这并不妨碍海氏现象学的巨大开启性意义。下文关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将主要在这种开启中进行。
二、“实践本体论”:切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处
在哲学中,本体的选择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无法避开本体论问题,它是哲学“是其所是”的表征和确证。本体论不但成为哲学与科学划界的标志,而且决定哲学建构能否圆融。它与哲学相互缠绕,如影随形。黑格尔有个比喻: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宇里边没有至圣的神一样(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页)。本体论之于哲学,亦犹神之于庙宇。神赋予庙宇以神圣,本体论使哲学成为它自己。需要澄清:第一,本体论不是追求世界本源的理论。对世界本源的探求属于宇宙论的范畴。本体论以解决存在者何以存在为己任;第二,本体论是哲学“是其所是”的标志,本体论形式的不断转换是哲学追寻新的表达方式的体现;第三,本体论并不意味着唯心主义,它和哲学的唯物、唯心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找到一个恰当的原初出发点,以便让“存在”自身如其所是地显现,是现象学的关键之所在。海氏找到的是通达存在的存在者——“此在”。因而,先行澄清“我”——“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成为一切存在论得以可能的前提。“实践本体论”是在那场影响深远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逐步形成的。“实践”对人的存在而言的始源性、内在性和开启性(即“活动……出来”的品格),使其有资格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明显体现。作为本体,实践是先于主客二分的逻辑规定,但这种规定固有其历史性特质。这就使其生成性不再借助于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规定而达到真正的自满自足。
就此而言,马克思哲学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颠倒”(实际上,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是由费尔巴哈首先完成的),也不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亦步亦趋,而在于“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所特有的“在”出一切可能的在者的生成性。
第一,实践的“超越”性。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意指孤立绝缘的“主体”,活动于现成存在的世界之中。就是说,人是有“世界”的存在,即“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P106)。马克思使用着诸如“对象”、“对象性”、“本质”等近代哲学概念表达着非近代的哲学视野。所谓“对象性存在”,是说人向来有自己的自然界并且必须在自己的自然界中才是现实的存在。一个没有自然界的孤立绝缘的主体是无法确证自身存在的:“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4](P106)。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种在世结构成就了此在的本质——绽出之生存。他特别强调,“绽出之生存”并非“站到外面”,而是“依据于那种在无蔽状态之‘外’(Aus)和‘此’(Da)中的内立(Innestehen),而存在本身即是作为这种无蔽状态而成其本质的”[5](P441);“此在向来已经超出存在者整体之外而存在了。这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存在状态,我们称之为超越(Transzendenz)。倘若此在在其本质基础上并不超越……那么,此在就决不能与存在者发生关系,也就不能与它自身发生关系”[5](P133)。就是说,“此在”的“超越”存在是“世界”前来照面得以可能的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人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本然欲求着他的对象,以便从其对象中证成自身的存在。正是这欲求,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生成和开启,成就了人的存在的展开。此即实践的超越性。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人进行感性对象性活动,构成人的在世存在的结构,即“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4](P105)。实践作为人的独特存在方式,使马克思决定性地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它提示着马克思哲学前提的两个原初关联的原则:感性存在和“让存在”。惟其如此,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才能作为“现象”而显现。如果说黑格尔哲学的近代性一般地在于其思辨性,那么,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近代性显然在于原初的人和自然的存在的非敞开性。费氏“人本学”对思辨哲学是一次“哥白尼式革命”,但封闭的“感性存在”不幸使费尔巴哈最终落入了形而上学。
第二,“自然”和“社会”作为“实践”的生成和敞开。在马克思语境中,“自然”并非首先意指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也并非意味作为主体的人存在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中。毋宁说,它指示出一种原初的张力——人与自然一体无隔,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让自然在出来”。亦即“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56-57)。这段话当然不能在主客二分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只有在存在论上,“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历史本身才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4](P107)。在近代哲学中,“自然”是一个与“人”处于对待关系中的无人性的客体,具有相对于人的存在的绝对优先性。这种看待方式不可避免地生出“自然从何处来?”的寻问。问题的回答成就了唯物和唯心的二元分裂和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追问客观的自然界得以可能的前提正是作为人的活动之敞开的自然。没有这个前提,自然界的存在就遭遇神学化的可能。因而“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P116)。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人让社会在出来”的性质。因为:在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中,“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4](P60)。因而,“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4](P84)。作为社会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征和确证。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4](P83-84)。
也许,海德格尔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此在”的存在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极富启示性:“因为在世存在属于此在的基本构成,存在的此在本质上就以处于世界内的存在者之中的方式而和他人共在,作为在世存在,它从来不是首先处于世界上的现成之物当中,然后才将其他人揭示为他们的成员。相反,作为在世存在,它就是和他人的共在,这和他人是否和如何实际上与它在一起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另一方面,此在也不是仅仅首先与他者共在,然后才在与他人共在中遭遇世内的事物,相反,与他人共在意味着和其他的在世存在——在世中共在……换言之,在世存在方面,共在以及在——中间有着同样的本源性。”[6](P249)甚至当“此在”处于“无聊”之时,反而更能彰显其“共在”性:“当我们并没有专门地忙碌于事物和我们自身时,而且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存在者‘在整体中’向我们袭来,例如,在真正的无聊中……这种深刻的无聊犹如寂然无声的雾弥漫在此在的深渊中,把万物、人以及与之共在的某人本身共同移入一种奇特的冷漠状态中。这种无聊启示出存在者整体。”[5](P127)“此在”的现象学描述并没有特别标画出“自然”和“社会”这样的概念,而是以“在世界之中”来意指“此在”的生存。他指出:无论是把世界表达为用作表示自然界之全体的名称(自然的世界概念),还是把它用作表示人类共同体的称号(人格性的世界概念),都是同样荒谬的。毋宁说,世界只是“作为某个此在之缘故的当下整体性,是通过这个此在自身而被带到这个此在自身面前来的”,即此在“让世界发生,与世界一道表现出某种源始的景象(形象),这种景象并没有特别地被掌握,但恰恰充当着一切可敞开的存在者的模型,而当下此在本身就归属于一切可敞开的存在者中”[5](P185)。此在与世界的关联不能被看作作为这一个存在者的此在与作为另一个存在者——世界的关系,世界不是一个存在者,它应当归属于此在。
显然,在始源的人的存在中,海德格尔的“世界”与马克思的“自然”和“社会”达成了视域融合。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和“社会”之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而言,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同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P83)。“现实的个人”在自身敞开中经历了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异化劳动把人变成原子式的个人,使他不是作为人的人而存在,从而远离了他本然的社会性。只有在历史中并通过历史,人才得以复归本真的社会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56),就是人在扬弃异化之后、向自己的本质的真正复归。
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时,“实践”的开启性得以充分彰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7](P54)。马克思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应当从“主体”(亦做“主观”——引者注)方面来理解。在西方哲学中,“主体”(译作“主观”似乎更为恰当——引者注)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认识论的主客二分之主体;二是存在论的先于主客两分的、自在自为的人的感性存在本身的主动性。这里的“主体”显然是指后者,即原初的主客无分、物我相融的人的感性存在的生命性。马克思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主体”,直接来自黑格尔的启发。黑格尔认为,概念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具有无限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寓自身于客体中恰如在自己家中一样自作主宰。由于人的感性活动取代“绝对精神”,主体性就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本真含义。需要指出,“主体”的这种意义绝不意味马克思在理解人的存在上的唯心主义姿态。相反,人的实践的主体性恰恰使其真正超越了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分裂和对立。
正如何中华教授所说:“实践开启了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存在。就此而言,它成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召唤者。一切存在者的‘是其所是’,皆成就于实践境遇的开显之中。在实践这一原初性范畴的展开中,一切可能的存在者‘是其所是’,即显示并证成自身。实践的开启性和建构性即在此被成就。实践乃是存在之源,它让存在者‘出场’、‘显示’、‘澄明’、‘绽放’……总之让其‘在’起(出)来。”[8]“实践”“活动出……来”的品格所具有的开启性使其有资格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本体论”就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
总之,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领悟马克思哲学的命运性契机。在此一维度中,实践“活动……出来”的品格,在开启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存在的同时,也成就了人的存在的超越性——自由。这就从“实践本体论”层面使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获得了恰当的理解。
[1]曾凡跃.超越实践本体论之争——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主轴的视域[J].探索,2011,(2).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保罗·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上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海德格尔.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洪汉鼎.现象学十四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何中华.实践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再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J].东岳论丛,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