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违约责任制度的不足与民法典立法对策
□刘廷华 [宜宾学院 宜宾 644000]
我国现行的违约责任制度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其实施效果明显偏离了法律本意,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目前,制定民法典的工作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本文拟对今后在制定民法典时如何完善合同编违约责任制度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一、关于强制实际履行规则
(一)强制实际履行可能引起无效率履行的威胁
缔约后出现的新情况可能使得合同履行的成本超过履行的收益,此时,经济效率要求不再履行合同。在强制实际履行规则下,守约人可能会坚持要求对方履行,有时是因为违约损害赔偿难以充分补偿其对履行赋予的较高的主观价值。但在更多的时候,守约人要求实际履行仅仅是希望以此作为威胁违约人的工具,提高在违约谈判中的交易能力。最终的情况是,守约人和违约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由违约人支付给守约人一笔远高于履行利益的赔偿以免除履行义务。注意,当事人双方将大量资源用于合作盈余的分配,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同时,违约人为了避免被威胁,也会将过度的资源投入到预防,不符合效率的要求[1]。此外,当守约人无效率履行的威胁是可信时,在此威胁下达成的交易往往会过度补偿守约人,这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法律必须阻止强制实际履行规则引起的无效率履行的威胁。
为了消除守约人无效率履行的威胁,必须通过立法使得守约人要求实际履行的权利变得不可交易。即,只要守约人要求违约人实际履行合同,那么双方当事人便不得再利用违约损害赔偿解决违约纠纷,除非当事人在合同中反向约定实际履行的权利具有可交易性。为了保证这种不可交易性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法律可以同时规定,一旦判令强制实际履行,将不再执行当事人事后自行交易达成的货币赔偿协议。如此,当事人通过赔偿协议规定的债务将变成自然债务,失去法律的保护力。预期到这种情况,守约人自然便没有了利用强制实际履行来影响违约谈判的激励。此外,违约人在事前也可能希望通过向守约人承诺给予一定赔偿以免除履行义务。如果守约人选择接受,纠纷可以及时解决。为此,法律可以规定在守约人起诉要求强制实际履行时,由违约人将这种承诺提交法院供守约人选择。一旦守约人接受违约人承诺的货币赔偿,那么法院可通过强制执行这种承诺而结案;如果守约人拒绝违约人货币赔偿的提议,那么法院判令的违约救济将只是强制实际履行。预期到这种情况,守约人将失去利用强制实际履行规则进行敲诈的动机。
(二)强制实际履行和守约方减损规则存在明显的冲突
出于减少社会成本的考虑,守约方减损规则要求守约人在违约后立即采取合理措施减轻其违约损失;根据强制实际履行规则,守约人可以坚持要求对方实际履行合同。但是,违约纠纷的解决总是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违约损失可能不断扩大。因此,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如果守约人能够利用市场完成实质性履行,那么就应限制强制实际履行的适用。通常,在给定守约人可以证明的偏好的情况下,如果他能够很容易地在市场上获得他不能善意地拒绝将其作为等同于合同约定的履行,那么守约人就可以利用市场来完成实质性的实际履行[2]。
不同于违约人实际履行合同,这种实质性的实际履行分两步完成。第一步,守约人在对方违约后立即采取行动在市场上获得替代履行。无疑,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减损措施。第二步,守约人向违约人索取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费用。与违约损害赔偿相比,实质性实际履行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反映了守约人的主观偏好,不仅解决了合同不履行导致的附带损失问题,而且避免了损害赔偿带来的补偿不足的问题[3]和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与强制实际履行相比,实质性实际履行避免了强制实际履行包含的诸如监督困难、机会主义和减损等问题[4]。
二、关于预期违约情形守约方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另一方当事人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不难看出,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是从违约开始的。问题在于,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发生违约,违约时间又该如何确定?[5]《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或通过自己的行为足以表明自己将不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又规定,守约方根据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解除合同的,可以要求违约人承担违约责任。这两个条文使用的词语是“可以解除合同”和“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似乎可以作如下理解:在预期违约情形上,如果当事人选择接受对方的预期违约,则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就发生违约,相应地,在他接受违约时就产生了减损的义务;如果当事人不接受预期违约,则直到履行期限届满后发生违约时才会产生减损义务。
注意,违约人有时会向对方发出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履行拒绝。如果守约人将其当作违约处理而采取减损措施,当履行期届满时对方又履行合同,法院有可能会认为对方没有违约,则守约人自己面临陷入违约人身份的风险。因此,按照我国的法律,当事人通常会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选择不接受对方的预期违约而坚持履行合同。这不仅造成预期违约制度虚有其表,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更严重的是,在模棱两可的预期违约情况下,守约人可能错过最佳的减损时机放任损失的扩大,这是无效率的结果。
对于模棱两可的预期违约的处理,美国法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9条规定了债权人请求提供充分之履约保障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就对方的债务履行有合理的理由陷于不安,则可以书面请求对方提供充分的保障。一旦债权人根据合理理由陷入不安并向对方发出了提供履约保障的请求,那么在对方提供充分的保障之前,他可以中止或者暂缓履行。在中止期间,并不发生违约,自然也不会引起减损义务。如果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提供充分之保障,则构成履行拒绝。相应地,守约人应采取措施减损。
综上,在预期违约情形上,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起始于对方的履行拒绝。如果当事人用言语或者行动表示履行拒绝而且达到非常清楚和确定的程度,则这种拒绝将构成预期违约,从作出拒绝之时起就产生了减损义务;如果当事人拒绝履行的表示是模棱两可的,并不立即产生减损义务。此时,有合理理由陷入不安的当事人有权利且有义务立即请求对方提供充分履约保障。如果对方在合理的商业时间内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则不构成违约;否则,自这段合理的宽限期届满之时起就构成预期违约,相应地产生守约方减损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守约人无视对方的履行拒绝,坐等履行期限届满:如果对方履行,不存在减损的问题。如果对方拒绝,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并不是从履行期限届满时起算,而是从对方做出履行拒绝时起算。
三、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通说持反对意见[6]。由于法律的不完善,造成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中,有支持的判例[7],也有反对的判例[8]。如此不统一的司法实践,无法指导当事人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自然不能有效指引人们的行为。
(一)反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无一成立
当前,反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主要有违反可预见性和增加缔约风险说、难以量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说、精神损害赔偿专属于侵权法说、防止滥讼说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惩罚性说等几种学说。这几种理由都难以成立。第一,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精神损害,违约行为同样可能会造成精神损害。提起侵权之诉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违约之诉则不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第二,当事人缔约目的可能并非是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安宁和快乐的享受,或者是为了摆脱痛苦与烦恼,明显包含精神利益。对于这类合同,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完全可以预见到违约会给对方造成精神损害。而且,是否应该预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实判断,通常以一个理性之人或常人等作为标准[9],这种客观标准的存在减少了可预见性认定问题上的争议。第三,允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其对合同的合理期待,无疑会增进其从事交易的意愿。第四,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难以量化,缺乏具体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可能造成法官在判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10]。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否则,我们应该断然否定所有的精神损害赔偿,因为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量定过程中。第五,如果违约事实上造成了受害人精神损失,那么法律强制违约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其主要目的在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从这个角度看,精神损害赔偿是补偿性的,并不具有惩罚性。而且,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违约率一直居高不下,断然否定违约责任的惩罚功能明显是不合时宜的。
(二)应一般性允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在一些合同关系中,当事人缔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精神利益。如果在违约时不赔偿精神损害,明显有违当事人缔约的初衷。因为,合同的本质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这种合意可以包含对精神利益的追求。而且,我国《合同法》第一条规定其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可否认,合同当事人的精神利益属于其合法权益。
在现实生活中,在纯粹违约、纯粹侵权以及侵权和违约竞合三种情况可能造成精神损害。纯粹侵权问题不属于本论文讨论的范围。对于纯粹违约引起的精神损害问题,按照现行的法律,当事人通常难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会导致违约成本的外部化,引起违约过多,明显不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对于责任竞合,有学者认为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时只能选择一种,不能使两种责任同时并用[11]。因为,一旦守约人能够以违约之诉请求违约人赔偿精神损害,就没有必要再规定“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12]。但是,在责任竞合的场合,我国合同法要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中一项请求权的做法无法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受害人选择违约作为诉因,则无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害人选择侵权作为诉因,则无法请求期望利益赔偿。因此,在违约责任之诉中应允许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诉累。
当前,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模式的选择,学界有三种代表性意见。第一,一般禁止而例外允许。如韩世远先生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原则上在违约之诉中不承认非财产损害赔偿,但是作为例外,在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以及可以正常预期到违约可能引发非财产损害的特殊情形下可以允许[13]。第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情况下允许。崔建远教授支持该观点[14]。第三,也有学者认为只要违约造成了精神损害法律就应该允许受害人在违约之诉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具体做法是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民法典中的“损失”,如无特别规定时,均包括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15]。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模式,支持一般性地允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但为了防止诉讼过于泛滥,造成运用该制度得不偿失,必须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进行必要的限制。例如,仅仅承认在非商业中存在精神损失,而且,精神损害必须是违约引起并达到一定程度。
四、关于违约金的数量调整规则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约定违约金与实际违约损失不一致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调整。更进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法院或仲裁机构调整违约金数量的条件为违约金数量和实际违约损失之间的差额大于实际损失的30%。无论其立法初衷如何,这一规定都显得突兀。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合同当事人自由约定的违约金条款理应受到尊重。而且,当事人约定违约金条款就是为了减轻债权人就债务不履行或不为适当履行所受损害之举证责任,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对违约金数量的调整使得该功能荡然无存[16]。笔者猜想,我国合同法违约金数量调整规则的立法初衷可能是:当违约金过分高于或低于实际的违约损失时,这种违约金带有一定的惩罚性。按照传统观点,违约责任是不具有惩罚性的。这里,有必要先对惩罚性违约金的合理性进行辨析。
(一)惩罚性违约金的正当性
目前,反对惩罚性违约金的理由主要有引诱对方违约论、增加社会成本论、排除外来竞争论和不当得利论等学说。笔者以为,这些理由都无法成立。首先,合同当事人双方都影响履行概率的情况并不普遍。而且,即使一方当事人为了得到惩罚性违约金而努力诱导对方违约,但对方当事人肯定会为了避免遭受惩罚而加大预防力度。预期到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当事人一开始可能就没有诱导对方违约的激励。其次,如果法院只是按照合同条款执行惩罚性违约金,为了得到惩罚性违约金而进行的诉讼过程的成本不会显著地高于为了得到补偿性违约金而进行的诉讼过程的成本。而且,断言执行惩罚性违约金的制度会引起更多的诉讼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法院全部执行惩罚性违约金,在发生违约时,守约人起诉的威胁是可信的,合同当事人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可能性更大。再次,允许惩罚性违约金也不会阻止外来竞争。因为违约收益等于来自第三方高价要约的收益和违约金的差值,提高违约金数量并不能相应地增加违约收益。约定过高的违约金还可能将高价要约人挤出市场。此时,合同当事人根本无法获得违约收益。而且,即使当事人不理性地约定了很高的惩罚性违约金造成市场进入障碍,这也应该是反垄断法而不是合同法关注的问题。最后,当事人约定了较高的违约金,完全可能是因为他对合同履行的估价高于常人。必定,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合同赋予了多少的主观价值,该价值在市场上无法反映出来。最关键的是,当事人约定惩罚性违约金,这种在未来可能遭受的成本通常会反映在合同价格中。因此,惩罚性违约金也不会引起不当得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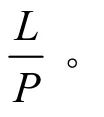
(二)违约金数量调整规则
违约数量与实际损失不相符时,不可因为当事人的请求就武断地调整,必须查明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23]:第一,缔约程序存在缺陷。例如,当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以及不当影响等干扰时,违约金数量可能就是显失公平的。第二,当事人对违约概率的估计可能过高或者过低,在判断违约损失时可能过于悲观或者乐观,在对违约金的理解上可能出现重大偏差,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当事人在约定违约金时可能也表现得不够理性,犯下错误。第三,有时,当事人通过承担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合同价格。此时,当事人约定较高的违约金就是风险承担的一种反映。第四,对履行赋予了较高的主观价值的当事人在缔约时可能会约定较高的违约金。第五,对于合同履行带来的可得利益,完全是一种推测,没有可以利用的财务数据,如果找不到合理的参照标准可以利用,法院在计算违约损失时非常容易出现错误。第六,当事人通常凭借经验考虑概率较大的几种典型状态,以此为基础计算出违约损失的期望值并将其作为违约金的值,但未来损失的期望值在很多情况下与实际损失都是不一致的。第七,在缔约后,可能发生情势变更,合同的基础丧失或者动摇,导致违约金数量和实际损失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
在查明违约金数量与实际损失不相符合的原因后,正确的做法是分成两个阶段来处理。在第一个阶段,应假想退回到当事人缔约时点去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违约金的数量是否合理,这会出现合理和不合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违约金的数量在缔约时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因为缔约程序存在欺诈、胁迫、不当影响等缺陷,则应赋予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选择撤销该条款或者调整违约金数量的选择权;如果是因为当事人自己的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不合理,法院没必要施以救济。第二种情况,违约金的数量在缔约时是合理的。如果当事人对合同赋予了较高的主观价值或者自愿承担了风险,那么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予调整违约金的数量;如果不是这些原因,则转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根据违约金数量与实际损失不相符的原因,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违约损失的确定过于复杂以致于当事人和法院在计算违约损失时已经犯下错误或者容易犯下错误,无疑应执行违约金条款。第二种情况,当事人在缔约时是按照损失的期望值约定违约金。当违约实际发生时,违约金的数量很可能与违约金不符。这种情况也应执行违约金条款,因为它实际上隐含了在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配,并且这种风险分配对合同价格已经造成了实质性影响。第三种情况,在缔约后发生了情势变更。此时,应允许调整违约金数量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势。
五、关于情势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情势变更的条件和适用效果进行了正式规定,但存在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尚待进一步明确。
(一)情势变更的适用效果
情势变更的适用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生情势变更后合同继续有效,为了消除情势变更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事人必须立即就合同变更与解除事宜与对方展开谈判。而且,在没有得到对方当事人同意时,在谈判过程中不得中止履行合同,否则,这种中止将被视为违约。同时,为了避免没有受到情势变更不利影响一方当事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而消极谈判,法院可以判令行为人赔偿对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其次,到底是选择变更合同还是终止合同,并不是由一方当事人任意选择的。由于情势变更规则主要目的在于消除情势变更造成的不公平的交易结果,因此,只有通过变更合同仍然无法实现此目的时方可选择终止合同[24]。实际上,《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第313条的规定正是如此[25]。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愿意终止合同则另当别论。最后,如果经过谈判双方同意终止合同,此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如果双方都没有开始履行合同,则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都已经履行了一部分或者全部合同义务,那么应该允许当事人取得相应的对价,而不是恢复原状。
(二)情势变更的适用要件
无疑,适用情势变更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了情势变更所造成的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显失公平问题,但是,适用情势变更引起合同终止可能造成连锁反应,最终诱发普遍的不平衡[26]。有鉴于此,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必须具备非常严格的条件,具体包括:第一,须有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注意,只有那些作为合同基础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才属于情势变更。第二,须情势变更发生在合同生效以后履行终止以前。如果情势变更发生在合同订立之时,应认为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发生的事实,则合同的成立是以已经变更的事实为基础的,不发生情势变更的问题[27]。此外,发生情势变更后,履行合同的成本可能超过对方当事人的估价。如若允许一方当事人擅自履行然后再提出情势变更的主张而要求对方调整合同价格,可能会出现无效率履行的情况,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受情势变更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在情势变更后应毫不迟疑地向对方提出变更合同或者终止合同的请求,不得擅自履行完合同后再援引情势变更规则。第三,须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所不能预见的。在决定是否具有预见性时,应以“理性人”标准为主,兼顾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来判断。第四,无论如何,可归责于当事人一方的事由绝不是情势变更。否则,当事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过错谋求好处或者逃避合同履行的责任[28]。第五,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没有承担该风险。如果当事人已经在合同上明确地或者以可推断的方式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作出了规定,那么就没有情势变更的适用余地。最后,需要强调,商业风险是正常商业活动要承担的必然后果,所以当事人不能因为发生商业风险而援引情势变更。
六、结论
现行违约责任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有待完善。第一,对于强制实际履行规则可能引起的无效率履行威胁问题,法律应规定强制实际履行命令的不可转让性。对于强制实际履行规则和守约人减损规则之间的冲突,在守约人可以通过市场完成实质性实际履行时,应限制强制实际履行的应用。第二,为了明确预期违约情形减损义务的产生时间,应赋予守约人请求对方提供充分履行担保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为了消除违约造成的外部性,应一般性允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第四,应承认惩罚性违约金的合理性,只有在缔约程序存在缺陷或者缔约后发生情势变更情形才允许调整违约金数量。第五,应进一步明确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条件及其效果。
[1]刘廷华.违约责任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0, (6): 19-23.
[2]FARNSWORTH W.Do Parties to Nuisance Cases Bargain After Judgments? A Glimpse Inside the Cathedral[J].U.CHI.L.REV, 1999, 66: 1055-56.
[3]刘廷华.论实际履行的适用与限制的法经济学依据[J].北方法学, 2010, (6): 110-119.
[4]EISENBERG M A.Actual and Virtual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 and the Indifference Principle in Contract Law[J].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5, 93(4): 975-1050.
[5]刘廷华.论预期违约情形下减损义务产生的时间[J].福建法学, 2010, (1): 8-11.
[6]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 42.
[7]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M].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87.
[8]唐德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239-243.
[9]迈 克尔 • D• 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 等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276.
[10]关今华.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18.
[11]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22.
[12]李永军.非财产性损害的契约性救济及其正当性——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二元制体系下的边际案例救济[J].比较法研究, 2003, (6): 47-62.
[13]韩世远.非财产上损害与合同责任[J].法学, 1998,(6): 27-30.
[14]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197.
[15]龙著华.违约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J].政治与法律, 2006, (1): 68-83.
[16]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22.
[17]VARGO J.The American Rule on Attomey Fee Allocation: The Injure Person’s Access to Justice[J].Am.U.L.Rev, 1993, 42: 1567-1578.
[18]COOTER R D.Punitive Damages for Deterrence:When and How much[J].Hlabama Law Review, 1989, 40:1143-1151.
[19]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M].沈宗灵,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77.
[20]GOETZ C J, SCOTT R E.Liquidated Damages,Penalties and the Just Compensation Principle: Some Notes on an Enforcement Model and a 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J].COLUM.L.REV, 1977, 77: 554-594.
[21]PARTLETT D F.Punitive Damages: Legal Hot Zones[J].La.L.Rev, 1996, 56: 781-797.
[22]OWEN D G..Punitive Damages in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J].Michigan Law Review, 1976, 74: 1257-1287.
[23]刘廷华.论违约金数量的调整——法经济学视角[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 (5): 84-88.
[24]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陈荣隆, 修订.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2002: 331.
[25]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 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455.
[26]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5: 266.
[27]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344.
[28]布莱恩·布卢姆.合同法[M].张新娟, 注释.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454-459.

